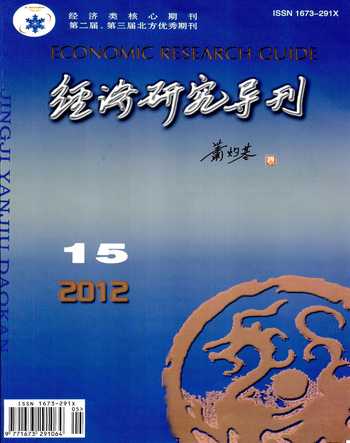试论何其芳对毛泽东形象的建构与寓托
王文圣
摘要:何其芳在奔赴延安之后,创作风格为之一变,从自我关怀为中心转变为热情歌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自《星火集续编》创作以降,何其芳以毛泽东为创作对象,从心灵理想的连贯性来诠释自己创作的转变。通过分析何其芳诗文,特别是他晚年诗文对毛泽东的描写,来揭示毛泽东是他心中“完美”的化身。在何其芳看来,毛泽东、“年轻的神”与诗人的形象是三位一体的。何其芳通过对毛泽东的抒情,更好地建构与寓托心中理想的自我。但是,不管何其芳的创作内容如何变化,他始终是一个注重自我阐释的自觉自主的现代诗人。
关键词:何其芳;诗文;毛泽东形象;建构;寓托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214-05
引言
何其芳到北京求学后,在不断的努力下,完成了《预言》、《画梦录》,成功建立了自我的风格,登上了中国的文坛。在《还乡杂记》、《刻意集》中,他整理旧作,立定脚跟之后投奔延安,又一度自觉地转化自我,再一次追求一种新风格的创造。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何其芳的写作实践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作品风格的递嬗即是生活形态的变化:从北京会馆与宿舍的苦吟,到奔赴延安初期采集报告式的写作,甚至是整风以后勇于投身政治宣传工作,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人力求在生活的实践中达成新风格的完成。延安之后,何其芳顿觉今是昨非,于鲁艺工作之余,写作了《夜歌》与《星火集》,不断宣示自己的转变。延安整风之后,《星火集续编》中的何其芳再无犹疑,将所有的文字奉献给了他热爱的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才将重心转入理论的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写作。
何其芳的写作一直都以“自己”作为关怀的核心,而不断地自我创造与建构,这是他一直的追求。我们不须过于放大何其芳在奔赴延安之后,风格为何产生转变的问题。应该注意的是,他为何在这次转向之后,便对中国共产党忠心不渝,而从此不再转移。关于延安以后作家心灵的旅程,历来研究者均以“自我忏悔”名之,认为何其芳在延安体制的规训下,不得已“再一次痛苦的投生”。从此,何其芳对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极度忠诚,成为歌颂光明派的先锋,并且在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遭遇挫折之后,仍然不改初衷,至死不渝。在翻检这些论述时,并与何其芳实际文本写作情况对照之后,我们便能轻易发现:这种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终身不渝的激进的印象,大多来自于《关于现实主义》以降,乃至建国后《西苑集》、《论红楼梦》、《文学艺术的春天》等著作中可以得到确凿的证据。①
何其芳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但随着后人对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文学机制的不同解释观点,何其芳此一人生抉择之价值似乎无法确证。不过,笔者以为这些异说得以各持一端,其核心仍在于无法或无意解释何其芳为何是同时代文人中转变最剧烈者;这些通过时代或集体机制而生之外部考察,永远有其难以挽救的盲点。
失去了对作家生命历程的理解与对实际作品实践内涵的探察,则无从得知诗人在自我追寻的路上,那一份不被任何“主义”框限的,终极的追求与关怀究竟是为了什么?随着何其芳生命阅历的厚实,终于能够以真实的、有所成就的“自己”作为写作的主要对象后,那曾经被呼唤的、高华而虚拟的抒情主体,是否在这样的人生长流中,终至泯没不存?所以,如果详细探察何其芳抒情模式的全貌,我们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至诗人辞世以前的为数虽少但意义非凡的诗文作品中去探究。因此本文试图从何其芳《星火集续编》以后的诗文创作为主,仍旧以文本的脉络切入,为延安以降诗人心灵、及创作机制的转变对毛泽东形象的建构作出合理的诠释。
一、何其芳对毛泽东形象的建构
让我们回到《还乡杂记》最末尾,诗人东望扬子江,感慨万分:
是啊,在树阴下,在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东去的扬子江的时候,我幻想它是渴望的愤怒的奔向自由的国土,又幻想它在呜咽。
二十六岁的何其芳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远方正烽火连天,诗人心中那份逝者如斯的感慨与忧患之心,实不难想象与了解。隔年,何其芳奔赴延安,抱着更伟大的人生期许,盼望又一次的精神的壮游。然而,为何诗人奔赴延安后,便忠心至死不渝,更以赤诚的红色诗人自命?少年的学院岁月中,何其芳不曾为任何单一时兴的思潮感动,只对那些书中所显现的精魂倾心,并往往在创作中以他钟爱的面具示人。于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推想:就实际的生活或何其芳的思维倾向来看,何其芳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寻、亲合,亦非是受到一套理论思潮或抽象之政治理念吸引;在何其芳内心情绪高涨涌动时,之所以能获得诗人全心全意之崇拜的,无非是具体的“人”,而这个“人”,就何其芳生命经历来说,则非毛泽东莫属。
何其芳崇拜毛泽东,并视毛泽东为完人。毛泽东能诗能文,又具政治手腕,而心中怀抱着救国、护国之宏大抱负的诗人,很自然地仰慕起这样一个英雄的形象,并以此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也可以说,毛泽东这个人的崛起,确实符合何其芳当时心中追寻的完美典型。毛泽东也就这样因缘际会地成为何其芳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他人”,牵引着何其芳往后的创作能量与表现形态。关于何其芳与毛泽东之间可能之关联,除纯然政治文化史角度的判断之外,最足观者,便是王斑与金观涛的研究: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一书,详细地以“崇高”美学作为切入尺度,描述了京派时期朱、梁二人对于“崇高”的歧见,并特别抉发梁宗岱所建构的阴柔秀美一系与崇高美学的关联;以及梁宗岱美学如何以“回收个体潜能,再造革命热情”的模式,被中国共产党革命美学吸纳的过程。 在王斑结合美学与政治话语的考察之外,尚有金观涛先生结合政治与思想,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归纳出毛泽东思想之一元性特质,分析了五四后“革命乌托邦”再现与形成的过程。这些考察,都对何其芳如何汇流于毛泽东美学的过程提供了宏观的背景。 笔者基本上不反对这些论述,然则在此处更希望以文本为出发点,在实际的作品中,考察何其芳与毛泽东之间,如何吸纳与投射的过程。
要了解毛泽东对何其芳的影响,与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文本的重探。何其芳在毛泽东逝世后,曾作长文《毛泽东之歌》,悼念他心中伟大的完人,对于两人之间的每一次接触,都全心、仔细地加以记录。因此,我们应从《毛泽东之歌》的细读,是如何详细描绘何其芳心中的“毛泽东形象”。
何其芳自述到延安后,提出了见毛主席的要求,并很快就实现了。而诗人和他会面后,是这样的:
我们向他说,我们想写延安。
毛主席爽朗地幽默地微笑着说:
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毛主席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手,说一座山弯下一只手指;但紧接着又严肃地加上一句:也有一点点可写的。①
何其芳当时没有回答,后来却在《我歌唱延安》中,将毛泽东所说的“一点点儿”作了如下的诠释:
一点点儿?依据我两个月来的理解,依据我诚实的语言,这个形容词的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很多很多”。我充满了印象。我充满了感动。然而我要大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
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
从“一点点”到“很多很多”,是诗人自己的理解与体会。虽然我们不知道何其芳所交出的“延安的空气”是否合乎了毛泽东“有一点点可写”的期待。但可以知道的是:毛泽东的寥寥数语,仿佛给了何其芳莫大的启示与鼓舞,化为诗人往后许许多多歌颂延安的篇章。从何其芳这样的自述中,很明显的,何其芳对毛泽东一开始就充满了崇拜,认为毛泽东是一能知他、识他之人,表现了对毛泽东强烈的认同感。
延安整风之后,何其芳又与毛泽东会晤,此时毛泽东问诗人“你们是歌颂光明的吧”,又问“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纵然何其芳心中激起一阵挣扎,但却都没有回答。此时毛泽东复言:“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诗人仍旧没有回答,但却有了以下的体悟:
我当时直觉地感觉到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警句,而且也是批评的比较重的。虽然当时我并不理解,我也永远记在心底了。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我才开始有些理解。过了几年,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下诗人“直觉地”接受了毛泽东的“警句”,虽不理解却也永远记在心底。而且此后多年,在文坛的风风雨雨里,何其芳都谨守着这种“忍受委屈、不再解释”的原则。如此,我们也可以知道,真正撼动何其芳,让他深埋心中作为信条,并忠心不渝的开端,就是毛泽东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此次会晤结束时,何其芳这样描写分离的场景:
毛主席高大的身躯站起来,送我们出窑洞,继续和我们一起走着。到了一片比他窑洞的平地高一点的地方,又走了好几步,我们再三请他留步,他才伸出手来和我们一一道别。毛主席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眼睛看着我们,停顿一会儿,好像把重要的革命任务交给我们,期望我们努力去完成,期望我们哪怕献出生命也要努力去完成。
我们激动地走在回桥儿沟的路上。我们似乎从幼稚的少年时代长大了许多。我们在归途中是沉默的,像是各自沉入思索中去了。
毛泽东一个握手、一个凝望,就让何其芳感受到伟大的任务,而瞬间长大了许多。此类仿佛心有灵犀的感应,在《毛泽东之歌》中不断地被强调,尽管诗人 只是台下的一个听众,却都在毛泽东演说时感到醍醐灌顶,斩获甚丰。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何其芳心目中,毛泽东甚至能看到连诗人自己也看不到的“自己”,如毛泽东对他说“你这个干部就是柳树性多的同志吧”时,一如往昔,何其芳不明白却也不发问。之后何其芳从毛泽东的演讲中,自行领会了柳树性的意涵,并自我诠释说:“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普通党员,和毛主席接触的机会极少,他对我的了解却是多么准确啊!”此处我们可以看到,何其芳与毛泽东实际上的互动是很少的,但在这极少的交会中,诗人却感觉到一种真实的联系与关系。又如在重庆时,毛泽东说:“何其芳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认真”,何其芳面对这样的评价,自己对自己说“在他指出之前,我自己是不大清楚我应该努力发展这点好的因素的”,且“伟大的领袖了解干部就是这样深刻,甚至比你自己还了解的清楚”。每个人都有连自己也不了解的部分,但此时,何其芳却认为毛泽东了解他,比他自己还清楚,而且还能看见连何其芳都看不见的那个“自己”。行文至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之歌》里,一个凌驾于自我意识之上,且至高如神的形象渐渐浮现。
当何其芳从惊险的活动中好不容易全身而退时,毛主席一句打趣地:“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竟把憔悴的、瘦脱的不成形的诗人点活了起来,他惊讶于“毛主席还认得我”,欣喜之余,他说:
如果有一面大镜子立在我面前,我很可能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我会对镜子里的人问:“你是谁”,然而毛主席却还认得我,毫不迟疑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诗人不仅能够从毛泽东身上看见那个“看不见的自我”,甚至能因毛泽东一句呼唤,便找回遗失的自我。在身心交瘁,那样茫然的时刻,主席的一声呼唤,便能让何其芳瞬间找回当下实存的感受。由此亦可见得,毛泽东的至高形象已然确立。在《毛泽东之歌》的最后,何其芳这样描写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使我们温暖,使我们生气蓬勃,使我们像绿色的植物一样茁壮成长。他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真正受到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的人,他的肉体可以衰老,他的精神却永不衰老。
此番感动过后,何其芳更说道:“这些涌现在我心底的记忆,就像一支鸣响着巨大、雄壮、快乐、深沉、繁复而又和谐的声音永远鼓动我前进的歌曲。”这也就是何其芳心底的“毛泽东之歌”,这是何其芳创作能量的泉源,也是他放在心底,不断用以自我鼓舞的一首最深的诗。
通过对《毛泽东之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何其芳心中的毛泽东形象,如何被描绘、确立,乃至不断被提升的过程。但我们也必须明白,在这些看似详细而极度认真的记录背后,其实也都只是诗人心中的投影,此一建构的过程,如诗人自己文中所述:
多么可惜,多么遗憾,人的记忆不可能把一切经历过的事情都清楚地记得,即使是很难得有、很可珍贵、很不寻常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记忆力是不错的,写文章要引用什么材料,翻阅读过的书就可以找到,不太会记错。但我这个原来只做过一些很单纯的工作的人,从1944—1947这几年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做过一段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后,记忆力就大为衰退了。这次写回忆录以前,我一个一个地去访问那些一起到毛主席那里去,现在还在北京的同事。我们各自以各自的回忆来互相提醒、互相补充。这样我们集体回忆起的谈话内容,比我们当中一个人都多的多。但比起当时的实际情况,却还是少的很。
诗人晚年记忆衰退,加以病魔缠身,却仍试图以最真诚的态度为毛泽东立传。但难以挽回的,是斯人已远的现实:文中所显现者,终究不是毛泽东,而是何其芳心中的理想。
由此角度来看,《毛泽东之歌》虽是对毛泽东的回忆录,其实却是何其芳记录他在遇见毛泽东后,在毛泽东的指引下,不断发现崭新的自己,并向理想迈进的过程。所以,毛泽东仿佛接替了那“年轻的神”的地位,成为牵引诗人心中抒情主体的枢纽,面对毛泽东时,诗人就能感受到那不断前进着的自己,①毛泽东的故事也就是何其芳自己的故事。如同何其芳当年,要在真正回乡时,才听见从江水里传来的歌,也要到毛泽东形躯消灭之后,诗人才得以听见他自己心中那首伟大的“毛泽东之歌”。在投奔延安之后,何其芳转以对毛泽东的投射,以回照出那个理想的自我,这种动力形态的变化,便是何其芳抒情诗文对毛泽东形象建构的根本原因。
二、毛泽东、“年轻的神”与诗人形象的三位一体
在何其芳诗文对毛泽东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是他心中“完美”的化身。而究竟何其芳为何会以这样的姿态,在往后的人生中亦步亦趋地追随毛泽东呢?若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何其芳少年时最钟爱的《预言》一诗,我们就可以发现:《毛泽东之歌》中频频出现的、何其芳与毛泽东之间的“默示”,和《预言》中“我”与那“无语而来无语而去”的“年轻的神”所达成的默契相对照,可说几乎是如出一辙。
遇见毛泽东,是何其芳心中“预言”的成真,毛泽东也就成为诗人“年轻的神”的投射:那足以体现何其芳心中之呼唤与追求的、理想与至美的化身。在毛泽东的牵引之下,何其芳那抒情的主体得到了吸纳与制约,不管是那想象中升华的自我,或是夸大的对自己的想望,在毛泽东出现后,巧妙地汇流为一,诗人的生命也就因此达成了一种稳定的、动态的平衡;所以,遇见毛泽东后,他宁可暂缓创作,努力学习理论,以成就那最好的诗,正如1971年时《写给寿县的诗》中,他说
十三年了,我的诗还只有题目
这是长的多么慢的植物,
十三年了,在我心底的种子
还没有壮大到破土而出!
为了等待那首最好的诗,诗人甘心沉淀再沉淀,此处的“植物”与“种子”所等待的。自然是那来自毛泽东的、理想的阳光的浇灌。之后,诗人接着叙述他回到北京时的喜悦:
我少年时在这里流连光景,
在这里我看见卢沟桥的炮声,
我看见你骄傲的头垂下,
日本法西斯的军队进城。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
毛主席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
北京获得了新的生命,
你的青春无比壮丽。
我头上的白发来的太早,
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老,
年轻的血液在我身上奔腾,
我听见你的名字就心跳。
诗中何其芳回顾少年离开北京时,那些流连光景的过去,和古都蒙尘的过往。如今一切都已被刷新,北京因着毛主席又再度复生,“获得了新的生命”,且“青春无比壮丽”。拟人化了的北京城,受到毛泽东的点化而重生,诗人在这有着毛泽东的、重生且壮丽的北京城中,也随之重生。他不知老之将至,且体内有“年轻的血液在奔腾”。但更耐人寻味的,是紧接着“我听见你的名字就心跳”一句,更是令人想起《预言》中那“心跳的时刻”,那理想闪现的瞬间。至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我听见你的名字就心跳”中的“你”,其实就是“青春壮丽的北京城”、 “毛主席”以及诗人心目中那至高至美的“理想自我”,三者一体显现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境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在长长的追寻之后,何其芳终于赶上了他心目中年轻的神。如今,他并非当年那个在夜里寂寞的与死接近,而在早晨方感到露珠一般欢欣的他,诗人这样描述自己:
九月的尘风拂着清寒。
我在长安街上大步行进,
像一个奔向未来的人。
我身体强壮,肺部扩张,
和树一样枝叶开放,
好像一口气可以吸进
环绕我的整个北京的早晨!
年轻的诗人不畏清寒,仍然在奔向未来。此时何其芳在诗里身心安顿、自足自得,呼吸着理想世界里新鲜的空气。所以,相信在诗人的心中,只要是为党、为毛主席、为理想奉献,那么无论是学术工作的束缚,甚至是文革的苦辛,纵然痛苦,但诗人都能承受,甚至甘之如饴,只因诗人心中的“预言”终于得到实现,并即将成真。
但毛泽东的逝世,却让此一平衡又再度遭到破坏,使何其芳的“预言”又一次地失落。此刻作为实体的毛泽东已经不存在,但我们却更清楚地看到何其芳心中毛泽东形象之真身:便是何其芳对“年轻的神”的召唤。如他哀悼毛泽东时说:
悲痛一定要转化成力量,
因此,虽然我很悲伤,
我不曾在你在世的时刻,
写出壮丽的毛泽东之歌,
我现在的歌唱带着哭声,
现在的歌唱抑制着悲哽,
我仍然把他献在你灵前,
像用我采集的花编成的花环。①
“我采集的花编成的花环”,指的便是“我用韵文编织的花环” ,也就是诗人的诗。面对理想的失落,诗人仍然要化悲愤为力量,以歌代哭,并化为献给毛泽东的诗篇。诗人不断宣告自己还年轻,还可以奉献、追逐。毛泽东逝世,理想破灭了,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诗人的抒情模式也因此再度重整。年迈的何其芳仍不断在诗中呼唤理想,在《我控诉》一诗中,便以“毛主席!毛主席!我向你控诉!”开篇,而全诗十节中,第一、三、五、六、八、九、十,都以对“毛主席!毛主席!”的呼告开始。《我控诉》一诗中除了诉说自己的委屈,与对未来的期望之外,全诗便缭绕着对毛主席伟大形象的呼唤,透过诗再一次召唤心中的理想,以安慰自己的失落。 综观何其芳所有诗作,我们也恰巧可以发现,何其芳的感叹与赞叹虽多,但实际呼告过的人物,却也只有“年轻的神”、“自己”和“毛主席”,而这三者相互映照的关系,也就在毛泽东逝世后,在《我控诉》的完成中,一并呈现出来了。
由于何其芳的骤逝,我们也已无从得知晚年病人中的诗人,是否仍酝酿再一波的自我创造。但可以确知的是,这些中晚年作品中,他已经打造了一个安顿自己灵魂的场所,便是那文字中无限美好的理想世界,与那个永远奉献着,追索“爱”、“美”与“牺牲”的“我”。而毛泽东作为何其芳生命中“预言”的点化者,使何其芳原本一体双声的内在对话,转为三位一体的抒情模式,而在其伟大形象崩解之后,又引发了诗人更强大的创作能量与样态,故毛泽东于何其芳生命及创作历程的意义与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结语
总之,在何其芳晚年的诗文中,清楚地展现了他心中的毛泽东形象,并在诗人心中得到投射。在何其芳抒情诗文的探查中,我们可以明白,毛泽东乃是何其芳心中“理想的化身”。在与毛泽东相遇以后,何其芳的“毛泽东之歌”,实际上包含着诗人自己自我修洁的理想。而在诗人对毛泽东诗词的完美评价,与进行以毛泽东为题材的创作时的创作心态的纠葛中,我们亦能看见诗人面对的,仍然是自我不断创作的实践。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以这样完美的姿态被何其芳所接纳,则源自于与诗人心中“年轻的神”形象之呼应与契合。在诗文的内涵中,更可以看出诗人的“自我”和“年轻的神”与“毛泽东”,确实有着微妙的联系。毛泽东在世时,确实成为牵引诗人创作能量的枢纽,但在毛泽东逝世后,诗人对理想的一贯追求又重新复现,可见何、毛二人之间确有其遇合、交互牵引乃至解离的过程。并在此一过程中,诗人都始终保有一定的建构与自觉。因此对于诗人与毛泽东之间,单纯解为非理性的崇拜,或软弱的依附都不恰当。最后透过对诗人晚年诗作的精读,也能够知道何其芳并没有失去创作的主体性,他仍在陶铸一个更完美的自我。是故,我们以此为基础,审视所有何其芳的诗文创作,更足见何其芳是一位具有“艺术的创造的自觉”与“高度自我意识”,并以此成功造就自身价值的现代诗人。
参考文献:
[1]何其芳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何其芳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3]何其芳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牟决鸣.何其芳诗文掇英[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5]林志浩.何其芳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6]尹在勤.何其芳评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7]王建元.现象学诠释与中西雄浑观[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8]王雪纬.何其芳的延安之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灵轨迹[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
[9]石晓枫.白马湖畔的辉光:丰子恺散文研究[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出版社,2007.
[10]江弱水.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从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1]江震龙.解放区散文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
[12]何锐,吕进,瞿大炳.画梦与释梦: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13]吴晓东.象征主义与现代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4]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5]易明善,陈文壁,潘显一.何其芳研究专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16]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俞元桂,姚春树,汪文顶.中国现代散文十六家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8]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9]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20]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1]王培元.从象牙之塔到延安窑洞——何其芳三四零年代的文学道路[J].新文学史料,1998,(4).
[22]王丽丽.何其芳诗《预言》、《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赏析[J].名作欣赏,2001,(4).
[23]王泽龙.论中国现代派诗歌意象艺术[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6).
[24]王鸣剑.论何其芳散文和诗歌的审美追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社版,2004,(11).
[25]王雪伟.痛苦的求索——20世纪30年代末何其芳的创作转型现象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4,(6).
[26]朱金顺.五十六年前的一桩贬鲁公案——兼替《何其芳全集》补遗[J].鲁迅研究月刊,2001,(8).
[27]朱金顺.何其芳全集佚文考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
[28]李玫.倾听自己的呼吸——何其芳《独语》分析[J].名作欣赏,2001,(6).
[29]李夫泽.何其芳的小说《浮世绘》浅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1).
[30]吕晴.略论何其芳在延安时期批评的自由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4).
[31]树阴下的默想[G]//何其芳全集:卷1.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309.
[32]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92-151.
[33]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演变:第1卷(重印本)[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2005:275-338.
[34]我歌唱延安[G]//何其芳全集:卷2.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41.
[35]写给寿县的诗[G]//何其芳全集:卷6.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55-57.
[36]北京的早晨[G]//何其芳全集:卷6.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63.
[37]我控诉[G]//何其芳全集:卷6.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96-111.
[责任编辑 王玉妹]
——兼及一类史料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