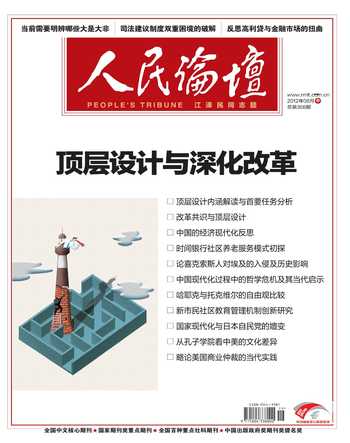唐代休闲体育文化研究
曾宇
【摘要】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时代之一,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为休闲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形成了蹴鞠、击鞠等表演类,拔河、踏青、登高等节日类,踏球舞、剑器舞等舞蹈类休闲体育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民众的生活情趣,也促进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唐代文化休闲体育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体育又一次得到大发展的时期,其休闲体育发展的主要特征为开展项目多,参加体育活动的人遍及全社会。唐代休闲体育大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宁和经济的繁荣。统治阶级的热心倡导,勇于进取和开拓的社会精神风貌,以及民族大融合等都对唐代休闲体育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表演类休闲体育文化活动
蹴鞠。唐代长安盛行蹴鞠,史书中有不少记述蹴鞠的史实。《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既扬武宗训为宾客,二人凭贵,无学术,惟狗马、蹴鞠相戏嬉昵。”唐代的寒食节盛行蹴鞠活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习俗。杜甫在《清明》诗中写道:“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韦应物在《寒食》中则写道:“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他又在《寒食后北楼作》中写道:“园林过新节,风花乱高阁。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他还在《寒食后北楼作》中写道:“园林过新节,风花乱高阁。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唐代女子也参与蹴鞠活动,主要是运动量较小的“白打”。“宿妆残粉未明天,总在朝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这就是描写宫女在寒食节时,宫女参加“献球”的情况。当时,蹴鞠在民间也时有所见,唐人康骈的《剧谈录》就记载:“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装褴褛,穿木履,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王维在《寒食城东即事》中对民间流行蹴鞠也有记述:“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柳里”。
击鞠。击鞠是一项骑在马上挥杖击球的运动,也叫击球或打球,后人又称为马球。击鞠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表演类休闲体育项目。在《封氏闻见记·打球篇》中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唐太宗最先提倡向西蕃人学习打马球。唐太宗令习打球,首开唐代长安打球风气,标志着唐代击鞠的兴起,并逐渐获得较快速发展。月灯阁是唐长安城举行蹴鞠和马球赛会之处,故有“月灯阁球会”之称。按照唐代惯例,经过殿试之后的新榜进士,主考部门要为他们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球赛。唐代长安城不仅有男子击鞠,而且还有女子击鞠。王建在《宫词》中就写道:“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步打球。步打球就是徒步挥杖打球,是从骑马打球演变而来的,被认为是早期的曲棍球。唐代举行“献球”活动时,就有步打球活动。王建在《宫词》中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
角抵。唐代角抵已从“角抵戏”中逐步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体育项目。在崇尚豪侠勇武的唐代,角抵戏不仅重视戏剧性的表演,同时注重于能“宜勇气,量巧智”,“决胜负,骋趁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的角抵。唐代有专门从事角抵的专业队伍,其组织名称叫“相扑朋”。“内园恒排角抵之徒以备卒召”。内园中的“角抵之徒”是有组织的专门从事角抵的专业人员。“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也,已在外祗候”。这则史料不但说明唐代已有了专门管辖“相扑人”的组织机构,而且还是一种传统的休闲体育表演项目。
节日类休闲体育文化活动
拔河。春天盛行拔河,这与农业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春天是一年农事的开始,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常用不同的形式来祈祷农业丰收。“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拔河”就是“百种戏”的一种。“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震惊远近。俗云以此庆胜,用致丰穰”。这描述了隋代南郡襄阳地区拔河的情景。在鼓声、歌声、欢呼声中,制伏邪恶,夺得农业好收成。唐玄宗在《观拔河俗戏并序》中云:“俗传此戏必致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稔。壮徒恒贾勇,拔矩抵长河。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噪齐山岌,气作水腾波。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唐代宫廷也盛行拔河。景龙三年(709)二月己丑,(中宗)及进士薛胜在《拔河赋》中透露,这场比赛的另一个目的是“耀武于外”。因为,应邀参观拔河的胡人首领看完拔河后说:“君雄若此,臣国其亡。”中书令张说看完拔河后,也在一首《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诗中写道:“今岁好拖钩,横街敞御楼。长绳系日往,贯索挽河流。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
唐玄宗在位时,也喜好拔河运动。他曾在兴庆宫举行过千人拔河比赛:“明皇(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进士薛胜为《拔河赋》,其词甚美,时人竟传之。”举行此种大型拔河比赛,按李隆基的话说是“以求岁稔”。早期的拔河是用篾缆,唐代则用大麻絙,长四五十丈,麻絙“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前,分两朋,两向齐挽”。这样背向而拉的拉牵方式,与现代拔河面对面拉引的方式完全不同。比赛时,双方都击鼓指挥。隆隆鼓声,使拔河赛场充满战斗气氛。
登高。农历九月九日,俗称“重阳节”,是中国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人们常在这一天,外出登高,饮菊花酒,头插茱萸。“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唐代登高风气很盛,反映登高的诗文也多。在长安城,以登大雁塔的人最多。岑参就曾与高适等一齐登上慈恩寺里的大雁塔并写下了“下窥指高鸟,府听闻惊风”的名句。唐代皇帝则常在西内苑登高饮宴。唐中宗李显就曾在重九日登上临渭亭,并写下了《九月九幸临渭亭登高》的五言诗:“九日正乘秋,三杯兴已周。泛桂迎罇满,吹花向酒浮。长房萸早熟,彭泽菊初收。何藉龙沙土,方得恣淹留”。
踏青。唐代的踏青活动仍然盛行。因而,不少诗人为此写下了不少佳句。杜甫的“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许浑的“踏青会散欲归时,金车久立频催上。收裙整髻故迟迟,两点深心各怅怅。”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踏青活动。
秋千。唐代寒食节,秋千是一项受人喜爱的活动。王维在《宫词》中写道:“春风摆荡柰花枝,寒食秋千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和凝在《宫词百首》中也写道:“司善厨中也禁烟,春宫相对画秋千。清明节日颁新火,蜡炬星飞下九天。”唐代宫廷也有秋千戏。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半仙之戏》写道:“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晏乐。帝呼为半仙之戏。”
竞渡。唐代竞渡,比起前代有很大发展,但仍俗盛端阳竞渡。唐代竞渡用船装扮华丽,更富有竞技性和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唐代宫廷盛行竞渡戏,唐玄宗就曾亲临兴庆宫的兴庆池边,观赏竞渡。“拂露金舆丹旆转,凌晨黼帐碧池开。南山倒影从云落,北涧摇光写浪回。急舸争标排荇度,轻帆截浦触荷来。横汾宴镐欢无极,歌舞年年圣寿杯。”“急舸争标”,说明争夺胜负的场面还是相当激烈的。唐玄宗以后的皇帝,则去大明宫的鱼藻宫观竞渡。其中兴致最浓的要算唐敬宗李湛。他在位期间(824— 826),就先后观赏过4次竞渡。宝历元年(825)七月,他还诏令王播造竞渡船20艘。
围棋。唐人对围棋的认识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下棋与弹琴、赋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以善弈为荣,以不善弈为耻的风气。在崇尚弈棋风气的影响下,唐代的围棋十分普及,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唐高宗李渊,嗜好围棋“至于通宵连日”;武则天时的左拾遗卢藏用,“工篆隶,好琴棋”;唐玄宗与“亲王”对弈时,曾发生过“呙子上局”的闹剧;僧一行应召入长安从事天文观测和历法改革时,曾在燕国公住宅与围棋国手王积薪对弈;唐宪宗时的医人郑法,“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翰林院棋待诏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 。
舞蹈类休闲体育文化活动
踏球舞。踏球舞是一种女子舞蹈,又叫胡旋舞,由西域传来。唐玄宗时,西域康、米、史、俱诸国常向大唐王朝进献“胡旋女”。《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唐人段安节《东府杂录·俳优》也记载:“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球子上,其妙如此。”唐人王邕在《内人蹋球赋》中描述了宫内女子在球上作舞的情景:“球上有嫔,球以行于道,嫔以立于身。出红楼而色妙,对白日而颜新”,“球体兮似珠,人颜兮如玉;下则雷风之宛转,上则神仙之结,……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封氏闻见记·打球》称胡旋舞为“蹋球之戏”;“今乐人又有蹋球之戏,作彩画木球,高一二尺,伎女登蹋,球宛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
剑器舞。剑器舞也是西域传来的一种舞蹈,属剑舞中的一种。舞者手持双剑,合着乐声节奏,翩然起舞。开元间(713—741)女艺人公孙大娘就精于剑器舞。著名书法家张旭看过她的剑器舞后,草书长进,传为一时佳话。司空图在《剑器》词中曾感叹地写到:“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潼关一败胡儿喜,簇马骊山看御汤。”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