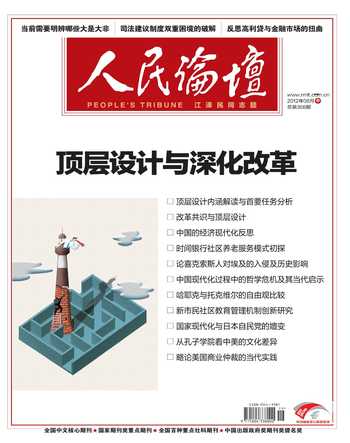法律视野下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
黄丹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集中显现,并形成多种利益群体,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新形势下,了解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属性、树立法律视野下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法律视野群体性事件新思维
群体性事件,是指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定数量的群众参与实施的,采取游行示威、静坐、上访请愿、群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罢工、罢课、罢市等非法手段,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群体性行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会引起很多负面效果,但另一方面,如果地方政府早作准备、创新思维、完善机制,同样会使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成为深化改革、创造社会和谐的契机。
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属性
信访权利的法律依据。其一,信访权利的宪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上述规定是信访权利的重要宪法依据,同时表明行使信访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管理和反映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也是公民对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状态进行民主监督的重要方式,直接体现了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的宪法原则。
其二,信访权利的基本权利依据。首先,从人性的角度看,向公共权力主张权利和谋求实现某种利益诉求,既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一种本能,也是实现自我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信访权利是每一名社会成员理应享有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彰显社会正义的一项自然权利和道德权利,它先于宪法而存在,具有相对恒定的价值,是公民对抗来自公共权力侵犯的有力武器。
其次,从权利的主体看,每一名社会成员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和意愿)都可能成为信访权利的主体,而且无论是古代社会的臣民,还是现代社会的公民,以及不同国家的公民,都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享有这种权利。这种权利的普遍性表明,信访权利本身超越了特定时空,带有普世性的价值特征。
再次,从权利的客体看,信访权利的客体既有关于人身权利方面的诉求,也有关于政治权利方面的诉求,还有关于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方面的诉求;既有个人自身的权利诉求,也有多人以上的集体权利诉求。这种客体的广泛性表明,信访权利不同于普通法律所规定的法律权利,是一种综合性的基本权利,由多种基本权利组合而成。侵犯信访权利,同时就是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多种基本权利。最后,从宪法的渊源看,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五种关于诉愿的权利,即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控告权,都可以视为信访权利的宪法渊源。在内容上,信访权利主要通过反映情况,提出批评、建议的方式来实现;在功能上,信访权利带有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民权利提供救济的双重功能,总体上与宪法第四十一条所列举的上述五种权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明信访权利蕴含着同样的基本权利因素。
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属性。最初我们将群体性事件称作“群众闹事”、“群众事件”,20世纪80年代称“治安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20世纪90年代称“突发性治安事件”,21世纪初,称“群体性治安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直至2004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使用了“群体性事件”的说法。2005年,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首次向世界媒体使用了“群体性事件”这一称谓。自此,群体性事件在主流媒体和官方话语体系中,逐渐成为一个中性词,这反映了我国政府对此类现象基本态度的改变,不再仅从政治角度进行批判,而是从政治和法律的共同视角来看待这一社会现象。
一般来说,群体性事件在开放尚不完全的过渡阶段较多发生。一方面,社会相对开放、宽松,群众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见;另一方面,社会相对封闭,民众诉求表达缺乏渠道,只好采用群聚抗议手段。因而,这个时期群体性事件会频频发生,成为常见的非正常行为。它具有如下属性:
多属人民内部矛盾。我国群体性事件绝大部分是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其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局部矛盾出现尖锐化的表现。人民内部矛盾既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也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本质。
事件的主体,是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的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成事主体的群体特征不明显,事先不存在紧密联系性,事中所具有的联系性在事后消失。
事件表现方式是非理性、非正统集群行为或称为群体行为的方式。即聚集不特定的多数人参加,一般表现为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之间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方式。
主体的主观要件。其动机是主动表达出来的,一般可纳入以下三类,即或表达诉求(即表达意愿、提出要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
事件的法律地位。就具体的群体性事件而言,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尚未违法的行为,有一般的违法行为,还有打砸抢烧杀、破坏生产建设、冲击党政机关等严重犯罪行为。
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案例分析
笔者调研发现,某市在长期处理信访事件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合法、科学的处置原则,即信访事件“有理有序的,解决问题;有理无序的,先解决无序,再解决问题;无理有序的,做好解释宣传工作;无理无序的,依法处理。”该市依据这个原则,成功处理了发生在2009年的一起群体性事件。
起因是该市一大型企业面临改制重组,因对此不满,企业职工将公司大门堵住,不让职工代表进入厂区参与企业改制重组的投票,并演变为规模性聚集,最多时达1000多人。在该市市委、市政府的妥善处理下,该事件持续2天后结束。企业生产经营恢复正常,重组改制也顺利完成。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对此事件的成功处置给予了高度评价:“措施有力、方法得当、效果明显”。
在此事件发生后,该市市委书记、市长第一时间到达企业,亲自与厂领导、车间主任和职工代表进行对话,倾听诉求,解释政策,并连夜召开常委会,提出解决意见。指挥部在将处理意见利用宣传车向聚集职工反复播报后,聚集职工于第二天中午全部离厂,第一次聚集被妥善处置。但到了第三天,几百名职工又迅速聚集,而且事态有升级的苗头,指挥部此时迅速下达指令,调集警力,要求群众限时撤离。在限时撤离过程中,在职工拒绝撤离的情况下,指挥部派武警插入人群进行分割、民警设置警戒带隔离,对聚集职工进行劝解。对拒不离开并有违法行为的职工进行强行带离。
之所以采取果断措施,是因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都有一个“发酵时间”,即从导火索的出现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之间要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如果在这段“发酵时间”内没有及时有效的处理,事件就会迅速恶化,暴力升级。而且,该市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慎用警力、警械、强制措施,因此,在此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公安干警与群聚职工无肢体接触、无受伤。
树立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
看待事件新思维:社会常态。现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社会底层群体和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剥夺感与丧失感,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舆论不放开、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通、体制机制存在问题,使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在所难免。因此,看待群体性事件,应以社会常态视之。
分析原因新思维:利益视角。今天之社会,是经济社会、市场社会,在发展中,有一部分人分享改革成果不多,他们起事,一般皆由经济利益而起,当然也由经济利益满足而落。
处理方法新思维:疏导原则。社会稳定分为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静态稳定是禁止做什么,老百姓不满,禁止他表达,以堵为主;动态稳定是有不满说出来,如果有道理就赞成,并进行制度调整,即以疏为主。面对群体性事件,主要方法是疏导,采取干群对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等资源,化解事件中的利益冲突,必要时可适当向民权让步。
维护稳定新思维:主动创稳。我国目前维护稳定的思维是压力维稳,即中央过多考虑对基层政府施压,没有给出制度性的解决渠道,使地方维稳工作处于政府维稳和民众维权的张力之中,地方政府成了中央和民众之间的夹心层:地方政府在沉重的行政压力之下欲完成以零上访为目标的任务,而民众在权利受损时就以各种非常规的方式冲破规则的限制,造成了地方政府对上扛不住,对下管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在不影响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迅速平息弱者的抗争。这种压力维稳机制会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压力反弹越来越大,直接威胁中央政府的权威。
(作者为中共丹东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法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