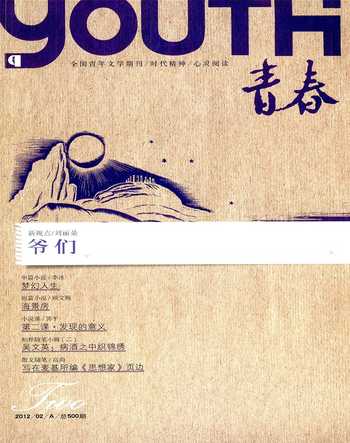李作家的《杀字系列》
柏桦
前不久,韩东来成都签名售书,在一次抽空的闲聊中,我突然谈起了一个我长期思考的问题,即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的本性或许是恨而不是爱(T.S.Eliot曾说过一个诗人应该“keep intensity”,我以为“intensity”的本质应是恨,因它比爱更强悍,也更具穿透力),但人都会伪装,肯定只会说爱是人的出发点,绝不会说恨。关于我与韩东对此话题的展开谈论,在此就不赘述了,我从此却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件旧事。正如标题所示,李作家(李柱)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对人看上去似乎爱很多(具体情节恕不说来),但其实却是一个杀气(我指的是虚无而有些老实的杀气)很重的人。下面,是我真实地回忆并叙述他1980年代的一小段令我难忘的生活。
一连许多天(当然是1985年的春夏之交),李柱为了写好他那日思夜想的《杀字系列》小说,开始认真地体验起了生活(因为他坚信,写作来源于生活这一“可爱而无辜”的教条)。首先他注意到他家隔壁一家小餐馆门口的一位杀鳝者的日常工作。只见那杀鳝者手脚麻利,仅单手提起鳝鱼,将那鳝头在脚盆上一摔,趁那鳝鱼头脑昏过去的当口,就在洗衣板上将那鳝的肚子剖开,一刀一刀切下去,最后将那鳝骨连带鳝头丢在一个桶里,又将那鳝片丢在一个塑料带里,来回重复,动作快速准确,没有半点闪失。那鳝的杀法细小婉转,使他还产生了一点艺术的享受,只是胸中一口杀之豪气顿消,似乎只落得个杀伐的浅吟低唱,看了几日觉得无趣,也就不去了。
为了增加内心的杀之密度与强力,为了亲历杀的气氛和血腥,不久,李柱就常去离家稍远的市场,观看各式各样的杀害过程,杀鸡、杀鸭、杀鹅、杀鱼,只要哪里开杀他就往哪里钻,睁大牛眼(须知李柱眼睛极大且鼓)死死盯住。由于日日去看,弄得那菜市上杀家禽的人觉得十分怪异,而且见他一脸杀气,又是一个瘸子,所以也不敢惹他,只是背地里议论一番,认为这人有些疯癫。久而久之,他还与市场上一个杀鸡快手搞熟了。那杀鸡者一次问他:“你对这杀鸡杀鸭如此有兴趣,是不是也想学呢。我看你也不是从事我们这个行当的人,那你天天来看是为了什么?”
“我是作家,经常给报社写稿,最近我正在为报社写一组‘杀字系列小说,我这叫作家体验生活,观察你们这些人是怎样杀死动物的。”
“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是一个作家,了不起,了不起。不过,我们乡下杀猪不知你看过没有,如有兴趣,我专门陪你去看整个杀猪过程,那是真正的大东西,那些人才可称为屠夫,我们这些杀鸡的与他们比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了。”
李柱一听,牛眼一翻,大为兴奋,说道:“好,就这么定了,改天我同你一道去你们乡下看杀猪,耽误了你一天时间,我请你吃酒,如何?”
那杀鸡者又瘦又矮,还是一个独眼,一听还请吃酒,也高兴起来:“要得,要得,改天上午你到市场,我们一道去乡下看杀猪,至少可以看到杀几头猪的过程。”
这一日,李柱果然与那杀鸡人来到乡下,当时已是下午时分。独眼人将李柱带到屠宰场,一阵怪臭腥味扑面而来,李柱精神为之一振,鼓起双眼,拖着一条瘸腿走了进去。
里面已是好生热闹,只见几个人将一只猪儿从地上抬起,放到一张土砖砌的台子上。猪儿一抬上去,脖子正好卡在宰割的要害处。那肥猪一副受难的样子,似乎预感将被宰,发出狂呼乱叫的声音,那惨叫声也逗得地上待宰的猪儿同声惨叫。独眼走上前去对那杀猪匠说了些什么,杀猪匠回过头来对李柱咧嘴一笑,还走过来握了一个手。李柱握住那油浸浸的厚手就象伸进猪油里一样,再瞧那杀猪匠,五短身材,一身肥肉乱颤,笑起来就像猪头,耳朵又大又肥,似乎也抖了起来,说是欢迎作家来参观,说完转身就朝那嚎叫的猪儿走去。李柱还没来得及看清他右手怎样出刀,一把尖刀已插入猪儿的喉咙,猪血当即喷涌而出,李柱此刻也感受到一股热浪,心里也遭受到一股从未体会过的高速的快乐与满足。
接着李柱又看到那杀猪匠杀死一头病得无力挣扎的老母猪,那老母猪皮肤打皱,杀出的血又乌黑又稀少,哼也没哼几声就断气了。断气之前,那老母猪一直茫然地盯着李柱,仿佛要乞求什么。李柱一双牛眼也一直盯着那老母猪,一眨不眨。突然,李柱眼睛一翻白,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也发出杀猪般地嚎叫,声音盖过待杀的另几只猪儿,那声音不仅把杀猪匠和独眼杀鸡人吓了一跳,连那几只猪儿也吓得不敢叫了,直直地盯着那地上翻滚的人不像人,猪不像猪的东西。
独眼人和杀猪匠赶快跑了过来,杀猪匠一看李柱双眼翻白,上来就是几个耳光,又端来一盆清洗猪内脏的清水刷地倒在李柱脸上,李柱打了一个激楞,又嚎叫起来,声音更尖,嘴歪斜着,张得大大的,口水及白色泡沫顺着嘴角往下直流,全身也抽搐起来,那瘸腿一个劲地抖,那好腿像僵尸一样伸得笔直。
独眼人也着急了,突然情急生智,赶快跑到外面扯了几大把青草回来,一把一把地往李柱口里喂,李柱歪着个嘴大嚼起来,杀猪匠一时也受到启发,知道这人癫痫发了,也跑到猪圈去提了一桶猪潲来,将那猪潲水倒在一个破盆里,再将李柱的头按入盆中,李柱好像久渴之人,立即开始了狂饮乱嚼,好像饮下了什么起死回生的药,饮下了琼浆玉液似的,吃了青草又饮了猪潲水,李柱的嚎叫减弱了,逐渐变成了低吟,慢慢地完全平静下来,白沫也不吐了,身体及四肢开始恢复正常,那黑眼珠也从那一片白眼中钻了出来。最后独眼人将他挟到一张靠背椅上坐下,又拿一张湿毛巾给他擦脸,过了好久李柱才回到原来的神态,但内心也确实起了完全的变化了,恐惧、疯狂、愤怒、痴呆,血与残杀在他内心冲撞着、化合着。他也想亲手杀些东西了,但猪这庞然大物他是不敢杀,那就杀鸡吧。
再说李柱那日去乡下看过杀猪之后,杀之快意就不停地在他内心涌动。回到家中第三天上午就去菜市买了一只母鸡、一只公鸡,并告诉家人下午要在院中亲自操刀宰杀。
中午吃完午饭后,李柱睡了一个午觉,起床后特别换了一身运动装束,也想显示一下杀的利索和快捷。他先到院中踱了几个圈,再将那两只鸡放在院中作最后的玩耍,还去米缸里抓了一把米来喂,像是要给死刑犯饯行一般。只见那鸡旁若无人地将米啄来吃了,又到院中潮湿的墙角去刨那地下,找些小虫来吃。李柱看了一阵就跛着一条腿去厨房磨刀。正磨着磨着就听见院里的鸡咕咕地吵了起来,举头从窗台望出去,只见那两只鸡正在戏耍,那母鸡肥硕地在前面奔着,那公鸡雄赳赳地在后面追赶,鸡冠鲜红,直扑过去,一下就骑在母鸡背上,只见那母鸡做了一个投降的样子,把身子伏在地上,直打哆嗦,那公鸡一跨就上了母鸡的背,又见那公鸡把尾巴向下朝母鸡屁股一压,刷地一跃,就心满意足地跳了下来。那母鸡好象沾了一身灰,浑身鸡毛竖起抖了一阵。公鸡似乎觉得有趣,上去鸡头一点,朝那母鸡脸上啄了两口,然后又用鸡腿去刨地面,鸡头在地上不停地啄,那母鸡也兴奋了,突然旋了几个圈,抬头去捕那一两只小飞虫。李柱看到此处心里就涌起一股古怪的杀气,操起菜刀跑到院中去捉鸡,他想先宰那母鸡,看它还兴奋得到几时。李柱本是瘸腿,一走路屁股一翘一翘的,那屁股只有拳头般大,或者根本没有,只有两条瘦腿连在身体之下。他续扑了几次也没扑到那母鸡,倒把那母鸡追得神经质起来,连鸡毛都硬硬地竖起了,似乎觉得又一只大公鸡要追它做那事。追了一阵,还没追到母鸡,那公鸡好像在一旁看笑话离得远远的。突然李柱发现墙角有一个大筐子,他抓起筐子就去筐那鸡,筐了两次没有筐住还跌了一个跟斗,嘴上和鼻子都沾了泥,很是气恼,接下来第三次,李柱就像疯了一般几个猛追,最后总算将那母鸡筐在筐子里了,就伸手去抓那鸡,旁边那看笑话的公鸡这时觉得不妙,颈项上的毛也倒立起来,冲向李柱,对准李柱额头一阵猛啄,啄出几个口子来,李柱怒火上冲,举起刀就横砍过去,公鸡眼尖灵活,翅膀一拍就飞得远远的,咯咯地叫着再不去管那母鸡了。
李柱喘着粗气将母鸡从筐里一手捉了出来,用菜刀去抹那鸡脖子,抹了一半血就溅了出来,那母鸡痛得直扑,李柱一慌,手一松,母鸡倒在地上,又一阵乱扑。李柱瞪着一双牛眼楞在那里,突然大叫一声就朝那鸡头砍下去,使足平生力气连刀都陷在泥地里,鸡头飞到一边去了,那鸡脖子还陷了一半在地里。又过了一会儿,李柱如梦初醒,才想到那公鸡,一看公鸡已吓得在院里疯跑了。他提起筐子又去捉那公鸡,那公鸡胆子要壮些,也要疯些,捉了半天也没捉住,李柱一急,口水也不停地流,抹一把擦在运动裤上,稍歇一阵,再鼓起干劲去扑那公鸡,连扑几次,终于一只手抓住了公鸡的翅膀,顺着鸡翅膀就将那公鸡提了起来,那公鸡脖子上的毛根根倒竖,鸡嘴半张,鲜红的鸡冠也歪在一边,雄不起来了。李柱一阵狂笑,想到额头上的几个口子又是一阵愤怒,操起刀就去割那公鸡的脖子,突然公鸡一使劲,腿一踢,那菜刀一滑却割到李柱自己的手指上,李柱忍痛又去割那鸡头,割了一半,那公鸡掉落地上,鸡头虽切了一半,公鸡却英勇地站直了,昂着头,鸡冠又竖了起来。李柱一看自己的手指已割掉一小块皮肉,伤口流血不止,再看那公鸡还如此威猛,心中杀气大发,热血上涌,头发也像公鸡毛一样根根倒竖,操起刀去砍那公鸡,公鸡脖子流血,但仍在做最后亡命的疯跑,李柱连滚带爬再次把那公鸡捉拿,这次李柱心里更狠,把那公鸡提到厨房,将鸡头按在菜板上,一刀剁下,鸡血溅得四处都是,哪知道这鸡的头被剁下后,公鸡居然又站立起来,李柱大吓,以为出了鬼怪,呆立在那里,只见那无头公鸡在厨房里乱飞乱扑,一连打碎了好几个碗盏,最后突然向李柱胸口猛撞过来,李柱吓得往后一退,头碰在墙上,立即起了一个大包,跌倒在地,好久才从地上爬起来。李柱这时惊魂未定,又觉嗓子冒烟,赶紧将刀一扔,回自己房中连喝两大盅茶水。从桌上一面镜中李柱发现自己完全变了一个模样,一身肮脏,鼻子上的泥和嘴角边的口水混在一起,头发如乱草,手上、衣服上、脸上尽是血迹。而一阵阵杀伐的快意也随之叩击心头,随着这快乐在内心的起伏,李柱操起钢笔,铺开纸张,就在桌上写了起来,杀字系列第一部:“亲手宰鸡”与“相看杀猪”。
时光飞逝,如今已是2008年初夏的光景了,某日夜晚,李柱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去参加他的一个婚礼(李柱如今已年届50,是第二次结婚),说是与一位女法官喜结良缘,还说我务必出席,并说他还要写他的“杀字系列”小说,当时,我正处于独饮后的眩晕中,除了震惊,也不知说什么好,当然事后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他和女法官的婚姻,我是百感交激的。
责任编辑⊙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