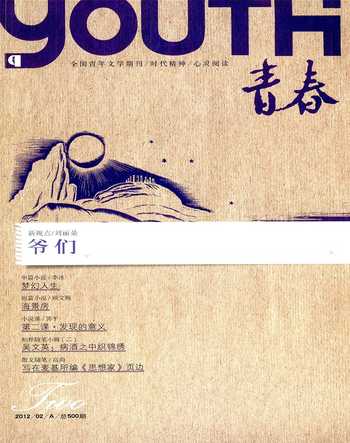明白
李露瑶
姑父能够娶到小姑,大家都说,明白立了大功。
明白是我家的一条狗。很多年后想起来,我始终没弄清楚明白怎样立了大功,就像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一条狗为什么叫明白。
明白是什么时候到我家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似乎明白一直都游荡在记忆里。明白总是那么大,白色的毛暗淡无光,泛着陈旧的黄色。明白每天都在忙碌,忙碌着寻找失散的孩子。
或许我忘了说,明白是条母狗。每年明白都会做一回妈妈,人们聚成一个圈,咂着嘴,评论着每一条小狗。一个月之后,这些微睁着双眼的肉团就会被抱走,要么隔着几条小路,要么隔着几条河流,要么隔着几个村庄。明白每天忙碌着寻找每一个孩子,舔毛喂乳。“你真是个好妈妈。”我拍着明白的头说,然后开始剥火腿肠。
我喜欢吃火腿肠,明白也喜欢。在我美滋滋地嚼着火腿肠的时候,明白总是安静地趴在我脚边,专注地看着我。“你吃吗?”我举着火腿肠在明白眼前摇晃。明白还是盯着我。然后我就掰下一截火腿肠,远远地扔出去,明白和我一起看着火腿肠飞起,落下,滚几个滚。然后明白转过头,继续看着我。
“好吧,给你。”我重新掰下一截,放在明白面前。明白低下头,用前爪捧着火腿肠,歪着头吃起来。
这样的游戏玩了一遍又一遍,当然,这样时候大多在周日的上午,阳光温暖明媚,看见屋前道路上扬起的灰尘。
不时有车停在门前,人声、脚步声。这时,明白会突然竖起耳朵,放下火腿肠,低低地“呜”一声,冲到大门边,卖力地叫嚷一阵。
接着会有圆的、方的、或者看不清楚形状的脸露出来,有人喊“这狗咬人吗”,有人问“小孩儿,你家大人在吗?”
这些人,都是来向小姑求亲的。每到周日,小姑都会给我一大包火腿肠。我大大方方地收下,然后尽心尽职朝大门坐着,对着门外的各种声音作出回应,“这狗咬人”,“家里没人”,“大人出门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姑从护士变成了医生,求亲的人越发得多了。爷爷乐呵呵地对别人说:“自家狗不咬一家人,姑娘的姻缘天注定。”明白,似乎成了一桩姻缘的决定人。
自然,进了家门,没有被明白挡在门外的唯一一位求亲者,是我的姑父。这件事在当时成为传奇,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说起。但是,准确地说,姑父进了家门,却不是唯一的一位。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叫陈木头的叔叔。这件事,或许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
当时我正在犹豫是接着吃一根火腿肠还是再吃两根火腿肠,明白安静地趴在我的脚边。
“小朋友,你家大人在吗?”太阳正对着我的眼,来人只成了一个黑影。我眯着眼睛才认出是陈木头叔叔。他的眼睛亮闪闪的,他的嘴角弯弯的。我点点头,向后一指。
许久之后陈叔叔才离开。他的眼睛不像刚刚那样明亮,他对我笑笑,从口袋里拿出两块糖给我,又摸摸明白的头,走了。
“一个木匠也上门来了。”爷爷的声音。
“无父无母,姑娘嫁过去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奶奶的声音有些忿忿。
我吃着糖,拍着明白的头问:“明白,明白,你为什么叫明白?”明白当然不会回答我。
很多年后,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清楚地记得当日的细节,而对大家津津乐道的姑父的传奇却有些模糊。
姑父什么时候到我家的,我不知道。或许因为他连看我一眼都没有,就直接走进屋了。因此,我也没有看见他。我低着头拨弄着明白的耳朵,因为那天明白耷拉着耳朵,就连我剥好的火腿肠,明白也只是舔了舔。
姑父出门的时候,我才看见他。黄、瘦,这就是我全部的印象。
我跑进屋,告诉母亲,明白病了。母亲看我一眼,问:“你觉得刚刚那叔叔怎么样?”没等我回答,母亲接着说:“国家干部,年轻轻的,不容易啊。”母亲一个人说着什么,没问明白的病。我怏怏地走出门去。
此后,求亲的人渐渐就没有了,姑父几乎天天都会来。全家人都对姑父表现出极大地热情,小姑则一天到晚微红着脸颊,腼腆地笑着。大家说,姑父无父无母,以后小姑嫁过去没有负担,自自在在;说姑父面有富贵相,有前途;说小姑命里修来的福气;当然,也说明白会挑人。爷爷乐呵呵地说,“自家狗不咬一家人,命里注定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周围的大人突然变得那么奇怪。一天,我问正在洗碗的母亲:“明白为什么没叫?”
“什么?”母亲问。
“明白为什么没对姑父‘汪汪叫?”我怕母亲听不懂,特地加上了拟声词。
“小孩子家知道什么。”我最讨厌别人喊我小孩儿了,虽然我确实是个小孩。
“我什么都知道。”我噘着嘴说。
“哦,知道什么,知道火腿肠好吃?”母亲笑着走过来,拧拧我的鼻子。
我抹去鼻子上的水,“小姑给明白喂肉汤了,我看见的。”怕母亲不信,我又加上一句,“爷爷也看见了。”
母亲回头瞪我一眼,“你懂什么!这叫门当户对。”
我当然不知道什么叫“门当户对”,但是母亲完全无视我的样子让我十分生气。我跑到门外,拽着明白的耳朵大喊:“明白,明白,你明白什么?”
尽管我什么也没明白,小姑还是嫁给姑父了。
小姑出嫁的那一天,屋前屋后的桃花全都鼓胀开花瓣,张扬地怒放。在震天的鞭炮声中,花瓣雨一样地飘落。有老人说,这正应了“桃之夭夭,宜其室家”的古话,是个好兆头。姑父穿了一身簇新的西装,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像鱼一样穿行在酒席中间,招呼客人、递烟敬酒。
婚宴上的人们都夸赞姑父礼数周全,招待周到;羡慕爷爷奶奶有福气;夸说明白有灵气儿。
明白这天却没显出多少灵气,它像疯了般,对着纷纷扬扬的桃花瓣狂吠不止。我奔过去,大声喊:“明白,明白,你怎么了?”明白还是对着桃花乱叫。花瓣轻轻地飘落,粘在明白身上、鼻子上,明白仰着头,对着漫天的绯红“汪汪”。
结婚后,小姑还常常住在家里,姑父也就当然地住在一起。这让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怀不满。我却很高兴,家里多了一个人就意味着多一个人跟我玩。
一天,姑父看见明白用爪子挠痒,对我说:“明白要洗洗澡了。”
见我面露疑问,姑父说,用一点点“灭虱灵”,以后明白身上就不会有虱子了。
姑父找来一个塑料桶,满满地倒上井水,将一包“灭虱灵”倒在水里,搅拌一下。然后示意我把明白抱来。
姑父从地上捡起一个破旧的塑料袋,拉长,将明白的嘴扎起来。然后抓着明白的前腿放进水里,只露出头。明白两条腿在水中剧烈地踩着,嘴里“呜呜”地叫着。
姑父让我舀一勺水倒在明白头上,说这样才能杀死全身的虱子。明白在水里扭动着身子,姑父牢牢地按住它。我迟迟没动,听见爪子和桶壁摩擦的声音。
姑父腾出一只手,准备拿身后的舀子。这时,明白突然从桶中跃起,远远地跑出去,在门前的田地里急速地奔跑,一圈又一圈。明白会死的,我想。姑父指着桶里的几粒黑点对我说,看,这就是虱子。
明白在田野里奔跑、在泥土里打滚,湿漉漉的毛上沾满了泥浆。晚上的时候,明白已经成了一只泥狗。皮毛沾满泥浆,一根根粗细不一,简直就像一只刺猬。
泥土掉落之后,明白依旧挠痒。姑父说,再洗一次虱子就没有了。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因为小姑生了小宝宝。姑父每天在家、医院、工作地之间来回,顿时忙碌了起来。
每晚姑父都要从家里带一罐鸡汤去医院,每晚明白都会跟着姑父去医院,然后再跟着姑父回来。姑父逢人便说,晚上有明白跟着,什么神神鬼鬼、歹人恶人都不怕。有一次,姑父一晚上都住在医院,明白就在医院门口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明白披着一身白霜走回家。大家都笑说,明白到底是条狗,下霜还躺在外面。
小姑抱着孩子在院子里晒太阳,明白站在旁边摇着尾巴。晒着晒着,明白就会追着自己的尾巴原地绕圈,左一圈、右一圈。婴儿瞪着眼睛看着明白,大家也都看着明白。这狗,你看,哈哈……
笑声哄然炸开,再像浮尘缓缓地落地。奶奶的骂声就杂在笑声的缝隙里。奶奶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因为河西面新建了一片厂房,白天黑夜,机器隆隆。
对于这片厂房,人们除了称赞就是羡慕。人们说陈木头叔叔靠这片厂房发了家,人们称赞陈木头叔叔给村里修了路,人们羡慕陈木头叔叔给丈人丈母娘买了大房子。
奶奶的抱怨更多的不是因为机器,而是因为陈木头叔叔。这连我都感觉出来了。
不过,奶奶的抱怨没持续几天。姑父升官了。
姑父升官后接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灭狗。因为某地的狂犬病已经成了灾害,所以,消息所到之处的狗都应该被杀死。姑父每天坐在宣传车里,在临近的几个镇子里宣传,高音喇叭里竭力地叫嚷着:“积极响应号召……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力争消灭每一只狗……”
姑父回来的越来越晚,明白还是每晚去接他。后来,我们突然意识到,明白也是一只狗。
杀狗的风潮终于刮到村子里,像一个期待已久的节日到来一般。人们拿着绑着镰刀的竹竿,在路上寻找游荡的狗。“……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高音喇叭的声响整日回荡。在高亢的声波里,全村的人都陷入杀狗的狂热情绪里。每只狗都瑟瑟缩缩,夹着尾巴在墙角边慌慌张张地四处张望。转过墙角,背上会不会插上镰刀,哪只狗能预料到?乡村的夜晚陷入了完全的寂静。
爷爷爬着梯子将明白藏在阁楼上。“明白,你千万不要叫。”我摸着明白的耳朵说。明白的耳朵尖尖的,直直地竖着。明白趴在两只前爪上,支楞着耳朵。“你一出声儿就会死的。”明白的耳朵软软的,我在明白旁边放了一大包火腿肠。
这天晚上,爷爷就跟姑父商量怎么将明白藏起来。姑父点起一根烟,黄瘦的面孔在烟雾里隐隐约约。这个,不好办吧。姑父慢吞吞地说,大家都认识明白。
爷爷抿了口酒,半天没说话。一根烟燃尽了,姑父重又点上一根。“真没办法?”爷爷问。姑父没说话。屋里有些闷,我悄悄站起来,准备到院子里去。
爷爷突然把酒杯摔在地上,“真没办法!”
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难以记清这句话的语气是疑问,是愤怒,是叹息,是无可奈何,还是其他。
第二天早上,明白不见了。我想,明白是死了。为了姑父的前途,明白需要牺牲。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人们的意愿不会改变结局。午饭的时候,姑父回来吃午饭。全家人似乎都很高兴。我偷偷爬上阁楼,看着一袋子火腿肠。明白怎么死的?是装在袋子里打死了,还是放在河里闷死了,还是被一把镰刀劈成两半……
母亲试图把我从阁楼上拉下来,我扭来扭去挣扎着。明白死了,明白死了。我冲母亲大喊。母亲看看我,说,明白没死。姑父把明白藏在宣传车里送给了一个朋友,他们会好好照顾明白。你姑父是个聪明人。
把狗藏在动员杀狗的车里送出去了,姑父真是聪明。我高兴起来,怪不得全家人都这么高兴。这里是明白的家,明白怎么会死呢。隔着这么长的光阴,想起母亲当时的话,我依旧满眼湿热。
我们都知道明白活着,可是明白始终没有回来。姑父说,那家朋友舍不得。爷爷张了张嘴,叹了口气。这么好的狗,谁会舍得。大家都同意爷爷的话,心里也感念着那位朋友。
姑父的新居要装修了,大家都去帮忙。表妹早已不是吃奶的婴儿了,也跟着大家做些小活计。她吃力地从楼梯下面搬出一个罐子,黑褐的土陶罐子,积了厚厚一层灰。我连忙走过去帮着将罐子搬出来,“这么脏,扔了吧。”
“说这里面腌着一只狗呢,好多年了。”表妹说。
【评语】
这篇《明白》,语言、心绪的进步很明显,平实、浅淡,力道内蕴。
作者的本意显然是为了写人,而着力的抓手却选择了一条狗。这一选择非常精彩,围绕着明白的命运,把与之有关的人写透写深写得微细,评价性议论性的过于直白生硬的问题全然避开了。情感的控制、理性思索的发抒因而都融于有血肉的形象之中,读之犹如平静人生中的惊雷在内心轰响。
文章前面的铺写很能沉得住气,态度与结局正相反。小姑婚恋这一对全家来说都非常重大的事件在一双清澈的眼睛中映现,真实、平常而有那么欣然有生机,以至于读到最后时,我们会发现此前所有的人的信息都与这结局息息相关,让我们坚实地理解这生活的冷酷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