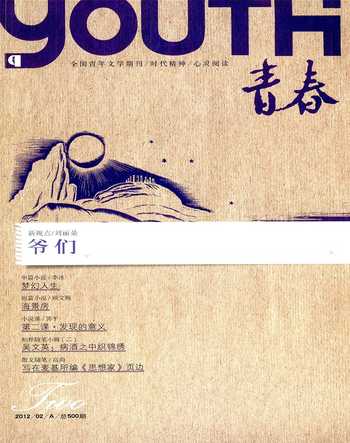归址
那节生物课上,我的思想居然开了小差。我认为其实我是有一个双胞胎姐姐的,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失踪了,在这件事情上父母对我守口如瓶,谈论另一个女儿在我们家里是个禁区,或者也并不是什么禁区,只不过是我的禁区罢了,也许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不仅谈论而且要大谈特谈,而且母亲一准要流着泪,躺在父亲的肩膀上,身体因为哭泣而抖个不止。父亲就像琼瑶剧里的男一号一边递上纸巾一边哄劝,乖,别哭了,别哭了。我相信她一定会回来,我有这种预感!
父亲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我的双胞胎姐姐回来了,就在某个我没来得及做好准备的当口,一个和我一样漂亮,甚至比我更漂亮的女孩子,猛然间闯入我的生活。她身上穿了与我毫无二致的衣服站在教室门口里顾盼生姿,没错,就是顾盼生姿,就像戏台上的青衣,喜欢翘着屁股探头探脑。当然,我姐姐要比青衣更优雅,也没有那么多忧郁,反倒热情开朗,拿青衣来比喻也许是错误的,或者叫她花旦吧。而青衣也许是用来比喻我的,我的内心正像青衣的满含羞涩,款款莲步轻挪,是这样的。班里男生从不敢多看我一眼,我通身总散发着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气息。可是,谁让我是尖子生呢?你知道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优秀人物的周边总是缺乏朋友的,因为优秀使他们站到了更高的制高点上,对于身后的人们,他们喜欢采取俯视的视角,抑或他们必须采用类似的视角,要知道有些时候是骑虎难下了。各科老师对我的宠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班主任生物老师,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是爱着我的,不是师生的爱而是男女之爱,而另外一些时候,我又会无端觉得他是我的父亲,因为那种爱护只能是一个慈父对其爱女的感情。各科老师的宠爱让我昏昏欲睡,让我自认为果然是天之骄子,我没有朋友,也不需要任何友谊,我将一切友谊看成马屁精的谄媚,看成不怀好意的企图种种。但是即便这样,他们还是一样热爱着我啊!这通过班干部选举投票的得票数就能看得出来。那时候我还坐在教室的第一排第一个位置,我同桌是邢林林,她的成绩只比我差五分,当然也是我最强劲的敌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邢林林的防备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为了保住全班第一名的位置,我几乎就绞尽脑汁,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除了吃喝拉撒睡,别的时间全扎到书本里。尽管这样我的成绩也不过只比邢林林多五分。
我们班的座次是根据名次来排的。每排四张桌子八个人,中间是两条走道。因此第一排是成绩前八名者,第二排是九到十六名者,依此类推。当然这样的座次并非固定不变,相反是经常变动的,每次测验结果发布之后,座次都有一次相当大的变动。这不仅是说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还包括生物课程的单科测验,显然班主任在无形中把生物成绩当成了全部成绩的一个标本,因此在我们班里你常常看到最后一排那些渣子生也是无时无刻不端着生物课本背书的。
所幸,我一直就在第一排第一个位置。可是姐姐突然来了,我有理由相信她有着和我同样高的智商甚至比我更高,站在生物学的角度上说,一母连胎,往往第一个孩子比第二个孩子身体要结实一些,发育要完全一些,就像老母鸡下连蛋的道理似的。我这样说当然没什么科学依据,因为我是尖子生吗,尖子生的特点就是自以为是,而且挺自以为是,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沉浸在这种揣测里面不能自拔。
我母亲一准要将脑袋靠在父亲肩上,然后泪水涟涟,简直有些装腔作势的姿态了,这样的母亲让我陌生。但是,我认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在我离开家的时候,他们将脑袋靠在一起,从某个秘密的地方搜出一本发黄的影集,然后指着某个初生的婴孩说,看吧,我们的女儿,看吧,可怜的孩子!母亲又装腔作势了,泪水潸然,甚至将脑袋压得更低几乎就靠在父亲胸肌上面来了。我掐断这种肉麻的联想,姐姐就是这时候走进教室来的,说实话,我没看到她站在门口顾盼生姿的情形。你知道的,尖子生的特点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哪怕操场上原子弹爆炸,尖子生也绝不会交头接耳。一切关于顾盼生姿的描述全是邢林林告诉我的。邢林林说,丫的真骚!一看就是个狐狸精,我敢保证,不出两天就有男人被她勾上手!邢林林说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得咬牙切齿,好像恨不能将我姐姐撕成碎片。我知道她是嫉妒,因为她相貌丑陋,一条清晰的刀疤从左耳一直缠绕到下巴右侧,就好像她现在的脸并非真实的脸而不过是一张面具。她当然同样地嫉妒我,甚至背地里散播谣言:张依依比我高了五分,不过是喜欢勾引班主任罢了,你们等着瞧吧,他们早晚上床!你们等着瞧吧!
当年我父亲和母亲是怎么跑到床上去的我不知道,我父亲是母亲的代课老师,但是他们不能算严格的师生恋范畴,他们年龄相仿,母亲读夜校,父亲不过是暂时顶替那个患痢疾的老师来上几天课,那几天课还没结束,父亲就被母亲勾引到床上去了,一定是母亲勾引了父亲,你知道的,在男女问题上面,一定是女人的错!人人都是这样理解的。就像邢林林觉得我一定勾引了班主任一样。
我的姐姐突然来了,但是,在她身上我没看到任何关于亲情的流露,她看我的眼神虽然有点怪异,但那绝不是亲情。我一直认为亲情就像春风拂面,但是姐姐看我的眼神,有点秋风扫落叶。当然,她很少这样看我,因为她几乎就不看我,仅有几次的目光相撞,秋风扫落叶让我心慌。我认为那是没道理的,她是我的双胞胎姐姐啊!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子宫里呆了9个月零10天,我们应该是最亲近的人呵!可,事实上我们非但不亲密却好比有着深仇大恨,难道姐姐不肯原谅当年我对她的取而代之?你难道不知道,那时候我和你一样手无缚鸡之力,对于父亲的遗弃或许当成礼物馈赠给某些什么样的人物,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意思呵!我既没有在你脸上甩出巴掌喊一声“贱人,你给我滚”更没在你屁股上踹上一脚将你踢下楼梯。
那时候我把脑袋埋在书本里,我听到优雅的脚步声不疾不徐从我身边走过去,她的经过带来了一阵风,带了深秋的寒意,我下意识就紧了紧衣服,我的眼睛一直停留在桌上的生物课本上。邢林林说,如果你继续这样看书,眼睛迟早要瞎的。我知道她不过是危言耸听,她太喜欢嫉妒我了。
不疾不徐的脚步声从我身边经过,我嗅到一股麦草的香味,好像小时候我躺在麦草丛中的感觉一样温暖,我奇怪一刹那间心底里翻涌而来的温暖,是亲情,没错!
大家好,我叫张依依!
讲台上面一个声音如同百灵鸟,婉转清灵,当然这些形容词都不具备声色,都没法表达那个声音带给我的颤栗,早前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也有类似的声音,我实在想象不到这样的声音会从另一个人嘴巴里发出来。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抬头,我始终将脑袋埋在书本上面,那是生物课本。这时候邢林林就开始小声嘀咕了,她很喜欢这种小声嘀咕,因为她知道我从不和她说话,比如她提醒我眼睛会瞎掉吧,她采用了指桑骂槐的方式,她一手拿了一只橡皮一手拿了一支铅笔,她模拟动画片配音演员的音调让橡皮对铅笔说,如果你继续这样看书,眼睛迟早要瞎的。橡皮继续对铅笔说,别以为你会得意很久,看有一天我怎么将你清空。
讲台上的声音刚落,邢林林又小声嘀咕了,丫的真骚!一看就是个狐狸精,我敢保证,不出两天就有男人被她勾上手!邢林林这次的嘀咕和往常不太一样,往常她的嘀咕是针对我的,这次她是针对另一个人,因此她好像有了和我攀谈的欲望,好像我们已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但,我对于她的举止相当鄙视,我认为除了学习成绩之外她可真称不上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然,第一名的我也不是,第三名撒欢成性,第四名小偷小摸,第五名毛病不很外显却是个忧郁症患者,常常拿跳楼去刺激他们宿舍兄弟们的神经。第六名爱说粗话,第七名随地吐痰,第八名更夸张,居然有偷窥嗜好……但就是我们这样一群人每年都会获得一枚“品学兼优”的奖牌。因此我们就“品学兼优”了,对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质疑。
我绝不打算和邢林林攀谈,因此,我莫名地看着邢林林那幸灾乐祸的眼睛,然后又沿着她的视线朝讲台看过去,那里站了一个美人,她说她叫张依依。不仅和我同名同姓而且外貌和我简直是一模一样,也穿了同样的服装。只是她的举止落落大方,笑容可亲可敬,显然她很擅言辞,简短的开场白一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这时候我又看着邢林林,我知道我的眼神里有求救的意思,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怎么了,我求救地看着邢林林希望她能说一些什么,我奇怪以往竟是如此厌烦她的絮叨。可是邢林林还是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姐姐插班到这边之后,我的注意力就再也无法集中了,我幻想镜头下父母是怎样把白花花的身体纠结一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制造了我和姐姐,然后他们又是怎样无情将其中一个丢弃,而在此以后的漫长岁月,母爱在母亲心底一点点的复苏觉醒,终于长成参天大树,可是,姐姐却来到我身边了。我坐在前排,敏感的意识到姐姐的眼睛像一枚匕首,从后面斜刺过来。按照我们班的规矩,新来的学生不管之前成绩如何,都要坐在最后一排。姐姐就是坐在最后一排和一群渣子生呆在一起,我从心底里非常同情姐姐的处境,但是对于很快改变我是抱有信心的,这种信心甚至到了让我担忧的地步,我知道姐姐迟早会将我驱逐到邢林林的位置或者别的什么位置,然后将我的位置取而代之。我当然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但是自从姐姐来到我身边以后,我就清楚地明白这一天是迟早会发生的。看到姐姐冰冷眼神的一瞬间,我懂了蓄积在其中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我知道我是在劫难逃!
我的背上扎着那把匕首,雪亮的匕首,大有一刀让我毙命的意思,我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全在监控之下了,因此我常常是一整天一动不动地坐在那边,常常弄得浑身酸麻,下课后那腿就像刚从手术台上下来一样,麻得不敢走路。邢林林早已看透了我,因此她就一手拿了橡皮一手拿了铅笔,嘴巴里是锣鼓开堂的伴奏,叮叮咚咚铛铛。“好戏就要开场。”她唱道。然后让橡皮在空中飞舞一番,接着咚的一声鼓锣,橡皮落在原地,劈出优美的大叉,她又唱道,看洒家怎样将你擦得个干干净净!那铅笔就在她的支配下一点点地朝后面退,退到闭塞的墙角落里。
这时候从最后一排传来咯咯咯的笑声,这笑声实在是太悠扬了,我知道那是姐姐的笑声。但是我不敢转身去看姐姐。姐姐和后面几排的男生们都熟悉了,后面几排的女生们也喜欢她,她们背地里说这个新来的张依依人很豪爽。他们都称呼姐姐“新来的张依依”,为的是和我加以区别。姐姐的笑声悠扬,就连邢林林也被感染了,邢林林回过头来的时候没有小声嘀咕,她还停留在姐姐笑声的感染中没有出来,直到接下来那堂数学课上到三分之二的时候邢林林才自言自语感叹道,多么开朗啊!但是不久之后,关于姐姐和杜岳声恋爱的消息就传出来了。我们前面几排的同学都在小声议论,对此都是满满不屑,邢林林更是为她的先见自鸣得意。她嘀咕道,怎么样吧,我说的没错吧,勾引了吧,狐狸精吧,快上床了吧。我就知道是这样的,我早就闻到狐狸的骚味了。她右侧的第三名扶了扶眼镜低声说,昨天晚上我看到杜岳声买避孕套了。第四名则趁这个当口偷了第三名的钢笔之后也跟着说,没错,避孕套!第五名一下将脑袋埋在桌子上嘟哝道,多么肮脏的灵魂呵,这个世界我没什么好留恋的!第六名说,操吧!操吧!操死一个少一个!第七名本打算吐一口痰无奈那痰太浓粘在喉咙眼里上不去下不来。第八名偷偷拍了拍自己的小腹臆想,“新来的张依依”有什么勾人之处呢?
但是后几排的人对姐姐和杜岳声谈恋爱这事情的看法就不同了,他们称之为友谊。但是对于我们前几排的人来说宁肯相信老母猪上树也不会相信男女之间只有友谊而不上床。中间一排的人处在游离状态,我猜他们挺分裂的。因为有时候他们听信了前几排人的言说就相信姐姐和杜岳声果然上床过的,但有时候他们又被后几排的人拉过去又觉得姐姐和杜岳声之间其实只是友谊。但是到最后他们也分化成了两个极端,一部分人深信姐姐和杜岳声的性关系一部分人则捍卫他们之间的神圣友谊。
也是这时候我开始注意到杜岳声的。之前总觉得他不过是上海黑帮老大的翻版,是个极残忍极好色的家伙,因此对于杜岳声我向来不正眼来瞧的。当然对于后几排的渣子生我的态度大抵如此,不知道他们在课堂上都在做些什么勾当,总之他们的成绩都是烂泥巴扶不上墙的,频频的零分、负分成了前排我们的饭后谈资。在我们眼里他们是蠢笨的、无望的、没什么前途的,他们应该因此羞愧而死,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因羞愧而死而且就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应该羞愧,因此他们就更成为一群无可救药的人。起初我还担心姐姐沉落在泥沼里但是后来也就不为她担心了,她既然要堕落我是阻拦不了的。可是当我注意到杜岳声的时候,我好像突然才发现他其实是个美男子,尤其是他那嘴唇,你注意过周润发的嘴唇没?杜岳声就有着周润发式的嘴唇,扁扁的、流线和缓,丰满、富有弹性,色红而不艳,型大而不夸张。我第一次看到那嘴唇就动心了。这时候关于杜岳声的种种传闻突然就出现了,当然它们早就出现了,但是我一直沉迷在书本中,因此我的感觉是他的传闻怎么一下子就那么多了?我刻意旁敲侧击去打听他的事情,这时候我和邢林林突然变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邢林林总是有很多关于杜岳声的消息告诉我。从邢林林的嘴里我看到了一个迥异的杜岳声,他仁义、善良、哥们义气!是个很江湖的人。我当然不知道那是邢林林一厢情愿的虚假构思,她欺骗说自己和杜岳声是青梅竹马的小朋友,后来因为她的脸受伤才使杜岳声离开了自己。那时候我听信了邢林林的片面之词,根本就没发现她述说的漏洞百出。既然杜岳声善良讲义气就绝不会因为外表的变更而遗弃青梅竹马的女孩子,并且,现在的情况是,杜岳声像我们前排的人从不正眼瞧他一样也从不正眼瞧我们,包括邢林林。
这时候我倒希望他和姐姐果真是在恋爱了,他们最好是真的恋爱而绝非孩子之间的把戏,他们的爱情最好是能开花结果,我希望能给他们的孩子做姨妈,这样我就有理由去他们家串门而可以经常看到杜岳声的嘴巴了。
我和邢林林的友谊很快就崩溃了,我们就像阻拦在坝子里的两股洪水最终各奔东西。邢林林再次拿着橡皮和铅笔配音道,我们永远是对立的,我永远会把你擦个干净,我相信,你会很快爱上杜岳声的。哈哈哈哈哈。
我会很快爱上杜岳声吗?但是邢林林这话却像一道咒符,我因为这句话而爱上了杜岳声。在那些夜里,这咒符不停萦回我的耳际,“你会爱上杜岳声的,你一定会爱上杜岳声的。”起初还是邢林林的口气和嗓音,后来就索性变成我自己的口气和嗓音了。我说,我会爱上杜岳声的,没错,我一定会爱上杜岳声的。我每天晚上这样规劝自己,就好像一个并不虔敬的教徒说服自己皈依那样,我们把内心深处的东西埋藏着,一旦被别人发现,扯出来,我们却将责任怪罪在别人身上。我硬说对于杜岳声的爱是受了邢林林的诅咒,这显然是错怪了邢林林,首先她不是巫女,没有巫术,不会扰乱人的思维和意念,她不过是个善于嫉妒的第二名。其次她也和我一样爱着杜岳声,这一点我肯定是没错的。她爱杜岳声,因此她才在背地里散布了我姐姐的消息,在她的散播里,我姐姐是个类似妓女一般的狐狸精。
我很矛盾,杜岳声是属于姐姐的,我怎么能介入他们之间的感情里去?我可以做第三者,但不能做姐姐的第三者。可是我又矛盾,既然姐姐不肯承认我们之间的亲情关系,并且将一把匕首狠狠扎在我的后背上面,以至于差点置我于死地中,那么,我凭什么还要去爱这样的姐姐呢?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公平竞争的陌生人?
你们可以想象我被两股力量挟持着落进万劫不复之境的结果。
那时候我已经忘记稳固自己第一排第一个位置的努力了,那时候我既成天提心姐姐的匕首,又压不住如火如荼般对于杜岳声的爱情,没错,他们就是两股力量裹挟了我。我不知道会被这两股力量带到哪里去,我想,只要有杜岳声就好,至于姐姐,我好像一下子就不需要了。并且对于母亲思念姐姐的泪水涟涟,也已经深恶痛绝。我似乎找到了更为强大的动力,那动力使我可以轻易就抛弃了亲情。可是姐姐将那匕首插的更深了,她和杜岳声欢快的笑声从后面传过来,一波一波,浪一样打着我的躯体,我像漂浮在浪尖的死人,一个尸体,我思想再也无法集中。生物课上,班主任提到某个问题让张依依回答,我因走神居然没站起来,可是姐姐恰巧就站起来了,这没什么错,她也叫张依依,除了班里同学喊她“新来的张依依”之外,全部任课老师都只喊他张依依。他们并不因我第一名的身份而加以区分的做法让我尤其恼火。更为可恨的还是班主任对姐姐微微一笑,姐姐流利的回答更是让我目瞪口呆。邢林林在一边捏着橡皮笑声唱,早晚把你清空的。迟早的事。
第二次月考之后,我果然被安排到第二排了,不是第二名,是第二排,第二排最后一个。但是邢林林没能把我清空,清空了我的是姐姐,她成了全班第一名,直接用自己的肉体把别人的肉体挤开,用自己的肉体在别人肉体曾经占据的位置稳固下来。我猜邢林林还是会经常一手执笔一手橡皮的演“桌面剧”,她发誓要清空身边的人,但是她的成绩却远远在其之后,而再也不是五分的距离了,是五十分,那对她来说,已经是强弩之末。
第三次月考我到了第三排,第四次月考我到了第四排,依次类推,第N次月考之后我该是掉在太平洋里了,但是教室里没有太平洋,只有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角落,我居然从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到了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角落,当然最后一排的座次完全是自己随便坐的,老师已经放任我们自流。我是自愿到那个角落里去的,在我看来,反正都是最后一排,有什么差别呢。对此班主任的态度是冷漠的,就像从来没有我这个人一样,有一次他从我身边走过,那条寂静的走廊,除了我们两人之外,就是夏蝉烦人的聒噪,烈阳的火焰从廊顶上破损的空隙里烧下来。我本以为他会说点什么,某些意味深长的怪罪或是期许。他也果然说了什么,他说,天气可真热啊,你瞅着吧,傍晚一定下雨。如果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看着我的,而是像邢琳琳那样指桑骂槐,我会知道他的在乎,然而,他不仅是看着我的,而且一脸温和。
我一直害怕落地凤凰不如鸡自己会被后排的渣子生们欺负,但是我马上就发现自己错了,他们不仅对我和善有加,而且对于我的到来并没任何渲染,好像我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一样,这种淡然让我感激。他们都是哥们义气很重的人,并且他们一点也不蠢,他们的脑袋比我敏捷了不知道多少倍,但他们就是不喜欢背书,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喜欢,是的,他们很遵从自己的意志而不喜欢盲目跟风。我旁边正是杜岳声,他从最后一排的第二个座位搬到我身边来的时候礼貌的问了一句,可以吗?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慌乱中我忘记了回答或者做一些类似回答的举动。但是后来杜岳声告诉我,一看到我脸红就知道我答应了。因此,他就这样做了我的男朋友。但是我们没有上床,关于前面几排人们的种种猜测:避孕套、上床、孩子、人流,全是无中生有。
现在我坐在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角落,我的身后是一堵结实的墙体,我的左边是同样高大结实的杜岳声,有时候,他会扭过头来看看我然后冲我微笑,我从没见过一个男人的眼睛里有那么多的温柔。我第一次从这个方位去观察前排的人,我知道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是低着头的,我的目光永远只停留在书本上,而现在,我的头是抬起的,或者说,我是昂着头去看前排的他们。杜岳声再次扭过头来看看我,对我微笑,真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因此,我,哭了。杜岳声看到我的眼泪有些着慌,是的,是着慌而不是惊慌,好像他早知道我会这样,杜岳声一边掏出纸巾递给我一边牵了我的手,我们两人悄悄从后门溜出教室来到操场上,杜岳声说,我知道你不甘心,你还是要回到你来的地方去的。那么我愿意陪你一起努力。我听了这话却突然伸出手去掩了他的嘴巴说,不是的!我说,我愿意一直呆在这个地方。我说,我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宁静过,我说,我不想再过刀尖下的日子了。然后,我第一次,扑在他的怀里。我告诉他,就在刚才,我突然幻想自己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她取代了我的荣誉,我则取代了她的爱情。然后我紧紧抓了杜岳声的肩膀生怕他像一团羽毛一不留神就飞走了。
【评语】
这篇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意识都相当老到,密实粘稠的语言传达出的正是内心的窒闷,而其隐匿的尖锐通过臆想中的形象表现出来,显得既真切鲜活,又有在一定距离中凝视血肉中撕扯出血肉的陌生化效果,非常强烈。而作品的主旨——仅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念头——又在这独特的设置中实现了某种安慰与释放,催人泪下的、火热的安慰和释放。令人心旌撼动的还在于,我们宁愿相信,文章最终的“现实”也同样未曾发生,只是一种火热的臆想而已。
作者简介:
苇子,男,1983年生,山东人客居上海近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散见《黄河文学》、《芳草》、《时代文学》、等报刊杂志。作品曾获2009年度《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