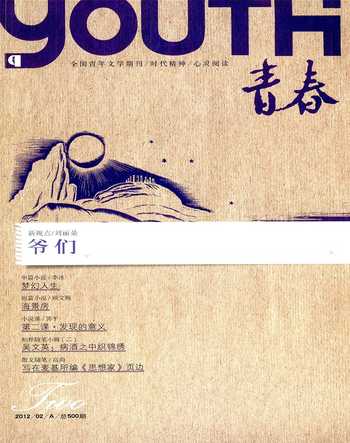礼与情之冲突
陆琴 黄诚
编者语: 文学在今天似乎极大繁荣,各种文学样式、流派、题材、内容、实验纷纷登台,一波接着一波,真让人叹未曾有。然而果真未曾有,完全凭空而降,抑或古已有之,今天的文学只是变换了形式而已?
《青春》杂志向以推出文学新人和新作为己任,故一直刊发最新作品。经过本刊多年的推动,诸多新人登上了文坛,诸多新作已广为人知。本刊开设“存在与影响”这个专栏,表面在观古,实际为知今,为了理解当下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需要向前看,看看今天文学的活水从哪儿来。从前的经典作品其实从未湮没,它们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潜伏在今天的作品之中,“存在与影响”这个专栏就是试图探微索隐,温故知新,研究作家、作品的存在与影响。
为此,我们特邀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学者刘涛主持该专栏,并欢迎海内外学者、作家参与。力图勾画出一幅晚清迄今的文学地图。
因为种种偏见,通俗文学作家一度被历史遗忘,当大家意识到文学史需要“两只翅膀飞翔”之时,通俗作家们才纷纷被人记起。姚鹓雏这位在民国享有盛誉的作家被文学史的经典论述抛弃在历史的洪流中,但一度其影响曾很大,后来尽管声明不彰,但对文学史中关于礼与情问题的作品影响其实一直不绝。
《燕蹴筝弦录》是姚鹓雏最早完成的小说,文本据朱彝尊本事和《风怀二百韵》演为说部。小说共三十章,每章取《风怀诗》中二句结成回目。姚鹓雏说:“忆民国二年冬,上海某书局始倩余为文言长篇,余撰《燕蹴筝弦录》一书应之,中叙朱竹垞《风怀诗》二百韵本事,即取其诗二语,为每回之目。”姚鹓雏凭借自己的才情和笔力将历史未曾定论的人物本事铺演成一部长篇小说。
一
《燕蹴筝弦录》以鸳机、寿姑和嫦姑三个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和悲欢离合为主调。寿姑、嫦姑是鸳机的表妹,因母亲之命至鸳机家朝姑母,鸳机与寿姑一见钟情,暗中传情,而鸳机母偏爱嫦姑之长厚。后因战乱,二姑回家与老母一起至鸳机家。为躲避战乱仓皇出逃,二姑母病重身亡,临终将嫦姑许为鸳机。战乱平定,归家后,鸳机为避与嫦姑的定亲,随友道子至云南。鸳机走后,寿姑病重,鸳机母为她寻婿,寿姑得知后寄发与鸳机。鸳机辞官归家,寿姑未婚夫病逝。后鸳机至京得官,寿姑病愈重。鸳机母欲举家迁京,寿姑强为欢颜,众人误病愈,寿姑留家。寿姑临死焚诗。期年,鸳机与嫦姑新夫妇至寿姑墓祭拜。
在小说的自序中姚鹓雏说:“情有所独到者,天必靳之。其靳之也,乃所以福之也。如水然,洪流瀚漫,一泻千里,至于决堤败筑,不可捍御,则往往为患矣。天下至情之人,每于缱绻缠绵不可卒解之际,乃为礼防所迫,终自束约。……吾人解此意以言情,即亦自趋于纯粹洁白之境。此书所言,即为实证。书中事迹大类胜朝之初,秀水某巨公早年影事。要之寓言十九,无足深考,惟在著者之一,固不欲矫前人细行,指陈其事,以为后生口实。实则今日言情之书夥矣,旖旎风光,固已为载笔诸君发泄已尽。成此书后,亦欲使读者,发情止义,之名辈风流固自有别,则区区之意也。”姚鹓雏创作小说并非仅仅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为生计而创作的同时既考虑到娱乐大众的目的,也有浓重的道德说教的目的。姚鹓雏借小说宣扬的是欲使人发情止义,以情超义。
小说充斥着礼义(道德)和情感的悖论:鸳机与寿姑互相钟情对方却碍于鸳机母之命、寿姑母临终之言而不得,两人郁郁寡欢,寿姑也为情付出己之生命。在礼义(道德)的面前,个人之情变得如此的懦弱,连想要表达的欲望都没有。鸳机至始至终没有违背母亲之命,寿姑至死也没能向姐姐嫦姑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即使作为第三者的嫦姑、鸳机母事事明了,这份情感的两位承担者却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道德的压力。鸳机越是想要逃离他与嫦姑的亲事,越是想要躲避母亲的压力,越被拉回原处,身处进退两难的境况。除了道德与情感的悖论,小说还涉及了个人的命运与宏大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在不被任何人掌控的战乱年代,身为个人的个体如此的渺小,只能随波逐流,无可与之抗争。因此鸳机与寿姑的这份爱情要在道德与战乱之下小心翼翼的维持,讽刺的是,他们的感情在战乱中没有冷却,反而升温,只是一遇到道德的压力,就变得苍白无力。
《燕蹴筝弦录》以鸳机、寿姑为男女主角,男主为英俊潇洒的书生,女主为美丽动人的小姐,鸳机和寿姑的感情真挚而又纯洁,没有丝毫欲望的涂染。小说为鸳机设置了情感的考验题,在金陵鸳机遇到了歌伎云娘,没有因欲望破坏了他和寿姑之间的柏拉图精神恋爱。在这里,小说涉及的问题是欲望与情感的关系:是逢场作戏还是坚定情感的归属。正如姚鹓雏本人所说,在他所处的年代,欲望横流,众人在旖旎风光发泄殆尽后的疲惫和无力迫使姚鹓雏借小说反思,为鸳机设置考题。当然,姚鹓雏也给出了他的答案:最终鸳机忠于自己的感情。
小说中间插入鸳机友人道子与其妻子、歌姬柳娘间的情事似乎是鸳机、嫦姑和寿姑的翻版,最终柳娘触壁而死,寿姑因病而死。两位死去的女子均被称为“烈女”,这个称谓在男人的眼中是值得骄傲,令人敬仰的,但又有谁能知两位女子内心的苦痛呢?道子和鸳机作为两份感情的男性承担者均无力承担,相反,女子却以残害肉体的方式忠贞情感,男性不得不为之汗颜。
礼义与情感的冲突是人的道德追求与本真欲望的冲突,至晚清,情感的追求,本真欲望的无限的膨胀,致使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萎靡。姚鹓雏仍想以小说说教,宣扬情感,他的重复并不是无用功,他推崇的情感是建立在互相忠贞的基础上的,在一个无限膨胀的欲望时代,这也算是一种克制和反省。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姚鹓雏宣扬的道德目的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他借爱情道德标准来宣扬情感的本真,以情超义,这只是一种无法改变现实状态不得以而为之的妥协手法。身处人世的作家不可能有能力去处理好礼义与情感的悖论,强迫寿姑和柳娘的死是作者期望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无力改变小说人物命运的被动抉择。女性肉体的消亡,超脱人世带来的是作者鄙弃的爱情的最高道德标准。
二
读这部小说,涉及了三个时间的维度:一是历史上真人真事发生的时间,二是姚鹓雏创作小说的历史时间,三是读者在读这部小说的时间。这三个不可能同时发生的时间杂糅在一部小说中,姚鹓雏无法避免真实历史本事的影响,读者也很有可能因小说的时间距离差误读文本。
历史的阴影笼罩着姚鹓雏创作的小说,他诠释的新的故事文本占据了历史的真实,小说的整个故事脱胎于《红楼》,正如徐枕亚评《燕蹴筝弦录》:“《石头记》为千古言情之祖,其佳处即在于能辨明情欲二字。然卷轶既多,寓意不少,统阅全书,显有影射。言情二字,绝非著者主旨。盖无意言情,而自得言情之正者也。姚子此作,芳馨悱恻,真欲托影《红楼》,而纯粹处深刻处似又过之。寿姑为潇湘影子,同其幽挚之情,不同其尖酸之性。嫦姑为蘅芜化身,同其大方之范,不同其阴很之心。宝玉与鸳机,同为千古情种,而其结果,一则恋情不遂,遁入虚无缥缈之乡;一则以义为归,自得名教伦常之乐,其立品均高出一层。诸母之于史太君,于母之于薛姨妈,亦同此例。其余诸人,各具一体,有相似者,有不相似者,固不必尽求其人以实之。要之,姚子之为是书,盖无意言情而自得言情之正者,其胸中不必先有一部《红楼》在,亦不必竟无一部《红楼》在。”女主寿姑很明显带有林黛玉的影子,葬花、临死焚诗,为情而死,她带有太多林黛玉的阴影,但是寿姑终究不是林黛玉,她的宽忍、她的默默等待,明知不可为非为之的情感冲动压倒肉体可承受的能力,为一种虚空的精神而死。寿姑必定会死,这是每位读者都知道的,区别在于是何种死法,也就是说姚鹓雏先设了寿姑的死亡(真实的历史人物并非如此),先设女子命运的最终结果,寿姑和鸳机都没能力去挽救消逝的爱情。寿姑的死,是她执意为情殉身的结果,鸳机最后与嫦姑到寿姑墓祭奠,被之前的婢女垂丝怒骂,鸳机昏厥,这是不是能理解成男性在面对爱情的承担时的软弱与无力。徐枕亚高调赞扬鸳机的齐人之福,认为他既得到了至真的感情,又履行了男子应尽的义务。从徐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晚期当时男性对于言情小说的暧昧态度,传统的道德(礼义)在晚清的价值定位系统中被重新审视,姚鹓雏想要以小说做道德说教——以情止义最终导致的将是欲望的横流。
姚鹓雏身处晚清作家丧失言情的技艺的尴尬境地之中(自《海上花列传》至《九尾龟》等描写妓女的书在晚期的滥觞,欲望、旖旎风光的书写已经造成了晚期作家失去创作的激情),创作《燕蹴筝弦录》重拾推陈出新的创作技艺。
在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姚鹓雏运用了新的创作技艺——学习西方着重人物心理的描写。《老残游记》、《孽海花》都曾尝试用心理描写的艺术表现手法,传统的研究者都认为心理小说作为独立的体式确立是在五四之后的现代小说中,鲁迅的《狂人日记》打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心理实验。我们不否认五四小说在运用心理描写的艺术手法上的卓越成就,但是也不能不忽视晚清作家对西方新式的心理描写的尝试和运用。《老残游记》和《孽海花》只是在小说中尝试运用并非自觉的贯彻到底,姚鹓雏则不同,在《燕蹴筝弦录》中他自觉地运用心理描写。男女主人公每一次内心的波动都刻画的细致入微:鸳机面对寿姑反复无常态度的担忧和揣测,寿姑面对鸳机情深意重的感情的不悔。姚鹓雏试图打破传统的说书人的话本小说的体例,以心理描写刻画人物内心,达到了传达人物情感的效果。
三
最后,想分析的是嫦姑在最后一章对鸳机的教诲式的长篇大论。嫦姑在小说中只开口了两次,一次是提醒寿姑勿忘至鸳机家的本意,二则是小说末尾。嫦姑的这次开口,是作者有意为之想促使鸳机与嫦姑的美好婚姻还是作者意图扳回在读者心中已成负面形象的嫦姑,使之重新获得读者的谅解?无论是哪种,作者既然让嫦姑开了口,那么就有她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是嫦姑自己的吗?我表示怀疑。表面上看嫦姑劝戒鸳机显示了她的深明大义,勉割私情,以求全大局的大无畏精神,但实际上是一位男性利用女性的声音(寿姑的声音只是为爱而发出,寿姑的在整个小说中的声音均在鸳机——这位男主的声音之下)高调地宣扬男性的地位,男性的义务和责任很多:男子必有事业必有志尚,要奉养父母,要延续子嗣,女性可以随时为承担责任的男性付出一切,这只是一个被淹没掉的嫦姑的声音。嫦姑的这次意料之外的发言表面上看是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男性控制了整个文本,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男性在面对女性声音表现出来的焦躁和不安,他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控制,讽刺的是,就如最后鸳机在寿姑墓前昏厥这一行为所表示的那样,男性声音和地位的表达在整个晚清社会都显得那么的软弱和无力。
嫦姑对鸳机教诲的基础是“我妹少时,日者言其命当夭折,且历荼蘖。即母亦常对我母语,二姑眉纤而秀,目曼而长,清丽过甚,恐无修龄。两肩瘦削,尤主少福。是语我闻之熟矣。今日之事,殆诚有数在,不可以人力斡旋。”嫦姑从一开始心里就很清楚,寿姑和鸳机之间最终是不可能走到一起,她也清楚地知道妹妹寿姑面对这份感情时的痛与苦,但是她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冷眼旁观事态的发展。不得不说,嫦姑冷血的近乎残忍。
姚鹓雏借嫦姑的口说出了鸳机与寿姑的感情最终破灭的终极原因,他承认不能被人力所掌握的命运,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手在操纵,任何人都不能避免。“以前的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鸳机面对嫦姑的解释作出的反应只能说是无力的妥协。
嫦姑与寿姑自小生活在一起,两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一个为鸳机而香消玉殒,一个以近似圣女的救赎者身份与鸳机结合,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嘲弄。
摆脱了说书人的角色,文本通过全知全能上帝式的叙述者讲述了一个有可能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的虚构爱情,嫦姑、寿姑、鸳机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在轰轰烈烈的不为人力所控制的大背景下发生。姚鹓雏创作小说,选择以寿姑的死,鸳机与嫦姑结合作为人物的命运结局,从这一选择我们可以看出姚鹓雏最终还是走了一条传统文人处理人物的道路,叙述的最终结果仍然是重复地对男性地位和身份的维护,甚至不惜淹没女性的声音与肉体的消亡。可是正如上文所说,鸳机最后在寿姑坟前面对垂丝的指责昏厥的行为恰恰显示出男性在面对女性的软弱和无能,在一个被阉割掉的时代,姚鹓雏的叙述选择无疑只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