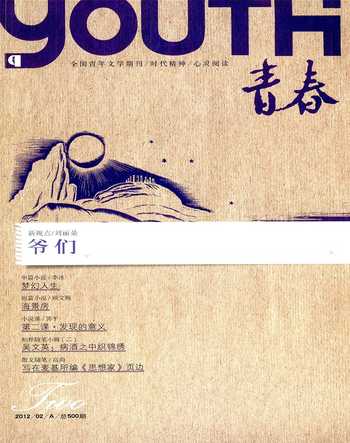梦域
鲍娘眼看着那片赤霞烧过来了。赤霞先前是乳白色的,如棉如絮,团团泛泛,柔软得似一群拥挤的羔羊,蓦地,像刑场上响起了杀人的炮声,鲜鲜的血在一瞬间就染红了半个天际。
四周寂静如死,一扫往日日暮前的喧嚣和骚动,让人平生无数的猜测和惊悸。灰灰的草房前,几株刺槐沙沙地飘下枯叶,一地金黄。院里的小菜园已透出秋天的衰败,显得凄零和无奈。老山羊单调地呼唤着子女,闹得世界更加静谧。十多只笨拙的母鸡认真地觅着晚食,“咯咯”的叫声拨撩出无数的寂寞和惆怅。太阳坠入西天,赤霞越来越辉煌,分明是熟透了的样子,急促地滋生膨胀,汇融着潺潺欲滴的一汪血。鲍娘手握一把青光铲,攫紧了心,惧怕那“血”要炸的样子,呆立在篱笆墙内,只觉身上那件用旗袍改制的月白色绸褂儿,慢慢地,一分一寸地燃烧起来了。
千万别出什么事情啊!
鲍娘虔诚地祈祷着。
她很担心地把目光挪到坡下,那里的暮气正在升腾。暮气像。层薄薄的纱,封锁了灌木丛中的那条小路。远处的田野和村庄早已被霞光覆盖,色彩绚丽,一片迷漾。突然,一只野兔从灌木丛中跳跃起来,似一只灰色的箭,迎着霞光扑去,落下的时候,回首朝鲍娘望一眼。鲍娘看到兔子的双目似两颗晶莹的红宝石。
很远的地方,传来了狗的狂吠声。
他于朦胧中听得有人上了跳板,待睁开睡眼时,甲板上已站立了七八条蒙面汉子。他禁不住心头一惊,惶恐地折起了身。
船家,快撑我们过河!其中一个高个子对他说。
他惺松着眼朝对岸眺望了一下。正是午夜时分,月色灰灰。镇子里早已灯息人静,只剩下黑黑的一团。夜风袭来,他有点儿抖,便轻轻地起了锚,撑篙让船离了岸。
船上的人都不说话,整个河套里只有他那“哗啦哗啦”的撑篙声。一只野鸭凄惶地叫了几声,他禁不住心惊肉跳。回首望那簇人,个个如雕,很稳地站立着,目光朝着镇子,一片贪婪。
这时候才有人发现他是跛子,相互传递,蒙面汉们的目光开始回拢。他跛着一只脚,在船上艰难地跳跃。脚跛撑出的船可不跛!有人戏耍他。他不介意,大度地回望他们一眼。他发现只有一个小个子对他的跛脚不屑一顾。
如果说出我跛脚的来历,会吓你们一跳!他冷傲地想。他想着就故意夸大动作在那个小个子面前晃动,小个子仍是无动于衷。他感到十分窝火。
船拢了岸。
高个子命那个小个子掏出银钱,撂在船舱内,然后对他说:等着我们,一会儿就回!
船拢岸的时候黑影们就有了某种感应,高个子话音没落,蒙面汉们已争先恐后地跳到了岸上。他听到杂乱的脚步声远遁,不一时,黑黑的码头上就又如死一般静。
他像是十分清楚这伙人要干什么,迟疑着卷了烟,默默地吸,目光盯着一处。许久,才突然像下了什么决心,猛地掷了烟头儿,站了起来——那红色的亮点儿如流星般在夜空里划了一道弧光,然后就传出“吱吱”的落水声。他朝手心里啐了一口唾沫,急促地撑起篙,跛着脚踮到船头,明亮的篙也就闪了一线,“扑嗵”落进了水里。接着,他又踌躇了一会儿,抬头望着朦月。飞云如野马般在月前飞驰,天地时明时暗。有风吹来,捎带着夜猫子凄厉的嚎声。他随着那叫声颤了一下。
诸位,恕老夫对不起了!
他朝着码头嘟嚷了一句,然后把篙搭在了肩上。
突然,从船舱里传出一个低声:别动!
他凝固一般定了身子,只觉从背沟内朝外窜着凉气。他知道这是一帮行家里手,逼他孤注一掷。他没有回首望,心中猜测着船舱里的人应该使用的是什么枪。他知道他不会开枪,他们眼下离不开他。他泄气地重新蹲下来,又卷了一支烟,嘟嚷道:老虎不吃回头食,退路就不该放这儿!若有人放了暗眼,不让人连窝践了?
这时候,岸上已传来了枪声。
枪声把她的心一下提到了嗓眼儿处。她面色如纸,双目间拧满愁云。那时候霞光已弱,夜幕如网般收拢着视线,渐渐地,坡下便一片模糊。
几年了,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她喃喃地说。
仿佛是枪声惊动了她的儿子。柴门响的时候,她看到五岁的儿子从草房里仓惶而出,睁大了惊异的眼睛望着她,幼小的脸庞上写满惧怕和诧疑。
妈妈,这是啥响?儿子奶声奶气地问。
她无言地朝坡下望一眼,对儿子说:不关小孩子的事!啊,乖!
爹回来了吧?儿子又问。
像是有一阵冷风袭来,使她凝成了一尊雕塑。儿子无意中触到了她的担心处,她开始有点儿支持不住。儿子跑到她跟前,抱住了她的双腿。母子俩的目光无形中汇聚到一处,盯住丈夫回归必经的小路。
西天如泼了血,坡下一片猩红。那条小径已被灌木丛的黑影匿盖,像一个幽深幽深的黑洞。
突然,坡下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有人高喊:抓住他!
她一下搂紧了儿子,浑身颤抖不止。
他受了伤,跑不远的!坡下的叫喊声越来越清晰,继尔,嘈杂的脚步声便如锤般擂在了她的心上。暮色苍茫之中,她看到无数顶大沿帽已开始在灌木林里晃动。
她终于看清,那是一群黑色的警察。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感到镇定不少,便直起了腰,想象着那个被追的人,脑际间充满着血腥……
丈夫何时逃跑的她压根儿不知,被人叫醒的时候,床前全是蒙面大汉。她慌乱中拢过绫被护住粉白的身子,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那片诱人的白光消失之后,蒙面汉们互望一眼,有点不知所措。
你穿上衣服吧!一个低沉的声音命令她。
她如受惊的小鹿,许久才缓过神来,急急穿上了衣服。
你丈夫哪里去了?那个低沉的声音问她。
我不知道!她胆怯地回答。
那人松了一口气,对另几个汉子说:只有带上她了,回去也好给头儿有个交待!
她被捆了,蒙了双目,然后像麻糖一样被捣进一条布袋里。黑暗中,有人“嘿”了一声,她就觉得如腾云驾雾般悬了空。热热的喘气声夹带着股股大蒜臭在她的胸前荡漾,有一只手极不老实地在她的屁股上摸来摸去……突然,前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她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命令扛她的人说:快把她扔掉!
不……我不累!扛她的汉子喘嘘嘘地说。
你跑不脱的!低沉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她丈夫叫来了警察,你知道吗?
不用你管!她听到扛她的汉子吼了一声。
这时候,忽听有人高喊:头儿来了!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狂风暴雨般刮到她的身边。马的喘息声如雷灌耳,铁蹄叩地的声音显得骚动不安。前面巷口处已传来抓土匪的高喊声,子弹呼啸着开始在头顶上飞来飞去。
是“票”吗?马上的人火急地问。
是……是的!头儿!扛她的汉子回答。
快把她交给我!你们从东门口突出去,外面有人接应!马上人的话音未落,她就觉得有双粗壮的手已经抓住了她的胳膊和大腿。当马的体温和马上人的体温与她的体温相融时,她的耳畔早已充满了“呼呼”的风声……
枪声越来越紧。
不一会儿,码头上便响起杂乱而紧张的脚步声。镇子里乱作一团,锣声呐喊声撕打声阵阵传来,喧嚣在夜空中飘荡,清晰得让人心惊肉跳。匿藏在船舱内的人再也耐不住,爬出了舱门。他看到一团黑影朝他走来。
快准备开船!那“黑影”命令他。
蒙面汉子们气喘吁吁地上了船,身上都背着大包小包。沉重的洋钱撞击甲板声相继落音之后,留守在船上的那人才急迫地问:大哥,出了什么事儿?
货刚上手,就被人发觉了!赶巧又碰上了镇公所的巡夜队,差点儿栽了!高个子抹着汗水说。
人齐了吗?
高个子这才环视一周,说:可能还差小个子!
等不等?
来不及了!
开船!
他开了船。
不料船刚离岸,他看到那个小个子气喘如牛地跑下码头。小个子边跑边呼喊:大哥,等一等!
没人回话。许久,他才听到高个子说:八弟,为了弟兄们,你就留下断后吧!
你们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呐!
他感到小个子的喊声很凄凉,迟疑了一下,对高个子说:让他上来吧?高个子望他一眼,生气地说:不关你事!
这时,他看到岸上已有火把光亮,旋即,码头上一片光明。镇公所的巡夜队和赵家酒馆的家丁们呐喊着叫骂着,子弹开始在船的周围跳荡。
小个子仍在凄怆地高呼:大哥,你们不能撇下我呀——
船上的人都铁青着脸,在冷冷的月光里如一群灰色的泥塑。
岸上的火把已奔下码头,有人高呼:抓住他!抓住那个小个子!
他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很替那个小个子担心,禁不住回首相望。火光中,他看到小个子掷了包袱,一头扎进了河水里。那时候,船已到河心。岸上的人只能呐喊打枪,声音也渐渐少了高昂……
船上的人这才松了口气。
妈拉个巴子,吓老子一跳!高个子低声骂着,掏出枪,朝着对岸打了一梭子。高个子打完之后,吹了吹枪管儿,然后面色阴冷地望了他一眼。
他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勾着头从高个子面前走了过来。
他灵巧地玩弄着一支枪。
那支德国造的小左轮如黑色的乌鸦在他的手里“扑楞”了一会儿,然后又被他紧紧地攥住。他下意识地吹了吹枪管儿,乜斜了一下不远处那个被绑的女人,咽了一口唾沫。
你一定不想死!他说,可是没办法!
被绑的女人一脸冷漠,静静地望着前面那个男人。她看到他又卸了枪。那枪被卸得七零八碎,似一堆废铁。废铁在阳光下闪烁,显示出能吃人肉的骄傲。他用手“洗”着零件,眨眼间,那堆废铁又变成了一只“黑乌鸦”,在他的手中“扑扑楞楞”展翅欲飞,然后又被牢牢地攥住。
怎么还没听到枪响?芦苇荡的深处传来了故作惊诧的询问声。
头儿,舍不得那娘儿们就放了她嘛!有人高喊。
一片戏闹声。
他蹙了一下眉头,抬头望天。天空瓦蓝,白云如丝,轻轻地飘过,穹顶就显得无垠而辽阔。阳光在湖水里跳荡,堆银叠翠。芦苇摇曳,晃得人醉。那女人仍在盯着他。他看到女人那乌黑的秀发上沾满了芦花,白皙的脸冷漠无情,丰腴的胸高耸如峰,看得他禁不住热了身子。
他终于掏出一粒花生米大小的子弹,在口里含了含,对着阳光照了照,然后又在掌心中撂了个高——稳稳地接住,说:这回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他说着暸了一眼那女人——正赶一阵小风掠过,女人的旗袍被轻轻撩起,裸露出细细嫩嫩的大腿。白色的光像是烫了他的双目,他巴不住打了个愣,觉得周身有火窜出。
头儿正在好事儿哩吧?那边又传来了淫荡的呼啸声。
女人看到他那刚毅的嘴角儿被面颊的颤动牵了一下,那张年轻的脸顿时变型。他终于举起了枪。那支枪的弹槽像个小圆磙儿,如蜂巢,能装六粒子弹。弹槽磙儿可以倒转,往前需要扣动扳机。她看到他把那颗子弹装进子弹槽,然后“哗哗”地倒转几圈后对她说:这要看你的命了!
里面只有一颗子弹,如果你命大,赶上了空枪,我就娶你为妻!他又说。
她望着他,目光里透出轻蔑。
你知道,土匪是不绑女票的,女票不顶钱。有钱人玩女人如玩纸牌,决不会用重金赎你们的!他说着举起了枪,突然又放下去,接着说:让你死个明白!我们想绑你丈夫,没想弟兄们错绑了你。我们不是花匪,留不得女人扰人心。不过,若是我要娶你为妻,没人敢动的。但我又不想娶你这个有钱人的三姨太,所以这一切要由天定!
他说完,又旋转了几下弹槽磙儿,才缓缓举起枪。
女人悠然地闭了双目。
那时湖心岛坡上很静,一只水鸟落在女人脚下,摇头晃脑地抖羽毛。芦苇丛里藏满了饥饿的眼睛,正朝这方窥视。
他一咬牙,扣动了板机。
她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望了望面前黑黑的一团,勾下了头。一缕黑发如缎带般垂下来,覆盖了她的半个脸庞。
你丈夫是个匪首,六年前的案子犯了!一个穿黑制服的小胖子对她说。
他跑了!不过,他受了伤,跑不掉的!小胖子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又对她说。
她垂着眼皮,只是紧搂着儿子。儿子惊恐的双目胆怯地望着黑衣警察,像是止了呼吸。
远处,仍有零星的枪声响起。
搜一搜!小胖子命令其他人说。
黑团在一瞬间扩散,小院里开始有几多幽灵般的黑影在晃。一阵骚动。终于没搜出什么,小胖子带头坐下,其他人也各寻地方坐了下来,很疲累的叫骂声响起。她看到小胖子掏出了香烟盒,然后摸出了火柴——光亮起的当儿,她看到小胖子淫邪地看她一眼,接着,她便听到小胖子“啊”了一声。
原来是你呀?小胖子惊诧地站了起来。
我不认识你!她泛泛地说。她的眼皮一直垂着。她知道这个小胖子认出了她,心中一阵惊悸。
你不认识我可以,但总该认识陈二爷吧?小胖子狞笑着走过去,一把扳起她的头,猛吸了几口烟——红光映出她的俊目。徐娘半老呀!怪不得二爷常常念叨你哩!小胖子说着在她脸上抹了一把。
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女人,你认错人了!她固执地回答。
小胖子突然嚎叫一声,拔出了手枪。她一下把儿子藏在身后,哀求说:你贵人大量,别跟孩子一般见识!
小胖子捂住那只被咬的手,愤怒地朝天上放了两枪,恶恶地骂:土匪崽子,若不是为着陈二爷和你娘的面子,我非打死你不可?
打吧,求你再打一枪!她望着他说。
他摇摇头,走过去说:我说过了,只打一枪!你赶上了空枪,说明你命大,也说明咱俩有缘份!
她冷笑了一声,说:你想得很美呀?
你想怎么样?他奇怪地问。
我想死死不了,也想认命!她望了他一眼,松动一下臂膀,拢了拢乱发回答。
怎么个认法?
我也打你一枪!
他怔了,不相信地望着她,好一时,突然仰天大笑,说:够味儿,真他妈够味儿!怪不得陈佑衡那老儿喜欢你!我今日算是寻到了对手,就是栽了也值得!他说完便把枪撂给了她,然后又掏出了一粒“花生米”。
她接过那粒子弹,装进了弹槽儿,然后,熟练地把弹槽磙儿旋转了几圈儿,对着他走了过去。
她举起枪,姿态优美。
他吃惊地张大着嘴巴。
大哥!苇丛中的人齐声呼喊——声音里充满了担心和惊悸。
她笑了笑,又转了一回弹槽磙儿,对他说:如果是空枪,俺就依你!说完,重新举起了小左轮。她的手有点儿抖,瞄了许久,突然,颓丧地放了枪,好一时才说:俺不认命了,只求你从今以后别再当匪,好生与俺过日子!
他愕然,呆呆地望她,像是在编织着一个梦
你命不好,我愿意跟你去受罪!她不知为什么眼里就闪了泪花儿。
他疑惑地走过去,接过那枪一看,惊呆如痴。
俺转了两次,可那子弹仍是对着枪管的!她哭着说:那时候,俺真想打死你!可一想你命这般苦,就有点儿可怜你了!你不知道,俺也是个苦命的人啊!
他愤怒地扣动了板机,枪声划破寂静,苇湖内一片轰响。然后颓萎地垂了手枪,对她说:好!我听你的,带你去过穷日子!
四周一片骚动,无数条汉子从芦苇中跑出来,跪在了他的面前,齐声呼叫:,头儿,您不能走啊!
今日能得鲍娘,也是我马方的造化!他平静地说:弟兄们,忘了我吧!
有人带头掏钱,他和她的面前一片辉煌。他望着那片辉煌,跪下去做了个圈揖,哽咽道:弟兄们的恩德我永世不忘,但这钱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我马方一文不带!说完,他掏出那把左轮枪恭敬地放在了地上。她走过去架起他,然后拾起那把左轮,说:你当过匪首,说不定迟早会出什么事,带上它也好做个防身!
他哭了。
对岸的辉煌逐渐消失,只有零星的火把在风中摇曳。叫骂声夹杂着慵懒的呵欠声也开始稀疏,不一时,码头上便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船终于拢了岸。他喘嘘着刚刚支稳篙,就听到蒙面汉子们跳岸的慌乱声,接着,黑影们狠狠地朝岸上跑去。
他暗自骂了一句,重重地放了篙,刚欲坐下,突见从船舷处露出了一个脑袋。他认真瞧去,差点儿叫出声来。那是小个子!小个子望他一眼,然后就十分敏捷地爬上船,急促地躲在船舱一隅,掏出了枪。
枪法极准。枪声单调又悦耳。眩眼工夫,码头上就躺倒了六七具尸体。等痛苦的呻吟声和恶毒的叫骂声消失之后,那里一片死寂。小个子直了腰,吹了吹枪管上冒出的蓝烟,对他说:这几个家伙不讲义气,真他妈的欠教训!小个子说着已跑到岸上,拣回大包小包,放在船板上,对他说:你留下一包,任你挑!只是要顺水送我一程!
他望了望那堆包。包有大有小,在夜色里像死人的骷髅。他咂了一下嘴巴,许久才说:送你一程可以,但我不要你的东西!
小个子笑了笑,从一个包里捧出几大把银元,撂进船舱里,然后对他说:上船时给你的是假的,这回全是真的!
他怔了一下,心中升腾起被人耍了的耻辱。他狠狠地望了望岸上的几具尸体,横过了篙。
船顺水而下,使人产生出十分欢快的心境。两岸黑魃魃的丛林像在逆走,一忽儿便被撇在了身后。小个子望着落在很远处的码头,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他一只手抹着汗水,一只手极畅快地去了蒙面黑布。小个子去掉蒙面黑布的时候很得意地望了他一眼,使他一下目瞪口呆!他做梦未想到,小个子竟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娃娃!
这娃娃是个土匪种吧?陈佑衡狞笑着走过去,身后的两个家丁也笑声不止。
她搂紧了她的儿子,对陈佑衡说:你别过来!你若想让我回去,就别动我的儿子!
好,好!果真还是我的三儿!陈佑衡的大金牙在灯光里闪烁,乐然地说:自从你被马方劫走之后,我找得你好苦呀!刚才小胖子去给我报喜,我还不相信哩!三儿,这是梦吗?
三太太,二爷一听说你还活着,连夜就赶来了!为着他老人家这片痴心,随我们走吧!两个家丁说。
那时候,夜已深。门外风声吼得紧,似狼嗥虎啸。坡下传来烈马焦急的嘶叫声,在夜空里显得豪放又壮阔。
让我收拾一下!她平静地说。
痛快!不愧是当年的小三儿!陈佑衡兴奋地说。这些破烂玩艺儿一样甭带,坡下有轿车,不误天明赶到城里!
她警惕地望了那个枯瘦的老头子一眼,抱起儿子走到里间,窸窸窣窣地整理着什么。不一时,她站在了门口,胳膊上挎着个小包袱。
二爷,我儿子怎么办?她问。
你说呢?二爷笑着反问道。
我知道二爷的脾气!堂堂陈府里是容不下一个土匪种的!
小三儿是个明白人!陈佑衡面透凶色,说:你说对了,我陈某的脾气没变!
你打算怎么办?她又问。
马方抢我老婆,我自然要报这个仇!陈佑衡咬牙切齿地回答。
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她一下竖直了蛾眉,藏在包袱下面的那只手迅速地亮了出来。
枪!她有枪!两个家丁失声叫道。那时候,枪声已响,陈佑衡倒在了血泊里。一个家丁正欲还击,被她击中了手脖儿,血涌一片。
她用枪逼着两个家丁,冷笑道:你们也知道我鲍娘的枪法!冤有头,债有主,陈佑衡欠我多少你们心中也清楚!今日老娘不想多杀人,快滚吧!
这时候,她看到她的儿子已经站在陈佑衡身旁,先用小脚踢了踢那个干瘦的老头子,然后拣起他手中的枪,对着门外的两个家丁瞄了又瞄……
小个子显得十分得意不停地玩弄着手中的枪。那是一把小左轮。小左轮手枪在小个子的右手旋转,像一只欲飞的乌鸦,“扑扑楞楞”地挣扎一时,又被攥住……他一下子睁大眼睛,像傻了一般,直直盯住了那把枪。
你要干什么?小个子警惕地问。
我在看你玩枪!他不平静地说。
认得这是什么枪吗?小个子问。
德国小左轮!他回答。
你也懂行?小个子再一次瞪大了眼睛。
他摇了摇头,许久才说:只是听说过!过去有个土匪叫马方,也玩这种枪!
你认得马方?小个子像是凝固似的。
他又摇了摇头,对小个子说:我也只是听说过!他二十几岁就当了匪首,后来抢了一个有钱人的三姨太,二人成了家。他听了妻子的话,从此改邪归正。他带着他的妻子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藏了起来,男耕女织,亨受了人间天伦!可天不容他,一天,他当土匪时做的大案犯了,遭到警察的追杀。他受了伤,只得撇下他的妻子和五岁的娃娃离乡背井!后来,战争四起,再没人追杀他,可他去寻找他妻子和儿子的时候,那里已变成了一场梦!他至今不死心,仍在寻找,找了十多年……
他现在在哪?小个子急切地问。
就在你的面前!他感到极痛苦。
小个子怔然片刻,望到了他的跛脚,跪了下去,凄凄地叫了一声爹。
你娘还在吗?他问。
我娘还在,就在前面一个小村里!小个子满目泪花儿,哭着说:你走之后,陈佑衡去逼我娘,我娘杀了那老头儿,也遭到官方追捕!为了活命,我娘带着我到处躲藏,两年前才来到这里……爹,我和我娘也寻了你十多年呐!娘急白了发,哭瞎了眼……为养活娘,我十三岁就跟人拉杆子!你看,用的就是当年你的那把小左轮!
他接过枪,仔细地抚摸,叹气,良久,说:这一切,你娘知道吗?
儿子摇了摇头。他呆呆地望着儿子,凄然地说:你娘常给我说,无论何朝何代,土匪都没有好下场!孩子,你知道吗,你冷了你娘的心啊!
爹,这一切都是被逼的呀!儿子哭着说:娘亲双目失明,我刚满十岁就帮人家放猪放羊,起早贪黑,挨打受气,可仍是混不饱肚皮,养不起娘亲……儿子泣不成声。
他怜悯地望着儿子,说:我闯荡一生,方悟出饿死不当贼的道理!孩子,如若你娘知道你下了黑道,她会怎么样呢?儿子泪眼如痴。
如果你疼你的娘亲,就该从此洗手!
我与我娘相依为命,我怎能舍得我娘?可事到如今,我已满手鲜血,洗得净吗?儿子为难地说。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固然不易,但只要狠下心来,是能做得到的!他望着儿子说。
儿子望着他,迟疑着。末了,咬了咬牙,终于把右手食指伸进了口中。
一瞬间,他听到了令他心碎的骨断声。他面色如铁,走过去扶起儿子,撕下布衫上的衣摆为儿子缠了手指。他爱抚地拍了拍儿子的肩头,许久才说:快上岸唤你娘过来,我们要远离这个地方,去享受天伦之乐!
儿子应声下船,飞似地爬上国防堤,去向母亲报喜讯。可是,当他兴高彩烈地搀扶着娘亲重新回到河边时,那里却是一片寂静……
第二天,那座古镇的门楼上悬挂着一颗人头。然后消息传开,说是当年的马方昨夜带人抢了赵家酒馆,被镇公所巡逻队追得走投无路,匪首马方带着所抢钱财投案自首了……
儿子用土牛推着盲母,来到城门前。满头白发的鲍娘静静地站在远处,“望”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面色如铁。许久,她才惘然地说:马方,你屡教不改,让俺娘儿俩好寒心呐!
儿子流出了悔恨的泪水,他禁不住跪在了地上,凄惶地唤了一一声:
爹——
责任编辑⊙青鸟
作者简介:
孙方友,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自1978年开始,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等发表作品,获报刊文学奖70余次,多篇作品被译为英、法、日等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