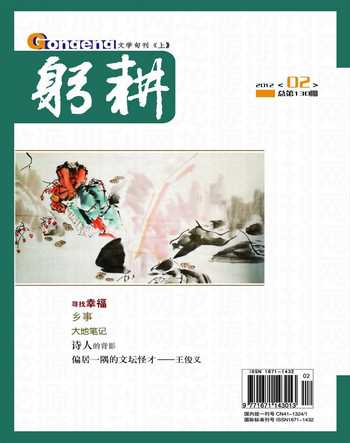芦苇的光芒
李新军
打苇子要用特制的镰刀。半月形的铁器上,泛出铅色的光,收敛,柔和,能看出岁月沧桑的味道。不是那种贼白,像新出窑炉的大件瓷器,摇出满地碎块状的太阳光芒。这是湖水洗尽铅华的素白,露出大自然的底色。镰刀所指处,还有其他杂乱颜色,等待岁月将它们漂染干净,变成能够产生淡淡忧伤的白颜色。镰头锋刃以外的刀脊上,时而滑动出湖的脸谱,却没有青苔般的锈,乌黑,磨两下,同样泛出白。镰刀本来就是湖泊的异物,它不是湖里游梭的鱼,不是懒得跳动的蛙,也不是呼唤同伴的麻鸭。它有点像居住苇丛里的水鹳子,平时看不出它的机敏,可每到冬季来临之时,它就跟着渔樵的小船,在湖里横冲直撞。
打苇子,要赶在没有结凌前下湖。如果湖上结出薄凌,渔民们就轻易不到湖上行船,这叫封湖。老天封湖,船还到湖上做甚?凌每天加厚,船强撑着在湖里左冲右突,转眼冻在湖心里,又无法沿着薄凌走回去。在没有冻结实的冰凌上走,肯定得有冒险精神,倘若掉进湖里,那可不是闹玩的。老辈人传承下来的生存法则里,有一条属于经验积累的东西,就是要在结凌前做完湖里的活计。否则,这湖里生长一年的东西,无论活鱼嫩虾蒲草藕菱,都要扔到荒无人烟的湖泊里,任谁都拿不走了。湖里出产的东西有季节性,采菱挖藕捕鱼捉蟹的季节占了多半年,等到芦荻灰头土脸漂浮在水上,湖民们不用别人招呼,放下待补的独笼,待织的鱼网,待收的干鱼,待卖的干虾,待苫的鱼屋,操起镰刀和篙桨,解船到茫茫大湖中找自己的滩地,打苇子,捆苇个子。
起初有茅蕻头荡漾在水里,接着泛白的苇皮,像犁开水面随波嬉戏的毛刀鱼,从湖里溢出来,到船道上找吃食。如果到船舷边拾篙,可能有凌包裹在篙壁上,给劳顿经年的篙披上簑衣。湖边的老树最早知道起凌了,它探在水里的树根缝隙里,藏着晶莹的凌花,只有细心的人,才能在解船锚时,看到那不经意的冰凌花。湖里找营生的人心里明白,再不下湖打苇子,这湖里的收成,肯定打个不小的折扣。
如果冷不丁看到挂在船舷旁的镰刀,还以为船家捉到了两条硕大的翘嘴鲢子,挂在油漆斑驳的船舷外。或者还以为活着,竹杆斜放在靠近水面的地方,镰刀头犁出细若游丝的水线,以为饿急的浮游鲢鱼,大着胆子追船讨食。割苇的镰头是特制的,体形厚重硕长,抡起来削苇如泥,省力气,铺得开,割成扇面样,如同土匪腰里杀人如麻的大刀,令人不寒而栗。庄稼把式手中的麦镰,简单小巧,容易攥握,镰刀在麦棵间探进探出,犹如兴奋起来的游鱼,使劲在水里穿梭往返,却没有苇镰的豪迈和锐气。苇镰在岸上毫不起眼儿,它知道自己根本不用磨出寒气,只要探进水里,照样露出锐利的锋刃,再坚韧挺拔的苇子,在镰刀散发出来的凛然之气中,都要甘拜下风。
打苇的渔樵必须站在船头,手里的镰把多长,他的手就能触及多远的湖面。镰试探着沉入水里,触摸到苇子的根颈,接着如暴风骤雨般捋过苇子的下身,这是苇子们最痛快的时候,它们在湖里待了很久,已经站成风景,现在终于有机会被捞到船上,载运回寂静的渔村。渔村里的年青人很少到湖上讨活路了,他们结伴到遥远的城市,湖泊只是他们童年的回忆,他们采菱的手,已经经不起水的浸泡,这才晓得自己变成了湖里的陌生游客。镰浮起沉下,渔樵依赖手中的感觉打苇,没有感觉,缺乏打苇的经验,站在摇晃的船头,累个半死,也打不出多少苇草。打苇是个力气活儿,毛头小伙干不了这个,风蚀残年的老汉和杨柳细腰的女人,同样也打不了苇子,只有在湖泊里磨砺经年的汉子,才能义不容辞地扛起两杆苇镰,顺便捡半块磨刀石放进裤兜里,到水湾里解开自家苇船下湖割苇。中年人利落,稳重,下手准,在船上胯稳脚直,比锚还沉实,眼睛眯一条缝,比鱼鹰还锋利。湖镰在手中攥得紧,有耐力,迎着泛白的苇丛,抡起镰刀。镰刀悄无声息地钻进水里,与黑脊白腹的翘嘴鲢子没有什么两样,它经过的地方,稠密的苇子到处呻吟,它们“吱呀”地叫着,惊起苇丛里准备衔草筑窝的苇鸟。正在脱去老皮残衣的苇子们,将竖起的身子挺直了,就好似躺在嫁床上的新娘,舒服地傻看泛白的天空。我知道镰刀扑到水里,并非是兵不血刃,泛白的镰刀,触摸到泛白的苇子,苇子轻脆柔韧的外表,即刻从新鲜的苇杆中,溢出甜腻滑润的血。血为白色,随着镰刀的挥动抛撒于湖面。苇镰窜出水面,它带起的苇棵里,有水蓼金鱼藻面叶藻之类,它们就是跟随芦苇慷慨赴死的壮士,横尸在小船周围。
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夕阳下,孤独的刀斧手驾起一辆马车,他的面前,是无数奔跑而来的影子,那些修长俊俏的芦苇,大概是准备任由他屠宰杀戳。他顿生疑惑,蹲在船尾,想伸长了脖子,对着镜子般平滑油润的水,嚎上几嗓子,却没有发出声音。再伸长了,还是出不来声音。这腔子干燥如火,好似晒干的湖草。
我在湖上见过那种贼白,在炎热夏天,贼白就像旱地上的贼子,在湖里到处都有。夏季火热浪漫的性格,让湖里生长的动植物染上激情,鱼贼白,阳光贼白,甚至连无故泛出的水朵上,也贼白。湖里人俚语谓之“翻花”,这是淤泥让大鱼搅起的水朵,水朵贼白,说明日头正盛。到了冬天,湖里的贼白逐渐褪色,柔和,不再刺眼,湖里的草被阳光榨干了颜色,露出植物的底色。苇子是这底色,用它编织的苇席是这底色,剥皮晒干的杞柳是这底色,还有湖堰上种的毛白杨,也是这种颜色。镰刀就是这种底色,本质,坦然,不矫情,威而不矫,是属于大器类型的物件。湖泊里的冬天没有血色,它所有的碧绿,都被大自然储在某个角落里,不轻易示人。绿是湖泊血脉里的东西,是传统,是供在香案上的诸神的衣裳。
所有的物件泛出白。植物泛白,水泛白,天空泛白。松木铺起的小船,当然不能例外。渔樵指给我看,我才看出来,这经风受雨破败不堪的船,是要拖上来整修了。打完苇子,将船拖到岸上晾透风干,砸好灰腻子,补缝抹匀,再刷新桐油。桐油刷两到三遍,轻怠不得,自己的物件,还要指望它干活出力。打上腻子的船,身上缠出无数道绷带,趴在湖边干枯的草地上,活像沙家滨戏里架胳膊拄拐的伤病员,找向阳的湖涯坐下,或者躺在干枯的草丛上,看湖怎样慢慢地肃杀,孳生出凝重的表情。
草也泛白,却不是素白,留有草棵上的原酱色,原来绿色还藏匿在这难看的酱色里。刷上十斤八斤上好的桐油,浸满油香的小船,才焕发了青春,湖水泡出的木质色,如街上刚做过美容的年轻女子,吸引着走过湖滩的人。
仍然站在水里的芦苇,茅蕻和外皮越来越有泛白的意思,掉落到水里,不沉底,跟着风走,旋起在寂静无声的湖面上,被我看作驿道上走过的流浪诗人,这是冬天的湖上风景。它们也会跟散乱的苇叶,聚集在苇丛里,被哪家不愿意向南迁徙的野禽相中,略微整理一下,就成了越冬孵蛋的鸟墩。冬天的阳光撒在鸟窝上,想把苇皮茅蕻之类的草芥镀上一层金色,想在草窝里无故下几个金色软蛋,这不中。这些就是草芥的东西,依然故我地泛白,它们被温暖的野禽压着,被渐冻的湖泊呵护着,直至化为一坨淤泥。
所有湖里的水生植物泛白,甚至漫延到看鱼人的房屋棚寮上。凌泛白,霜泛白,雪也泛白。在湖滩上扭起笨拙身子的麻鸭,不由地加快行走速度,它们害怕停下屙屎时,被泛白的风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