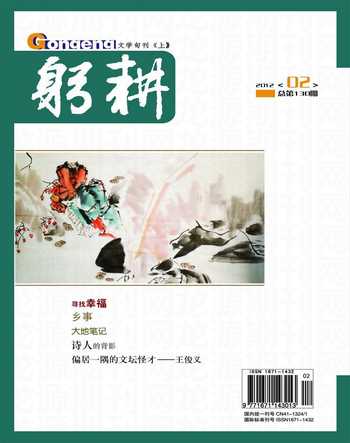偏居一隅的文坛怪才——王俊义
孙晓磊
无疑,在当今的南阳甚至整个河南,王俊义都因那种蕴含在其小说、散文、诗歌中卓异的思想向度、观念意识上的独特性以及陌生化强烈的语言表达形式而成为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
1979年8月在《百花园》以诗歌《家》而登上文坛的王俊义,几乎同时又在《奔流》上发表了诗歌《茶》。从此,他便以其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语言以及绝然不同于他人的风格占据南阳文坛的重要位置。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他,曾在县教育局上班而后到文联供职,先后发表过散文200余篇,诗歌70多首,中短篇小说90多篇。其中,小说《嗡嘤》,诗歌《中国的微笑》及散文《竹溪浣女》、《腊酒飘香》、《一个世纪儿的雕塑》、《母亲》、《月亮领着灵魂走》等作品分获省以上多种奖项。特别是他那些意识流散文,有评论称其反映了20世纪末期人们的心灵路程,同时也是对于散文形式的一种探索。
一直以来,被公认散文成就最大的他,却还是相当在意自己的小说创作的,在自己所有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中,他个人曾认为比较满意的“是描写地域风情的淇河小说系列,这些作品有的被国外翻译。日本的汉学家柴田岗夫在研究这19篇小说”,其自豪感溢于言表。
同他近距离接触可以明显地感知,他无论从思想格调到个性相貌特征,还是从铮铮傲骨到精神内涵都绝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另类角色。他的散文更是弥漫出一种对传统文化具有王氏颠覆意味的气息,流露出对以往言说形式的不屑,这种反叛意识是在寂静无声中孕育和改变的。在这种改变中,他依仗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而获得述说的资格,进而在反思中获得情理扩张的机会,他审视宿命与命运、诘问人情与世故,坚守“失意者的心情和黄酒融合在一起,就是诗歌”的文学理念。他善于用意象串起一个个文化符号,使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吸引你痛快淋漓地畅饮由精神酿造的琼浆玉液,并欣然接受他的那种个性化十足的散文形式带来的阅读快感。
比如,在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中,他的解构历史是设法坍塌那个社会的主流元素,击中那个时代代表器物的精神要害,而后通过语言的逻辑力量致那个时期的荒谬于不忍卒读的地步。由此,他把文化和历史写进清风明月中,写进春耕秋收中,写进思乡恋情中,写进得意者的雄浑苍劲中,写进失落者的蓬勃激越中,使历史的观照性有了现实的载体而变得生动、新颖,使文学有了营造氛围的着落而得以寻找到新的真谛。这种转承起合的荡气回肠,这种晨钟暮鼓的清冽警示,这种裹挟思想的杂陈印记是那样地令人铭心刻骨。他这种论理既非纯粹理性又非绝对感性,既有逻辑又无规则,随意、任性甚至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然而,他却能够收放自如、自圆其说,这种坚持物质客观性基础上的文化思维,显得深邃、繁复、意味深长。
太有形式感和个性十足的王先生,理所当然地对文学流派的异彩纷呈是持包容态度的。他说:“一个作家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没有一个接纳各种流派的心态,那么他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但可以肯定他写不出好的东西。”因而,他自己也对绚丽多姿的语言实验极有信心并乐此不彼。而且,写过朦胧诗歌的他对语言又是十分敏感的,他的一些更多充满诗意的复句写作,显示了他能够掌控语言复杂意象变化的规律。在他所有意为之的文体实践中,他更多偏重于意蕴化语言表达的嗜好。特别是他那异于常人的散文写作尽显新奇鲜活的文格风貌,语言机警睿智、含蓄隽永、犀利尖锐,拒绝直白和肤浅,远离乏味和苍白。他的修辞常常是假借一种意境而折向现实中,而调侃则更显黑色幽默,体现一种与当下错位的不屑,靠这种错位和假借把相关的意像放大扭曲至变形。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有些散文甚至完全可以当作讲述故事的小说来读,而且他这种讲述给与文本的润色仿佛流淌的音乐,荡漾着主旋律的音韵,在他《黄酒的浪漫与乡村的浪漫》的吟唱中调节音符,再以生命独特体验的纽带串起命运的旋律,于是,酒与辣子的结合造就出一个决绝的不屈灵魂,折射出酒神精神的狂放和浴火再生的血性。这种驾驭语言与不断转换和拓展叙述空间的努力,很好地呈现和验证了他复杂而充满意识流动韵味的思想,也为他打上更鲜明的王氏专有的写作烙印。另外,他的独特还可以从他像“面包是一种地里长的,不是电脑长的,因此,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的花朵,不是果实”等诸如此类的言说判断中可见一斑。
尽管他注重言说方式,但我更以为王先生是那种靠思想和伦理写作的作家。他始终认为:“文学的另一个高度是一个作家的作品对于真理的追求,尽管文学不是哲学,但是在对于真理的追求上,却和哲学一样,真理是文学的一颗明珠,没有真理,就没有真正的文学,就没有文学的高度”。而且,他强烈而平等的现代意识也使他从来不曾停止过对真理的探索和对生命的极大尊重,他说;“在生命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人人都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是他写作富于思想性的有力保证和文章具有道义的价值穿透力的根本力量所在。他还说“一个作家,他可以写出好的作品,但他可能没有知识分子的惟一属性,就是社会良知,就是应该在第一时间说一个民族良心应该说的话”。这是一个灵魂的孤傲,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南阳作家能够跟上时代步伐并与更大范围之外的作家对话的资格。
当然,与之相联系,每个作家对于死亡、未知和孤独这三个终极恐惧都会有自己的见解,王先生也是如此,他说:“小说究竟要写什么呢?不外乎对于死亡的思考,对于一个人和一群人和一个民族命运的思考,对于一个人向死而生的思考,世界上成功的作家与作品,无不是在这个特殊的范畴下写作”。事实上,人对于死亡、未知和孤独这三个终极恐惧,在常态的生活中更主要地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实际上人也正是在与他人、自然、社会的冲突对立中,逐渐明晰了自我意识和责任。所以,作为作家的王先生,在表现人与自然的文化关联中,更能够以拟人手法来状物、摹景、写情。在他的眼里和他的一些作品中,人被幻化成为动植物,动植物成了人格化的高级生灵,因而,他可以在思绪和想象里倾注人的情感、唱着诗意的赞歌,以物类人、攀附比拟,寻找灵魂的栖息地并标上文化分类的界碑,打磨出属于他的清晰而独特的文化记忆。而且,他在文本中延异着这种文化记忆的碎片,使当下的叙述造成与既往事件割裂,然后又用文学的意蕴弥补这种断裂和穿越时空带来的裂痕,使客观上“日头叫天狗炒菜吃了”的不可能变成语言上的可能。
进入新世纪后,经过这之前相当一段的文学实践和磨砺,在更具典型意义的生命体验的不断掘进中,在思考表达的更多尝试里,王先生的文学思想愈加成熟,对世界本体的形而上追问有了更加迫切的自觉意识。
所以,从《村庄与时间》、《时间是谁的》开始,他对时间的探讨有了更为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这些作品拿时间、历史、文化与人们的精神领地做为写作的由头,有了厘清和超越历史的想望。他说:“一个作家过多的担心历史的条件是不是允许我这样允许我那样,一个作家在历史的缝隙里写作与徘徊,那么,他的作品就只能仅仅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而不能深刻的反映历史的全貌和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由于有了跳出历史回望的期盼,他的作品能够有意识地把人们的思绪拉向历史的纵深和指向时空的未来,延展着人们对事物普适价值的回味空间,多了些建造和安放灵魂栖息地的港湾,而少了些追名逐利的煎熬和喧嚣,使人由入世的纷争走向归途的宁静和平淡,人生真的目的才会变得昭然、明朗和洁净。
想象呈现艺术魅力,经验提供生命质询的力度,两者是主体的艺术创造所必需的。用文化去度量灵魂自律间的差异,并使这种考量切入人性的核心和文化的本质,就愈发显得王先生的文化传播理念和语言感悟的另类。尽管王先生也写苦难,但他的苦难更多表征的是散文特质的一种对宿命不屈的文化抗争。他的夹叙夹议轮廓模糊且不露声色,是纯情的感慨有度,而不是虚饰滥情的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尽管他语言犀利,但更呈现一种立体般的纯厚、深远。
王先生在文本中时常不由自主地展露他的语言优势,他的语言狂欢是一种内在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从来不缺乏自信。他的一个个否定动词的肯定判断见解精辟、描摹别致,感悟和表达使主旋律成了深藏不露的另一种隐喻,多重的复句使他说彼而言此的依据贯穿和涵盖其他,语不及意成了意带笔随的起始,主题的述说变成辅助的捎带,聚焦的细节却不引领表达的主体,那一掠而过的惊鸿才是昙花一现的题眼,就这样,当主题隐匿在纷繁中而直逼终极问题时,精神便有了可以存放从容的释然和妥帖,而思绪却漫天遍野地四处招摇,文化便在他的精妙构思下得以张扬。所以,充斥于他作品的哲理性复式语言的娴熟运用,使复句有着更为斑斓多彩、摇曳多姿的开放的时空背景——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现实的,无疑,这加大了语言内涵的思想包容性,像《彩虹是天蛇的儿子》等很多篇目,都似乎要用不同意象来牢牢地裹紧一个社会形态的表征,在世俗恩怨的纠结阐释上体现他语言比较空灵的天赋。
读王先生的作品,还时时体会到他的正反判断是朴实而又带有狡黠意味的句式,这种句式极尽评判、述说之能事,围绕事体呈现事物的社会品性并揭示其意义所在,力图周延地去印证文化引领的信念,进而去还原和见证语言表达的情感色彩,见识一种胸怀和气度,这种穷尽可能的选项有一种雄辩力量和志在必胜的气概,引领我们走向悖论思考的彼岸,使我们由彼及此、由表及里地感知文学的熏陶,沉浸在他为我们强力营造的不容置辩的梦幻般地审美发现和想象中,从而得以在精神层面上去看待世态万象。尤其是他的这种呈现是激情四射、个性鲜明而鲜有中庸的似是而非,他并不在意别人如何评价他特立独行的主观味很浓的个人观点,他甚至是偏激、偏执地表达自我,淋漓尽致地听从人性的驱使,毫无顾及地袒露自己的灵魂仪态,尽管这种呈现有时并不那么绅士和大度,但性情中人毫不刻意掩饰自我的可爱便裸露在大众的面前。
王先生的散文大多是从议论的本体出发,抵达他心中纠结的一件往事,采取从叙事的陪伴中走进故事的终结,然后扩充它的精神含量、增大它的内涵、引申它的意义、增设它的意蕴形式,而后再折向散文的广阔天地和他所预先设定的主题。于是,一个平凡的事件就会因了他的主体意志,而使这种述说和构思的策略有了更大的幽默感和形式感,有了语言表述上的陌生化,这种陌生化的感觉,是他在反思历史中揉入了传统文化的因子和颠覆现有语言模式所迸发出另类思想火花的结果,也是他在时间的流逝中激情澎湃地张扬人性、意欲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更是他抵力拼足表达自我与理性对决的结果。
由于对时间思考的不断深入,王先生总能以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潜藏在生活表层下的那些质感很强而又易为常人忽略的东西,然后表达那些生命体验中最为深刻的咒语或谶言般的意境,把经灵魂过滤的世相塑造成命运起航的风帆而高高挂起在逼视精神的领地,而后在驶入人生终极生命运行的轨道中,去找寻抚慰心灵的家园。
可以看出,他孤独灵魂的吟唱不仅是离愁别绪,更是对一个村庄文化的传承标本的思索,体现出一个浪游天下、漂泊不居的精神游子对自己灵魂的放任和洒脱。从这里出发,灵魂将走向何处?无论是出于对背叛村庄走向未来的母体质疑,还是亲近文化疏离自然的情感纠结,也无论是从心所欲的节制,还是无欲则刚的率性张扬,都肯定超越了他精神依赖的泥土,意味着他对既往反思的创新,所以,背叛的智慧是土地赠与他的怀念过去的思绪和对理性思考的阐释,走过土地就走进了时间的记忆,迈过村庄就可能脱离了精神的领地(《总有脚步背叛了泥土》),就这样,他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放飞理想、放任思绪,任意念眷顾情的思恋,让意境荡起思的莲漪,使意蕴包孕景的纵深,开辟境界,舒展情怀,使时空的存在衔接上花香的意味,让心的奔放涂抹上爱的彩绘,如行云流水,似命运奔突,让狂放贯穿历史,使瑰丽燃放现实,于是,《千年酒歌》的吟唱就有了不可或缺的大风歌式的现实意义。
某种意义上说,王先生的另类来自于他对时间的深入探讨。他总能使自己的思考深入到时间的隧道,从劳作延伸到生产,从梦幻穿越到现实,由自然而社会,由社会而人伦,纵横驰骋、一泻千里,进入到纯粹思想的精神实质里去,靠推理和想象验证人文那更多可能的答案,使物质的块垒进入到时间的虚拟,从独语和感悟中读解自然之道的人文观照。于是,永恒和速朽、当下与历史、微小与伟大、渺茫与清晰、方寸与宇宙,至小和至大,成了他一目了然的辨析历史的思维空间。他的有些散文甚至直接是以文化的因缘解构历史、村落和时间的神秘为己任,于是,时空中的一切有了全新的意义,一切成了新的阐释,一切有了新的注解和命名,他以询问质疑着历史和时间,并以文化的名义刀削斧砍着时间中的自然差异,使社会、自然、历史、思维在被王氏坦然剥离的潇洒中显示更加文学化的轮廓。
当然,王先生的写作也使我们看到,当他对时间的形而上思考有了更为抽象的概念时,他的价值观以及对于物质和意识便会产生微妙的变化,他与文学的距离就有了若即若离的变移空间,也使他的思想能够天马行空、述而不乱地畅游其中。于是,他在时间里的思想旅游,不由自主地强化着“存在与感觉”、“理性与人性”、“物质与生命”、“梦想与现实”、“经典与浪漫”、“记忆与遗忘”、“落寞与伤感”、“悖论与否定”、“柔软与流淌”、“模糊与复原”等时空观。那么,他也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将真实放逐给虚拟的专属于作家的这么一种权利——虚构和想象——这是一个更能体现作家创造力的品性。
其实,在现代,任何一个想在文学创造领域走得更远的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仅会把逻辑生活中的跌宕起伏拓展开来,更会注重时空错位的拼接等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以使文本的厚度增长、思绪的空间增大、想象的意蕴扩展、思想的容量增加。比如王先生也写故乡是灵魂的栖息地,但他更多的乡愁是反思人的孤独、焦虑、无所事事又惶惶不安的灵魂漂泊,这种如深宫怨妇般发出哀怨的低吟浅唱,像流浪者的居无定所和精神的游移不定给人造成更大的生存压力,当然,这里它更是让“月亮领着灵魂走”的想象有了穿越时空、拉长记忆的功能。同时,王先生把片段和闪回应用在本应一维化的散文中,无疑拓展着思想和想象的认知空间(《西蒙的葡萄园》)。而且,他在句法构成和裁剪修辞上也用到了意识流、甚至还有蒙太奇、拼贴等来扩充他的表达,像“1996年的夏天,雨天从葡萄架上滴落下来,一枚葡萄叶子……落在《弗兰德公路》的扉页上。我把这枚叶子拾起来,发现……西蒙引用莱奥纳尔……”这种言说方式富含文学意蕴,其起承转合更利于文化见解的逻辑契入。
他的作品,还使我们看到,他散文的另外的精神向度是对于政治入木三分的理解和关于宗教的深刻认识。
我们知道,政治主要是靠颠覆利益集团的社会地位促使其角色的转换和实行利益的再分配,革命、改良、变革、改革莫不如是。这些观念性的意识反映在文学上,就促使王先生含蓄地写出世事沧桑而没有过多的指责,如《月亮领着灵魂走》的表达,实际上更有普适意义,也从而能够对人性揭示和人文精神的体现给予更为传神和持久的描写。
一般来说,直接的教化人的东西应该是偏重于理性,而感性的东西是通过浸润人而起到潜移默化作用的,所以,宗教的经典无论其教义如何、精神指向何方,都能够成为理性思考和文学写作的淬火之剑。
我们知道,东方宗教是实用性的,虽然东方的宗教场所大多建在清净偏僻处,但却总是难以阻断滚滚红尘中善男信女的功利追求,烧香拜佛成了世俗中最泛化而又基本与灵魂修为无关的活动,于是,宗教信仰在有些人那里反而演变成了徒增烦恼之举。相反,尽管西方的宗教场所建在闹市,但他们的宗教活动却鲜有功利色彩,祷告忏悔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心灵洗涤而无碍于世俗功利,是寻求慰藉减缓压力的修身养性纯洁心灵的自在之为。所以,从《禅宗的川端康成》看出,正是王俊义先生对东西方宗教比较后的清醒认识,使他的写作更多蒙上一层悬置宗教于不顾的色彩,也从中引申出他的文学观上的虚无主义甚至多少有点颓废的思想认识,他说“我的创作反映了我的存在没有多少意义”就表明了这点。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他身上那种在文学之路披荆斩棘、笔耕不辍、不断刷新和挑战自我的奋斗精神。
尽管王先生的小说和诗歌写作也都出手不凡并很有影响,但同仁公认他的最大成就还主要是在散文创作方面。特别是他散文中所表现出的那宽泛而深刻的思想、卓异的观念、多变而内在、纷繁又简约的句式,以及那些长句的腾挪翻滚、风生水起、判读的刁钻古怪、新奇意象,都是他深谙语言陌生化之真谛的有力表现,这为他的文本意蕴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瑰丽的形式色彩。
是的,我们确实可以轻松地感知和把握水向下流、人向上走的真理,却无法用经验知道时间、空间及存在的实在由何处来向何处去的规律,因此,对形而上的深入研究非常必要且更有意义,也因而王俊义的文本及其那些关乎文学性之外的东西就越发显得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