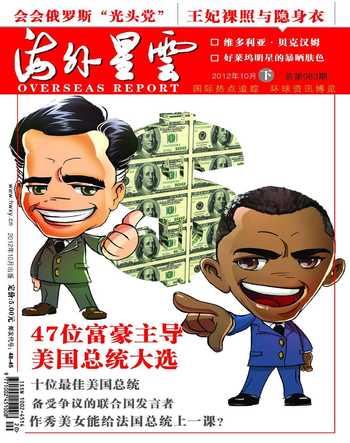优秀毕业生为何在澳大利亚当屠夫
杨绍华


在台湾工作两年,存不到钱,身上还背着不小的学贷,我到澳大利亚来,就是为了赚第一桶金,不用怀疑,也不必多作解释,我们就是“台劳”!
不是为了体验人生
我上晚班,上班时间是下午两点半到午夜12点。
我的工作是食品加工,在偌大的厂房里,我站在迂回曲折的输送带边,使劲地把送过来的冷冻羊肉去皮;去完了,放回输送带,没有皮的羊肉移动到下一个加工程序,我则继续为下一块羊肉剥皮。
在9个半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每隔两小时能休息一次,第一次10分钟,第二次20分钟,第三次,大约是晚上9点,我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终于,可以利用这次相对充裕的工作空档吃晚餐,走到蒸饭箱,拿出上班前自己在宿舍料理的简单便当,通常是炒饭。
我在澳大利亚,工厂位于南澳最大城阿德雷德;我来自台湾,今年27岁,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
这座工厂,说穿了就是一个屠宰厂。活生生的牛、羊运来之后,先被电晕,然后宰杀,屠夫一刀把牛羊的肚子剖开,内脏与血水“哗”地一声流到塑料桶子里。我认识一位同样来自台湾的年轻人,负责拿着水管“清洗牛肺”,经常,他的衣服会被牛的血水染成红通通的。
在这座厂房里,估计约有600人在同时工作着,其中,我想大约有150人以上来自台湾。
几年以前,听到学长学姐谈到他们的澳大利亚打工经验,工作很辛苦,但总是工作几周就自动辞职,把赚来的钱当成旅游基金,坐飞机玩遍澳大利亚各大景点,钱花完了,再找下一份工作。他们说,来这里是要趁着年轻“体验人生”。
但我的心里很清楚,今天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体验人生,也不是为了交朋友、培养世界观。我的目的很实际、很俗气,也很单纯,就是要赚钱。我曾经在台湾工作两年,当银行理财专员,但工作时间很长,三餐都在外解决,加上房租、给家里生活费用、偿还学贷等开销,工作两年下来,银行户头里的存款只有几万元(新台币,下同),还有30万元的学贷背在身上。我想,如果继续在台湾工作,这笔债务不知要等多久才能还清,遑论存到一桶金。
想要有钱赚
得专注在当地人不愿做的工作
据说,现在有超过1万名台湾年轻人正在澳大利亚打工,当然我不会知道每个人的想法,但至少我身边的台湾朋友,想的都和我一样。
“在这里认真地出卖劳力两年,然后带着200万元回家。”我们是这样约定的。
我的时薪有19元澳币,每周大约能赚800元澳币,差不多是新台币2.4万元;一年下来我的收入应该会有125万元以上。照理说,每年存个百万元并不算难。当然,前提是要”一直有钱赚”,而且,熬得下去。
要“一直有钱赚”,就得专注在“多数澳大利亚人不愿做”的工作。5个月前我刚来这里,天真地想要找一家餐厅端盘子,结果不到3天就被老板炒鱿鱼,他说我的英文不够好,但我知道,其实是一个澳大利亚本地的年轻小伙子取代了我。
很快地我认清事实,被归类为第一级产业的“农林渔牧业”,才是我们的金饭碗。这些产业的工作机会多半劳苦,所以很缺工,难怪澳大利亚政府说,必须至少要有3个月的第一级产业资历,才能申请”打工度假”签证延长一年。
结束短暂的餐厅服务之后,接下来我去农场工作,每天清晨5点,我们在“工头”家的门口集合点名,听他分派今天的工作,然后,十几个背包客挤进一辆破旧不堪的小面包车,一站一站,工头把我们陆续送到不同的农场。
我一度联想到那种二次大战电影里的画面,一群犹太人表情惶恐而疑惑地被送到一处一处的劳改营……可能想得太夸张了,但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
大致上,农场工作的时间是从上午6点到下午3点,中间约有两次、每次20分钟的休息,我就在农场里找个地方坐下,拿出自备的水壶和土司面包,分别解决早、午两餐。
比较起来,我喜欢现在的屠宰场工作;农场里的风景固然是好,空气清新,但工作地点和内容并不固定,搞得我每天都在充满不安的心情之中起床:“今天是要拔葱?整地?或者是要除草?今天的农场主人不知道脾气怎样?”
在屠宰厂里,除了刚开始会因为恶心吃不下饭之外,其他倒没有太大问题。由于上班的场所与内容固定,工作容易上手,与同事、主管的感情也比较融洽,不会遇到太严重的歧视状况。
接受歧视
是在澳大利亚的必经修炼
说到歧视,在澳大利亚,接受歧视是必经的修炼。听过比较夸张的案例,是工头对台湾来的女孩子毛手毛脚,也听过被恶意积欠薪水的、被围殴的;也有被人称作“黄猴子”,至于我,曾经车子从身边开过去,一群小鬼头不知道在叫嚣些什么东西,还朝我身上丢罐子。澳大利亚人爱喝酒,所以每到周五晚上,我们这种黄色面孔最容易成为酒醉年轻人的戏弄对象。
我忽然惊觉,我们来澳大利亚当“台劳”,其实就像是泰国人到台湾当“泰劳”。难怪,在澳大利亚打工的年轻人固然来自世界各地,但这几年人数增加最快的就属台湾;我又惊觉,原来,澳大利亚人眼里的“台劳”,其实就像是台湾人眼里的“泰劳”。(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