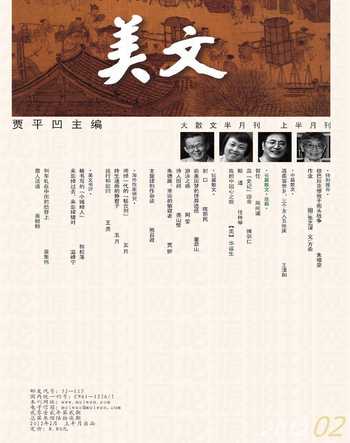垮掉一代的“粘合剂”
五月
自由撰稿、翻译者、图书策划人。在纽约与北京之间穿梭。著有散文随笔集《距离之外》、诗集《雨天的沙漏》(合著)等。
曼哈顿上城西侧的晨边高地一带,有一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它就是成立于1754年的哥伦比亚大学。
哥大的前身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资助建立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也是当时北美十三个英国殖民地中仅有的两个皇家学府之一。建校250多年来,哥大可谓人才辈出,不仅有如今的总统奥巴马这样的政治精英,也出过数不清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大师级人物。当然,这里也不乏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中最知名的,要数出生在距离校园三条街的J·D·塞林格了,如今,他故居的公寓依然安在,却很少有人前来拜谒,大概是由于他几十年来一直隐居在新罕布什尔的偏僻小镇,纽约的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个曾经的邻居。
说起哥大在美国文学界的地位,一定会使人想到50年代兴起于这里的“垮掉的一代”运动,文学史的专家们曾经评论道: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唯一一所诞生过整个一场文学运动的大学。这是因为“垮掉的一代”的三个代表人物——杰克·克鲁亚克,威廉姆·巴勒斯,和艾伦·金斯堡—— 都或多或少地与哥大有过某种联系,他们当年的活动中心也是在哥大的校园里和学生公寓中。然而,说到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哥大学生,由于他的参与和鼓动,“垮掉的一代”才有了核心和纲领;又由于他的亲身经历,几位作家才有了他们代表作品中的原始素材。
这个人的名字叫路西安·卡尔。
一
路西安·卡尔1925年生于纽约,5岁时父母离异,他随着母亲搬往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并在那里长大。
1943年,卡尔回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很快就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那时的卡尔是一位英俊潇洒、充满活力的名校大学生,同学们对他的评价都是“热情洋溢”“聪颖过人”一类的美誉。他阅读广博,才华横溢,文学、绘画、音乐无所不通,随口可以引出几句莎士比亚,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结交广泛,人缘很好,朋友不分男女,遍布校园内外。
他同宿舍的室友中,有一位来自新泽西的木讷犹太学生,一心想成为一名劳工法律师。这位室友始终记得,开学第一天,他就在楼道里听见宿舍里有人在播放勃拉姆斯的三重奏,对于一般更喜欢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来说,这不免有些令人惊奇。他推开门后自我介绍,知道那个喜爱古典音乐的家伙就是卡尔。很快,他俩就成为了好朋友。而正是卡尔,独具慧眼发现了这位室友的诗歌天赋,并鼓励他放弃做律师的俗路,“你天生就该是个诗人!”
果然,几年后,这位室友便以一首震惊美国文坛的诗作——《嚎叫》,一跃成为其后几代人的文化旗手,他就是艾伦·金斯堡。
入学不久,卡尔在哥大的艺术课堂上,结识了一位名叫爱迪·帕克的女生,并通过她,认识了帕克的男友——杰克·克鲁亚克。三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名叫“西端”(West End)的酒吧。
“西端”酒吧位于百老汇大道靠近114街的地方,由于它距离116街的哥伦比亚大学主校门只有两条街,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哥大学生课余周末的聚会场所。酒吧的招牌口号也直截了当:哥大人喝第一杯啤酒的地方!
几年前,崔健来美国巡回演唱期间,曾被哥大请去与学生们见面座谈。座谈结束后,很多人意犹未尽,便簇拥着老崔和他乐队里的几个哥们儿,来到“西端”酒吧海聊痛饮。酒吧的主厅很大,却吵吵嚷嚷地座无虚席。领班将大家带到里间的乒乓球厅,厅里只有一张球台,两张桌子,七八把椅子,挤进来的人可不少,只好轮流坐一会,坐累了的就上前挥拍较量几个回合。
那天晚上,老崔喝了不少德国黑扎啤,和大伙儿聊得挺尽兴,还在乒乓球桌上显了显身手。
这便是我对“西端”酒吧的全部记忆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西端”酒吧是个与“垮掉的一代”很有些历史渊源的场所。当年,正是在这里,克鲁亚克、金斯堡、巴勒斯等人相识、相知,一起讨论伟大的理想,品评彼此的作品。可以说,“西端”酒吧正是孕育了“垮掉的一代”的摇篮。可惜的是,当我再次前去拜访时,“西端”已经改弦更张,变成了一家古巴餐馆连锁店,只是在餐馆的招牌上还保留着“西端”的字样。
克鲁亚克比卡尔早几年进入哥大,却半途辍学加入了美国海军,结识卡尔的时候,他刚刚由于“心理因素”不稳,被海军辞退。那时候,克鲁亚克心情挺沮丧,住在女友的公寓里,无所事事。他已经不能算是哥大人了,只能算是哥大“家属”。初识的时候,他有些讨厌卡尔,不喜欢他频频向自己的女友帕克献殷勤。后来,克鲁亚克慢慢了解了卡尔,知道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对谁都是一样地“充满热情”,很快,他就和卡尔成为好朋友。克鲁亚克后来回忆到两人的友谊,曾经有一次,他钻进一个空汽油桶中,让卡尔推滚油桶,沿着百老汇大街,一直滚回家中。克鲁亚克将自己开始真正的严肃写作,也归功于卡尔的感召。百无聊赖的他在卡尔的鼓励下拿起笔,着手构思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小镇与都市》。
自从认识了卡尔之后,爱迪·帕克的公寓就成为哥大附近一群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人的大本营。宿舍里经常是高朋满座,人们高谈阔论,直到天明。帕克和她的女室友,卓安·沃尔沫,成了俱乐部理想的女主人。卡尔带来了自己的女朋友,带来了他的室友金斯堡,带来了他的老乡、哈佛毕业后跑来纽约当酒吧调酒师的威廉姆·巴勒斯。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三教九流的人士,包括吸毒成瘾的艺术家、除了做梦无所事事的“职业”流浪汉、甚至还有妓女和酒鬼。至此,十年以后风靡全美的“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全部聚集在位于118街的那间小小公寓里了。
卡尔引荐金斯堡、巴勒斯与克鲁亚克见面的地方,也是在“西端”酒吧。在一次周末晚上的觥筹交错之际,卡尔宣布了自己的宏大文学理念,这个被他称之为“新视角”的理论,源于他的一篇论文,“爱默生时代的先验主义和巴黎波西米亚精神”。其理论的三个纲领性口号是:
· 赤裸裸的自我表达是创作的种子;
· 艺术家的意识领域因感官紊乱而扩展;
· 艺术应该远离传统道德。
正是卡尔的这个“新视角”,奠定了垮掉一代创作风格的基石。日后,金斯堡这样评价路西安·卡尔:他是“‘垮掉的一代的粘合剂”。
二
还是在圣路易斯的时候,卡尔就结识了后来他生命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都比卡尔大几岁,都出身于圣路易斯的名门望族,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因写出《赤裸的午餐》而享誉美国的威廉姆· 巴勒斯,另一位名叫大卫·卡迈勒。
卡迈勒当时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英文和体育教师。在卡尔14岁的那年,卡迈勒带着他和一群少年去野外露营时,卡迈勒疯狂地爱上了他。不知是由于卡尔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将卡迈勒作为一个情人看待,总之,他一直感觉挺别扭,不知道如何把握俩人之间的关系。在进入哥大之前,为了躲避卡迈勒的跟踪,卡尔曾先后转学到几个地方,从马萨诸塞到缅因到芝加哥大学。但是,卡迈勒对卡尔的痴迷不但丝毫未减,反而与日俱增,不管卡尔走到哪里,卡迈勒都会跟随他到哪里。后来的“垮掉的一代”文学史研究者曾这样描述:卡迈勒像一个影子一样,寸步不离卡尔,他对卡尔的“性渴望”未能得到满足,其行为近乎“失去理智”,这难免引发卡尔抑制不住的恼怒,并终将带来巨大的麻烦。
对于年轻的卡尔来说,“麻烦”自然是先从自身开始。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生活正是因一次“事故”而终结的。那一次,他将自己的脑袋伸进打开阀门的煤气烤箱,只因发现及时,才幸免一死。对于自己的举动,卡尔后来解释那是一种“行为艺术”,但他的家人却认定,那是由于卡迈勒的无理纠缠而引起的自杀未遂。卡尔被送进一家医院的心理治疗病房,住了两个星期。刚刚搬回纽约的卡尔的母亲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儿子,帮卡尔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
然而,卡迈勒并没有因为差点出了人命而死心,他很快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来到纽约,住进下城的格林威治村。为了纠缠卡尔,他不仅在哥大的教室外面等候,在街上跟踪,爬到楼顶观望卡尔和同学们的聚会,甚至还顺着卡尔住所外的防火梯爬上去,坐在公寓的窗台前,默默地注视着“心上人”酣然入梦……
然而,1944年夏天发生的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他俩的命运,也改变了“垮掉的一代”作家们的命运。这件大事的中心人物,还是这位路西安·卡尔。
那年八月的一天,卡尔和克鲁亚克一时兴起,打算偷偷搭乘一艘去法国的商船,潜入巴黎,参加盟军解放这个城市的庆祝活动。曾经做过水手、会说一口流利法语的克鲁亚克装扮成一位法国乘客,而卡尔则扮作他的聋哑朋友,混上了停靠在曼哈顿港口上的商船。不过,俩人的运气实在是不好,在轮船即将离港的最后一刻被人识破、赶下甲板。俩人郁闷无比,回到“西端”酒吧大喝了一场,克鲁亚克提前告退,在酒吧门口迎头碰上了前来寻找卡尔的卡迈勒。
卡迈勒听说了卡尔和克鲁亚克的冒险计划之后,很是紧张,生怕自己从此失去了卡尔。他在“西端”看到“心上人”之后,才放下心来。他坚持要卡尔陪着他,到附近哈德逊河岸边的河边公园里喝酒谈心。正在卡尔心无旁骛地望着河水中来来往往的船只而忘情的当口,卡迈勒忽然解开了自己的裤子,不顾一切地压在了他身上。卡尔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他费尽气力挣扎,始终无法摆脱卡迈勒那沉重的躯体,气急之下,卡尔失去了理智,多年沉积的愤怒,一股脑儿地蹿上头顶。他掏出兜里的一把小刀,在卡迈勒的胸膛上,一连捅了十二下。几分钟之后,卡迈勒就咽了气。
这下捅大娄子了!没时间多想,卡尔用卡迈勒的皮带将尸体捆起来,上面压上一些石块,将其推下了哈德逊河。然后,他神色慌张地跑到格林威治村里巴勒斯的住所,希望老乡给他出个主意,该怎么办?他战战兢兢地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上一支,又抽出一支递给巴勒斯,香烟盒上还沾有一些血迹。巴勒斯一把抢过烟盒,扔进马桶,放水冲走,然后拿出啤酒,给他压惊。巴勒斯建议卡尔先去找个律师,然后到警察局去自首,如实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认个自卫过度,争取宽大处理。
犹犹豫豫中,卡尔又跑到帕克的寓所,想听听克鲁亚克的意见。俩人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先冷静观察几天事态的发展,说不定没人发现尸体,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过去了。主意已定,克鲁亚克和卡尔干了几瓶啤酒,然后一起走到附近的晨边公园,克鲁亚克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边在树下撒尿,边四处观望,掩护卡尔埋藏了那把杀人的刀子和卡迈勒的眼镜。一切安顿好,卡尔似乎定下神来,俩人一起出去看了场电影,吃了顿饭,又去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看了画展。
卡尔回到母亲家里,禁不住地胆战心惊,想起白天发生的事,他愈发坐卧不安。在母亲的劝导下,第二天,他来到纽约检察官的办公室,主动自首了。警察将信将疑,先把他扣押下,待找到尸体和作案工具后,才将卡尔作为凶杀嫌犯逮捕。巴勒斯和克鲁亚克也因知情不报、协同销赃等罪名被关进了监狱。
垮掉的一代,眼看就要彻底垮掉了。
三
一群好友昔日的快乐时光,被这起杀人案件搅得一团乱麻。克鲁亚克和巴勒斯作为同伙,交保释放的金额是2500美金,巴勒斯家底殷实,老爸立刻从圣路易斯汇了钱来。刚保释出了监狱大门,巴勒斯转身就溜回老家了。
克鲁亚克也给老爸打了个电话,父亲一听,勃然大怒,“我们克家从来没有人和杀人犯有过瓜葛。”喊完挂了电话,保释金自然踪影全无。他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求女友帕克帮忙了。帕克家是底特律的富户,父亲在富人区拥有几个高档汽车销售店,可是,帕克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克鲁亚克是谁啊?要想掏钱替他担保,“除非他是我女婿!”
帕克救男友心切,和克鲁亚克一商量,主意立定。几天以后,克鲁亚克在警察的陪同下,从监狱来到纽约市政厅大楼,和早已在那里等候的帕克公证结婚。帕克的父亲如约汇了钱来,他才得以出狱。
纽约的媒体对这起案件作了大量报道,名门望族的天才青年,纽约的常青藤学府,令人诅诟的同性恋丑闻……无一不是读者们津津乐道的头条新闻素材。卡尔最终以二级杀人罪被判刑入狱,不过,由于他认罪态度诚恳,又确实有自我防卫的动机,他在监狱里只服了两年刑。
克鲁亚克出狱后,就随同帕克回到底特律,做了“倒插门”女婿。不过,他俩的“救急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年就协议废除了。此后,俩人一直持续着朋友关系,帕克也出现在克鲁亚克的几部作品中,包括著名的《在路上》。
在卡尔事件发生的前后,还引出了另一段婚姻。帕克的女室友卓安·沃尔沫死心塌地地爱上了卡尔的老乡,温文尔雅的威廉·巴勒斯。沃尔沫当时是已婚之人,丈夫是哥大法学院的学生,因二战应征入伍去了欧洲。丈夫在中间回家探亲时,发现沃尔沫结交了一批“乌七八糟的狗男女”,还因克鲁亚克的怂恿染上了毒瘾,便和沃尔沫离了婚。这正好合了她的心意,在金斯堡的撮合下,沃尔沫和巴勒斯同居了。尽管巴勒斯是位公开的同性恋,但沃尔沫全然不顾,相信自己的魅力,坚定不移地把他勾引上了床,并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俩人从未结婚,但一直以夫妻相称,成为“事实婚姻”。这场“婚姻”本来可以成为他们这一群朋友中难得的佳话,不幸的是,几年以后,在躲避毒品官司逃亡墨西哥期间,一蹶不振的巴勒斯在酒后游戏时,一枪射中了沃尔沫的脑袋。
出狱后,卡尔在一家通讯社找到工作,从打杂做起,一干几十年,一直做到资深编辑,直到1993年退休。他在办公室颇受同事们的爱戴,编辑事业也卓有成就,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新闻后辈。他一反年轻时的风流耀眼,而一直保持低调做人,他甚至曾主动劝说金斯堡,将其成名诗集《嚎叫》扉页上献给的人物中,把自己的名字除去。
为了报答有难同当的朋友,他与“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保持了一生的友谊。他曾经是克鲁亚克后来一次婚姻的伴郎,并一直是他忠实的酒友、读者,和批评者。克鲁亚克的六部小说中,都有以卡尔做为原型的人物,包括《在路上》里的得米安。据说,《在路上》的手稿,那卷著名的一气呵成打印纸长轴,就是卡尔提供给克鲁亚克的。克鲁亚克一生最后的时刻,在酗酒吸毒、醉生梦死、病魔缠身的日子里,卡尔对老朋友一直不弃不舍,有求必应。
艾伦·金斯堡曾经以卡尔杀人事件为蓝本写过一本小说——《血歌》,后来在自己老师的劝告下,为了不给卡尔和哥大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没有发表。住在纽约的金斯堡在成名后的几十年间,还经常走进卡尔的办公室,就如何宣传报道自己的作品和社会活动,征求老朋友的建议和帮助。
1945年,巴勒斯和克鲁亚克曾经联手撰写过一部小说,故事完全围绕着卡尔杀人事件而展开。这部作品的存在,是多年后克鲁亚克的传记作者首次曝光的,名字叫《河马煮熟了》(And the Hippos Were Boiled in Their Tanks)。由于是唯一一部著名作家的联手之作,它一直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期待。2008年11月,在当年涉案的所有人物中的最后一个——路西安·卡尔—— 去世三年后,企鹅出版社才最终将其出版面世。
卡尔的后半生完全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十分注意往事不再被重提,注意自己的隐私不再被媒体曝光,他的婚姻幸福而持久,夫妻俩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为畅销书作家,实现了父亲曾经的梦想。
2005年,卡尔因骨癌不治而离世。他活了将近80岁,却是“垮掉的一代”里晚年最幸福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