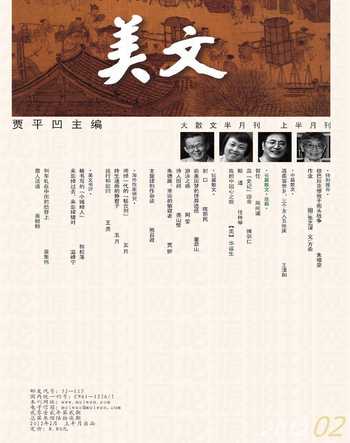作业
方希
六
相比四月影会,内部电影的这些刺激又显得没那么强烈。进入北电,张艺谋经受的刺激就一浪高过一浪。四月影会摧毁了他在摄影上的那一丁点儿自信。摄影系的同学有不少在进校之前都没摆弄过相机,第一堂摄影专业课,老师是从教大家怎么挎相机开始的。当时发的相机是海鸥205,侧面取景,老师要反复强调,一定要打开镜头盖,要记住转胶卷。基础的侧光、逆光、顺光、高调、低调,对于一张白纸开始的同学来说还需要学习,对于抄了三年书,拍了四年照片的张艺谋来说,没什么挑战。连老师也说,张艺谋的黑白平面摄影不用教,已经会了。
四月影会由王志平、金伯宏、王立平、李晓斌、李英杰等发起,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办了第一届完全由民间发起的摄影展。1980年在北海公园举办,1981年终于进了中国美术馆,登堂入室,这也是它的最后一届。
张艺谋去看的是第一届,四月初的北京还很冷,没开展,中山公园的兰室外面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那时候穿的都是蓝、黑,大多数人不说话,人群里有低沉的嗡嗡声。一开门,人群不是一个一个走进去的,也不是一列一列排进去的,人是一整块,一大砣,从室内移到了室外,你在人群中,根本就不能自主迈腿儿。”张艺谋说,他的影像记忆相当生动。
每张照片前面至少有五排人,张艺谋必须耐心地蹭到照片前,脸快挤到照片上去,得使劲儿撑着,后面人流的力量又在不断推涌。照片不大,好多也就A4纸大小,不凑近根本看不清楚。还得拿笔抄下照片下的诗,记感想,记构图。不过这次影展给他的刺激是,那种教材式、新华体平衡的构图,在这里似乎失去了魅力。
根据后来的统计,历时20天的展览,迎来了大约7万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进去了七八千人,而展览室只有一百多平方米,还不如今天经济宽裕的人家里面积大。外面春寒尚厉,里面人肉的热量高得惊人,臭得要命。就这样,进去的人都久久不愿出来。有的人反复去,抄下了所有作品的名字,并给它们一一编号,甚至还抄下了所有留言簿上的留言,仅留言就有三厚本。
四月影会的发起人之一金伯宏说,他们之前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关注,这种盛况是唯一的,以后也将不能复现。他们认为,图片本身不如底下配的诗更让人激动。不过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一年级学生张艺谋直接感受到的,首先还是照片的冲击。他的感叹和当时的很多人在留言簿上写的一样:“原来照片还可以这样拍。”
“四月影会作品中,把镜头对准了人,对准了社会,对准了生活的细节,抓拍所呈现出那种自然、那种真实、那种震撼,所传递的那种深沉的力量和尖锐的时代性,让我目瞪口呆。”张艺谋说。王志平为四月影会的“自然·社会·人”主题写的前言,为他的惊讶做了注脚:
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是时候了,就像应该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
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而并不一定存在于重大题材和长官意识里。
张艺谋说,摄影系的很多年轻同学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触动,因为别人是刚开始接触摄影,而他是照着教材,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的镜头只对准过风景、花卉、场景,即使对准人物,要么是怀念大人物的小人物,要么是装扮成大人物的小人物,或者是在精神上经过大词装饰的小人物。他深知当镜头对准小人物的难度,你需要强大的概念支撑,才能让小人物深层的意味真正像一颗子弹打中观者的胸膛。
年轻的同学并不震动,也许在于,他们见得多,跟那个圈子或多或少有些熟悉。视野开阔,见过世面,眼睛可能被世面占满,但没有刺激,没有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不容易形成心态上的震撼和创作上的转向。认识作品后面的人,也没那么容易有神话,有时候一场生活八卦的价值,在于摧毁了对一个人作品的仰慕。
给张艺谋印象最深的,是《画家石鲁》那幅作品。石鲁是陕西人,张艺谋在咸阳厂里的时候就经常听朋友说到他,也看过他的画作。老画家“文革”中被整得很厉害,江青批判他的画作“野怪乱黑”,是“黑画家”。照片里的他垂垂老矣,形容枯槁,极消瘦,脸上线条很硬。老人一脸的倔强、愤怒、不平。这不是一幅平衡构图的摆拍,是石鲁瞬间表情的抓拍,一图胜千言。底下的那四句诗张艺谋到今天还记得:
白了一头黑发,
掉了一口白牙。
总算活过来了,
可怜的“黑”画家。
抓拍所展示出来的强悍的穿透力,加上诗的张力,张艺谋说,“我被打垮了”。回头看看自己那些被人夸过、自己也曾小有得意的摄影作品,张艺谋挥挥手:“我这些玩意,妈的,雕虫小技!”
张艺谋极少说粗话,他用词精确,节奏出人意料,加上神形兼备的肢体语言和变化的表情,常会出喜剧效果。我时时感觉在听单口相声,不论是回忆他在工厂的苦闷,还是上大学时的压抑,他从不用沉迷往事的口气说自己,他自嘲起来尖刻,逗趣儿,这次冲口而出的不雅之词,能想见他当时对自己否定的决绝。
《画家石鲁》是摄影师李江树的作品,张艺谋以为下面的诗是摄影师写的,从李江树的回忆中知道,配诗并不是摄影者的工作,而是四月影会发起人的设计。这几句是诗,李江树到了2008年才知道,出自赵小芹之手。
看完四月影会后,张艺谋几晚上睡不着觉。他努力消化影会上那些照片的冲击。影会上的数百幅照片,按照影会的发起人的回忆,里面包含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手法上也相对丰富。把镜头对准人,对准沉默底层的那一类现实主义作品,引起的轰动最为强烈。这也印证了张艺谋的感受。
不过这个刺激远没有结束,1979年年底的星星美展又给张艺谋带来了更深的搅动。接下来,他看到了《今天》的手抄本,看到了遇罗锦的《秋天的童话》。“我翻开书,从第一页一直到看完,姿势没有变过,心潮澎湃,潸然泪下。满腹的话无从说起,想要给人写信,要抒发,最后憋得没办法,写诗。我记得写了四句,最后一句抄高适的《别董大》,‘天下谁人不识君——凑的是律诗,前三句自己押着韵,我没研究过古诗,半文半白。现在看,可能跟顺口溜差不多。”北岛那一批朦胧诗人的一些诗句,张艺谋至今还记得。
“我算什么?井底之蛙。在咸阳的工厂里,前纺车间,织袜车间,平时在渭河边儿转悠拍点儿东西。你看看北京,波澜壮阔,四月影会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敏锐、先锋、深沉。星星美展,也都是一批人,现代、直接、彪悍。北京,藏龙卧虎。这就是1979年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这是颠覆性的印象。”张艺谋说。
2009年,王志平在纪念四月影会30周年的邀请函前言中说:
《四月影会》宣泄着年青摄影人的纯真、执拗、求索与才华。他们不拜神佛、不惧霜寒、不惊荣辱、不坠俗流、不谋私利、不辞劳辛。
他们得到了千百同仁和万千看官的认同、呵护和击赏。
《四月影会》如一艘前行的破冰小舟,为以后中国摄影艺术的开放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先锋作用,《四月影会》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绕不过去的一页。
张艺谋说:“在我的个人经历上,这几个事对我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尤其是四月影会。当时我认为,这些民间的、非官方的创作者们是英雄。至今我也这么认为。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一群人,一批人,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中国社会、政治、未来的思考,锋芒毕露、深沉浓烈,相当震撼。也许从今天看,作品还有幼稚的地方,呈现上还有不够完美的地方,批判的角度是否那么到位,那么合适,我们都不去说它,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爱国的、激情的、带有思考的展望和忧患意识,让人心脏爆裂,让人想要由衷地致敬。”
七
四月影会让张艺谋震动之余,也让他无比沮丧:“完了,这辈子踩风火轮也追不上人家了。我算是没出息了。”
摄影系前两年学的是平面黑白摄影,后两年才开始用16毫米摄影机学动态。张艺谋感觉,前两年在学校学的,不如他在影会上看到的东西对他更有用。
从张会军整理的78班摄影系课程设置上看,在前两个学年,专业课上的重头戏——摄影技术、摄影构图大概对张艺谋意义不大。不过电影胶片、电影技术、美术史之类的课程对张艺谋来说还是很能学到东西的。
四月影会最直接的影响,是张艺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抓拍,将镜头对准平民百姓,对准陌生人。北海公园刚出现了哈哈镜,北京人扶老携幼买票进去照镜子,在镜子面前看到自己熟悉的样子变形得那么滑稽,既吃惊又好笑。张艺谋买张票进去,在屋里转悠,拍了很多张。《哈哈镜》系列就是这么来的。
那时候还流行带蛤蟆镜不撕商标,以此为荣。张艺谋跑到颐和园,待了三个星期天,拿海鸥205抓拍了上千张照片。今天剩下的已经不多。这样奢侈地拍照片,可以完全不考虑成本,大约是请刘大模帮忙放照片时代的张艺谋做梦也不敢想的。
那一年在北京还召开了南斯拉夫现代艺术博览会,首次在国内公开展览裸体变形的现代艺术。和四月影展一样,来的人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不完全是艺术界人士。张艺谋早早进去,守株待兔,在女性裸体雕塑背后拍摄参观者的不同表情。有意思的是,这些照片中拍到了星星美展中的名人马德升,他风格凛冽的现代派木刻版画,在年轻人中影响很大。拍的时候张艺谋并不知道,后来有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德升。张艺谋觉得很荣幸。
这套作品原本想拿去发表,后来给退回来了。“可能主题上没那么主流,没那么先进。虽然是变形的现代雕塑,毕竟还是女性裸体,还是敏感和刺激的吧。”张艺谋分析。
四月影会的最后一届,是进入美术馆展览。张艺谋在受益于影展之后,也斗胆跟北京同学问,看他如果拍个东西能不能参展。北京同学跟影展的一些人认识,别人回来的反馈非常好,说欢迎。张艺谋马上行动起来,开始创意自己的参展作品。
《啊,一代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的。让张艺谋深受影响的拿相机直面民生,直面社会,基本上很难实现。他还在上学,跟社会没什么真正的接触。北京电影学院当时在昌平朱辛庄,学校的复建正开始,校址是借用北京农学院的地方,说好了,等新校址建好了还得还给农学院。
现在的二环外,在当时已经算偏僻了,现在的三环,当时基本是郊区,大片的农田,路都很窄。张艺谋每回进一趟城,下午掐着点儿还得赶紧赶回学校。
反映民生是行不通了,张艺谋必须另想办法。“我当时还是有那个胆量,虽然我跟着人家学,受到人家的影响,但是我还是想,精神上一致,但形式上我得来个不一样的。”
“黑白摄影最主要的就是影调,我决定用低调,大面积黑,感觉这种沉郁的、浓烈的味道跟我自己的感觉很相符。从摄影风格上看,就是跟风。但是被别人震了之后也想表现出个性,以前镜头都是去寻找,去发现美,目光投向自己,发现我们的十年也有意味。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精神世界,如果用照片表现,应该会引起同代人强烈的共鸣,也会带来震撼。我给这套作品起了个名字《啊,一代青年》,其实就是想了个大词,把自己搁在里头。”
张艺谋想好了创意,用照片简洁地表现出从1966年到1976年他们的遭遇和变化。
1966年,红心向阳,追逐,崇拜,政治狂热。
1968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设计了一个人蹲在墙角。知识青年从青年运动、八九点钟的太阳被打到最艰苦的农村,一下子没人管了,直接面对真正的生存艰难。苦闷,看不到希望。
1971年,迷惑。那一年的林彪事件对这一代人影响很深。张艺谋还记得一个同学把他和其他几个人拉到屋子里,蜡黄着脸,跟他们说:“北京来的消息,副统帅,死了。”
“啊?怎么死的?病死的?”张艺谋声音低沉,一人分饰多角,当年秘密交流的场景活灵活现,还有画外音。张艺谋语速很快:“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革命怎么办?接班人怎么办?”
同学说:“听说是摔死的。”
“啊?我脑子里迅速地转,怎么摔的?洗澡不小心?要不就是下楼梯……”
同学说:“驾飞机逃跑摔死的。”
“啊?逃跑?往哪儿跑?”
“背叛毛主席。”
张艺谋回忆,同学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声响雷,一枚炸弹,每一个信息都出乎意料,震得自己七荤八素。信仰产生了严重垮塌。
1974年,批林批孔,传言邓小平要出来恢复工作……这些复杂的信号让人看不懂。用一个人的一只大眼睛来表现当时的惊诧和观察。
1975年,邓小平复出,工厂里也开始提“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这是没有过的,感觉有了点曙光。
1976年,纪念总理的“四五事件”,用一只攥紧的拳头表示当年那句著名的“扬眉剑出鞘”。
十年的历程用低调表现完了,张艺谋觉得意味不够。最后用了一张纯白的画面,什么都没有。图片说明打上一个省略号。那时候的人看见一张白纸,立刻就会想到毛主席的话:“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张艺谋想用这个表示,一切重新开始。这张白纸,应该是他当时的得意之笔。
构思好了之后,张艺谋马上回到咸阳去找当年帮助过他的刘大模,请他帮忙把这些照片放大。七幅照片,每个都有一个全开那么大,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处理。张艺谋又从工厂里找人帮忙,做了七块板,把照片直接裱到板子上去,没有做镜框,无边界,表面平展,这些深黑仿佛随时会流溢。七张大板精心包裹,送到北京,送上1980年的四月影展。
这个系列从精神上看,从观察别人到反思自己,形式上、色调上都让人有强烈的印象。张艺谋说:“我就想跟别人做的不一样。”
在美术馆上展后,张艺谋在展厅里看见这七张照片,非常醒目。他假装是个陌生人,在观众背后听大家的反应,看大家的表情。他看留言,有人说自己在整个影展里最喜欢的就是《啊,一代青年》。张艺谋悄悄高兴。
这是张艺谋受到四月影会和星星美展的影响之后,要表现社会同代人共鸣的作品。在形式上特殊、张扬。他苦练的这一手,未必在精神内涵上多么超绝,多么创新,但是在形式表现上,呈现出自觉的、强烈的个人风格。这些需要在今天还要连篇累牍介绍背景的作品,对当时每个看到的人都无需解释它的寓意,自然意会。
形式的创造,并不意味着别扭和不诚恳,张艺谋觉得他不过是找了个不一样的形式,去表现不言而喻的隐喻和象征,也没有丝毫牵强的地方。
张艺谋听说王志平在看到这个系列之后,觉得不错,说如果有机会可以见见。张艺谋听了既光荣又害羞。“人家是谁呀,那是四月影会的发起人,人家组织了影响这么大的一个展览,太厉害了。我就是一个学生,哪好意思去见人家?”张艺谋说,“我今天都没有见过王志平,我不知道怎样表达他们那些人对我的震撼,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感激。”
八
张艺谋有意识让自己工具化,是从给别人抄大字报开始的。他的毛笔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练起。不过他没想到,入学后没多久,针对他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校园。
大字报主要是从美术系贴起的,针对美术系学生何群。何群是北京人,父亲是画家、雕塑家,有些美术界的背景。关于何群上电影学院的事件有多种说法。何群是1978年扩招进来的,据说考试本来不合格,后来有一封署名“何群”的告状信,申诉北京电影学院为了照顾美术界某位官员之子,打分作弊。文化部要求复查美术系学生的所有绘画成绩,包括何群,核查结果成绩合格,何群上了学。美术系当年扩招了六个人,何群是其中之一。
电影学院原本计划招生116人,那一届实际录取159人,绝大多数是扩招,像张艺谋这样通过文化部部长绕过考试直接进入学院的,算是破格录取,不算扩招。
大字报是美术系的老师写的,落款是“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部分革命教师”,质疑扩招何群的合理性,认为这是长官意志,强压下来,不公平。矛头直指上头的领导,也就是文化部。大字报不仅在电影学院贴,还在西单民主墙以及文化部的六个直属院校,包括美院、工艺美院、音乐学院等。虽然已经是“文革”之后,但是大字报的风潮还依然延续,任何人,有任何意见都可以贴大字报。贴就是为了让人看,食堂、浴室、厕所,凡是人多必去的地方,都是大字报的展示场。
“何群事件”的大字报炮火很猛,一个星期一批,贴了三四批,不少外校的同学也都看到了。“我当时如坐针毡”张艺谋说,“我太知道了,说着何群,接下来就是我了。”对于黄镇部长和学校之间的几次交流,张艺谋是2003年才得知的过程真相,当时他只知道是他写给部长的那封信对他上学起了作用。若论长官意志,张艺谋的获益不比何群更少。
“果然,我也很快上了大字报。何群就是大字报上的美术系何某,而我,就是摄影系的张某某。”张艺谋现在觉得,自己是在陪绑。主角是何群,谈着谈着把自己捎上了。张艺谋一直隐隐感受到的编外感,在这次大字报事件中得以坐实。
“我觉得很没面子,抬不起头来。”张艺谋说。进校之后的一系列刺激,让张艺谋感觉到自己和别人的知识和信息上的巨大差距,加上大字报的力量,他更沉默了。同学们都觉得无所谓,对他也很好,其中还有一些北京的同学,时不时告诉他一些秘闻、背景。“人家写大字报的没有针对我张艺谋个人,人家是针对这个现象,从他们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个不合章程录取的学生。”张艺谋说,“我没有什么好记恨的。”
张艺谋的同学张会军,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他回忆这段时,特别提到,学校是把张艺谋当作正式学生看待,摄影系所有学生享受的教学设施和待遇,完全一样。他还特别提到,张艺谋曾经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这段张艺谋一点没聊。
张艺谋原本就小心,大字报事件出来之后,“我夹着尾巴做人,好在原来就夹着,也夹惯了。”张艺谋说,“我很谨慎,什么事都付出百分百努力,不能让人家抓住我的一点把柄,觉得我不配待在这所学校。”同学张会军对张艺谋前两年的描述是,“时时处处拘谨,沉默寡言,做事,学习,说话谨小慎微”。
大字报就像头上掉了一只靴子,张艺谋大二下学期第二只靴子有了动静。1980年暑假前,教务处的沈老师、招生办的刘老师和摄影系的主任韦老师找张艺谋谈话。一开始还是肯定了张艺谋在学校的表现,以及他的专业能力,接下来话锋一转,说到他上学的特殊情况,是文化部部长特别批准,学院破格录取的。当时黄镇部长给电影学院领导小组的批示中提到:“张艺谋并不一定等四年毕业,学习一两年后就可以分配到电影厂去工作。”现在学习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可以结束学习。
张艺谋觉得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除了说明感谢学校的培养之外,还提出是否能给一个证,大专的,肄业的,什么都行。老师们说,要回去讨论一下,因为没有这个先例。
“我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也从来不抱怨。我已经很幸运了,是例外中的例外,若不然,我还在工厂拍风景,哪能有到北京来长见识的机会。有这一天很正常。”但是张艺谋很清楚,如果没有个学历证书,他回到西安做什么,哪个单位能接收他,都是说不好的事。
谈话之后,“我一天都不想在电影学院待了。人家对我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人都有自尊心,我不能再厚脸皮留下去。”张艺谋立刻给他在西安的同学张健写信,他要做好回西安的准备。
张健的父亲张毓秀是摄影界的前辈,当时在《陕西青年》杂志社任职。张艺谋跟张健说,自己可能会被学校退回,请他问问他父亲,看能不能在《陕西青年》或者其他地方给谋个职位。张艺谋破格录取在陕西是大事,很多人都知道,他大学二年级还在《中国青年报》上刊发过获奖的摄影作品,在陕西摄影界很轰动。张健回复的信息让张艺谋非常兴奋,只要你有个毕业证,不管是什么级别的,你都可以来,甚至可以把你推荐到陕西画报社去。
陕西画报社对张艺谋而言,地位崇高。虽然这些年在北京长了不少见识,但他知道,那些听起来像上书房的地方,就自己这点儿出身,这点儿名不正言不顺的身份,根本去不了。当年陕西画报社的业余通讯员到国棉八厂采访拍照,个个都很牛,背着单反哈苏相机,到处走,拍多少胶卷都给报销。张艺谋说,“我就偷偷看,有时候能鼓起勇气上去跟人套套近乎,摸摸相机。”张艺谋当年走过陕西画报社,“看见那几个字儿都哆嗦,出汗。如果能去,那太好了”。
这针强心剂打下来,张艺谋激动了:“不学了!去画报社拍照片去。什么拍电影,不弄了!”可是老师们给的答复当头泼了他一盆冷水:什么文凭都不能给。
没有文凭就去不了画报社,学校表示可以退回文化部,可是张艺谋和文化部没有半毛钱关系,文化部没有义务去安排一个当初破格录取的学生。张艺谋心灰透顶。他跟老师们说,希望自己能留在电影学院继续学习。老师们让他先写个申请,要报到文化部。
“我很苦闷,坐在宿舍,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当时就觉得,只要有个地方要我,我立刻就走。但哪儿能要我呢?”张艺谋说。关起门来写申请,愁眉紧锁,原本不用锁看起来就很愁了,现在锁上,看起来苦不堪言。两个同学郑鸣和邢树民看见了,张艺谋跟他们坦白,实在不想待了,要不就不写了,走了得了。两个同学强烈反对,他们都是在社会上工作过的人,知道文凭对于一个正式工作的重要。他们劝张艺谋,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定要写申请,争取在学校留下去,学完四年。
现在的中国也许不讲究出身,人民群众甚至更乐意听到一个教育背景残缺的天才创造的奇迹,美国乔布斯和盖茨也都可以放弃大学学习,但那时候的中国,对文凭的尊崇,是全社会的风气,也是对“文革”十年知识轻视的反动。文凭对于一个人,几乎相当于腰间的一条宽皮带,扎上它,才能底气十足迈着正步走进正经单位。
申请递交上去,让等回音。直到放假,还没有任何消息。张艺谋临走跟田壮壮说:“哥们儿这个假期走了,可能就回不了电影学院了。”整个假期张艺谋度日如年,也不能跟家里人说。他每天最怕见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来信,如果有来信,就说明他的申请被驳回。
既然没有通知,说明至少没有拒绝,张艺谋去学校,一路忐忑。
根据张会军的记载,学校7月8日收到张艺谋的申请,7月15日以正式文件形式向文化部提交报告。7月18日,学院派人去文化部汇报工作。8月1日,文化部领导做出批示:“根据学院教务处同志介绍的情况,可以让张艺谋学完四年。”这个时间,张艺谋正在家急得挠墙,他并不知道他的问题已经解决。张艺谋后来分析,有可能别人觉得他通过文化部进来,不知道是哪个路子的皇亲国戚,人家认为肯定早有人一溜小跑告诉他结果了。
到教务处签到,张艺谋紧张得心揪起来,教务处的老师也没有明说,直接让他签到了。张艺谋晕晕乎乎地隐约觉得自己的问题可能解决了,正云里雾里一通瞎分析,路上被系里的郑国恩老师叫住了。
“郑老师是唯一一个正式地把这个消息用非正式的方式通报我,勉励我的人。他自己都未必知道,那几句话对我的意义,我提了两年的心,终于落地。我们那时候和老师之间亦师亦友,直到现在,我见到郑老师都毕恭毕敬,他对我说话的神情,对我的宽慰,我不会忘记。”张艺谋说。
如果电影学院当时同意了张艺谋的请求,给一个大专毕业证,张艺谋毫不犹豫就会去陕西的某个杂志社任职,电影导演张艺谋就不会存在。如果说他还有可能跟电影有点关系,用张艺谋同事的话说,“就剩下拍电影剧照一种可能了”。
九
张艺谋骨子里是想憋着跟别人不一样的人。人无我有,人有我异,想让东西一出来就能吓人一跳,形式主义打死人。在中学当黑五类,插队时当狗崽子那会,刷标语画主席像,在内容不可能有变化的情况下,力图把尺寸做大,颜色做艳,让人立马觉得不一样。
张艺谋自己倒没这个感受。他觉得上了大学之后让他有旁顾比较的机会,才有标新立异的想法。摄影系前两年学的黑白平面摄影,对张艺谋没有什么难度。什么侧光、逆光、侧逆光、影调,已经不用从头学起。相比刚开始接触摄影的同学,张艺谋之前四年摄影的经验,让他有点余力。既然他从头学过,知道同学们的作业会往哪个方向走,干脆他就另寻他途。加上四月影会的影响,他自己拿着相机到处逛,做了不少作业之外的功课。有意识地从比较严谨的现实主义自我训练,转向形式化和风格化。
《中国姑娘》就是这么来的。这不是作业,那时候他大一,有了自主创作的意识。他想要拍一个高调的东西。大一回家,跟表妹说好,让她在班上找个长辫子的姑娘,越长越好,最好长过屁股。表妹把人带来了,人长得也不赖。从张艺谋在西安的家出来,过了小南门,就是城墙,没有遮挡,天空做背景。姑娘穿着白衬衣,表妹在旁边拉开一张白纸当反光板。拍完之后拿红墨水修了修版,最后出来和他设想的差不多,除了脸部的轮廓之外,就是一条大辫子。
这张照片后来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照片上的姑娘据说后来当了空姐。“跟这张照片有没有关系,我就不知道了。”张艺谋说。
这是张艺谋做的独特化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也不落伍。中国风的味道在,也还有处理上的特殊味道和感觉。一个大一的学生拍的东西在高级别的报纸上发表,在全班同学里面也是个特例。最近有一个外国人要写一本关于中国摄影和中国的书,还来找到张艺谋,希望拿这张照片做封面。
准备参加1980年的四月影会那会儿,除了构思出《啊,一代青年》之外,又想到,既然可以拿镜头对准一代人,干脆再做一个高调的系列,用几张静物摄影来描述自己。这也就是《我的路》。红领巾代表的儿童时代,滴着墨汁的标语表现的文革到来,草帽代表的上山下乡,扑克和烟盒代表在工厂沉闷无聊的岁月,黑纱上的小白花表现1976年“四五事件”,最后一幅用条尺圆规体现出1978年之后向学习的回归。“那个时代的人看到这些画面无需解释,谁都懂。”张艺谋说。
这个系列他并没有拿去投稿,也没有给别人看过,就是一个自主创作。那段时间虽然大字报事件已经过了,第二只靴子还没有掉下来,心里的不安虽然存在,但是该干啥干啥。
摄影专业课上布置的逆光作业,是张艺谋标新立异的另一个明证。正常的逆光作业也就是拿个石膏像,光从背面打过来。张艺谋琢磨着逆光作业可能有点搞头,在宿舍的小床上自己设计。床上放着两摞书,中间架上玻璃板。上面放三个酒杯,玻璃板撒上水,小台灯顶光照下来,调整光的调度和玻璃板上的水,最后出来诡异的光影重叠的效果,是实在的逆光,又有抽象的意味。
张艺谋的女儿非常喜欢这张作业,她在美国学导演,跟张艺谋说,今天她的同学们也未必能交出这样的作业。这份逆光作业原本张艺谋是较为满意的,女儿一夸,他更为满意了。
他这些巧思未必能得到老师的表扬,当时的老师们还是更强调基本功,顺光、逆光、侧光,先老老实实打好基础,对于张艺谋这些刻意不同的创作性作业并没有正面夸奖,只是淡淡说:“喔,这也是逆光。”放一边。
“我觉得老师们怕夸我之后把同学们给带偏了,教学大纲上鼓励的是基本功作业,不是创作性作业。”张艺谋说,“但是主课老师张益福一直给我高分,对我很器重,只是口头上不当众夸我。他把我的照片推荐给《中国摄影》的夏老师,《中国摄影》是摄影界最权威的杂志,今天依然是,我在上面发表了好几幅照片。这些老师们当时帮我都帮在关键处。”张艺谋承认,他交这类作业有点显摆的意思,不过老师没理会他的小虚荣,他有点小失落。
黑白平面摄影构图上了两年,大三开始教动态摄影,拿摄影机了。这时候身份问题刚刚解决,张艺谋说:“在上了两年学之后,我终于知道我可以以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的身份毕业了,以后可以真的做电影了,我开始认真考虑未来。”
张艺谋的同学们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大三之前的张艺谋过于拘谨,大三之后,开朗多了。这时候有人提醒张艺谋:“你在平面构图上用心太多,但是电影是运动的,你切不可让平面意识太多干扰你,否则你出不来,会走火入魔。”这句提醒对张艺谋有当头棒喝之用,他越想越觉得别人说得有道理,成也萧何败萧何,平面构图虽然是他看重的,但很有可能干预他对电影镜头的处理和把握。从1980底之后,他再不考虑创作性地摄影,直至今天。张艺谋并不容易被说服,只要是他听进去,觉得有道理,行为上立竿见影。
“我今天顶多拿相机帮人拍个照,跟创作两回事。好的数码相机我都不会用。”张艺谋说。他坚决不再碰相机,虽然有不少人觉得,平面他再做下去,一定有成就。
今天回头来看,张艺谋觉得别人提醒得很到位。回顾刚开始做摄影的几部电影,从《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到《大阅兵》,摄影构图带有强烈的平面痕迹,过强的平面意识会伤害电影的运动性,《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虽然有名,它的造型不是由运动构成的,这里面明显带有张艺谋的痕迹。“后来到了《红高粱》,一开始就颠轿、扭动、唱歌,就是要扔掉平面。”张艺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