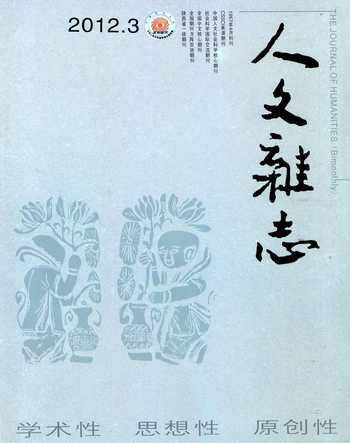竹简本《缁衣》首章补释
晁福林
郭店简和上博简皆有《缁衣》之篇,并且可以和今本《礼记·缁衣》相对读。这是研究儒家文献变迁的一个极好的材料。所以,简本甫一面世,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除了原考释者荜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以外,还有不少专家发表卓见,为简本《缁衣》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今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简本《缁衣》首章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敬请专家指正。
一、简本《缁衣》首章引诗释义
上博简和郭店简《缁衣》首章引诗情况基本一致。为讨论方便计,现将两个简文一并引录如下:
夫子曰:“好 (美)女(如)好兹(缁)衣。亚(恶)亚(恶)如恶(恶) (巷)白(伯)。”则民臧 (力)简文“臧”,是“咸”的误字。其下一字原作“”形,郭店简原考释者释为从力从它之字,裘锡圭先生说当释为“”(《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李零先生说同,并谓读为力,“是尽力、竭力的意思”(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0页)。而型(刑)不屯。诗员(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郭店简《缁衣》)荆州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17页,释文第129-132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子曰:“丑 子(好)(美)女(如)丑 子(好)纟 才(缁)衣,亚(恶)亚(恶)女(如)亚(恶)(巷)白(伯)。”则民咸 扌 力(力) 这个字原作“”形,对其上部的解释,颇多歧异。今从李零先生所释,从手从力,释为扌 力,读为力(见其所撰《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二):〈缁衣〉》,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08-409页)。而型(刑)不(蠢)。诗员(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上博简《缁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图版第45页, 释文第174-1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这两句简文,专家一般都把“缁衣”和“巷伯”作为诗篇名。这样标点的根据是今本《缁衣》确实是作为诗篇名称来用的。但是如此理解,于解释简文却有不妥之处,说喜好《缁衣》这篇诗作尚且可以,但若谓厌恶《巷伯》之诗却实难通。有鉴于此而提出卓见者是裘锡圭和彭浩先生。裘先生指出:“如简文‘恶恶如恶巷伯句‘巷伯上‘恶字非衍文,则孔子或《缁衣》编者似以为《巷伯》作者‘寺人孟子在诗中所指斥之谗人,即地位较寺人为高之奄官巷伯。” 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郭店楚简〈缁衣〉的分章及相关问题》,见《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7页)。裘先生未提简文“缁衣”的问题,并且论“巷伯”时加上一个先决条件,即那个简文“恶”字非衍文。这显然是持矜慎的态度来进行论析的。后来,彭浩先生指出“简本的‘好美者自然是作为人所喜好的朝服的‘缁衣,而非是称赞贤者郑武公的《诗·缁衣》。一字之差,意思迥然相异”。 彭浩:《郭店楚简〈缁衣〉的分章及相关问题》,见《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7页。彭先生所说的“迥然相异”是正确的,但相异在何处,却语焉不明。裘、彭两位先生虽然提出卓见,但尚未进行详细论析,今试补充讨论如下。
愚以为简文“缁衣”“巷伯”皆不当为诗篇名,这样判断的理由在于,如果说“恶巷伯”的“恶”字是衍文,那么“好缁衣”的“好”字也当是衍文。我们现在找不出理由说简文这两个字都是衍文,并且从诗本义看,这两个字也不当定为衍文。依裘、彭两位先生卓见,我们可以判断简文“缁衣”和“巷伯”皆非诗篇名,而应当是两个名词。
简文“好 (美)如好缁衣”,在《论语·子罕》篇中有一个十分接近的用例,那就是: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前人注解以为孔子此语,乃是“疾时人薄于德而厚于色”。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612页。在逻辑的排列上,此语与本简简文的“好美如好缁衣”,是一致的;只不过一是以否定(“吾未见”)来达到肯定的句式,一是直接肯定的句式。孔子之意是,如果人们喜好“德”能够像喜好女色一样,那就好了;如果人们能够像喜好缁衣那样爱美,那就好了。所蕴含的意思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喜好女色而轻于德;喜好缁衣而轻视真正的美。
二、“缁衣”之“美”与周代服饰观念
为什么会有以玄黑色的缁衣为“美”这种社会观念呢?这是我们应当探究的一个问题。
缁衣,是周代的黑色朝服。《诗·郑风·缁衣》毛传云“卿士听朝之正服”,《诗·羔裘》郑笺说是“诸侯之朝服”。缁衣与玄端相同, 玄色与缁色俱黑而稍浅,所以说“缁与玄相类,故礼家每以缁布衣为玄端也”(唐贾公彦《周礼·冬官·画缋》贾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四十,中华书局,1980年,第918页)。孙诒让说:“玄与缁同色,而深浅微别。”(《周礼正义》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第3316页)。都是自国君到士的各级贵族的正服。唐儒孔颖达说缁衣“是诸侯君臣日视朝之服”。 孔颖达:《论语正义》卷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5页。为什么周代要以缁衣为朝服呢?周代重视服色,春秋时人有“五色精心” 《国语·周语》中。之说,认为不同的颜色反映着不同的德行品格。郑玄认为,君臣服缁衣,这种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是“忠直且君”,臣下服缁衣表示着对君主的“忠直”,而国君服缁衣则“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 《诗·郑风·羔裘》郑笺。《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第340页。表现出君主的尊严。依照儒家观念,许多事物都有德的象征意义,这称为“比德”。 儒家“比德”的事物最典型者是玉和水。如《孔子家语·问玉》篇载孔子语即谓“君子比德于玉”,《大戴礼记·劝学》载孔子语“夫水者,君子比德焉”。缁衣也是被“比德”者。缁衣之色是天之色, 《周礼·考工记·画缋》“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孙诒让谓:“玄黑同色而微异,染黑,六入为玄,七入为缁,此黑即是缁,与玄对文则异,散文得通。”(《周礼正义》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第3306页。)所以黑色喻庄严之意。卿大夫服缁衣,表示对于君主的尊敬之至,并且“性行均直”,“躬行善道,至死不变”,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340、334页。所以说“德称其服”。黑色表示庄重正直,但并不鲜活亮丽。春秋时代,社会上比较喜欢用华丽悦目的红、黄、紫等色彩作为服饰的颜色。社会上的贵族服饰多有趋亮丽的倾向。就连比较守旧的鲁国也是如此。鲁桓公就是一例,本来玄冠缁衣是君臣共用的服色,但鲁桓公偏要显得亮丽些,所以文献记载“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也”。 《礼记·玉藻》。鲁桓公此举,表明喜紫之风已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他不用黑色的冠带而用紫色的。这说明社会上已经流行紫色,所以鲁桓公要时髦些。但这些并非是社会观念的主流,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依然是表示正直忠君的缁衣所示的玄黑之色。
孔子重视服饰的颜色,《论语·乡党》篇所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应当是合乎孔子本意的说法。孔子赞许正色,“恶紫之夺朱”。 《论语·阳货》。本简简文“好美如好缁衣”,说明孔子对于喻意正直、忠君的黑色是赞许的,认为好美者当像喜好缁衣那样喜好正直而庄重的黑色。这里所说的“好缁衣”,指的正是当时社会上一般士人的干禄风习,是对于从政所带来的富贵的艳羡。
再进一步想,“好美”的“美”,似乎还包括着人生之美。孔子对于天下国家的改造与发展,持积极入世的态度,在他的心目中这正是人生之美。 儒家对于“避世之士”取尊重但不赞成的态度。认为那些隐士不顾“长幼之节”和“君臣之义”,所以是不合乎“义”的。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表明孔子实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赞许缁衣,是他这种人生态度的一个表现。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社会上一般士人对于入仕干禄趋之若鹜,与孔子所持为改造社会服务于国家而入仕的态度是有差别的。本简简文所云“好缁衣”,简文意谓如果人们都像喜欢缁衣一样爱美就好了。所谓“好美”的“美”,一方面是以玄黑之色所喻指庄重严肃的色彩之美;另一方面也表示着对于积极入世的人生之美。这里的“美”,不妨理解为孔子所赞许的真正的“美”,而非世俗所趋的鲜艳之美。
三、恶人“巷伯”
我们再来看简文提到的“巷伯”,它见于《小雅·巷伯》一诗。这是一首痛斥谮谗之徒的诗。其作者在诗的末章已经言明是“寺人孟子”。前人对于诗人孟子是否即篇名“巷伯”的问题讨论甚多,毛传无说,郑笺明谓是两人,后人多不同意郑笺此说,清儒陈启源据《周礼》力辩郑笺此说为是。 陈启源说:“《周礼》‘内小臣、‘奄人而称上士,是奄官之长,故笺以巷伯当之。伯,长也。寺人无爵且属于内小臣,则奄人之卑者,故不以当伯长之称,宋之说诗者谓寺人即巷伯,已失据矣。……夫内小臣与寺人并列于《周礼·天官》属下,明是二职,岂未见之乎?”(《毛诗稽古编》,见《清经解》卷七十二,上海书店,1988年,第401页。)以后学者虽然再力辩,终不能回答陈启源提出的关键问题。毛传谓:“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将践刑,作此诗也。”这是比较可信的说法。诗人(即寺人孟子)在诗中大声疾呼:“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意谓谮谗之人实在是太坏了,把他丢弃给豺虎,豺虎都不愿意吃他。把他丢弃到蛮荒的极北之地,那里也不愿意留他。只能把他交给苍天来处置了。
此诗所斥的谗人是谁呢?
毛传解释诗中“杨园之道,猗于亩邱”之句时谓“杨园,园名。猗,加也。亩丘,丘名”,清儒胡承珙细绎毛传意,说:“谓谮人者由近而加远,由小而加大,如杨园之道而横及亩丘也。” 胡承珙:《毛诗后笺》卷十九,黄山书社,1999年,第1027页。谮人者“由近而加远”,谮害寺人孟子者当距其不远,最有可能的就是“巷伯”。巷伯之职见于《左传》襄公九年,位列司宫之后,当是奄官之首。巷伯可以上下其手、构谗谮非,诬陷报复。《后汉书·宦者传》赞谓“况乃巷职,远参天机。舞文巧态,作惠作威,凶家害国”,对于巷伯之职的重要与构谗的便利说得十分明确。寺人孟子因谗被刑,他痛恨巷伯之谮害,但又因为自己还要在巷伯手下做事,所以诗中不敢提巷伯之名,而只是构谗之徒,诗序的作者知寺人之意,所以尽管诗人无巷伯字样,但还是以“巷伯”名篇。裘锡圭先生指出《巷伯》一诗所痛斥的“谗人即地位较寺人为高之奄官巷伯”,是很正确的。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汉儒基于对《小雅·巷伯》诗旨的理解,或将“巷伯”作为受谗被刑者,例如,《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为巷伯而伤悼;《后汉书·孔融传》有“冤如巷伯”之辞。皆将巷伯作为蒙受冤曲的人物。我们今得简本《缁衣》关于“巷伯”的简文,可知汉儒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依《巷伯》之诗,应当肯定巷伯是进谗谮的恶人,而非受冤者。汉儒若鉴于此,当会为“巷伯”“正名”的吧。
要之,简本《缁衣》首简的“好 (美)如好缁衣。亚(恶)亚(恶)如恶(恶)巷伯。”意思是说,喜好美如同喜好缁衣,厌恶丑恶如同厌恶巷伯。如果我们把“缁衣”“巷伯”作为诗篇名来理解,文意就不大通顺,“美”和《缁衣》之篇没有直接的关联,“恶(丑恶)”的也不是《巷伯》之诗。如此看来,简文这两个词还是作为普通名词(而不是篇名)为优。然而,在今传本《礼记·缁衣》篇里,这两个词确乎是作为诗篇名称的,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原来,后儒在编撰此篇时已经将语意转变,并且去掉了两个动词,在今本《礼记·缁衣》篇中,这段话变作“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意即“好(喜好)”贤才如同《缁衣》诗所描写的那样,“恶(厌恶)”恶人如同《巷伯》里所写对于巷伯的痛斥一样。这样的转变,去掉了两个动词(“好”、“恶”),语意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猜想,前面提到的彭浩先生所说的“迥然相异”,大概就在乎此。
四、《缁衣》首章意蕴的变化
我们这样解释“缁衣”与“巷伯”,是否合乎简本《缁衣》首章的意蕴呢?
先来分析简本的文辞。这两个简本的文字、句式都是基本一致的。简文《缁衣》本章主旨在于证明孔子之语的正确,说明如果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将会发生的社会效果,那就是“民咸力而刑不动”。 郭简简文“屯”,上简附加有刀旁,当系羡划。“屯”,诸家或比附今本而读若试,或读若顿、惩、陈等,似皆不若《郭店楚墓竹简》原考释者读为“蠢”为优。后来刘钊先生亦释读为蠢(《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页)。按,蠢有动之意,《说文》训为“虫动也”,《尚书·大诰》“越兹蠢”,伪孔传“于此蠢动”。《尔雅·释诂》“蠢,作也”,郭注“谓动作也”。是皆可以说明屯可以读若蠢、释为动。清儒朱骏声说“屯”字可以假借为“偆”(《说文通训定声》“屯部”,中华书局,1998年,第799页)。偆意为蠢动,《白虎通·五行》“偆,动也”,《风俗通·祀典》谓“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是可为证。总之,屯可读若春之声的蠢若偆,意皆为动。“民咸力”应当是针对“好美如好缁衣”来说的,民众都去为进入统治阶层而奋斗,会尽力为君主服务。“刑不动”则是针对“恶恶如恶巷伯”来言的,民众都有憎恶谗谮小人的廉耻之心,则会奉公守法而使刑罚设而不用。本章末尾引诗“仪型文王,万邦作孚”作结,也与孔子所言的好美、恶恶之语有关系。孔子以继文王之统为己任,战国时期儒者更是把周文王奉为最著之圣人,就羞耻之心来说,孟子就有“如耻之,莫若师文王” 《孟子·离娄》上。的说法。儒家认为关乎“美”、“恶”的是非感、羞耻感十分重要,所以要搬出文王为证。
大家知道,今传本《礼记·缁衣》已经将相关内容做了重要改动,我们来探讨这个改动的情况和原因,应当是有意义的事情。先看一下今本的内容: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重要的改动有两处,一是去掉了简文两个“如”字后而的“好”与“恶”;二是将“民咸力”改为“爵不渎”;三是将“好美”改为“好贤”。愚以为这三个改动都有深意在焉。我们先说第一个。
后儒所做的更动,很明显的是去掉了两个“如”字后的“好”与“恶”。这对于疏通语意,显然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是“好贤”,那就应当如《缁衣》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来好贤,这就是今本所谓的“好贤如《缁衣》”的意思。如果不去掉“如”后的“好”字,那就成了好贤如同喜好《缁衣》一诗了,意思就显得迂曲。同样的道理,既然“恶恶”,那就应当如《巷伯》诗中所写的对于谗谮之徒的无比厌恶、痛恨。这就是今本所谓的“恶恶如恶《巷伯》”的意思。如果不去掉“如”字后的“恶”字, 那就成了恶恶如同厌恶《巷伯》之诗了,意思就很难讲通。
再说第二个改动。简本“民咸力”是说普通民众,而非专指贤才,而今本的“爵不渎”,则是针对贤才来说话的。只有“贤才”,才能够加官进爵。爵位在周代还是比较严格的,不像后世汉代那样普及泛滥,官府可以进行普遍性的赏赐,人人都唾手可得。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认为,爵位的赏赐是治国的重要手段,晋国太傅叔向曾经对执政之卿韩宣子说:“爵以建事,禄以食爵,德以赋之,功庸以称之”。 《国语·晋语》八。诸侯国君主的“好贤”是与爵制相关的。《礼记·王制》谓“爵人于朝,与士共之”,赏赐爵位是很慎重的事情,要在朝廷当着众士人的面公开举行,起到鼓舞和奖励贤才的作用。《王制》篇还说“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这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情况的反映,当时贵族的世袭制逐渐削弱,举贤才的呼声日益高涨。今本《礼记·缁衣》篇将“好美”改为“好贤”,可以说是这呼声的表现之一。在孔门弟子们看来,关键在于举贤才,把爵位给予真正的贤才,让他们据于高位来协助君主管理国家。所谓“爵不渎”,孔颖达谓即“爵不滥”的意思,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卷5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01页。只有把真正的贤才选拔上来,爵位的赏赐才不会滥而不当。
再说另一个更动。《缁衣》本来是一首赠衣诗, 《郑风·缁衣》一诗自毛传郑笺开始,一直被作为君主关心大臣的诗,或者是假托君主好贤的诗。当代学者或据此诗本义作出正确说明,认为是贵族妇女为丈夫改衣授粲的赠衣诗(闻一多:《风诗类钞乙》,见《闻一多全集》第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7页;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219-220页)。因为诗中有“好贤”的字样 ,所以历来的解诗者多据此而言诗义。今得简本《礼记·缁衣》为证,可以推测,在较早的诗经解释里,如孔子到子思时期的儒者,确是将《缁衣》一诗作为赠衣诗来理解的。其原来的意思是好美要如同喜好缁衣那样,厌恶丑恶要向厌恶巷伯那样。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可以将《郑风·缁衣》这首小而短的诗作具引如下: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这首小诗,可以意译如下:
缁衣多么合适呀!破旧了,我就再做一件。我到你的公馆[拿回旧的]。归来时,我会将一件粲粲的新衣送到你的手里。 《缁衣》诗的“粲”意当与《小雅·大东》“粲粲衣服”相同,毛传“粲粲,鲜盛貌”,是准确的。自毛传以来,后儒多释授粲之粲为餐,指精美饭食。从《缁衣》诗意看,“粲”,以释为鲜盛美观的衣服较优。
缁衣多么好看呀!破旧了,我就再做一件。我到你的公馆[拿回旧的]。归来时,我会将一件粲粲的新衣送到你的手里。
缁衣多么大方呀!破旧了,我就再做一件。我到你的公馆[拿回旧的]。归来时,我会将一件粲粲的新衣送到你的手里。
从《缁衣》中,可以看到诗的主人公对于缁衣的喜好之情,所以对缁衣有“宜兮”、“好兮”、“蓆兮”之叹美。 关于《缁衣》诗“缁衣之蓆兮”的解释,一般认为与前两章的“宜”、“好”同为赞美之辞,指宽大。独清儒陈奂谓与“宜”“好”“不同义”(《诗毛氏传疏》,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60页)。按陈氏此说不确。《说文》以“广多”训蓆,在诗中蓆当指缁衣宽大得宜,亦美也。从主人公的口吻看,应当是那位穿缁衣者的妻子。在诗中,缁衣所喻指的状态(“宜”、“好”、“蓆”)皆当为“美”,而非“贤”。后儒泥于《郑风》皆写郑国君主之事,所以把此诗意蕴理解为君主的善善好贤,今本《礼记·缁衣》此章就将“好美”,更动为“好贤”。这个更动的社会背景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招纳贤才,“贤”(而非“贵”)的影响日增,社会需要一首敬重贤才的诗作,而将《郑风·缁衣》诗旨的理解稍加更动就可以适应了这一社会思想的需求。我们可以说,简本的“好美”,是对于《郑风·缁衣》的本义的释解;今本的“好贤”是对于它的引伸义的演绎。孔子和他的及门弟子是以诗本义为基础来说诗的,所以强调“好美”。编撰《礼记·缁衣》的儒者, 据南北朝时期沈约所说,《缁衣》出自孔子之孙子思之手(说见《隋书·音乐志》)。若此说可信的话,那么《缁衣》的写定时间距离孔子之世已有近百年的时间。没有墨守师说而加以稍许的更动,将“好美”改为“好贤”,适应了社会思想发展的需要。从简本到今本的一字之更的后面,原来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与思想变迁的背景。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