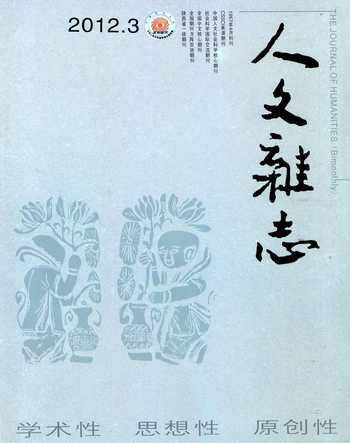“物”的多重面相
鲍永玲
中国古典思想中“物”的用法似乎不难理解,引申常用词有“万物”、“生物”、“事物”等。“物”的英译是“thing”,德译是“das Ding”,似乎也简单明了、并无疑义。倘若我们查索“物”在中国现代哲学范畴史中的位置,不难发现,它始终处于较为边缘的状态。如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等, 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物”的分析基本集中于对“道器”、“心物”和“格物致知”等问题的附带论述中。然而,西方学者则敏锐地指出,在“things”和“物”之间,存在着近代西方范畴化模式与古代中国人的根本区别。艾兰认为,对“物”的几个现有译法都不合适,如“creatures”将物只限定于动物的生命,“things”的原始意义是指无生命的客体,而“living things”似乎也是个误导,因为它在我们心中设置了生物与非生物的对立。 [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张海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9-110页。
单提“物”字,并且从文字的源头重新发问“何谓物”凸显出重新探索人类古老智慧的必要性。在这里已有先例可循,海德格尔曾指出,人们必须重新发问:“何谓物”,“何谓物性(die Dingheit)?”他在其名篇《物》(Das Ding, 1950)中,也曾追溯古高地德语的“thing”和“dinc”实际上是指“聚集”,它将天、地、神、人汇聚在一起,即人在“物”中与天、地、神相接触,使它们彼此趋近、相互映射,共同构成“世界”(Welt)。拉丁语的“res”指那些相关于人的事件和情形,这些含义仍然部分地保留在德语“Ding”和英语“thing”中;只是,本常用于说明“res”的“causa”这个词,在被译成“Ursache” (原因)之后,却被强加了因果性的意味。 M. Heidegger, Das Ding“, in: Vortr|ge und Aufs|tze (Gesamtausgabe, Band 7),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0, S. 177. 海德格尔对“物”的关注是非常显著的,《存在与时间》(1927)、《什么是物》(1931)、《技术的追问》(1950)和《物》(1950)等作品都体现出他对“物”的关注,“物”成为众多追问的基础:如《存在与时间》中的“锤子”、“话筒”,《技术的追问》中“圣杯”,《筑·居·思》的“桥”,《物》的“壶”都是海德格尔所钟爱之“物”。但从本文分析可看出,如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然生长物”和“人工制造物”,二者可勉强对应于“物”、“器”之分,“锤子”、“话筒”、“圣杯”、“壶”等皆属“器”也。杨庆峰、闫宏秀在《多领域中的物转向及其本质》(《哲学分析》2011年第1期)一文指出,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生存哲学和现象学都存在一个“物”的转向,它可看作是对传统语言学转向的回应;凌继尧在《物的意义的生成》(《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借用鲍德里亚的“物的意义”理论,指出工业设计使人置于封闭的、环环相套器物圈的圆心。这里的“物”,实际上都指的是人工制作的“器具”、“器物”,不是自然形成的“生长物”。“物”、“器”在现代语境里的混淆,显示西方表象式的迷误也深刻地侵入了汉语思维。在这样的几重转译之后,人类对“物”和“自然”之始源富有智慧的理解,被表象性、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所湮没了。由此,“物”在现代语境里被解释为属性的实体和承担者,感知多样性的统一,或者赋形的质料。
我们如何打破这种表象性的迷误?在近代东亚语境里,汉语“物”和英语“thing”对译之后,“物”也逐渐被单向度强化为主客对立关系里的“外物”、“对象”,它从汉语文字源头所蕴涵的独特智慧和丰富的多重面相被渐渐遗忘。 如现代汉语学者解《名实论》开篇:“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冯友兰先生解:“物为占空间时间中之位置者,即现在哲学中所谓具体的个体也。”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劳思光先生解“指物”时亦指出:“所谓‘物,则指具体对象,即表个别事物。”参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但如艾兰所指出,古汉语中的“物”,实际上以植物生长和再生为原型,却包含了水火、矿石、风气、植物、动物、人类等一切万事万物。只有以植物生长和再生的隐喻为根基,“物”的一系列思想簇群,如庄子的“物化”、儒家的“成物”、宋明理学的著名话头“万物一体之仁”才可得到恰当理解。同时,如陈淳《北溪字义》卷上“命”条所云:“人物合论,同是一气”、“人气通明,物气壅塞”,“气”论乃是中国古代“物化”、“与物同体”思想的本体论基础。但要一一描勒出“物”在古典汉语语境里的“多重面相”,词源学考察和细致的文本分析,则是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
一、“物”之三训
《说文》: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玉篇》:凡生天地之间皆谓物也。《易·乾卦》:品物流形。又《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又《玉篇》:事也。《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疏:物,事也。《礼·哀公问》: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注:物犹事也。
《周礼·春官·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注:谓毛色也。又《夏官·校人》:凡军事,物马而颁之。疏:物即是色。《楚语》:毛以示物。又《周礼·地官·廾人》: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注:物地占其形色知咸淡也。草人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左传·昭三十二年》:物土方。《注》: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
又《玉篇》:类也。《左传·桓六年》:丁卯,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注:物,类也。谓同日。 张玉书等,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651页。
《康熙字典》收“物”之上述列释有三个指向。首先,“物”来自“勿”,而“勿”最初的含义,可能与“刎”(区分开来)有关系。据考证,在华夏文化的早期,“白”色和“勿”色可能分化得最早:“白”包括所有浅色,“勿”包括所有深色(或杂色,如赤、黄、青等)。接着,“黑”被放到色谱末端,代表最深的颜色。 郭静云:《幽玄之谜:商周时期表达青色的字汇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而“物”这个字,“勿牛”,裘锡圭认为这可能是“杂色牛”,商人祭祖礼常用的一种祭牲。因为同时被使用的,其实还有“勿马”、“勿牡”之类。王元化先生亦指出,按照王国维《释物篇》:“古者谓杂帛为物,盖由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帛。”即“物”的本义其实不是“万物”,而是“杂色牛”,“推之以名杂帛,后更因以名万有不齐之庶物。因此,万物乃物字的引申义。”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故上引《康熙字典》诸条释里“物”亦指鸡牲、牛马的“毛色”,或“土色”,或“云色”, 《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郑玄注:“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孙诒让《正义》:“凡物各有形色,故天之云色,地之土色,牲之毛色,通谓之物。”或引为“类别”之义,其实都是“分辨义”。还可引申为动词观察、区分,如“物色”。 汪涛:《殷人的颜色观念与五行说的形成与发展》,见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但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物色”指自然事物富于生命感的外在形貌:“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人谁获安?” 《庄子·达生》云:“凡有貌相声色者,皆物也。”“物”所具的这些意思,正是因为“物”有“形色”,“形”、“体”、“色”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区隔和界限之分。《齐物论》所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更清晰地指示出人类语言的称谓能力使“物”在混沌中呼之欲出而区别于他物。
其次,“物”绝非现代意义上理解的那种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具有“生生”、“生成”的过程义。“物”当然不仅仅是指那些繁衍滋生的草木动物,石头、气、火之类都包括在内,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内含φυσιζ之创生的一切自然生长物,故“凡生天地之间,皆谓物也”。从这个意义上,万物之生乃是“Ereignis”的绽出,“物即事也”。 海德格尔在《路标》里花了大篇笔墨来讨论的physis,尤其是“论φυσιζ的本质和概念。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这篇长文。参见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若以庄子的观点来看,“通天下一气”(《知北游》)、“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至乐》),气凝聚而生人生物,体坏形散之后,复返天地之一气;死事与生事,不过是气的聚散变化而已,故《文心雕龙·物色篇》亦云:“枢机相通,则物无隐貌”。
最后,“品物流形”是指既然有“物”,就有“形状”和“秩序”,“万物以形相生”(《庄子·知北游》)。如张载说:“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正蒙·动物篇》)也可以说,“成物”就是“(他)赋形”、“(自)践形”的过程,故《礼记·哀公问》:“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这里所说“流形”、“生物”,显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强调自然创生性;但又可以稍加分辨。如亚氏分“物”为“制作物”和“生长物”,中国思想里则分为“物”和“器”。亚氏认为“制作物”并非按照φυσιζ的涌现产生,而是按照逻辑规律等制作而成。这里显然将人造物(器)纳入一种比“生长物”还要次等,即摹仿之摹仿的位置,这一思想后来颇具主流位置。
但在中国思想里,“物”、“器”关系具有一种复杂性。如对应亚氏“(广义)生长物”,是老子的“万物并作”或孔子的“百物生焉”;对应“制作物”的则是“器”,如老子所说“朴散则为器”(第二十八章),或《玉篇》引《老子》曰:“璞散则为器”。“朴”乃未斫之原木,或王充云:“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论衡·量知》);“璞”则是未理之玉石。所以,“器”的特点其实亦是从“块然”而有所赋形和成形。对待“器”的看法,儒道颇有些差异,如老子“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第二十八章),庄子所说混沌被凿七窍而死的故事,都是反对人工赋形而“起伪”。孔子则夸赞子贡为贵重的礼器“瑚琏”,又说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当然,这里“不器”的意思应是,君子更有其他的大用,不仅仅限于“器”的具体作用上。甚至我们现在还常常可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父母高辈痛心责备子女道:“不成器啊!”都显示了“器”须人工陶冶、养成。可见,一般而言“物”指自然成形,也可指事;“器”则是人工赋形,且“物”乃以自身长成为目的,而“器”以其用为目的。不过,“器”的含义在《易传》里有了些许变化,如《易·系辞》:“形乃谓之器。”王弼注:“成形曰器。”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何不用“物”来定义“形而下者”,却用“器”来定义?可能还是因为“物”有“事”义, 阳明那里的“意之所在为物”,也不是说成“意之所在为器”。这里的“物”,就被阳明训为“事”。当然,阳明对“格物”,以“正心”为“格”的解释也不一定合于《大学》原本。考察《大学》释“物”不多,其用法近于《中庸》,亦是“物”“知”对举,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尽道矣。”劳思光先生认为,这里的“物”和“事”互训,指的都是工夫的“对象”,即下文的“意、心、身、家、国、天下”等。见劳思光:《大学中庸译注新编》,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第7页。但要从“本末”这个常常形容草木的意象来看,“格”也许可以理解为“树高长枝”,而“来”、而“至”,而“止”。且“(万)物”(万事)多以自生自灭、复归其根为目的;而“器”,却暗含了一种以“朴(璞)散”而成为“他物”,即工具化、实体化的倾向。
这也说明,《易传》里的形而下世界是一种“下学”,即人所居有的“器”之世界。在宋明理学里,“气”也被认为是“器”,这里气显然隐涵了“气”亦以化生万物为目的。王船山所谓“盈天地之间皆器也”,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8年,第1026页。乃是以道、器、物为“气”的不同面相,即“统此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而成。”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427页。这是发展了朱熹的观点:“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引自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936页。在他这里,传统的“道”、“器”不过是指“物之道器”,即“物兼道器”。换言之,“道”、“器”乃是“物”的两种属性,谈“道”、“器”关系实际上是论“物”的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 李秀娟:《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船山学刊》2009年第1期。异曲同工的是清代诗论家叶燮论“物”的三要素“理”、“事”、“情”:“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者,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一木一草”乃是“物”,将“理”、“事”、“情”统于一身。可见,早期儒道对“物”、“器”看法有不一致,亦有融合、变迁和交错,但在价值论上对“器”却并无贬低。因为重要的是,“器”也须顺自然天性而造成,乃是“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易·无妄》)的产物,却并不强调亚里士多德所指“人工制作物”的摹仿之摹仿特性。
二、生生物化
考究一下先秦的哲学史,会发现,有趣的是早期道家非常重视“物”(万物)的意象,而儒家却要次之。例如《论语》中“(百)物”仅出现了一次: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孟子中“物”二十二见, 据杨泽波先生的考证,物在《孟子》二十二见,主要含义有二:一是物品、物件。如“物皆然,心为甚”;“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夫物则亦有然者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流水之为物也”。二是事情、事物,即牟宗三说的“行为物”,如“既不能令,又不能命,是绝物也”;“此物奚宜至哉”,“舜明于庶物”,“故有物必有则”;“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参见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81页。“生物”连用多次,如:“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物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滕文公上》)“流水”也被称为“物”,或许因“流水”有“不盈科不行”的天然秩序:“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尽心上》)孟子还首开“心”“物”对举的用法,如:“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梁惠王上》)“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并比《中庸》更早地将“己”“物”并提:“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总的说来,孔孟对“物”字的探讨比较寡淡和平常,也没有更多地将“物”上升到生机勃勃之宇宙论层面上加以讨论。但《孟子·尽心上》提出了一个崭新命题:“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里将“万物皆备于我”和“乐”的境界、“反身而诚”的工夫、 “仁”的生命情感放在一起讨论,但“万物一体”与“仁”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
反观老庄,“(万)物”在其思想体系中,与“道”、“德”、“命”等词语相互渗透、共鸣,其内涵极具生命力,其画面极具感染力。 有学者考证,《庄子》中“物”字出现202次,复合词“万物”出现了100次。参见张京华:《说新道家》,《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如老子:“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八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十六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为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三十四章)“道者万物之奥”(六十二章),“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干。故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细,生之徒也。”(七十六章)可见,老子的“(万)物”图景描绘了一切天然生之、长成的草木历程。它们的种子必须在适当的季节和环境中发芽,而不是在背“时”的情况下。借助水气的滋润、渗透,种子在土中发芽、柔脆茎叶渐渐绽露、舒放花蕾、落下果实,枯萎而归根……这样有秩序“常道”,却不是恒常(canstant),而是包含一系列的变化和痕迹;不是ruhig(安静的),却是大音希声的“Stillness”。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变化中也有消逝,消逝中也有变化。”
从上而言,在老子,“人”只不过以一茎之身而厕身于“芸芸万物”之中,故描写草木萌生时的柔弱微细,枯萎时的坚强枯干,完全也适用于描写“人”。相映成趣的是,孔子对“天何言哉,万物生焉”的赞叹,亦显示出忘我的对宇宙之生生不息的静观。然而,在孟子处,虽仍将“德之端”形容为“易生之物”的萌芽,但所谓“正己而物正”、“万物皆备于我”,都显示出一种己身从“物”疏离、对待的倾向。作为对比,不妨再看一下庄子,我们就会发现,在孔子和老子非常清新质朴“万物静静生长、凋谢”的画面,在庄子这里要复杂、斑驳得多。
一是在老子的“(万、生)物”意义上用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逍遥游》)这里的“物”、“生物”、“万物”等,都可理解成大道流行而产生的“自然之物”,人、动植物乃至山石河流等都可涵括在内。“许由曰:‘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大宗师》)“物”是“天地覆载刻雕众形”,但庄子在此却并无如混沌被凿七窍而死的贬低,而是颇有赞美之情。这种赞美之情,或许是因为“物”乃自然生成,而非“器”那般是人工造就的。
二是在进一步抽象的“道”论意义上用的。“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大宗师》)“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德充符》)总体来说,庄子对由“生生”之“道”产生的“自然物”,基本持亲近态度。“道无终始,物有死生”(《秋水》),人与物乃是浑然一体共振于混沌之气中,“显形”短暂而生的“自然物”本身就崭露为意义。但同时,随着语言的发达,“物”抽象到一定程度而多指涉贵贱、荣辱、善恶、是非、曲直等名利道德的无形“人为之物”时,庄子就多有排斥之意,如“物累”(《刻意》)、“丧己于物”(《缮性》)等提法。
如此,庄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物物”、“物际”、“物累”和“物化”思想。它们体现出《庄子》里“物”论的多向度和复杂性。 参见顾文炳:《庄子思维模式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59-62页。(1)“物物”明“道”的主导功能,说明“物”的一体性、多层次和相互联系性,如《知北游》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己。”(2)“物际”明“物”之极限和相互的分际性:“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知北游》)(3)“物累”(《刻意》)指出“物”对人心会有引惑。(4)“物化”则强调“气”之本体的流动性,使死生无际、道物无际:“物化”一词依次见于《齐物论》、《天地》、《天道》、《达生》和《则阳》篇,意味都稍有不同。如《齐物论》讲述庄周梦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郭象在《庄子注》中解释为“死生之变”,成玄英疏为“物理之变化”,陈鼓应先生将其解释为“物我界限之消解,万物融化为一”。《则阳》篇则说:“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阖尝舍之!”其实若从“环”的角度来看,“始卒若环”的万物流变却是生生灭灭,“无终无始,无几无时”,“化”是自然而然的生命历程。 《老子》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亦静,天下将自正。”故《寓言》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如此,“以道观之”,“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 (《天道》),自然会获得“至乐”的生命体验。
“化”点出了“物”之为物的重要特性,即无论是草木,还是土石,都有自己生长、形成的“历史”,“物”有悠久的训为“事”的传统,而“事”和“史”在古文字中恰恰是互训的关系。它们指向一个正在生成的、活生生的世界,就如同里尔克所说:“只有物能向我言说。罗丹的物,哥特式教堂上的物,古代的物,——所有完美的物。它们将我指向它们的原本,指向运动中的、活生生的世界,简单的、不加解释的,作为通往物的契机。” R. M. Rilke: “Brief an Lou Andreas-Salomé”, 8. August 1903, in R. M. Rilke, Ruth Sieber-Rilke u. Carl Sieber (hrsg.): Briefe aus den Jahren 1902 bis 1906, Leipzig: Insel Verlag, 1929, S. 117.孔子曾经赞叹:“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正是春夏秋冬的四时流转,寒来暑去,“雷以动之,风以散之”,大雁南飞、鳜鱼回游,这些才形成了真正丰盈的时间和历史,而非那些苍白、线性、带有刻度的物理时间铸就了历史。
《礼记·月令》更是提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某日立夏,盛德在火”;“某日立秋,盛德在金”;“某日立冬,盛德在水”。这些日子仿佛因此而变得无比丰盈、成熟,如同“德”的含义,善美、正大、光明、纯懿。这些物,金木水火也随着变得丰盈无比,以致整个自然界都充溢着它们的意象,而在那一天成了自然界狂欢的节日。《中庸》赞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又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圣人”的职责正是“发育万物”,使“万物”各自达致生命灵性的顶点,直至“盛德”。这一目标在儒家看来,只有借助“成己”与“成物”才可实现。
三、“物”之成、序、位、格
若深入分析《庄子·逍遥游》里“樗”以及《达生》里“蹈水之道”的对话,就可知庄子已有意凸显两种自然观间的矛盾——如前者,惠子对“樗”抱持世俗的实用功利主义态度,“物”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并无独立意义;庄子则从“大道流行”角度认为“物”之涌现本身就是意义。后者,孔子代表知性立场,人与物乃是驾驭与被驾驭的主客分化的关系;吕梁丈夫却以“蹈水”实践证明“人”与“物”本就是浑然一体的亲缘关系。 王焱:《庄子道境中的物:以庄书中的两段对话为切入点》,《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这两种自然观的矛盾和理解上的复杂性,是由人类智性本身发展趋于抽象所决定的。如《荀子·正名》里的“物”仅是“大共名”:“万物虽众,又是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人”在斑斓万物、气象流转的图象里被凸显为中心和主体,“物”则逐渐推远、抽象为“外物”和“名词”,这种源初神秘的同根相生、共振性在常人、世俗间被渐渐遗忘。
本来,初民认为“物”“人”都为天地生成、同声共气而相互感应,故有“物感”说;其神秘性又使人敬畏和恐惧,故有“拜物”说;但人对物源初的依赖性,使人又有了《左传》、《周礼》所谓“官物”、“材物”之需要。如此,管理、裁制“物”的意识逐渐强化,“制物”、“胜物”在《荀子》、《韩非子》里反复出现,“役物”而不为“物所役”渐成焦点。在此背景下,庄子用“樗”和“蹈水之道”的故事,凸显了两种“物”观的矛盾。原始儒家对时代的这一困境和矛盾也并非没有反思,所谓“成物”(《中庸》)、“序物”(《乐记》)、“位物”(《易传》)、“格物”(《大学》)等,都是儒家对此提出的应对方法,以下分殊之。
《中庸》二十五章指出:“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成己”乃是人的自“践形”,“成物”则是“辅助万物”,使万物的本性真实完整地显露和实现:“成己”是“尽己之性”,“成物”是“尽物之性”,二者的根基皆出于“诚”。《中庸》里提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又说“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这些说明了“至德”、“盛德”和“诚”之间有着联系,正是“诚”才使“物”完满地、自由地生成,各得其所、各安其生,使道周流无蔽而达到生命完美的最高度。所以,“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其实就是“自成”,朱熹释“诚”为“自然无妄”(《朱子语类·性理三》),或“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朱子语类·中庸三》)因为“自诚明,谓之性”,“物”能够不受人力干涉而自然、自由地生长,显示自己的“天命之性”,也就展现了“天地至诚”。而“成物”的实现,就是让禽兽、昆虫、草木等万物自然、自由地成长,使其天赋本性真实完整地显露和实现,即“因物成就而各得其当”、“全其形而遂其宜”。
对“诚”的这种强调,使人与物不至于从源初状态上就疏离开来,亦使人在处理与万物的关系中不至于僭越过多,而是致力于“参赞天地”。因此,《中庸》和二程等倾向于把“成物”看成圣人、仁者的德行,《易传》、荀子和朱熹等把“成物”看成君主、君子的责任和义务。 杨胜良:《论儒家“成物”思想》,《孔子研究》2009年第3期。如春秋时史伯指出,“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舜、上祖、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大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他们都可使万物乐生、各得其所,使其后代地位显赫而得天下。但史伯认为当时周室因“去和而取同”不能“成百物”而衰落(《国语·郑语》),故指出“成物”乃是“达己”、“成己”的前提。但实际上,儒家的“成物”更近于理想而非现实,即使是荀子说“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仍然回到了“裁制万物”的老路上。
在“心”“物”区分的格局下,“物”已被推远,“成物”是发挥人的智性以认识和辅助万物。朱子将“赞天地之化育”解为“赞助”:“人在天地中间……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种必用人;水能润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炊物,而薪炊必用人。裁成辅相,须是人做,非赞助而何?”(《朱子语类·中庸三》)而人能“赞助天地”,首先必然要以理性的认识和实践为前提。除此设想外,古人也试图用人文、礼乐驯化“物”,如《乐记》所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通过“乐和同,礼别异”,外在被推远的“物”又被重新组织到社会伦理和文化的秩序里。
“物”不再因其自在的野蛮性而使人们“拜物”,而是以“比德”、“寄托”、“抒情言志”等手法使礼乐文化更加可感、亲切。所谓“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在看似纷繁杂乱的事物态势里,儒家试图寻觅出一种出自主体心灵的和谐感、整体感和秩序感。“礼也者……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这一点也很清楚地体现在张载对“天秩”和“礼”的思考里:“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正蒙·动物》)“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经学理窟·礼乐》)在这里,张载将“天秩”与“礼”几乎相等同了。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礼作然后万事安”(《礼记·郊特牲》),在“礼”的框架里,“事”和“物”常常通用。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六“致知”条所云:“君臣父子国人之文,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朱熹亦说:“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朱子语类》卷五十七)这是因为“物”在礼乐文化的浸淫下已经更多地吸纳进“事”和“史”所具有的“职责”涵义, “事”字的古文由三个部分构成:“又”代表手,拿了“屮”(即古文字“草”初文),代表种植的作物,插进“口”中,“口”代表土地上挖的孔穴。由此,“事”的本义是“农事”的“事”,象种植之形。它抽象引申为“事业”、“事情”、“事物”的“事”后,另造形声字的“莳”代表它的本义。其实,在甲骨文中“事”和“史”、“吏”、“使”完全是一个字,后来才分化为不同的字。参见臧克和:《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4页。“事”与“史、吏、使”的关系从《说文解字》的解释里也能看出,如“事,职也。从史,之省声。” 另《韵会》:仕吏切,大曰政,小曰事。《广韵》:“使也,立也,由也。”若将“物”训为“事”,则“物”也必然将吸纳一定的“职责”意味在内。即要求别异、正位、成序:“礼以定伦,德以叙位”(《荀子·致士》)。“物-事”既被“礼”收摄、又被“礼”归约,其结果是对“物-事”提出了“位”的要求。“万物莫不位矣”,“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赞叹皆显现出文教制度对物-事的人类伦序要求,在《易传》里这点体现得尤其显著,这也是周初以来人文理性和礼乐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姜勇:《“物”的上古文化意涵:以〈易传〉为中心的观念考察》,《华夏文化论坛》2007年。
除了“成物”、“序物”、“位物”,“格物”观亦反映着“物”在先秦时的复杂内涵和多重面相。回溯“格物”观最初产生的语境,可知其亦是原始儒家面对两种“物”观的矛盾和困境提出的应对方法。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云:“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孟子虽已将心物对举、己物并提,但在这里,“物”更须人们的警惕,它是伫立于人性对面的客体、对象,它牵引和诱惑着人性之好恶的产生。“物”在此不再与人同根共源,而是近似于异类和他者,人性被动地受着物的牵引,不可避免地产生众多欲望、迷惑和好恶。就如《礼记·乐记》所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在当时,老庄和原始儒家无疑都意识到了“物”的这一危机,但却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如庄子提出“无物累”(《刻意》)境界,避免“丧己于物”(《缮性》)。从此路径发展下去,就可理解晋人葛洪《抱朴子》为何强调人不要为“物”所拘制,而是要掌握“物”“理”变化和借助“神物”来增强人的生命:“能知要道者,无欲于物”,“不以外物汩其至精……常无心于众烦,而未始与物杂”,“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
作为原始儒家经典的《大学》则明确地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目标,必须落实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渐进的过程里。其中最为重要、最为模糊和争讼最多的即是初始阶段的“格物”、“致知”二条目。明末刘蕺山曾就此指出:“格物之说,古今聚讼者有七十二家。” 戴琏章、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册,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第771页。其争议最大者,一是朱熹《大学章句》另补“格物致知传”,二是阳明《大学古本旁释》认为“格致”未尝缺传。作为现代研究者,我们亦很难准确复原《大学》里原始“格物”说究竟是何涵义。但综观宋明理学家如二程、朱熹、王阳明、王心斋、罗近溪、刘蕺山等的义理辨疏,他们对“格物”说里“物”的诠释与理解其实多有偏离古义,但这里也不妨看作是对“物”之多重面相又一重华丽的中古时代折射而加以考辨。
朱熹定《大学》为学者入德之门,认为其要全在“格物”,释“格”为“至”,谓“物”为“犹事”,并为“格物致知”提出两个前提,即:“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这种“求理”的自信心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二程,如“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如此,“格物”即“致知”,“凡天下之物以扩充吾心之知识”,这种求理于物的外向工夫,更重要的乃是强调人、物关系上的智性桥梁。阳明虽据此批评朱子格物论乃是求理于外、舍本求末、遗内逐外的义外之学,却在将“物”释为“事”时有相似之处。依阳明“格物”基本义有二:(1)“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2)“物”者“意之用”,“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如此,“格物”并非“即物穷理”和“扩充知识”,而是“致吾人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这更强调祛除物欲、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同时“物”也完全被收摄到了具有伦理人文性的“事”内。一方面,这种解释符合“物”与“事”、“史”通的古义,另一方面万物与人之间神秘的同生共源、共振联系,通过阳明融会《易传》“气”之“感通”思想而提出“万物一体之仁”又被重新发掘了。
阳明后学王心斋的“淮南格物”则有新见,释“格”为“絜矩”、“格式”,“物”为由本至末、无所不包。心斋将《大学》“格物”与“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解释相打通,以“身”为“物之本”,以“家、国、天下”为“物之末”,建构起一套以“安身立本”为特质的格物说。“身”的观念,在这里较诸“心、意、知、物”这一系列概念更具根本性的地位,也使“视天下为一人”、“大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更易理解。他的这些见解深刻地影响到了罗近溪和刘蕺山。如近溪说:“我身以万物而为体,万物以我身而为用”(《近溪子集·数》),“概天下而举之,大物也。举天下之物而身之,大本也。身本天下之物而先之,大学也。”(《一贯编·大学》)他的“知格功夫”(《一贯编·四书总论》)将“格物”与“致知”相联系,“致知”的对象是“物之格”,即事物的本末先后,而“致知”的结果则是“物格”。蕺山将“格物”之“物”解释为“良知之真条理”、“至善”、“独体”、“意根”、“无物之物”,认为“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完全将“物”内化。同时,为避免由此带来的“便内遣外”倾向,他通过“理一分殊”、“体用一源”、“万物一体”的方式,贯通了内在道德本体(“物”)与外在道德活动(“身、家、国、天下”)的关系。 参见吴震:《王心斋“淮南格物”说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世昌:《罗近溪的“格物”说:从“格物”之悟谈起》,《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高海波:《试论刘宗周的“格物”思想》,《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3期。
从朱子到王阳明、王心斋、罗近溪、刘宗周等,对《大学》的诠释表现为由“格物”到“致知”、“诚意”的重心转换。这一方面表明宋明理学道德实践和理论辨疏在趋于深化、精微,从另一方面来看,对“格物”之“物”的种种诠解也未免渐渐流于生硬而略有牵强附会。故朱熹释“格”为“至”,杨慈湖释为“去”,阳明释为“正”,心斋释为“格式”,罗念庵释为“感通”……对“格”的解释虽然各个不同,终究还是因为“物”字的下落有些不实在的缘故。
四、与物同体
上古时期“物”的多重面相里虽然折射出抽象化、对立化的倾向,但它在学者们的警惕下始终有被消隐的态势。一方面,“物”通过“礼”之定位,被收摄、归约到与人的活动同节奏、共秩序,如《礼记·礼器》所云:“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鬼神飨德”。在“物无不怀仁”的前提下,孔子的忠恕之仁道可以推己及人、推己及物,成就“万物同体”的伦理宇宙秩序。 如东汉《白虎通义·乡射》论“射礼”,这里正体现了一种“推己及物”:“夫所以亲射何?助阳气,达万物也。春气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达者,夫射自内发外,贯坚入刚,象物之生,故以射达之也。” 另一方面,真正对“物-人”同体不分、伦序共建起奠基作用的,还是《易传》以“气”、“生”为根基的“感-通”思想。 姜勇:《“物”的上古文化意涵:以〈易传〉为中心的观念考察》,《华夏文化论坛》2007年;贡华南:《味与味道》第二篇 “感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孟子·尽心上》就已提出了一个崭新命题:“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里将“万物皆备于我”和“乐”的境界、“反身而诚”的工夫、 “仁”的生命情感放在一起讨论,但“万物一体”与“仁”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儒家强调“推”法,此思路似乎影响到《庄子》外篇的《天道》:“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然而,恕仁之道毕竟是推己及人、推己及物,从“我”“推”扩开去,似乎造成只以“我”为中心的宇宙观。这个“推”字,至少对于物,只能是单向的,这里的“仁”就并不是本体意义上共通共振的“仁”。“仁”的意义本来不限于“推”,“推”只是一种内在工夫而并不即是“仁”本身。另外,《庄子》那里已经凸显了“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逍遥游》云:“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后来石门慈照禅师进一步提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同根”在这里殊为重要:不是同根,自然无法从人外推至天下万物;基于同根,天下之万象万物皆可收摄为一。这点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得到极大发挥,并最终成就直至现代新儒家仍然极为重要的核心“万物一体之仁”。 陈荣捷先生指出:“万物一体之理论,为宋明理学之中心。由二程经过朱子陆象山以至于王阳明,莫不言之,而阳明之说此观念与仁之关系,最为直接。”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在这样的思想体系里,人在万物中的独特地位巧妙地通过老庄“灵明”概念来突出,而万物与“道”水乳交融的关联则以《易传》“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来打通。
薛瑄对“心”、“物”和“理”的关系提出了有趣的比喻:“理如日月之光,大小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则光在物,物尽则光在光。”(《明儒学案》卷七《河东学案》)陈淳则说:“人气通明,物气壅塞”。这些譬喻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一个源泉(光或者气)出发,都可指向阳明所说的:“天地万物”乃“同此一气,彼此相通”。同时,光与气“通明”与否,更指示出人是否具有万物之灵的地位。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传习录》里的著名答问:
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请问。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传习录下》)
相似的一则阐述是: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传习录下》)
“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这是“万物一体之仁”总是息息相通、互相共振的缘由。这种“气”的流通、共振被称为“仁”;而“感通”正好指往来周流,既无僵固方向,又不受范围的限制。“仁”作为人际、物际之感通,由此建立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与他人、物(哪怕是草木、瓦石),其实原本就都处在声气相通的“共通体”之中。在此,“连接我们的,实际上是我们对于生存的共同参与,是一股穿过我们、令我们颤动的生生之气”。 [法]弗朗索瓦·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宋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然而,“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之贵,正在于“人心那点灵明”和“发窍”,如同水和气的共振总是有着分散的漩涡,“天地万物”的“一体之仁”正是由那无数漩涡的核心,即人的灵明,在彼此激荡、影响而成。这样互融互通的一气流行,从单个“人”的漩涡来讲,“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传习录·下》)。而修身功夫正在于,“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在此境界中,“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传习录下》)综合两处来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话头,正是糅合了儒家的“推”法、老庄的“一”法和《易传》的“感通”,而其宇宙论基础则是灌注生命力的道论和流行万物的气论。只有同时肯定了“仁”和“感通”,主客的界限才会泯除无余,被认知化的“物”才能真正与人齐等,“仁”才能得到充分的扩充,宇宙也才是真正生生不息的宇宙。
可见,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物”从来不是僵死的客体或者枯燥的抽象者,而是内部包蕴着动能与元气的有机体。“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邵雍《观物内篇》),贵为“天地之心”的“人类”,亦不过是万物之一物而已。在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的儒道经典文本里,我们可发现,“物”始终闪烁着自内而外显形的独特光辉和具有丰富意蕴的多重面相。借助词源考察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将使人们更深地理解“物化”、“成物”、“序物”、“格物”、“与物同体”等思想的内在相关性,并将这些看似独立乃至对立之“物”的面相凝结为一个整体。这对思考“物”之现代意蕴也是颇有裨益的。
责任编辑:张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