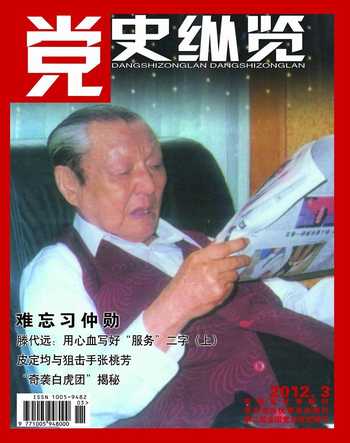徐延松:壮士由来报国终
华泽昆


徐延松(1928-1966),曾用名徐鹤年,笔名林郁、凌汉、徐世白、徐子馥,1928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今明光市)柳巷乡桃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2年参加革命,194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1966年6月23日被残酷迫害致死,时年38岁。
投身革命,坚定信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烧到了徐延松的家乡,面对国土沦陷、民不聊生的现实,少年徐延松心里深深埋藏着一颗革命的种子。
1942年,年仅14岁的徐延松就参加了革命,在抗日反“扫荡”斗争中为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做情报工作。1943年8月,党组织送徐延松到大柳巷附近的泊岗小学读书,同年9月由陈林沛、孙遇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5岁。
1944年8月,徐延松由党组织选派,转入专门培养革命人才的“盱凤嘉公学”学习。
据当年公学学员、曾任中共滁州地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徐其绵的回忆:从各个区乡学校转到盱凤嘉公学学习的同学,最早有8位党员,他们是:丁淑仪、王玉之、华人秀、陈东福、郑玉霞、秦言章、徐延松、徐其绵。这8位党员成立一个党支部,共同在一起过组织生活。
徐延松在盱凤嘉公学期间曾创作出不少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有一首他16岁时填写的《满江红》词,其表现形式受南宋抗金英雄岳飞《满江红》词的启发,曲调也是相同的,但其思想内容却具有全新的时代意义:
“伟大中华,文明国,神圣无匹。堪憎恨,和平领土,顿遭侵袭!四亿同胞沦水火,猖狂倭寇逞凶虐!怅兽蹄踏碎锦山河,腥风逼!
高山怒,河水咽,家国破,万民泣。英雄汉唤起救亡声急!万众一心齐抗日,枪林弹雨冲锋力!好男儿奋勇建奇功,歼顽敌!”
这首词不仅抒发了徐延松慷慨激昂的战斗情怀,同时也深深激励着同学们的革命斗志。
1945年2月,徐延松从盱凤嘉公学毕业,先在古沛小学任教,并被派到淮北抗日军政大学速成班学习,随后被调到盱凤嘉县文工团任音乐组组长,不久又调到泊岗小学任教。
徐延松以文化教育战线上的工作作为自己公开合法的身份,掩护他在党的领导下所从事的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当时直接领导徐延松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上线是陈道行和华文超,徐延松的下线有徐向玲、杜剑秋等。他们多次秘密地向洪泽湖里的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送情报、送盐及其他必需品,经历了多次惊险的斗争。
2011年12月21日,中国新四军研究会《铁军》杂志社副社长黄忠金访问了86岁的徐素明(即徐向玲)老人。老人回忆道:
徐延松15岁入党,我那年16岁。我们入党材料都是他写的。
延松交给我的任务主要是送情报,把写有情报的纸条卷好,扎在辫子里,有时缝在衣角边,挎篮子割草做掩护。有一次,我在腰间裤袋那里装了一斤半盐,送往洪泽湖。后来延松要我走另外一条路,闯过敌人岗哨,把情报埋在指定的地点,上面用芦苇叶打个结做记号,洪泽湖里派人来拿。
1946年7月,因国民党军队进犯,我军主力向北撤至山东一带。陈道行、徐延松、徐向玲等留在皖北敌我“拉锯战”地区坚持秘密斗争。徐延松则继续以“泊岗小学教师”这一公开身份做掩护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陈道行向徐延松托付了一项新的秘密任务,即:保管党的两份文件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物品(包括陈毅任新四军军长时所作的五言排律《病苦乐》二首)。
当时皖北地区敌我形势非常复杂,在那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十分危险。徐素明老人回忆道:
延松主要在盱凤嘉一带活动,他为革命冒了很多险。他是我的领导,我是地下交通员,是送信的。每一次给我军送情报,都是由他直接给我下达任务;但是他自己执行另外的任务时,都是同上级领导单线联系,从来不告诉我。
有一次,遇到国民党还乡团追查,有个大嫂就是用大缸把延松藏起来,躲过一险。
还有一次,延松在古沛集一个村子让国民党还乡团抓了去,说“抓到小共产党”,被打得奄奄一息,延松始终不招。幸亏他事先把情报埋在地里,敌人没查到。
同我们一起干地下党的还有杜剑秋夫妇,他们后来到了福建。这两个人也了解延松当年的革命斗争事迹。
不久,陈道行在同国民党还乡团的一次拉锯战中负伤不治,不幸牺牲。徐延松在失去上线和下线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组织交给的任务,随身珍藏着党的文件,在苏北、皖北一带秘密隐藏。
1947年春,徐延松穿过敌人的封锁,来到江苏泗洪县魏营乡大庄集,找到一位可靠的老人,妥善地将党的文件等重要物品埋藏在这位老人家中灶台前的地下。解放后,徐延松将以上物品取回并交给党组织,这两份文件由当时的蚌埠专区档案馆收藏,陈道行烈士遗物由南京军区收藏。国庆十周年时,“安徽省蚌埠专区搜集军事历史资料办公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庆祝建国十周年筹委会南京军区分会”分别向徐延松颁发了“捐献革命文物纪念证”。
1947年正是我军即将转入战略反攻之际,此时皖北一带的国民党还乡团活动异常猖獗。徐延松写于1947年的《七律•宵征》,记录了他有一次连夜急行寻找我军报告敌情的情景。诗前小序说:“残敌驻潼河、双山一带,余乘夜寻找我军报告以便歼灭之,一路沿淮河前进,且喜村人俱睡,宿鸟不惊,惟有渔人时弄桨声。”诗的前四句写道:“书生何事作宵征?为报军情乘夜行;但使斯民除祸害,莫教残敌有余兵!……”
徐延松一家满门忠烈,远近闻名:舅舅和小姑父阚开石是革命烈士;同族的表兄傅毓芳、傅毓芝都是英勇善战的共产党人;大姑父袁晓可抗日战争时参加新四军,1946年随我军主力北撤至山东。
1947年底的一天,徐延松来到潘村镇池口与姑妈徐孝贤联系,在潼河口渡河的时候,被当时隶属国民党政权的潘村镇公所的人发现,这个人当即向潘村镇镇长密报说:“袁晓可的内侄来了,可能是共产党的探子。”潘村镇镇长命令镇公所的镇丁把徐延松捆绑起来毒打一顿,将其随身携带的钱物一抢而光。19岁的徐延松坚强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党的任何机密。直到其表叔季维兰(时任潘村镇保代表)出面说情,说“延松是来走亲戚的”,镇公所才将徐延松释放。
1948年10月,徐延松由表兄朱汉搓介绍到位于皖东北的凤阳十里程小学教书,他一边工作,一边寻找自己的战友和党组织。失去与组织的联系,徐延松心里十分苦闷,但他始终坚定信念,坚持秘密斗争。他曾以诗明志,写下一首七律《感怀》:“为抒积愤作诗篇,患难之中又一年;义士终怀报国志,丈夫从不要人怜;隐身暂作他乡客,糊口聊耕石砚田;信仰正宗唯马列,此心永远似钢坚!”这一年,他刚好20岁。
爱国情深,心忧天下
新中国成立之后,徐延松想尽快联系上当年自己做秘密工作的直接领导陈道行、华文超等,方才获悉他们两位均已牺牲,徐延松悲痛万分,写下了深情的诗句:“奠酒悼君君可知?睹君遗物倍相思;那堪风雨秋灯夜,重读《随军散记》时!”“岂料一年别,竟成永别离;伤心吊墓表,哀极不成词!”
此后,他一直做一名小学教师,先后在明光、柳巷、古沛、官地、里涧、义集、桃溪等地执教。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做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在1951年4月到5月间召开的治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在五河以下采取干支流分治的办法,其中的一项巨大工程就是开挖泊岗引河,将这一段本来向北迂回流经双沟又转头南下的淮河干道截弯取直,新开一条十几华里长的河道。如果施工方案选择不当,就会使一些村庄和大片良田从此消失。当地的乡亲们为此发愁。徐延松凭着早年所学的知识和他解放前做秘密工作时对淮河干支流及洪泽湖周边地形的了解,积极主动地帮助治淮委员会的同志查水道、绘地图、提方案。在浮山、下草湾、双沟、泊岗等淮河新老河道流过之处,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自费到蚌埠、上海等地向有关部门反映勘查情况,提出合理建议。令人欣慰的是,他的意见终于被采纳。按照最后确定的施工方案,不仅泊岗引河工程进行得更为顺利,而且柳巷、桃溪、丁坝、苗巷、义集等村落和大片良田也得以保留下来。柳巷乡许多了解情况的老人每当回忆起这件事,都感激不已地说:“多亏了延松出来忙这个事哦!”
1957年反右斗争中,徐延松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甚至被剥夺了过党的组织生活的权利。
徐延松当时每月工资38元,要藉以养活全家9口人(祖母、父亲、妻子及5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全国仍有不少地区受灾缺粮。徐延松同妻子阚锦荣商量说:“我们多少还能吃上国家供应的一点粮食,你看很多地方都没有吃的,大人小孩都在挨饿。我们要多挖点野菜,省点口粮救济别人。”就这样,他带领全家节衣缩食,每天以野菜粥充饥,晚饭经常不吃,一共节约了159斤粮食,存在自家领取口粮的凭证“粮食周转证”和“粮食调剂卡”上,全部捐献给国家,用以救济缺粮的灾民。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徐延松在家庭生活如此艰苦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一名教师爱生如子的情怀。当有些学生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时,徐延松挨个登门劝其复学,并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为他们交学费,买文具,鼓励他们发奋刻苦学习,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20世纪60年代中期,徐延松看到国家的林木资源受到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心中深为忧虑,认为亟需发展绿化事业。根据平时观察,他发现楝树有很多优点。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便带领自己的孩子和学生采集一些楝树的种子,在校园里选择一块空地种下去,第二年春天很快长出一片小树苗;再把这些树苗移栽到校外。在此基础上,他先后两次给国家林业部写信,指出楝树的种子容易大量采集,种下去成活率高,树苗很快就可以成材,应作为主要速生用材树种加以推广,建议林业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大采楝种、大植楝树的活动”,绿化祖国,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林业部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在黄河以南各省大力推广种植楝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坚持党性,铁骨铮铮
从保留至今的大量原始资料来看,徐延松早在1965年底就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手策划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早在1966年6月就对“文化大革命”明确提出质疑和否定。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并开辟“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专栏。徐延松读后,坚持认为《海瑞罢官》问题是学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他奋笔而起,化名“林郁”,从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撰写《应从悲剧角度着眼肯定〈海瑞罢官〉的积极意义》、《清官和贪官不容混淆》两篇文章,直接地支持吴晗同志。
在当时极端反常的政治环境下,如此旗帜鲜明的言论必然埋下祸根。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走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罪名铺天盖地地压到徐延松的头上,使他成为安徽省嘉山县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
于是,各种拘押威胁、捆绑吊打纷至沓来。对此,徐延松威武不屈,义正词严;对于种种指鹿为马的政治诬陷,他据理力争,逐条予以反驳。有人强逼他写检查,他说:“要检查很简单,六个字:反对阴谋陷害!”徐延松被害死的前一天(6月22日)夜间,他还在一份“检查书”上控诉:“我坚决反对那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号,千方百计阴谋陷害革命同志的假革命!……”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徐延松仍然坚持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利用别人逼他写检查的纸和笔,给当时的嘉山县委写信:
“敬爱的中共嘉山县委:
在当前复杂而又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凡是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经得起风浪的考验。可是,当一个人遇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必须依靠我们伟大的党来帮助解决。
我的家庭是贫下中农,早在祖父活着的时候,就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种种野蛮的压榨和迫害。”
写到这里时,非法拘押他的人发现他写的不是检查书,便对他又是一顿更加疯狂的毒打。
6月23日晨,徐延松已被折磨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有人别有用心地先后三次强迫徐延松到淮河边挑水,徐延松当即揭穿其犯罪企图:“叫我挑水,就是想害死我!”(见刑讯逼供记录及相关文字证据)据现场目击的群众所提供的证言,有人硬把扁担压上被害人肩膀,扁担两头各趴一个人往下压,又用砖头石块往被害人身上砸,用带刺的藤条抽打他。被害人昏倒在地,口吐白沫,有人拽住他的手脚,抬起他一次次往墙上撞。在被害人奄奄一息之际,有人把他放在绳床上抬到烈日下暴晒,再把他从床上掀到布满砖石瓦砾、高低不平的地上,先是抓住他的头发,然后拽着他的两条腿狠命地往河边拖。当日上午,年仅38岁的他最终被迫害致死。
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中华英烈》等报刊曾先后发表纪念徐延松的文章。
我们在他被迫害致死45年后的一天,找到了当年徐延松做秘密工作时直接领导的下线徐向玲。一提起往事,86岁高龄的老人潸然泪下:
“1961年是荒年,延松到芜湖开会,绕道南京想来看我,夜晚才赶到浦口我家里。我想多留他住两天,他说工作忙,要赶回去了。第二天早上,买了4根油条、4块烧饼和一包饼干给他带走。延松干革命时没穿过一双好鞋、一件好衣,没吃过一顿好饭,等日子好过了,他又被人害死了,好可怜哟!”
我们今天追悼和缅怀徐延松,重读他在祭奠革命先烈时所写的那些直抒胸臆、荡气回肠的作品,能深深感受到其中的真精神、真魂魄。这些写在几十年前的质朴而真淳的诗句,最能成为他的一生传神写照,同时也最能表达我们对他本人的无尽哀思:
“英雄自古为民死,壮士由来报国终。我国奇男皆义勇,甘将热血染旗红!
“河山壮气毓精神,革命红旗遍宇尘。一个牺牲万个起,全民都是继承人!……”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