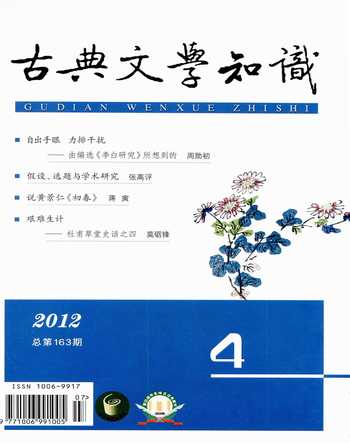理学思想的诗性阐释
阮堂明
张载(1020—1077),为“北宋五子”之一,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者。因徙居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世因称横渠先生。与一般学者年少时即好学深思不同,张载少喜谈兵,志气不群,慨然以功名自许。他生长的横渠,临近北宋西北边境,因此对于宋王朝与西夏当时已然十分尖锐的矛盾有着更加敏锐和深刻的感受,故而十分留意和关注西北边患,《宋史》本传载其“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张载由志在功名转向探讨儒家性理之学,缘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元昊反宋的触发。时朝廷急于稳定边境局势,召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张载因上书谒见,备陈关于用兵的谋略和计划,表达参与边防军事的愿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当时守边固防而急需用人的关键时刻,范仲淹并未答应张载,而是因为“知其远器”,觉得他在儒学方面会有更大作为,“乃警之云:‘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宋史?张载传》),将他的人生追求由志在功名引导到从《中庸》中探索儒家名教之乐方面。对于范仲淹“劝读《中庸》”之深意,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我们关注的是,经由他的劝导,张载的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折:由追求外王事业的经世之学转向于追求内圣修养的性理之学。《宋史?张载传》载,在接受范仲淹的劝导之后,张载“读其书(按,指《中庸》),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作为弟子,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记述张载求道时艰苦力索的精神时,曾这样写道:“(横渠)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正是这种数年苦心孤诣的辛勤探究,张载终于建立起一套足以抗衡佛老的理学思想体系,从而圆满完成了范仲淹交给他的重大任务。嘉祐二年(1057),三十八岁的张载进士及第,并约在此时在开封主讲《周易》,这表明他的思想此时已经成熟。然而遗憾的是,范仲淹早在仁宗皇祐四年(1052)已去世。历史并没有给张载提供向范仲淹请谒、汇报的机会。今天看来,范仲淹当时的劝导,可能使宋王朝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军事人才,却造就出一位卓越的思想家。程颐尝论张载《西铭》,称其“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清代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中也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高度肯定了张载为重建儒学、确立抗衡佛老的儒学之体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作为理学先驱,张载之学以乐天知命为本,以尊礼贵德为用,以《易》与《中庸》为宗,以孔孟渊源为法,为学主张“学必为圣人而后已”,认为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在于“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横渠之学有两个鲜明的特质:一是明体达用,注重经世致用。张载志气不群,年少时期既已树立起伟大的抱负和强烈的使命感,其学虽有关于抽象的理学本体论的建构,但并不空谈性理,不像其他理学家多局限或停留于自我心性修养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上,而是注重立体以达用。他曾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概括自己一生为学的宗旨。如果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着眼于心性之本体建构的话,“为万世开太平”则是讲由内圣心性开出经世外王。这四句话不仅表现了张载的理学思想是循着由内及外、由体及用的顺序而推进的,也体现出张载并非醉心或满足于思想体系的建构,而是具有立体以达用的明确追求。正是如此,举凡井田宅里之制、学校之法、婚祭之仪及古今之礼,他莫不详究。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张载之重礼,从根本上说即是这种经世致用学术追求的体现。二是追求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程伊川曾经说过:“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不过,最早发明此意并将此意阐发得最为详尽、深刻的则是张载。他从世界的统一性出发,将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都看成是以仁为纽带而普遍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在他看来,“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而非仁也”(《正蒙?天道篇第三》,《张子全书》卷二)。在《西铭》中,张载以寥寥二百余言,进一步阐扬仁德之覆载万物、普施无外,提出“民胞物与”的主张,将天地视为父母,民众视为同胞,万物视为朋友,从而使个体自我胸怀天下,放眼宇宙,把自己看成是宇宙整体的一个必要部分,把天地万物看作是与自己息息相通的整体。在这一境界中,个体的道德自觉大大提高,其行为不再是出于个人一己之私,而是基于普遍的价值、基于对人类全体与天下道义之担荷。反过来,个体也因为与天地万物一气相通而获得了来自于天地万物的支持,从而拥有了更大的精神力量。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言所体现出的宏大胸襟与气魄,从根本上说正是植根于此。说到底,张载作为理学家的历史地位,也正因为这样将仁义礼乐提高到天理性命的高度,加以哲学的论证,最终形成并确立抗衡佛老的儒学之体。
张载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长于诗歌创作。他的诗与他的“学必为圣人而后已”的理学事业紧密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理学思想的诗性阐发。比之邵雍、周敦颐及程颢等人因追求“孔颜之乐”和“曾点气象”而具有的鲜明诗性性情与风月情怀,虽然同样是理学诗人,张载因为少了从容涵泳之味,而多苦心力索之功,并未养成他们那种审美情趣化的诗性性情。与此相关,张载为文反对一味铺陈却无关宏旨的“闲言长语”,强调以“发明道理”为上。他曾批评程颐所作《明道先生行状》,认为“后语亦甚铺陈,若人体认,尽可以发明道理;若不体认,亦是一场闲言长语”(《张子全书》卷七)。张载此言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程颐以“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批评杜甫《曲江二首》中“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二句(《二程遗书》卷十八),二者可谓如出一辙。应该说,这体现了张载在诗学观念上的理学家立场。不过,他究竟并未像程颐那样明确宣称“作文害道”,这使他虽不重吟咏情性,但基于万物各有其理、君子须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的思想基础,仍然创作了一些诗歌。
作为理学家,张载的诗题材上有一个鲜明的取向,即往往直接以诗阐发其理学思想。像《克己复礼》、《圣心》等,即直接以儒家思想义理为题。《葛覃解》、《卷耳解》等诗,作为他借经以求道的产物又是直接取之于《诗经?国风》。这些诗皆是他求道过程中有得于心时所作的。他“尝谓门人曰: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命辞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精义入神者,豫而已矣”(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对于张载而言,诗歌创作并非体道之余时的吟风弄月,而是求道过程中体认与确证心性义理的一种方式。像他的《诗一首》:“学易穷源未到时,便将虚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辞赋,用即无差问不知。”便生动地展示了诗人求道未至时“心思虚寂”的精神状态,体现了诗人苦心力索的精神。张载作有《八翁吟十首》,以傅说、吕尚、周公、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及诸葛亮等八人,为“八奇翁”,分别吟咏。对于这组诗的创作,他曾解释说:“十诗之作,止是欲验天心于语默间耳。”(《张子全书》卷十四)所谓“语默”,出于《易》:“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按照这种说法,则《八翁吟十首》之作,完全是诗人“验天心于语默间”的一种“实验”,诗则成为这一实验的工具。其《送苏修撰赴阙四首》之四也云:“出异归同禹与颜,未分黄阁与青山。事机爽忽秋毫上,聊验天心语默间。”由这里可以看出,以诗“验天心于语默间”,于张载而言,乃是明确而有意识的。正是如此,张载的诗没有浅尝辄止地徜徉于理学思想中而表现出闲雅情调与精神自得的趣味,而是充分体现出与其“学必为圣人而后已”的崇高追求相应的坚卓刚毅与谨严笃实的精神。像他的《君子行》:“君子防未然,见机天地先。开物象未形,弭灾忧患前。公旦立无方,不恤流言喧。将圣见乱人,天厌惩孤偏。窃攘岂予思,瓜李安足论。”这首诗针对乐府古辞《君子行》而作(见《文选》卷二十七)。古辞《君子行》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比肩。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圣贤。”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古辞《君子行》中抒情主人公之谨慎忧惧、惶恐不安,而张载则明确直言“不恤流言喧”、“瓜李安足论”,体现出奋然无惧的卓然品格,从中不难体会张载“求为圣人之道”独立不迁的坚卓精神。
张载的诗还较为注重政治教化功能。他于礼乐诗书殚心以求,深明圣人制礼作乐删诗以沟通神人、正心化民之意。他曾说过:“兴己之善,观人之志,群而思无邪,怨而止礼义,入可事亲,出可事君,但言君父举其重者也。”(《正蒙?乐器篇第十三》,《张子全书》卷三)此言显然是对《论语?阳货》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注疏》卷十七)的解释。有意思的是,他置孔颖达对“兴”所作的颇具文学意味的“引譬连类”之解于不顾,而以“兴”为“兴己之善”;又将郑玄所解释的“观”乃是向外“观风俗之盛衰”之意,理解成“观人之志”(以自省修己),将诗的功能定位于道德教化上。他作有《古乐府》诗,该诗由《短歌行》、《日重光》、《东门行》、《鞠歌行》、《虞帝庙乐歌辞》等组成,共九章。在诗序中,他说:“载近观汉魏而下有名正而意调卒卑者,尝革旧辞而追正题意,作乐府九篇。末篇《鞠歌行》,今附以见怀寄二程。”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汉魏以来乐府歌诗意调卑靡,使歌诗重归于雅正,“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其实,此组诗除了张载明言的这层意思之外,还有更深的微意在。我们注意到,张载解《诗》而批“郑卫之音”时,曾这样说过:“移人者莫甚于郑卫,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颜回也。今之琴亦不远郑卫,古音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长言,声依于永,于声之转处过,得声和婉,决无预前定下腔子。”(《张子全书》卷五《礼乐》)这里,张载并未停留在对“郑卫之音”的批评,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宋代。其所谓“今之琴亦不远郑卫……决无预前定下腔子”,显然指的是当时初兴的词。他的《乐府诗》之作,即与他对新兴的词的批评有内在的关联。据《宋┦?乐志》载:“宋朝湖学之兴,老师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尝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寓之埙龠,使学者朝夕咏歌,自是声诗之学为儒者稍知所尚。张载尝慨然思欲讲明,作之朝廷,被诸郊庙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张载《古乐府》之作,真正的用意在于“作之朝廷,被诸郊庙”。其《短歌行》一首:“灵旗指,不庭方,大风泱泱天外扬。短箫歌,歌恺康,明庭万年,继明重光。曾孙稼,如茨梁,嘉与万邦,纯嘏有常。”此诗虽诗旨奥衍,但从“嘉与万邦,纯嘏有常”看,主要是歌颂圣君克明俊徳,制礼作乐以化成天下、协和万邦。张载的《古乐府》九章,虽不能说他是借诗以立言,这些诗也容或存在朱熹所批评的“做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朱子语类》卷九十二)之不足,但不能否认其“作之朝廷,被诸郊庙”的明确用意与追求。这其实不仅反映了张载注重诗的政教功能,欲以诵诗咏歌涵养性情,同时也透露了诗人志在经世的思想襟怀。张载有《老大》一诗:“老大心思久退消,个中终日面岧峣。六年无限诗书乐,一种难忘是本朝。”一面说“老大心思久退消”,但又说“一种难忘是本朝”,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体会这一点。
与追求诗之政教德化作用相应,张载也注重以诗言志,表达怀抱与追求。他说:“志至诗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体,故礼亦至焉。”将诗看作是诗人之志的载体。又说:“诗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张子全书》卷五《礼乐》)我们看其《古乐府》中《鞠歌行》一诗:
鞠歌胡然兮,邈予乐之不犹。宵耿耿其不寐兮,日孜孜焉继予乎厥修。井行恻兮王收,曰曷贾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见志兮,庶感通乎来古。搴昔为之纯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跃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廖哉寂焉。谓天实为兮,则吾岂敢,羌审己兮乾乾。
诗人自述怀抱,表达“为往圣继绝学”的志向。诗中“千五百年,廖哉寂焉”,意思即指孔子殁后,圣道莫传,诗人故而耿耿不寐,孜孜求以继之。从这里不难看出诗人抱负之宏伟。不过,细心体会,还可以发现,此诗在自述抱负的同时,还隐约流露了诗人精神上因怀抱未展而来的郁闷之感,这一点从“天实为兮”一句可以捕捉到。今按,“天实为”典出于《诗经?邶风?北门》:“已焉哉,天实为之。”据《诗小序》,该诗旨在“刺仕不得志也”(《毛诗正义》卷二)。“天实为之”,是主人公因遭逢暗君,虽勤身事之,终贫窭禄薄,遂将仕不得志的原因归之于天。诗中“则吾岂敢”一句与其说否定了将个人失志归之于天,还不如说是诗人以更婉曲的形式来表达这种郁闷。另外,“羌审己兮乾乾”一句,“乾乾”典出于《周易》“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孔颖达《正义》云:“君子在忧危之地,故终日乾乾,言每恒终竟此日,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周易注疏》卷一)诗人这里借用语典含蓄地表达了虽怀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之志却难以实现的郁闷之情,感情深隐曲折,含而不露,有“隐讽谲谏之巧”。张载在论及《八翁吟十首》时,又曾这样说:“近作十诗,信知不济事,然不敢决道不济事。若孔子于石门,是信其不可为然且为之者,何也?仁术也。如《周礼》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岂不知无益于救,但不可坐视其薄蚀而不救,意不安也。”(《张子全书》卷七《自道》)从这种“信知不济事,然不敢决道不济事”的语气中,也不难体会到其中的无可奈何意味。应该说,这里面也明显包含有诗人的不平之意。值得回味的是,张载因为“学必为圣人而后已”的坚卓精神而被抑制的诗人性情,却在这里不经意间地流露了出来。他虽然没有明确标榜诗之抒情,但“诗言志”本身既已包含了抒情或对抒情的肯定之意在内。如果说邵雍、周敦颐与程颢经由审美情趣化的道德人格的培养而趋近于诗人性情的话,张载则因为主张诗言志而具有或者说获得了诗人的性情——这大概是他当初慨然立志,求为圣人之学时未曾想到的。张载要么是扩大了主体自我的能动力量,要么是低估了外在环境对个人能动力量实现的制约与影响力;不论如何,我们从他对现实环境的简单化理解以及述为学宗旨时的“豪情”中,不是已经可以依稀看出他的诗人性情的一面吗?这样说来,当张载确立了自己为学的宗旨与方式时,其诗人性情就已经先期预设下了,这对于张载来说,几乎是无可逃遁的。当然,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夸大张载这种诗人性情。作为道学之士,他无法像文学之士那样执着于诗之抒情,诗之于他,“只是言志”;同时,因为气质刚毅,德盛貌严,他也难以有风月情怀,从而去吟咏性情,表现曾点气象。
不过,这并不是说张载就不具诗人之才情,写不出情韵俱佳的佳作。事实上,当他于体道之暇而稍有余裕时,仍然可以写出情韵生动的诗来。比如这首《和薛伸国博漾陂》:
几年烟浪掩遗踪,今意扶持古意同。簮笏每游高圣世,莼鲈聊为快秋风。轻阴岛屿莓苔湿,夜雨蛟龙窟穴空。南浦云峰晴不乱,北窗溪木暗难通。春浓岸柳成行碧,日暖汀花取次红。岁月可悲唐废苑,山河终近汉离宫。归禽影转沙堤曲,处士居邻竹坞东。星斗已知天象富,菱蒲堪喜地毛丰。持竿幸有鱼充鼎,混俗须嗟鹤在笼。吏隐苟能游物外,江乡何必羡吴中。
此诗为酬和之作,就内容而言,主要描写博漾陂周围的山水景色,表达对主人隐逸高情之肯定。虽然形式上为排律,但整首诗读来谐畅自如,势若贯珠。诗歌对景物的表现非常细致,如“南浦云峰晴不乱,北窗溪木暗难通。春浓岸柳成行碧,日暖汀花取次红”等诗句,不仅对仗工允,诗律谐婉,而且写景工细传神,富有鲜明的形象感,读来饶有韵致。另外,像其《题北村六首》之二:“求富诚非惮执鞭,安贫随分乐丘园。两间茅屋青山下,赢得浮生避世喧。”之五:“不堪烦暑病荒城,六月翛然寓野亭。珍重南山且归去,再来相望雨中青。”皆着力表达省分知足、安贫乐道之生命旨趣,毫无酸寒俭陋之态,体现出精神上随时善处、顺物而行之态,读来也颇有情致,从中可见张载性情的另一面。
总体而言,由于受以诗“验天心于语默间”,以及推崇诗之政教作用之观念的影响,张载为诗主张简易直截,正言而直歌,因而并不注重艺术技巧,不少诗较为抽象,不耐咀嚼,缺乏形象性与艺术感染力。不过,张载的诗原本即不以求工巧为意,倘执诗艺工巧以为度来衡量横渠诗的话,这反而会忽略他的诗,掩盖其诗的真正价值。在我们看来,张载诗的精髓与价值,就在于表现了诗人求为圣人之学时所体现出的刚健笃实、日新其德的精神,以及诗人充溢于其中的坚卓弘毅的弘大气魄与内在力量!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在“一物两体”辩证思想背景下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