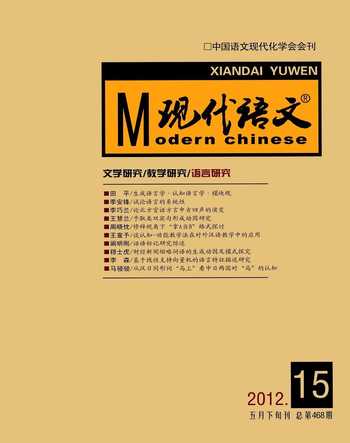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现象
林芳 张明林
一、引言
最近十多年来,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一直是国内翻译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纵览国内许多翻译期刊,论述翻译问题时涉及到的归化与异化问题众多。但是,总体看来,大多数论述似乎都从传统的译论角度出发,只是将归化与异化限定在对文本的语言学认识范畴的基础上进行单向的研究。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而翻译学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门重要学科,在人类的交往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翻译不仅仅要考虑到文本因素,还应该结合文本考虑其外部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认为“翻译总是植根于文化和政治体系以及历史当中”“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反映了译本产生的语境”(曲夏瑾、金敏芳,2011:48)。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关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关系。它的提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启示,将翻译活动回置于它所产生的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这一大背景下,研究翻译的归化与异化问题显得十分有必要。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建立在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翻译理论。后殖民翻译研究理论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王东风,2003:4)。后殖民翻译研究关注弱势民族、弱势文化和弱势群体,以文化生态平衡和世界多元文化为视角,努力创造世界文化多样性。这一翻译理论的提出使得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文体和风格等文本内部问题,一大批原先热衷于探讨翻译技巧的学者也逐渐将目光转向非文本因素,比如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至此,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权力转向”,权力关系后来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和翻译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与以前的各种翻译流派相比,后殖民主义翻译派更侧重政治、民族、种族等社会文化因素,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进行翻译探讨。该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西方世界的国家在文化输出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而它们常常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第三世界的弱小国家,企图实现思想文化上的绝对控制权。而处于文化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和意识,自己的文化传统面临严峻威胁,自己的意识形态受到冲击而逐渐嬗变。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相比,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通过对译本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描写性追述,揭示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以及翻译暴力的存在。”(金敬红,2004:136)
三、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下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这对术语是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来的。根据韦努蒂的界定,归化翻译是译者为了制造出透明、通顺的译文而将异域文本中的“陌生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翻译策略。而异化翻译是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中的一些“陌生性”的翻译策略(赵博,2011:22)。以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为视角,归化法是占支配地位的强势文化在将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文化的文本翻译过来时经常采用的翻译策略。强势文化凭着自身的优越条件,在面对异域文化时往往从自身的文化出发,对异域文化不屑一顾,甚至刻意抹杀其异质性,目的是“将外国的文本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由此消除文化差异,在他们周围营造一个被同化的同性缓冲区。霸权文化的成员因此也不会接触到真正的差异,他们被策略性地保护起来免受异质经验的干扰。他们不仅受到同化翻译的保护,而且还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五星级宾馆等的保护。(Robinson,1997:109)
采用归化法的译者往往会用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尽可能地根据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来对文本进行修改,使得译作看上去像是译者原创一样,丝毫看不出翻译的痕迹,使得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大大增强。但与此同时,原本弱势文化所具有的语言和文化的异域特点也被抹杀殆尽。这种归化翻译策略其实是以强势的西方文化为标准、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它所追求的恰恰是强势文化的差异性,强势文化想把自身的差异性强加给处于弱势地位、边缘化的其他文化,从而使得弱势文化把处于优势地位的强势文化的差异性当作一种普遍的意识来接受和认可,并使之得到推广,进而达到其文化霸权的目的。但试想一下,如果长此以往,一味地对与本国文化不相符的弱势文化持否定态度,排斥拒接,那么这些拥有强势文化的国家最终将走向“文化自恋”的歧途,各国文化间的正常交流也势必受到影响和阻碍,甚至导致全球文化的单一性,引发文化危机。针对这种翻译界归化法盛行的现象,韦努蒂对强势文化发起了挑战,这就是所称的“抵抗式的翻译”(Venuti,1995:291),即异化的翻译策略,以此来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异化翻译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翻译策略考虑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了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尽可能地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来看,异化翻译就是使译语读者和译者能够摆脱强势文化的限制,从而对强势文化提出了挑战。后殖民的翻译理论强调在翻译时对差异性的凸显,强调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对原文的差异性进行保留,故意对目的语文化常规产生颠覆性冲击。异化翻译策略使得弱势文化的语言和意识能够得到保留,在译文中彰显出弱势文化的异域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来自强势文化的冲击,纠正了由于归化策略盛行而可能引发的文化霸权问题,颠覆了强势文化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入侵,从而有助于重塑弱势文化的本土身份和异域特质。汉语中的“叩头”(kowtow)、“功夫”(kungfu)、“好久不见”(long time no see)、“饺子”(jiaozi)、“旗袍”(cheongsam)等就属于比较成功的异化翻译。这些词语现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式英语短语。它既保留了汉语中的异域特色,避免了殖民文化的侵略,又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虽然说异化翻译策略能够很好地保护弱小民族的语言文化思想等免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避免了霸权文化带来的文化单一性,但如果在翻译文本时译者不顾现实的语言表达情况,一味地硬译,不懂得适时变通,那么翻译出来的文本也会质量低、生涩难懂、让人费解,从而影响各国文化间的正常交流。
四、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不同选择
(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略
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强势文化引进其他国家的文化时,总是以自身的文化为出发点,试图保持其文化的高贵血统。归化法的翻译策略在西方国家已风靡多年,从17世纪以来,英美文化就一直实行“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标准。美国著名诗人、意象派的代表人物埃兹拉·庞德在翻译儒家经典《论语》时,就有很浓厚的归化主义倾向。例如他将《论语·八佾第三》中的“八佾舞于庭”译成“Corps de ballet eight rows deep in Head of Chi's courtyard”。在庞德笔下,东方古国似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芭蕾舞,此举显然不是让西方读者了解《论语》特有的文化沉淀内涵,而是直接向读者灌输其认为的东方儒家思想。又如在《华夏集》中,他就选取了大量中国古典的意象派诗歌。他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主要不是为了宣传中国的诗歌文化,而是为其文学目的服务,利用汉语作为一种文化斗争的有力武器。因此他翻译的诗歌往往篇幅短小、言简意赅,忽略了中国古典诗歌原有的韵律和形式。庞德通过归化翻译这种方式,刻意忽略了东方文化的重要作用,保护了西方强势文化的优越性。与此同时,西方的强势文化也积极向位于边缘地位的弱势文化强行输出其意识形态、政治理论、价值观等思想,企图通过这种方法来巩固自身文化的强势地位,实行文化渗透。西方国家尤其热衷于向弱势文化输出大量的宗教方面的词语来实行其文化侵略。例如“Judas Kiss”(犹大之吻,指可耻的叛变的行为)、“The Sword of Damocles”(达摩克利斯之剑,指时刻存在的危险)、“Eden”(伊甸园,指人间天堂)、“Scapegoat”(替罪羊,指替别人承担罪责)等。以上这些短语对译入语读者来说早就不再陌生,并且已经成为译入语文化的一部分。西方强势文化通过向弱势文化传播大量的诸如此类的翻译,使得西方宗教思想和典故逐渐归入译入语国家的语言文化中,并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被译入语国家人民所接受,从而巩固了其强势文化的地位。
(二)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抗争
随着各地民族运动的兴起,弱小民族文化思想也开始觉醒,为保护本土文化免遭西方强势文化的侵略而进行顽强抵抗。为了保持汉语弱势语言的地位和纯净性,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开始用富有本民族特色的词语来翻译外国的文学著作,以此来弘扬本国的语言文化,而不是一味地追随强势文化语言的步伐。例如,大多数英美国家的诗歌刚刚被介绍到中国时,都被翻译成古体诗的形式。中国翻译家之所以采用归化的策略来翻译外国诗歌,一方面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背景,将英美诗歌译成古体诗的形式有利于读者加深理解;另一方面也很好地保护了本土的语言文化,用古体诗的形式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诗歌。在中国文化的输出方面,中国译者也是有意识地尽可能保留汉语的语言特色。在英译中国古典巨作《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凭借着高超娴熟的翻译技巧,运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手段对其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信息作了准确的处理,最大程度地传递了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深刻挖掘了中国的文化内涵,再现了汉语的语言风格,并向西方学者介绍了中国特色的文化,被誉为中国古典典籍英译的典范。例如在翻译《红楼梦》中“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这个句子时,霍克斯译成“And now this new cousin comes here who is as beautiful as an angel and she hasn't got one either……”而杨宪益夫妇则译成,“Even this newly arrived cousin who is lovely as a fairy hasn't got one either……”这里,“神仙”一词的翻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象。霍克斯按照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背景和民族心理,将其译作“angel”。但事实上林黛玉与“angel”两者之间的文化内涵相差甚大,此种翻译不利于向读者传达汉语特有的文化内涵。杨宪益夫妇则按照汉语文化中的意象用归化法译作“fairy”,忠实地体现出了汉语的文化色彩,既传神又达意。在翻译“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时,霍克斯译作“Your uncle is in retreat today”。而杨宪益夫妇译作“Your uncle is observing a fast today”。事实上,“斋戒”这个词是东方文化所特有的,是守戒以杜绝一切嗜欲的意思,在西方的宗教信仰里没有这个词汇。英语中的“retreat”表示“清净、静修、隐居一段时间”的意思,它只是包含了“斋戒”很小一部分语义。杨宪益夫妇的翻译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汉语文化的特色,赋予它独特的东方色彩。如果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背景来说,这都是弱势文化维护本国文化地位、弘扬本土语言文化传统、抵制强势文化殖民侵略的表现。
五、结语
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背景下,归化与异化策略往往与殖民化和解殖民化联系在一起的(骆萍,2006:135)。强势文化民族和弱势文化民族的译者往往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选择归化或是异化策略。事实上,归化与异化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因此,在翻译中我们绝不能将归化和异化对立或是厚此薄彼。译者应该将这两者翻译策略结合起来使用,这样既能向他国传递本国的语言文化特色,又能引进他国语言文化中的精华之处。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同的国家只有坦然面对异质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和提高自身的文化地位,各国的文化交流才会越来越频繁、密切,各国语言才会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Robinsin,Douglas.Translation and Empire[M].Manchester,UK: St Jerome,1997.
[2]Venuti,Lawrence.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
[3]金敬红.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4]骆萍.后殖民语境下异化与归化再思[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5]曲夏瑾,金敏芳.翻译“策略”再思考——从后殖民视角看中国话语体系边缘化与翻译策略的关系[J].外语交流,2011,(6).
[6]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4).
[7]赵博.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翻译观[J].中国电力教育,2011,(26).
(林芳 张明林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315211)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