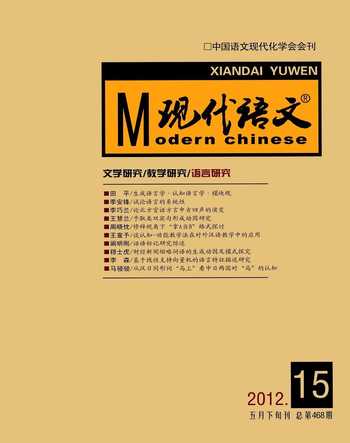释“蹈”为“搯掐焰”辨析
“蹈、搯、掐、焰”四个字,本无比较可言,充其量勉强称得上是形近字而已,如“蹈、搯”,声符均从“舀”;“掐、焰”声符均作“臽”;或者说“搯、掐”形符均从“扌”而已。虽然笔者无意对此四字进行说解,但偏偏这四个字却成为同释一句话中一个词的四种不同的解释。笔者早就有意解决此问题,但无奈功力不足,撰文尚欠火候,蹉跎半年之后,立意已决,方才动笔写下这篇微型文字,供感兴趣的学者、读者参阅,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与讨论。
本文涉及的主要词是“蹈”,原文出自《汉书·李广苏建传》(上)。请看原文:
“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此文系《苏武传》中的一段,写苏武出使匈奴后,因其副使张胜参与了一起欲劫持单于之母归汉的“谋反”事件,事败后苏武等人被扣,苏武处变不惊、欲自杀身死以报效汉王朝廷。事件描写得简练紧凑,且扣人心弦,苏武的表现更让人感到荡气回肠、感慨万分。之中涉及到苏武自杀后,卫律进行施救之情景,“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之句,对于“蹈”之解,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据笔者查阅就出现了四种截然不同的诠解:
一是依原字“蹈”释作“践”,《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蹈,践也。”“蹈、践”按古注看是同义词,两者都是脚向下着地,相当于“踩”。然“蹈”是用力向下跺,方向与力度与踏相近。《礼记·乐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此乃顿足起舞)《史记·司马相如传》:“乘骑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躤。”(此是说以脚(蹄)下踩之践踏义。)
二是杨树达先生释作“搯”(“轻击”之义)。郭锡良主编之《古代汉语》(下册,第525页)教材也持此观点,对上段句释为“在地上挖坑,放置在没有火苗的火堆,把苏武面朝下放在坑穴上,轻轻敲打他的背,使淤血流出来。蹈:通“搯”,叩,轻轻敲打。”《说文》:“搯,击刺也。”《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通俗文》捾出曰掏,掏即搯字,本训捾。按:捾,搯也。……击刺与抽同,于六书为假借。”搯又训为“叩”也。(按:击,《说文》:“攴也。”《段注》:“攴,小击。”)指上下左右横向之叩击,轻击是指适度之叩击,与重击相反。“叩”常指用手敲击,也可以器物(杖、石、木等)敲击,也指轻击。但根据笔者考查,在史上辞书并无“蹈”可通“搯”之记录。但是两字有共同之声符“舀”,《说文》云:“抒臼也。”抒舀,又作“揄、挹”,释作舂(扌寿米之谓)。“舂”与“扌寿”与“搯”之动作相同,彼此印证了“舀、搯、蹈”应是同源字,其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共同反复践踏、击打之动作特征,故此相互借代应是符合语言文字使用规律的。
三是释作“掐”字,此乃郭在贻先生之建言,其在《汉书札记》一文中云:“……依鄙见,蹈似当为掐(掐讹为搯,再借作蹈)。”《大庄严经论》卷三音义引服虔《通俗文》:“爪案曰掐”,又《汉学堂丛书·佚书考·张辑蓓埤苍补遗》:“掐,抓也,谓爪伤也。”“掐其背以出血”,意为“用手指掐捏其背使淤血畅通,殆即俗所谓刮痧也”(郭在贻,2002:45~46)。而且他还征引了徐复先生的读《汉书札记》一文,作为自己主张见解之佐证,郭在贻先生并未明说,但笔者经探究后推断,恐是徐复先生释“搯”为“焰”,“焰”与“掐”的声符同为“臽”所致。
第四,就当属徐复先生的主张了,先生在文中说:“……《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二章有这样一段记载,‘铁木真遇泰亦赤兀十二骑,铁木真独与战,敌骑十二矢并发,伤其口喉,痛甚,昏坠马。不儿古勒(人名)燃火热石,投雪于石上,引铁木真口,以蒸气熏之,及凝血出,呼吸遂通。这就很好地说明蒙古族也有同样的急救法,事情也正好类似。笔者因此比照两处文字,根据其风俗习尚,考知《汉书》的‘蹈背,决不如杨先生‘蹈当读为搯,而应当是‘焰背形近的误文。据《说文·炎部》:‘燄,火行微燄燄也,字与‘焰通用,引申的意思就是熏了。此文正好是“以火微熏其背以出凝血”的意思。”(郭在贻,2002:46~47)
以上四解,除“蹈”用原义外,其余三解,都是比较熟识的专家级学者,当然有的是笔者有缘结识的,有的则是通过拜读其著作结识的。树达先辈之著作《词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及其训诂释义等已成为笔者案头之重要参阅著作,大有常读常新之感,徐复先生则是笔者上世纪70年代岁末于南京训诂学研讨班(由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主办)的恩师。先生的学问、文章自是笔者之楷模,研讨班结业后又一起筹办训诂学会,学会成立之后先生任副会长、顾问,笔者曾任正副秘书长之职,于工作、学术会议期间耳熏目染,受益良多。在贻则比笔者仅小一岁,却是训诂学界之“骄子”与后起之秀,只是疾病缠身,英年早逝(仅50岁就撒手人寰)但却著作夥众,因此从感情上讲很难割舍谁,但继而一想还是以学术真理为重,不徇私心为好。笔者想两位先辈及一位同辈的在天之灵也会同意吾之做法的。
杨说:地上挖坑,置无火苗的火堆,苏武面朝下伏在火堆上+轻击其背。
郭说:地上挖坑,置无火苗的火堆,苏武面朝下伏在火堆上+手掐、按其背部。
徐说:舍弃了两说的共同部分,只是强调用微火熏其背部。
比其三说加上蹈背(即用脚踩)四说,笔者想用末位淘汰法来进行筛选。由于苏武系用刀刺杀前胸,积血于中,在当时无医药及救护人员的情况下,卫律情急之下采用上述手法是无可争议的。既是伤口在前,而置积火在后,恐怕于事无补,再说,前胸伤口处已经置火熏烤,在后重复又意欲何为?徐先生恐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其说存在明显漏洞,不应依从。
其次是伤口不是箭伤,而是刀伤,刀刃较剑等其他兵刃为阔,伤口显然较长、宽且深,而流血多且时间稍久,定是呈血块(凝固状),仅用烟熏火烤是不能凝血化瘀的,因为用手掐之动作恐难以奏效。这就是说大面积的出血与凝固用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况《说文》无“掐”字,“掐”当是汉后出现的。《段注》云:“《文选·长笛赋》:搯膺擗摽。李善引《国语》及韦《注》而云苦冾反,殊误。苦冾反当是掐字,从臽声,爪刺也。下引《魏书·程昱传》:‘魏书程昱传曰:昱于魏武前忿争,声气忿高,边人掐之乃止。是则从臽之掐,于搯膺毫不相涉也……”(段玉裁,1988:596)。所以,笔者认为“掐”字之释恐于伤情及使用手法均不合适。
另外,由于苏武受重伤,而卫律又是人高马大,体重不轻,由其于苏武背上蹈踏是不可施救之法,那么剩下的只有“搯”了,用手叩击其背助伤者活血,且能据其血瘀状况的进展,转换手法,于情于理又是可能的,因此笔者同意杨先生之解释。
对词义之训诂一定要照顾整个语句之前后叙述,切不可先入为主。当然符合实际也是非常重要,不能想当然。另外,分析词的通假,特别是确定用字的错讹更应谨慎,像“蹈”与“掐”,形符和声符全不相同,为说释而全改字形是不可取的,理应杜绝,除非有确凿之据,否则不宜采用此法。以上浅见能否站得住脚,还望行家学者斧正之。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郭在贻.郭在贻文集·训诂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2.
(马振亚吉林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13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