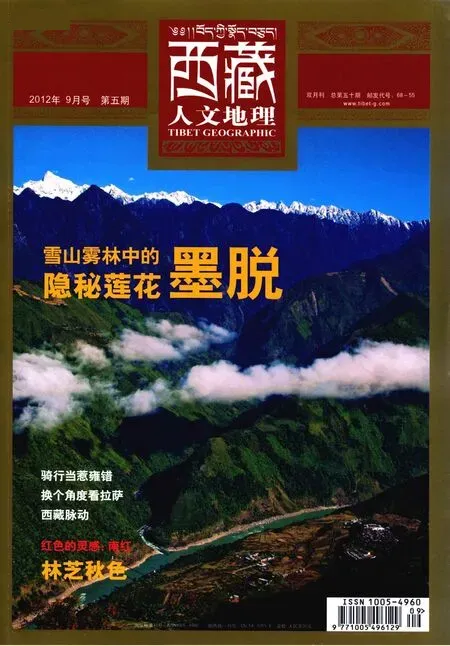雪山背后的桃花源
冯帅



线路一:派镇——松林口——多雄拉山——拉格——汉密——背崩
在众多进出墨脱的线路中,由米林县的派镇到背崩乡的道路不算最险峻,却是在整个墨脱以及背夫文化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一条路。整条路集雪山、原始森林、峡谷、田园风光为一体,沿途从最高海拔4221米直线下降到665米,垂线下降3556米,最大坡度系数达70%,平均坡度系数40%,从山地寒温气候带,直落于亚热带湿热气候带的背崩乡。
进出墨脱有两座雪山被称为“死亡的雪山”——一座是位于墨脱县城东北方向的金珠拉山,一座则是西线进墨脱县必须翻越的多雄拉山。海拔4221米的多雄拉山口,即使是到了盛夏时节,北坡仍然披挂着铠甲般的冰大坂,而这已是翻山的最好时机。这条路,除了每年6个月(6月—11月)的开山季节,其余时间都是大雪封山,鸟兽难行。在春夏交替的时候,是雪崩的高发期,在40度以上的坡度,当积雪处于不稳定且接近临界状态,一遇降水或狂风,受其触动必然发生雪崩。所以,春末夏初仍是翻山的危险时期。
通常,翻越多雄拉山的最佳时间段为每天上午,每当中午12点过后,多雄拉山口就会浓雾大起或狂风大作,这时再翻山,行人或会被狂风卷走,或可能因受冻而身体难以支撑,死在山口,迷路也极其危险。1988年和1989年,解放军两架向墨脱县运送物资的黑鹰直升机,也因为气候原因前后在多雄拉山坠毁。
从多雄拉一路下山,经过拉格、汉密、老虎嘴、到达背崩,沿途中需要穿越蔓藤交织、幽暗泥泞的原始森林,翻越地势陡峭、险象环生的大山,还要防备多种毒虫和蚂蝗的叮咬,路段都是依悬崖峭壁修建,万分艰险。当地对这段路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墨脱县路不是路,多雄拉上午过,一步两喘爬着走,走上坡进两步,退半步。下陡坡不是路,拄着拐杖倒着走。”如果在雨季走这条路,就进入了“地无三尺平,天无半日晴”的世界。三天的路程,只能顶着雨水踏着泥泞行进,一步一滑,双脚被水泡的苍白、肿胀、麻木。还要防备山上出乎意料滚下的石块。有的地方更是踩在泥石流和塌方上,更有面临被塌方覆盖的可能。
当地村民年复一年走在这样危险的道路上运送物资,每年从开山的6月起到11月结束。从早期的背夫运输,逐渐演变成骡马运输,如今公路的修通,背夫数量逐渐下降,当地村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背夫文化,以及当地的骡马文化,都将成为过去。
重返背崩乡
2006年,在我第一次徒步墨脱的行程中,背崩乡是呆的最久的一站。
那时,走过了最艰辛的汉密到背崩32公里路程,一路途径老虎嘴、蚂蝗区以及14处大小塌方,早已让人疲惫不堪。当远远地看见雄伟的解放大桥横跨在雅鲁藏布江之上时,豁然开朗的心情不言而喻。到达解放大桥,就意味着这一天的徒步结束,正式进入背崩。
背崩乡,犹如一颗美丽的绿宝石镶嵌在雅鲁藏布江畔,乡政府位于山坡顶上的原生态门巴族村落——背崩村里。这是个极美丽的村庄,一栋栋尖顶的木房(人字形屋)层层叠叠错落在山上,每当清晨白色的雾气围绕在村庄周围,宛如一处清新的桃花源。
住在乡政府的大院里,眼前一片绿色的草地,门巴族的一群孩子好奇地聚在我们身旁,那些孩子大多光着脚,飞快地在草地上奔跑,山上更可以俯瞰美丽的雅鲁藏布江。背崩乡,可以说是这一路艰辛的徒步之旅中第一次走入到稍微密集人烟的村镇。
炎热的雾气中,家家户户的走廊上,种着野生兰草,开出各色野性娇艳的花。这是雅鲁藏布大峡谷深处的自然优势,这里的村民,过得与世隔绝,悠然似神仙。
2012年5月23日,时隔6年,我再一次抵达背崩乡。
这是我第一次坐着皮卡车从墨脱县进入背崩, 2009年2月背崩公路竣工通车,省去了29公里的徒步路程。接我到背崩的朋友,由于越野车坏在了县城,只得在当地租了一辆皮卡车。朋友在县城采购了大量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他说通车后,不需要翻越多雄拉山,一些普通的物资都可以在县城买到。原需一天的步行,现开车只有2个小时。然而,墨脱依然展现出车通不久物资匮乏的一面,买两桶白色的乳胶漆,跑遍了县城只买到了不到半桶。
县城到背崩的山路已经修通,但坐在车上,依旧可以感受到在墨脱地区修路的艰辛——一些路段十分狭窄和泥泞,有的地方甚至需要闭着眼睛才会不那么害怕。经常跑这条线的司机却不以为然——“有什么怕的?现在好走多了,以前路只有一车宽呢!”这条路如今仍是时断时通,一场大暴雨后,常常又被塌方阻断,需多日维修。
车子终于到达背崩,车窗外瞬间挤满了当地人好奇而热情的脸。
这时,我忍不住向四周环顾——依然美丽的背崩,依旧热情的门巴人——我们顺着沿山的梯田而下,一直从背崩村铺展到山脚下的营部(墨脱戍边模范营)。
背崩,我又回来了。
逐渐消失的背夫
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我从山脚下的营部,走往山上的背崩村——也是“重温故里”,去往乡政府的所在地。
五月底,不下雨的背崩甚是闷热,没爬多高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路旁,有一排被阳光照的金光闪闪的风旗,光线透亮,让人睁不开眼。
乡政府还在老地方,新修了水泥房,门前堆满了建筑材料,不见了当年鲜绿的草地。这些年的背崩,随着通车,变化自然是不小。派出所工作的一名“郭达”(门巴族里对于男孩的称呼,女孩则叫“乌鸡”)带我去村里家访。准备去拜访一位老村长,被家人不好意思地告知:已经喝醉了。随即,我们来到一位老背夫向荣的家里做客,一进门,首先接受了主人敬的三大碗黄酒。三碗下肚,已经开始有点微醺了。
酒带出了回忆。
今年46岁的老背夫向荣,从13岁起就开始背东西了。早期的墨脱,没有马,靠的是人力运输。80年代开始,随着骡马道的打通,马帮逐渐代替了背夫运输。最开始,墨脱县的骡马运输主要是地方政府和部队组织,近20年来,进入墨脱县的物资需求急剧增加,民间骡马驮运也随之发展起来,一些有经济条件的群众购买马匹,参加山内外的运输,增加经济收入,也用马为自己到山外销售土特产品和采购。向荣说,当年赶骡马最多的时候是同时赶8匹,马是乡政府的,帮着乡里运输,自己也赚一些劳工钱,顺带运一些自己的东西。
向荣并不是专职的背夫,主要形式还是以赶骡马为主,为了与骡马的速度保持一致,他们不能负重太多,沿途没有休息的机会,只能跟着一直跑。向荣说,他每次最多只背50斤,而那些专职背夫最多可以背到120斤以上货物。
从背夫的双肩到骡马的碎步,墨脱缓缓前进了一步。而包袱里的货物,也随之改变。
80年代,门巴人每年翻山出去,运输的大部分是食盐,这是他们最缺乏的东西。到了后来,也主要包括清油与大米以及派镇的干核桃、奶渣。有些物品是可以用背崩本地的特产予以置换,例如,当地的竹编篓;一种被当地人称为“那尼”的草药,据说是一种可以当烟抽的藏药,有筷子那么粗。向荣说,当时盐是五毛钱一斤,通常一家人一年会吃上五、六十斤,那时看来,盐十分贵重,因为是无法用东西置换的。如今通路后,盐的价格便宜了许多,不再是“奢侈品”,家里的用盐量也增加了三四倍。
小小的山路,直通饭锅。
在门巴人的伙房里,时常可以看见房梁上挂着一块块猪油,有的是用猪肚包住,像一个个囊。背崩乡主要的农作物是以水稻为主,其饮食习惯与内地人很像,炒菜为主。但在以前,一日三餐里,很少见到油。按照当地人的传统,每年只有过年时,才可以杀上两头猪(这是村里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情况)。把肉去掉,留下皮和脂肪(肥肉),将盐均匀地撒上(作用是防虫保鲜),再倒上本地的包谷粉,放上两个月,等到收稻子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每次吃的时候,就把肉割下来一点,在锅里化成油。背夫向荣说,这些油必须省着吃,因为要吃整整一年。
说起在过去运输路上的艰险,向荣说,其实自然灾害对他们本地人的危险仍然是不大的。因为同通常他们会选择一年中最好的5月到8月三个多月的时间去运输。这并不像普通背夫,4月和11月仍然还需要背运。但让向荣记忆犹新的是80年代最危险的路段“老虎嘴”的样子。在还没有打通马行道之前,当地人用一种白色的光滑的石头,修葺在悬崖峭壁的边上,这段路赶上骡马可想而知。
除了背夫的身份之外,向荣还在当地村里行使着一些喇嘛的职责。我们来的时候,正好一家人在举行法事。村里有人过世,按照当地人的习俗,第21天和49天都会举行一场法事,全村人都会参加。而向荣负责神圣而庄重的敲鼓仪式。
向荣有7、8年没有出去背过东西和赶过骡马了,他自称现在已经退休,开始养老了。家中运输的活儿,也交给了他的大儿子达瓦森格。达瓦森格在背崩也算是小有名气,公路刚刚修通的时候,他一狠心投钱买了一辆皮卡车,很快就从骡马运输转型成汽车运输。不光如此,他还在背崩村里早早开起了客栈、餐厅以及小卖部。今年,达瓦森格又卖掉皮开车,贷款买了一辆三菱猎豹越野车,继续做着跑车的生意。
如今村里参加背运以及骡马运输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在背崩的这些日子,我们曾想雇背夫从背崩往返汉密进行采访,背夫居然成了最难寻觅的人。最后由于连续多日的降雨而取消了行程。
据统计,背崩村全村现在有100多匹骡马,不过都用不着了。村里像向荣一样的老背夫,说退休后最大的心愿就是每天吃饭喝酒,生活无忧。向荣家里最老的一匹骡子也是7年前买的,这些骡马现在只是偶尔帮着在附近运输一些东西,并不会再走远路了。而向荣家里,如今再没有一个背夫了。
他们代表着墨脱一个时代消失的背影。
泡在黄酒里的生活
在墨脱的一系列采访中,明显感受到,没有好酒量还真的不行。去当地人家里,必须要喝酒,从黄酒、啤酒喝到藏白酒,有人甚至故意以不喝酒就不接受采访的“热情”态度来“刁难”我们。冀文正曾经就有描述在门巴族家里去做客喝酒的规矩:客人喝醉了,主人会认为看得起他,很高兴。若客人拒绝喝酒,将会受到特殊的惩处——别人喝多少,就往他都上浇多少,弄得满头满身湿透。
门巴人离不开酒,就像藏族人离不开茶。在门巴族的任何一个村落,家家都会酿酒,走进门巴人的家,伙房里吊着一串串黄色酒曲,是当地人酿黄酒专用的发酵引子,被称为“旁”。他们一年酿酒用掉的粮食,比吃掉的还多。背崩村也不例外,人人面色红润,坐在自己家的木廊上饮酒聊天,看见我们的到来,招呼着——“来喝一点”。
当地人笑着告诉我,这就是门巴人的特色,无论男女老少每天清早起来就开始喝酒,喝的是用当地特产的玉米和鸡爪谷酿的黄酒。门巴族的黄酒,藏语音译过来叫“曼加”,意为“鸡爪谷酒”。鸡爪谷系禾本科农作物,籽如白菜籽,色紫黑,穗头如爪状,生长期4个月,是当地重要的粮食作物。
门巴人的伙房里总是会挂着大大小小的葫芦和竹筒,都装满了发酵的酒,大人小孩饮酒如喝水。引用时,门巴人取出若干酒酿,装进一个下部有塞子的竹筒内,兑上凉水。拔开竹塞,缓缓流出的就是清凉可口的“曼加”酒了。这“曼加”酒度数不高,仅10度左右。初喝起来有点苦涩,由于每家酿的味道都不同,有的也略显甘甜和酸甜。喝惯了倒也清凉甘美,在夏季有着提神消暑的作用。我在一家门巴人家里,亲眼看见主人喝酒时,顺便给自己五个月大的孩子也喝——他们从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喝黄酒了!
无论是人背运还是骡马运输,黄酒在运输途中也起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门巴人的古老观念中,路上的高山、森林、河流里都有鬼神存在,遇到自然灾害和风险,都是鬼神作用的结果。饮酒表达对出行者最诚挚的祝福,并且能够辟邪驱害,保佑参与长途运输的亲人们一路平安。出行前,全村人要与出行者相聚一天,有人还请村中喇嘛念经祈祷,择定吉日。这时候的酒,与平时饮酒的含义也是不大一样的。每个家庭对这时酿酒的质量更为重视,习惯上人们认为,若酿的酒发酵,他们的心中就不安,认为不宜远行。要出山交换的家庭,如果觉得自己的酿酒技术不佳,就要请技术好的亲临指导,以便酿出味道醇美的酒来。
在这深山之中的酒乡背崩,空气里总有一股含糊不清的味道,一开始我不知道这味道是什么,却总是让人有一种迷迷糊糊快乐的感觉。就连看似沉默的村庄,都好像暗藏着热烈的情绪。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明白,这就是一种酒的气息,一股热乎乎、温润的、带有力量的气息。
在天地的角落,人们要生存,也要生活,还要尽可能地快乐。
怪杰拉伯雷在16世纪写成的法国奇书《巨人传》中,描写了巨人们寻找世界真理之旅,结果,他们走遍四海,从真理之泉中只听见了一句话:喝啊!
背崩的村民们显然找到了真理之泉,随时保持着一种微醺的状态来生活,糊涂清醒,各占其半。这也许就是人人向往的一种神仙般的生活。
我还是想拜访那位老村长,可连去三天,他都已经早早地醉倒了。
背崩,烟云如雾,山河如醉。
背崩完小与一位老人的故事
背崩乡的完全小学,在背崩村的一侧,爬上山坡可以看见一座显眼的二层的水泥白楼房。学校始建于1976年1月12日,前身为背崩村民办学校。从早期的只有1名任课老师,25名在校学生到如今有24名老师,231名学生。从只有一至三年级的3个班级到现在的从学前班到六年级的7个班级。36年来,背崩完小的发展与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这座学校的全名是“上海印钞厂墨脱背崩希望小学”,之所以叫这样的名字,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与一位来自上海的陈正老人息息相关。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望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这首诗描写的是战国时代的老人侯嬴。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惊涛骇浪中,指挥若定的正是这位魏国普通的城门看守侯嬴。在信陵君大军发出时,也是这位老人,自刎为大军壮行色。千古之下,其雄浑气派,丝毫不减。
七十老翁何所求?1980年从上海印钞厂退休的陈正老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如同秉烛夜游的学者,在暮年踏上了向人生朝圣的旅途。在美国电影《遗愿清单》中,两个身患绝症的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来到喜马拉雅山。而陈正老人则一步步地实现了这个心愿。
他承诺自己要在生命熄灭前爬100座山。
1995年,陈正来到了喜马拉雅山东麓,他一心要翻越多雄拉雪山,进入神秘的墨脱,这一年他75岁。然而他的雄心却被兵站的站长所打断,多雄拉太危险,绝对不适合这个古稀老人翻越。
陈正老人并没有打消这个念头,他认识了一个在林芝读小学的墨脱姑娘扎西玉珍,并向这个孩子学习门巴语。小小年纪的玉珍是多雄拉山的常客,她在墨脱读完三年级之后,不得不翻越多雄拉山来林芝读小学高年纪。上学校的路程,竟然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走过蚂蟥区、原始森林。在狂暴的雨季,甚至整面山坡都会滑坠到江里。
这条求学之路长达180公里,在雪山的那一面,墨脱县的儿童失学率高达70%。陈正老人努力学习门巴语,希望有一天,可以到墨脱给孩子们教书。
暑假时,玉珍启程回家乡,她说很快会回来。然而守候在林芝的陈正老人却再没有等到她的消息——12岁的玉珍在返校过程中,因吃了一包变质的方便面,死在路上。
老泪纵横的耄耋老人又来到多雄拉山下,面对锯齿般、刀锋般的雪山,考问着生命的意义。生命可以越过雪山,生命又如此脆弱,轻如一包方便面。生命究竟是什么?多雄拉雪山是否给出了答案?是否一定要将生命放在刀刃般的雪峰上,才知道其千钧之重?
陈正返回上海,78岁那年,他带着上海印钞厂全部职工为墨脱建立希望小学的捐款,回到了多雄拉雪山下。他谢绝了前来背他的4名壮汉,坚持要自己翻越雪山,走玉珍曾经翻越的道路,去早夭姑娘的家乡。
血压180/100,有心衰、房颤,脚水肿,这就是他的身体状况。然而这是一位老人对一座雪山的挑战,虽千万仞,吾往矣。这是老人对生命的承诺。
他翻过了多雄拉雪山,走过了玉珍曾经走过的道路,翻越了杨老三已经走过的山,蓝蓝将要走的山。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却走过了同样艰险的冰雪之路,找到了生命的重量。
在78岁这年,陈正走到了生命的最高点。
1998年,墨脱县背崩乡上海印钞厂希望小学建成。所有建筑材料,一砖一瓦都是在多雄拉开山期间用人力背进去的。这是一座被人背过雪山的小学。
生命如孤旅,生命如大醉。陈正和雪山的故事,正验证着那属于中国人浩浩天道:
七十老翁何所求?
探访边境地东村
从背崩乡向西南方向前进,顺着雅鲁藏布江水,就可以看见著名的非法麦克马洪线。紧靠这里的地东村原先曾是波密王深入珞瑜的桥头堡,如今地东是否依旧?难以抵达的麦克马洪线究竟是什么样?
从背崩村去往地东村,必须通过解放大桥,过桥后,一边是去往汉密的通道,另一边就可以通往地东村和最边境的西让村。
下到半山腰,解放大桥到了。6年之后,重新走上这座桥,感觉到它独特的沧桑感。在桥头,守卫在这里的军人,向我讲述了关于解放大桥的故事。
守桥军人 刘彦,26岁
“以前这边是藤竹做的桥,很古老,经常容易发生事故。后来修建了解放大桥。直到2000年的时候,因为易贡湖决堤,老桥冲毁了。花了9000多万元重新修建解放大桥。这些材料,全是人背进来的。包括桥上的大钢索,都是9个人一起背的。整整运了好几个月,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把这些材料备齐。
“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有10几个工人过年想回家。就急着出山,翻越多雄拉山的时候就被大雪覆盖了。
“守桥官兵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有一个守桥的老兵,整整守了七年,从来没有回过家。直到回家那次,他想家心切,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从背崩到了派镇。半夜到达派镇,当时出去的第一反应,是找游客借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流泪。这大概是03年的事情。
“我们平时每天6点起床,天刚亮的时候把桥门打开。一个人站岗,一个人在屋里。”
在这桥上驻守着,刘彦记不起有什么大事。
“驻站的时候,前任副连长,把站上的书全部看完了。书也少,然后他干什么呢?就把成语大辞典拿来背。书背了一半,就回家休假了。无聊到这种程度。
“06年的时候这里面有了第一座信号塔,是小灵通的,用卫星电话,打电话中间间隔很长时间,并且很贵,我们的一个战士,一个月欠了好几千块钱。
“在当地,流传着一个说法,外地人在墨脱这样闭塞的环境下呆久了,容易得一种‘病——墨脱综合症。得了这种病,最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数蚂蚁。看见蚂蚁搬家可以看整整一上午,有时候玩一直毛毛虫或老鼠,也可以玩一天。这些都是小孩子干的事情,不符合一个成年人行为的事情。”
也许这并不是传说,而在早期闭塞的墨脱,没有方式方法宣泄自己的情绪,会养成这样一种心里疾病,他们变得不语、单纯,与自然与动物格外亲近。
驻守在桥头,让上过大学的刘彦有大量的时间独自思考,在酒乡背崩,人人沉醉之中,这个重庆人最爱用的口头禅却是概括性的:“准确来说……”
“准确说,墨脱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点也不过分,女的还好,稍微清醒一点,男的每天都是微醺的感觉,脸红红的,见人就说进来喝点,这种境界很好。
“总的来说,要讲习惯的话,一个人对周边环境的妥协。客观上是我们对这边的环境的妥协,主观上是适应了。每年巡逻的时候,不要出事,维护好这边的和谐,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们三个人,一个排长和另外一个老兵,跟一个老百姓家签了一份协议,资助两个大女儿读书。现在一个女儿在读大学,另一个在读高中,我们还是很欣慰。”
离开解放大桥的时候,刘彦向我告别,并且没忘了“准确来说”。
“准确来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保持这边的祥和宁静,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其他的愿望都是微不足道的。”
去地东村,我是跟着换岗的战士们一起出发的。地东村距背崩乡乡政府所在地11.14公里。这11公里的路在墨脱的地域里算是很好走的了,上坡下坡的幅度不大,相对平坦。跟着行军的速度,去的时候因为正午天热,走了三个半小时。
地东和所有的门巴村落一样依山而建,沿山而上仍是大片的梯田。一进村,要爬一个数百米的坡,在村口看见很多百姓在水田里插秧,此时正是播种的季节。在阳光的照耀下,水田金光闪闪。也许我的闯入让当地人觉得惊奇,他们纷纷抬起头,随即又俯身劳动。
地东村隶属背崩乡管辖,全村97户共562人,是背崩乡人口最多的村。传说墨脱整个地区的地形很像多吉帕姆(金刚度母神)的化身,她的膝部叫地东绕东,即今地东村山头上。当年波密王嘎朗巴曾于1881年在墨脱地区设宗(县)宗址地东村,故曰“地东宗”。后因地东缺水,宗本(县长)聂巴朗 杰才将宗址改迁墨脱村的。
由于没有平地,所有房屋都由四根木头支撑着,两长两短。房屋上上下下,依次错落,翠竹、橘树,相映围绕,别有一番情趣。地处亚热带,地东的气候条件适合作物生长,这里的人一年四季都没有闲的时候。我正好赶上了最忙的时节,整个村落空旷而安静,在村委会的大院里,地东村的书记高荣向我讲诉了一些零散的关于地东的情况。
“村里面出去的都是女孩子,很多在县城和八一打工,当保姆,一个出去了,就介绍另一个。”高荣书记说:“村里生活很苦,也许她们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其实我们地东的气候非常好,物产也很丰富,柠檬、橘子和香蕉等都是这里的特产。有一种大柠檬(实为一种学名叫香橼的水果),有几斤重,味道非常香。”高荣感叹说:“国家也有一些种植和养殖的项目,现在还没有完全分到地东来,因为还没有通路。所有的成本都太高,一袋水泥到了我们这里就是400多块钱了。”
然而亚热带气候也有其可怕之处,例如热带病。“主要是地方病,以疟疾最为厉害。最近一次疟疾爆发是2000年左右,全村人都病倒了,不过那时候已经有了疟疾药,没有大碍。60年代早期的一次疟疾爆发,死了很多人。”高荣说。
村里有一个小小的卫生所,只有一名医生。没有药了,医生就自己去墨脱县城采购,到了乡里,再找人去背回村里。墨脱地区大部分地方都已经通车,医疗条件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据了解,墨脱县城已经可以做一些小型手术,可以照心电图和B超,而一些大的手术,通常还是会运往八一。地东村的村民,仍然继续走在背着病人翻山就医的这条路上。回想过去这条“人背上的路”,有多少人就因为路途遥远艰险而死在了路上。2006年,我在徒步墨脱的途中,就见到的一个病人被人用担架抬着翻越危险的多雄拉山。
地东村的旺加今年28岁,曾经是一个背夫。旺加全家共有7口人,取消了“刀耕火种”传统的耕种模式后,政府每年补助每人2000多元。随着背崩到县城公路的贯通,村里人大多从2009年开始停止了传统的骡马和背运的长途运输。
两年前,旺加从外面给家里背来了电视机和电冰箱,自己家的房子也重新盖了。他告诉我,如今最大的心愿是去拉萨朝圣,全家都在期盼着从地东到背崩公路修好的那一天,他们可以走出大山,前往心中的圣地。
临走时,在门前的走廊上,旺加和他的儿子站在那里,以一丝淡淡的忧愁看着我下山的路。
傍晚,村民们还在田地里劳动,一匹白马在半山腰悠闲地吃着草,夕阳坠落,照耀着宁静美丽的地东和它的南方。
最后我仍然没有看到墨脱与印度交界的地方,那个最南方叫做西让的边境村庄,还远在10公里处的深山中。
离开地东那个清晨,在回去的路上,我突然回想起看见的这样一幕:地东村的山上,一个淡黄色浴缸露天摆放在一栋房子的门口。这一定是有人辛辛苦苦从外面背运回来的,和电视机、电冰箱、报纸、信息和希望一同背了来。为什么要远隔百里背来一只浴缸?它承载着怎样的想象和期待?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最核心之地,在雾蒙蒙的夕阳中,躺在地东的山脊上泡一个露天澡,看着光渐渐退去,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这只浴缸仿佛一支无桨的小船,仿佛是洪荒时代就被巨浪泡在这里的遗存,像是承载人类最荒诞和最不可思议狂想的方舟。
我的想象力一下子无限延伸出去。这个场景的莫名出现,让整个地东村在我心里的意像一下子变得魔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