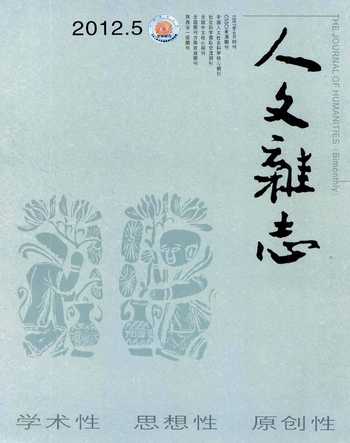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防区制下的军事贡役体制(1926—1935年)
王明前
内容提要 1926年至1935年四川防区制时代的军事贡役体制,具有行政变异性的特点。该体制是以军事机关取代民事行政为决策中枢,以团防建设为主要任务和以军事勤务为重要职能的县级行政为体制运行的关键环节,以依托保甲制度的团防建设为基层社会保障。其行政变异性表现为决策中枢层级的以军代政现象,以及县级行政的正常职能因以团防工作为中心任务和以战争勤务为重要职能,而呈现萎缩。这一体制始终潜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逐渐引发以军团关系不协调为表现的军事当局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四川防区制 军事贡役体制 行政变异
〔中图分类号〕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29-08おおお
1926至1927年间四川各派军阀纷纷易帜成为国民党新军阀的一个分支,但地方行政仍然沿袭自护国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防区制格局,并一直维持到1935年。对南京政府时期的四川军阀政治,史学界现有研究对四川防区制的性质与部分新军阀的行政努力做了探讨。①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或对防区制时代的地方行政缺乏微观研究,对其具体运作特点尚无规律性认识;或更多将关注目光投向防区制崩溃后四川行政格局的变化,反而对防区制时期地方行政本身缺乏必要研究。总之,史学界目前对1926年至1935年间四川防区制时代的地方行政,缺乏针对性的微观和实证研究。笔者根据档案资料,主要以重庆刘湘二十一军防区为分析个案,得出如下结论:南京政府时期四川防区制②时代的地方行政,是以军事机关取代民事行政为决策中枢,以团防建设为主要任务和以战争勤务为重要职能的县级行政为体制运行的关键环节,以依托保甲制度③的团防建设为基层社会保障的军事贡役体制,所谓军事贡役体制,其含义包含军事当局以军事暴力为后盾主导政治体制的目的和方向,和军事当局对基层行政与地方社会更多采取征收超经济的赋税“贡”和用于军事和工程的劳役“役”的两方面含义。这种政治体制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尤其常见于以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军事帝国,如古代亚述、马其顿、蒙古和印加等,中国元朝也具有类似特征,以作为征服者的统治民族向被征服民族征收贡役为统治方式。四川新军阀当局以军事机关取代民事行政为决策中枢,以团防建设为主要任务和以军事勤务为主要功能的县级行政为体制运行的关键环节,以依托基层保甲制度的团防建设为基层社会保障,行政关系具有浓厚的贡役特征。属于地方行政的变异形态。这一体制始终潜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最终随南京中央对防区制藩篱的破除而崩溃。
一、军事贡役体制的权力决策中枢:军事当局
刘湘是辛亥革命前后接受新式军事教育、在民初军阀混战中逐步崛起为地方诸侯的四川第二代军人的代表人物。他在1926年驱逐贵州军阀袁祖铭踞有重庆时,辖区不过巴县、璧山两县。但他在其后的第二次下川东战争中打败杨森和罗泽洲,抢占以万县为中心的下川东地区,从而巩固了在重庆地区的统治地位。截至1932年他与刘文辉的“二刘大战”前,刘湘二十一军防区在四川境内达到28县。刘湘二十一军在1932年二刘大战前的防区包括川东江北、巴县、綦江、南川、长寿、涪陵、璧山、铜梁、合川、武胜、石柱、酆都、梁山、垫江、开江、大竹、奉节、巫溪、巫山、云阳、开县、万县、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中江27县和川北邻水1县,另外还由于替参加中原大战的蒋介石填防鄂西18县,因此防区共计46县。(李白虹:《二十年来之川阀战争》,废止内战大同盟编:《四川内战详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266页。)刘湘为巩固其在川东防区的统治,一方面加强对部属二级将领王陵基、潘文华、唐式遵等的拉拢和控制,刘湘对部属的控制在同时期的四川军阀中是成功的,至少比无法遏制二级部属罗泽洲、李家钰自立的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和在二刘大战期间众叛亲离的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成功。对潘文华、唐式遵两位速成军校同学和王陵基这位军校恩师自然恩赏有加,不过对私下接受政敌刘文辉贿赂的蓝文彬采取果断措施则说明刘湘对部属的不忠仍然加意警惕。除了政治手腕外,刘湘防区的财富也使如王瓒绪和范绍增这样原属他系的部属不忍离他而去。刘湘还模仿黄埔军校形式开办培养本军系统军政人材的军校(罗伯特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56页),并以联谊会形式的武德励进会联络高中级军官的感情。(田一平:《武德励进会纪实》,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1984年,第189-206页。)另方面通过任用甘绩镛、刘航琛等能吏干员,建立起以嫡系二十一军为主导的军事贡役体制。
1928年12月20日,刘湘借第二次下川东战争之机,颁布戒严令,任命王陵基为江巴卫戍司令部兼重庆戒严司令部司令官,江巴卫戍司令部兼重庆戒严司令部公函(1928年12月2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1卷577。宣布:“我驻军区域奉军事肃清反动及图省府与裁兵实现起见,特联合友军协同戡乱,在此用兵时期为维持地方治安暨便利军事计,亟应根据戒严条例第三条之规定临时宣布戒严布告”。戒严令的主要精神是以军事机关代行民事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职能,规定:“在军警备地区内地方行政及司法要务限于与军事有关系,及以其管辖权限于各地之最高军事长官。但有权限争执时呈由军司令部决定之。于前项情形地方行政官及司法官须受该地最高军事指挥官之指挥;在接战地域内地方行政及司法事务之管辖权移交于该地之最高军事长官”,同时规定:“关于接战地域内与军事有关系之民事及刑事案件由军司令部或戒严司令部裁决之;接战地域县法院或与其管辖法院交通断绝时交与军事无关系之民事及刑事案件,不由军司令部或戒严司令部裁判之”。在戒严期间,军事长官拥有正常情况下无可比拟的权力,可以“取缔认为与军机有妨碍之集会结社罢工罢市或新闻杂志图书各种印刷品;民有物品可供军事之用所知因时机之必要得禁止其输出;检查私有枪弹药兵器火具及其它危险物品同时机之必要得押收或没收之;拆阅邮信电报或扣留之;检查出入船舶及其他物品或必要时得停止水陆之交通;监督指导各地民团农团等为各团体中有不法行为以致妨碍军事动作者得由军司令部或戒严司令部随时勒令缴械解散;接战地域内不论昼夜如适必要时得检查家宅建筑航行船舶等;寄宿于接战地区内之人民因时机之必要得令其退出”。虽然该法令假意承诺“因作战上不得已破坏人民之不动产但应酌量抚恤之”,但又事先强调“因其执行所受之损害不得请求赔偿”。二十一军司令部训令法字第172号(1928年12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1卷577。这一法令是刘湘防区军事贡役体制的发端。虽然该戒严令尚属紧急状态性质,但是一方面该法令强调军事机关的绝对权威,另方面又规定防区内军事当局可代行原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职权,并可全凭主观意志自由处置人民财产与人身权利,因而已经蕴含了军事贡役体制中军事机关代行民事行政这一主导因素。
1929年刘湘当局废除了民国以来沿用的重庆地区东川道行政区划,以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代之,聂荣藻:《刘湘防区时代的重庆教育》,重庆市政协文史委:《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1984年,第75页。从而初步建立军事贡役体制。根据1933年《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修正大纲》,政务处的职责范围基本涵盖了原东川道尹公署的全部行政职能,正副处长均由军长刘湘任命。该处总务科行使原东川道财政局的行政职责。该科第三股主管审核各县地方财政总分预计算;第四股负责审核各县田赋户口统计、各市县地方机关经费收支、事业成绩表编纂、各机关政务人员登记、各项实业统计以及团务统计事项。其内政科处理卫生行政、仓储及赈恤、地方自治、慈善及救济、寺庙管理、选举、市县行政官之任免考核、地方财政、礼俗宗教、禁烟、户口调查及人事登记等一般性民政事务。除民事行政事务外,政务处还代行司法职责。其司法科有督促诉讼进行、司法人员任免及考核、司法机关建设及改进、司法经费和监所管理等职责。建设和教育两项关系民生的事业则分设建设科和教育科主管。作为军事当局督导下的代行行政职能的机构,政务处的工作重点是团务工作。因为只有团务工作才能够充分承担军事当局所需的地方治安和军事贡役职能。政务处特设团务科办理团务。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修正组织大纲(1933年),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76卷31。
政务处的最终决策权掌握在军长刘湘手中。不仅“各科承办文件统由秘书主任秘书汇送处长副处长阅后,送军长判行”,而且“各科工作报告汇集后每星期送核一次,本处所属各机关工作报告汇编,准于下月五号以前呈报军长”。特别是政务处经费“由庶务员按月编制收支预算暨领款凭单送请该管科长转呈处长审核转送副官处汇呈军长核发”,修正政务处办事细则(1933年),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76卷31。均说明作为军事当局首脑的刘湘是二十一军防区的最高决策和仲裁者。
可见,刘湘当局以军代政,以军事当局代行地方行政职能,是四川新军阀当局防区制条件下军事贡役体制的权力和典章基础。军事当局代行地方行政职能,或可消除由于长期军阀混战造成的社会失控现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令统一和行政效率优化。但军事当局之所以强制代行地方行政职能,根本目的是要迫使地方行政和社会资源服务于战争勤务需要。正如法国组织社会学所分析:“权力不是某种权威机构的简单体现和产物,最多只是某种属性或某个产权。究其本质,这仅仅是行动者在某个特定的游戏结构中动用在其控制下合适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导致的始终属于偶然的结果,用以保证他们与其他游戏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与交易。因此这种关系作为各个不同行动者不同目标之间的特殊关系和自主调解关系时,总是和某个游戏结构联系在一起,这一结构实际上界定了行动者能控制的这些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必然性”。[法]克罗齐耶、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张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页。换言之,刘湘当局构建的由军事暴力机器加以维护的军事贡役体制,正是为了界定与控制作为决策中枢的军事当局与县级行政及地方社会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使之尽可能不具有偶然性,而更多具有可操纵的工具性的必然性。但是,由军事当局主观意志主导的军事贡役体制,在界定地方行政的不确定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地方行政本应具备的日常管理功能和与地方社会的有效磨合,从而引发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
二、军事贡役体制运作的关键环节:以团防建设为中心工作和以军事勤务为重要职能的县级行政
为实现对防区内社会资源的充分动员甚至超经济榨取,刘湘当局把县级行政作为其军事贡役体制有效运作的关键环节。
在以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取代东川道道尹公署的同时,刘湘当局发布《二十一军军区内县政府组织大纲》,以此为蓝本规划县级行政。一方面刘湘当局责成“各县户口应遵照中央颁定表示从速调查,按照县组织法区村里闾邻规定赶为编制完竣分别呈报备案”,以敷衍南京中央有关地方自治的行政建议;另方面刻意强调军事当局对县级行政的直接干预,要求“县政府各科科长在距军部较远之县得由县长遴选相当人员先行委任,一面查明该员履历报请本部核委”,将人事权控制在军事当局手中,并重点强化县当局的社会控制功能。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县公安局的组织上。大纲规定“县城设公安局,各乡酌设分局,先将常练改为公安队,除原有警款外即以原有团款为经费;各县财务局即由地方收支所及教育实业团款各收支员合并组织,局长下设各组收支主任负责掌管各该县收支并由县局督饬主管人员将收入款项首先清厘,次及统筹统支,在未经统筹以前仍应各归各款,不得挪移;各县实业局改为建设局”,并特别指出“各局局长除教建两局应照常供职外,公安局局长在本部未经简员委任以前暂准由县长择选相当人员呈候核委。各公安分局专由县专就本县合格人员选任呈请加委”,二十一军司令部训令务字1646号 本军区内县政府组织施行大纲(1929年3月3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76卷65。突出对县公安局组织工作的政策倾斜和审核力度。刘湘当局如此重视对县公安局的组织工作,目的在于借此加强对团务工作的监督与控制。1930年9月,二十一军司令部命令:“各县公安事宜并入县团务委员会办理”,二十一军司令部训令政字第8329号(1930年9月1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76卷59。从而实现了对团防的控制。
刘湘当局强化县级行政的职权特别是对团防的督导权,目的是使县级行政成为其军事贡役体制高效运转的关键环节。1932年至1933年间的“二刘大战”充分验证了这一体制的效率和县级行政的战争勤务功能。
这一功能首先表现为县当局协助军方维持地方治安上。如璧山县县长保证“在驻军开拔即调集各乡团队随时警戒防范甚严”。璧山县县长正局长吴国义致函二十一军军部(1933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76卷15。井研县当局“饬各乡办团人员克日恢复门户练,清查枪械弹药并各乡增加团练十余名,以维社会治安。此地接近战区,深恐敌军侦探及便衣队入城,目无驻军,督饬团防局调常练三十名,会同盐务缉私营第二队梭巡盘查防守城内”。井研县县长秦昆平致函二十一军军部(1933年7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76卷15。大竹县当局称“剿匪由梁竹粼垫四县清乡司令部办理,清共由清共委员会派员检查信电密探共匪踪迹”。大竹县征收局长罗鹏程致函二十一军军部(1933年7月),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76卷15。江北县当局“通令各镇乡仿照冬防办法设立哨棚更棚,派丁轮番梭巡,分驻各镇乡模范队,随时游击”。江北县县长苏学海致函二十一军军部(1933年8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76卷15。
其次,县当局还要不断应付军事当局征发的用于战争勤务的繁重劳役。在军事当局的严令下,各县当局为完成军事勤务任务不得不想方设法筹划铺陈。如1932年10月二刘大战第一阶段期间,作为二十一军防区最重要县份的巴县和璧山两县当局就不得不为力夫站的路线和转运方式问题自行协调。巴县县长向璧山县长提出如下建议:“县城起由白市驿直达走马岗为第一驿线,又以敝县城起由龙溪镇直达佛溪河为第二驿线。凡有部队由输出业西上此站,有运输力夫一到佛溪河接替换站后,自当选送璧山县城,即应由政府夫站交另派力夫接替前进。如军队由璧山县城东下至敝境佛溪河接替换站后,自当由该队另派力夫,接替转送。又如敝县运输至走马岗,接替换站特送至贵辖境来凤驿,则由该驿另派力夫接替送赴永川,如来凤驿代部队输送军用到达敝属走马岗,则该场又应援例接送来城,余则由此类推。庶呈以均劳逸而昭平允,至走马岗地当冲繁,兵站遵照已在该场设置兵站,并令饬敝县指派模范队两队共扎来凤驿借资策应听候调遣。敝县与贵属地唇齿相依界址毗连,对于夫站接替一层实有连带关系,特函达经希照并转饬连界来凤驿场与敝境团防切取联络,协商互助”。巴县县长致璧山县长函(1932年10月3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3卷621。
当然,军事当局出于其军事贡役需要,会对团防经费给以政策扶持。1933年5月11日二十一军司令部命令“本半年粮税附加每粮一两,着即征洋七元,但上届如有欠应即加入上数次内合并计算不得裹混重征。此外契肉丝车盐称等捐如系旧案亦准照列收,但须将契价总额呈报备查。公安局照章既应合并团委会原有公安经费,应即移做团款。各镇乡如旧有斗息猪称烟称神会庙产等项,团款应有该会酌量情形分别保留,作为民丁补助费。惟团款既经统筹,各镇乡如旧有租石租稳等捐应即一律取消,以后非经本部核准不得擅筹分文”。二十一军司令部指令政字第12813号(1933年5月1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76卷17。该令一方面取消了地方团防自主筹款的特权,另方面又对团防经费给以特殊关照,体现了军事当局政令统一的行政意图。
总之,县级行政当局在军事当局的威压下,只能通过加重对地方民众的盘剥来满足军事当局的现实战争需要。县级行政已经沦为军事当局构建的军事贡役体制下的战争勤务工具。
三、军事贡役体制的基层保障:与保甲制基层政权紧密结合的团防建设
民国四川战乱频仍导致社会环境长期动荡不安,成为团防建设的社会土壤。1919年3月颁布的《四川通省团练章程》集中体现了四川各界的团防建设理念。该章程于1926年12月被易帜的四川新军阀当局重新颁发,成为南京政府时期四川团防建设的蓝本。该章程宣称“以划一各县团练办法等重抽练门户壮丁俾能实行守望救助保卫地方公安为宗旨”。组织结构上以县团防局为基层领导机构,于“各县城内设立团练局总辖全境团练,以局长一人主之,仍受地方知事之监督;由局长延请本县公正士绅二三人择富有经验学识者充当本局参议,会商关于团务重要事件”,力求代表性与权威性的结合,即既强调县当局的督导权,又重视地方社会名流的积极参与。在编联上团防建设紧密依托基层保甲制度,规定“各县境内无论城乡市镇应按户编联团,十户为牌,公举牌长一人,十牌为甲,公举甲长一人,十甲为团,公举团正一人,由地方知事核准饬充,各团正隶属于团总头,附郭者直属于城内团练局”。在经费筹集上体现社会集资原则,规定“团练经费由知事督同局长将局用及全县需费各数撙节预算拟具收支表式呈送省总局督办核准;除原有团库仍作各该处办理民团及门户练经费外,只筹备常练经费应切实预算,按粮附带收捐由知事交众参两会孚议办法,办法呈核抽收方法或由征收局代收或地方公举正绅,由知事委派自行经理统收存储,由团练局请领分发备用,一俟匪风平靖,团练裁撤即日停止,前项所指原有团库以团保旧时置备办团之田宅年租神会解款及各地存款基本金生息之类是;各县筹集常练经费如因地方情形不同有不便于按粮附收者声明即由呈明准照省议会咨请筹集团费办法变通另筹”。四川通省团练章程,(1919年3月27日颁布,1926年12月6日重颁),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76卷119。
刘湘当局十分重视团防建设。根据1929年9月二十一军当局颁发的《改革团务办法》,团务工作的主旨是加强与基层保甲组织的结合。该办法规定:“照县组织法划定自治区为区村里闾邻者,即以自治区为团区,团长为甲长,每区为一区,团以区长为区团长,于必要时均得设副长襄办事务,但虽划分县自治区而未成立村里闾邻者,其场正以下团务人员应仍旧设置不得轻议变更”。经费筹集办法拟定以下四则:“粮税附加以统合其他附加计算不超过正税为限;租石捐率每石以二角为限,其起征数并须实收租谷五石以上;租稳捐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其起征数并须在五十元以上;大宗出产捐率由县团委会酌量地方需要情形拟订”。改革团务办法(1929年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3卷228。此办法虽然表面上规范和限制了征收额度,但较高的起征数足以保证团务经费之充盈。为把团务工作掌握在完全听命军事当局的县级行政手中,该办法特意强调“县团委会设正副委员长各一人,以县长为委员长,现任团委会委员长为副长,其未改建团委会者副长由团务局长充任”,使县长成为团务工作的核心,进而集中权力于军事当局。
其实,军事当局的根本利益考虑是建立符合军事贡役需要,并能够在战时实际承担地方治安和战争勤务职能的地方团防。为此军事当局在团队的建设和操练上用心良苦,经费方面更是给以政策倾斜。1929年颁布的《四川清乡督办署川滇边防督办署门户练纲要》,首先确定“门户练以挨户出练,一家一丁为原则”,体现寓团于民。具体办法是:“由团总督饬所属各团正编联户口十家为排十排为甲两甲以上或四甲以下成立为团,由团正挨户挑丁,凡年在十六以上四十以下者悉行编为练丁,禁止雇工长丁顶替充任,其因事障疑或有丁而不合格者,以免役费带之,团正选毕练丁造具名册三份,一份作底册,以两册交团总一存县署一存办事处”。编制“以十人为一班,三十人为一分队,三分队为一小队,五小队为中队,五中队为大队”。如无丁则必须交纳免役费,规则明晰:“团内大绅巨富本有合格练丁因游学营贸或其他障碍不能任操,每日铜钱六百或五百文;中人资产有甲项情形者每日铜钱四百文或三百文;薄有田产确无壮丁每日铜钱二百或一百文;小本贸易出外未归或现任教职各员每日铜钱一百文;单丁苦力资劳动在本团谋生计者每日铜钱五十文,鳏夫至四十以上及寡妇无子者概予豁免”。为提高团队的准军事化水平,门户练特意规定了枪械采购的量化指标:“团内粮户有地百亩或租谷百石以上者购甲种快枪一枝,地谷不满百亩但五十以上者购乙种土造枪一支,地谷不满五十但至十五以上者购丙种土枪一枝,大佃同,劳工及贫苦置听于丁种类择制一具”。虽然军事当局通过县级行政把团防建设的重要投资枪械一项硬性摊派给民众,但纲要反而强调这些枪械“虽系私人购置,但购得时须投凭团正注册编号逐一登记,并由本管团总分期汇报团练局转饬县知事备案”,四川清乡督办署、川滇边防督办署门户练纲要(1929年),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3卷188。等于变相剥夺了民团本应具备的自治性质和自卫功能。
总之,四川新军阀当局对团防问题的整顿与建设,本着紧密依托基层保甲组织层层落实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上,尤其在组织操练和经费落实上注重准军事化实效,发挥团防在军事贡役体制中的社会基层保障作用。由于团阀势力被清除,团防的这一保障作用基本能够满足军事当局的战争勤务需要。
虽然刘湘当局对地方社会战争劳役的征发是通过县级行政当局来实现的,但驻军就近与团防联络,或事出紧急直接求助团防征发贡役亦有发生。二十一军副官长王曜堂于1932年10月16日直接致函白市镇镇长萧奎全,称“军司令部命令拨夫三万名由贵镇办理拨交敝部一案,现已有日,刻因时机迫促,敝部应先事点编以便分拨,敝部兹定贵镇长烦为查照办理,俾利戎机”。二十一军副官长王曜堂致白市镇镇长萧奎全函(1932年10月1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3卷621。资料显示,由于刘湘当局对县级行政的强化与对团阀势力的清除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以军事当局为中枢、以县级行政为关键环节的军事贡役体制,在落实到基层团防层级时受到的干扰和抵制较弱,基本能够满足军事当局的军事贡役需要。
四、军事贡役体制的行政变异性
四川防区制时代的军事贡役体制是在民初军阀混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性。其他四川新军阀防区内的政治体制情况,如二十军军长杨森在其以渠县为中心的防区内推行“本军系统化”,重点抓团防工作,把防区内每县抽调团丁一营在岳池成立精练司令部加以训练,一方面充实正规军,另方面巩固团防维持地方治安。(马宣伟、吴银铨、肖波:《杨森的一生》,重庆文史资料(第四辑),1980年,第127页。)刘湘二十一军的军事贡役体制,因其体系完整,具有以军事机关取代民事行政为决策中枢,以团防建设为主要任务和以军事勤务为重要功能的县级行政为体制运行的关键环节,以依托保甲制度的团防建设为基层社会保障三大特征,而具有典型性。但是该体制毕竟不是正常运转的功能机制,而是具有相当的行政变异性。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该体制以军代政的行政设计,是其行政变异性的根本特征。其实,民国时代军事当局恃暴力凌驾民事行政之上的现象并不罕见。同时期各省多以军阀任省主席把持政务。如湖南新军阀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先后担任清乡督办署会办和省主席,但省政府和清乡督办署始终照常任事,并未被军部机关取代。即便上溯至北京政府时期,军阀主义的盛行也并未使代议制的国会制度消亡,省级行政督军署和省长公署长期并立共存。四川名义上虽然有省政府,但是在防区制条件下,省会成都由“保定系”的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和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三军联合驻军,刘文辉担任省主席;成都三军于1927年3月成立三军联合办事处负责协调驻成都三军的关系。是年4月又成立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由二十四军副军长向传义任处长,副处长由三军轮流派出。设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执法处、谍查室等机构,节制四川省会城防司令部、成都市公安局、市团防局、华阳县团练局以及三军共同担负的武装执勤部队,其功能类似刘湘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但并未取代民事行政机构,且管辖范围亦狭。(董维德、万金裕:《军阀统治成都的两个办事处》,成都市政协文史委:《成都文史资料选编(防区时期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83。)而“速成系”的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名义盘踞重庆。因此,刘湘当局撤销东川道尹公署而代以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一方面具有阻断“保定系”省政府向下层级的行政单位东川道发号施令的正常行政渠道,另方面也便利于军事当局直接督导县当局,强化其对团防的领导和战争勤务职能的锻造。
其次,正如前文所述,在军事当局的威压下,县级行政正常的民事行政职能被强行扭曲,是为该体制行政变异性的另一重要特征。
但是,这种非常态的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行政变异性特点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完全解决了的问题,或完全处于控制之下的社会。构成这些社会系统的个体或社会集体行动者永远不可能被限制在某些抽象而空洞的功能之中”。[法]克罗齐耶、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张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页。由于这一体制的主导因素是军事当局的暴力强制,一旦这一主导因素弱化以至于消失,这一体制必然陷于崩溃。除此之外,该体制即便在其全盛的1929至1933年间,其运转效率最高,且体系各层级磨合最协调的时期,也已经潜伏着巨大的制度危机。这主要表现为由于基层社会保障负担沉重,逐渐引发以军团关系不协调为表现的军事当局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征求无厌的贡役,特别是劳役征发,令地方团防苦不堪言。正如美国学者柯白所论:“由于强制力量作为取得社会权力的首要手段占了上风,发财致富便成为运用社会权力和强制力量的首要目的。政府和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参与勒索钱财。从社会中权势较小的集团尽量榨取财富已成为在社会与政治上出人头地的必然手段”。[美]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69页。如驻璧山县城炮兵七营连长王仕荣向巴县县长报告:“敝连前在贵府所领夫役八十名,夫头简银洲在璧山县领去夫役工资洋六十元,于途中私逃并率去夫役三十一名四处追寻无着”,炮兵七营二十七连连长王仕荣致巴县县长函,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3卷621。显系不堪忍受军方苛征集体逃亡的事件。其实这位王连长的暴戾行为早就为军运输处所察觉并申斥:“查此次新办力夫本埠及三里并江北各场均在担负,雇人多复杂,清查不易,且敝处应差只供短站,按站接替,劳逸较为平均,如果饬到前方供应驱策,其惟质与长夫何以区别,特换与运输之章处相抵触,否则追究无由”,二十一军运输处致炮兵七营二十七连连长王仕荣函,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3卷621。规劝他要尽量照章办理,尊重军方对地方“按次接替”的承诺,切勿把短期征召变为长期劳役。区区连长已如此蛮横,高级军官自然更是飞扬跋扈,以至于巴县县长唐殿丞致函模范三旅旅长廖海涛,苦苦哀求他能尽量照章办事,不致过分压迫地方:“顷接白市镇夫站报称,查近来本会奉令办理力夫,如职镇雇不足额则电话通知邻对各场补助送交等因,职镇遵办无异。兹模范三旅驻军需用力夫仅收本镇新办,如走马等即送交者不予收用。需镇地为永津孔道,此次军行所至,首当其冲,幅员有限,本处显雇交大多数之夫役,势将难能,请予转达驻军。章则规定名额由镇雇交只计人数,以不必分别区域,期曷办到等情。按此即查该站势难独立担负此多数夫役如属实在情形,特函转请各吾兄特别转饬按照章则规定如数派送于点交后即不再令该镇垫给伙食一切”。巴县县长唐殿丞函致模范三旅旅长廖海涛函,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3卷621。廖旅违背章程规定,欲将白市镇短期劳役改为“垫给伙食一切”的长期贡役。对此刘湘当局也曾下令规范征发行为。如1932年10月23日军方电令前线部队把长期违规征用的巴县民夫和骡马释回备用,并命令“各部下级军官不准将巴县驿站力夫作为长夫,不准以力夫充作兵士”。原件无抬头落款,时间1932年10月2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3卷621。但这种官样文章难以约束和遏止军方的胡作非为,以至军团冲突时有发生。江防军第一旅的高成勋营长就因军团冲突而向巴县县长交涉:“敝营住黄沙溪六连三排排长卢炳章报称,因军队往来拉夫购菜维艰,于五月二十九日派遣戴辉先二人到黄沙溪村附近一带买菜,殊尽日不归,于三十一日乃派士兵探寻,始知与民邹春发因买菜口角致起冲突,被马王庙团防以估买等词干涉捆送县公署收禁”。江防军第一旅第一团第二营营部公函(1931年6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3卷621。在军事贡役体制下军方占有绝对优势,故此事件恐多系乡民不堪士兵强买而抗争的结果。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军方,团防方面也只有忍气吞声,至多发出如下劝勉:“驻防津巴綦南各军师旅团营各官长各士兵同鉴:溯自下东战事发生以来,攸逾三月,我津巴綦南四县大遭不幸,竟陷为屯兵之所,一切饷款秣器物需索供应诛求无已。在此三日之间筹借款项有多至四五次以上者,其数目每县过数十万元,多属逮捕逼勒以得之,而师行所经估拉夫役或关闭多人于一室以待应用,或鞭挞刀刺于道路以促运搬。然而良莠不齐系统各殊,务请各级官长对于所辖部队无论平时战时务必力为约束,并希下级士兵及务严守纪律尊重荣誉,不作扰民害民之细则”。快邮代电,原件无落款,时间1931年,据内容推定为津巴綦南四县团防局联名致军方电,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民193卷621军团关系的不协调,其实是军事贡役体制下军事政权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的反映,是该体制危机的重要征兆。
综上所述,1926年至1935年四川防区制时代的军事贡役体制,具有行政变异性的特点。该体制是以军事机关取代民事行政为决策中枢,以团防建设为主要任务和以军事勤务为重要职能的县级行政为体制运行的关键环节,以依托保甲制度的团防建设为基层社会保障。其行政变异性表现为决策中枢层级的以军代政现象,以及县级行政的正常职能因为以团防工作为中心任务和以战争勤务为重要职能,而呈现萎缩。这一体制始终潜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基层社会保障负担沉重,逐渐引发以军团关系不协调为表现的军事当局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这一体制随着1935年防区制的破除而必然走向崩溃。オ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本文受厦门大学985工程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资助。
① 关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四川军阀政治的著作可参见: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肖波、马宣伟:《四川军阀混战(1927-1934)》,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美]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三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相关论文:黄天华:《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王友平:《四川军阀割据中防区制的特点》,《天府新论》1999年第2期;张瑾:《二三十年代影响重庆城市变迁的几个因素—论刘湘对重庆的军人干政》,《重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王春英:《试论国民政府基层组织-区署建制在四川的推行及其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
② 四川防区制是四川军阀政治的基本形式,学术界一般公认萌发于1911年辛亥革命时滇军入川,完成于1919年熊克武划分防区。其中以1917年2月17日把持四川省政的贵州军阀戴戡和罗佩金发布“就地划饷”令对防区制形成意义重大。后来“就地划饷”逐渐演变为“就地筹饷”,地方行政官吏也由驻军委派,防区制终于形成。(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94页)。
③ 目前关于民国四川的研究一般认为四川实行保甲制是在1935年防区制破除实行所谓“新县治”之后。如冉绵惠:《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推行的历史概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11期。但只要符合嫁接在基层政权之上的以户口清查和编户连结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控制,以及由基层政权负责人主持的团防建设这些条件即可认定之。因此笔者以下研究足以证明四川防区制时代不仅存在保甲制,而且保甲制在军事当局的营造下达到了准军事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