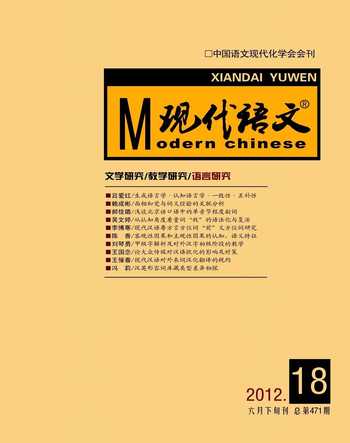面相知觉与词义经验的关联分析
赖成彬 张平
摘 要:维特根斯坦认为,“面相知觉”这一经验不能通过视觉印象或者对视觉印象的解释得到合理阐释,这种经验坐落在人类的实践和反应这个大框架中。类似地,语词似乎是意义的显示,词义经验根植于使用语词的技术。语词是经验的表达而不是对它的描述。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面相知觉视觉印象词义经验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第二部分有相当篇幅探讨“面相”问题。虽然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是由克勒的格式塔心理学激发起来的,但是他的旨趣不只是批判心理学理论,而且也在语词含义和理解他人心灵这两个问题上进行批判。本文主要分析维特根斯坦是如何探讨面相知觉与词义经验的问题以及这两者的关联。
对面相闪现这种现象,心理学或者认为这是由于视觉印象的“组织”发生变化,或者是由于我们对视觉印象的解释发生变化。维氏通过对“看见”“看作”等概念的分析,澄清了心理学上的混乱。他认为,面相闪现是根植于特定的学习和训练而获得的能力或技术。同样,在经验语词意义这种情况下,语词也有它的“面相”,我们不是把语词知觉为需要解释的声音或记号,而是直接就知觉到意义。这种能力不是精神的意谓功能,而是根源于我们在语言游戏中形成的运用语言的技术。语词的根须渗透在感性经验的土壤中,感性经验凝聚、结晶为语词的意义,语词标识着概念层面的理解。[1](P155)当我们掌握了语词的使用技术,语词似乎就“吸收”进它的意义,我们就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它。而且,我们对事物和行为活动的感觉,并不是有待整理解释的感觉与料,我们直接就在意义的层面上感觉到它们。
一、“面相闪现”的心理学解释的背谬
心理学从错误的、矛盾的视觉理论出发来解释注意一个面相这类经验。内省心理学认为,我们只能说“看见”一个事物的颜色或形状(严格地说,连形状都不能看见),而不能说“看见”了这个事物本身;而我们之所以似乎又总是能够看见事物,实际上是我们将某种“意义”附加到纯粹的视觉材料上的结果。于是,在内省心理学看来,注意一个面相就等于“看+解释”了。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我们的感觉与料从一开始就不是零散的,而是整体性的;感官本身就具有组织功能,因此,感觉与料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组织成一个整体了。
维特根斯坦通过概念考察,指出了上述两种心理学的混乱。在做这种概念考察中,他引入“持续地注意一个面相”“面相闪现”“面相盲”等概念,并且指出面相闪现这种视觉经验的根本特征是它内在的矛盾性。他说:“我端详一张脸,突然注意到它和另一张脸的相似。我看到它并没有改变,但我看得却不一样了。我把这种经验称作‘注意到某个面相。”[2](P230)在面相转换后,我们感觉到一张脸或一个图形与先前我们所见的完全不同了。然而我们又明白,这里并没有改变,还是那张脸、那个图形。但是面相盲患者却经验不到面相闪现,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意识到两张脸的相似之处,他只是不能经验到一个面相转跳向另一个面相。[2](P256)他通常不会说,他现在看到的图形和先前看到的既一样又不一样。经过面相转换后,他似乎看见一个不同的对象,两个面相之间似乎是不可共存的。
换句话说,面相盲患者意识不到面相转换中的矛盾。由于对这种矛盾的困惑,心理学家自然构造出矛盾的理论。维特根斯坦关于面相闪现的探讨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困惑。
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事实上是对象改变了,这才引起我们感觉到对象的改变,那么这种矛盾感就消失了。当然,他们所说的对象改变,并非是说对象本身改变了,而是说我们主观上所看见的或我们的视觉印象改变了。维特根斯坦指出,心理学家把视觉印象当作某种内部对象、内部图画。“内部图画”这概念的范本是“外部图画”,然而这两个概念词的用法并不相似。[2](P234)如果我们的视觉组织发生变化,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再现、描述我们的所见,来显示这种变化。但是我们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在看一幅兔鸭头图,我们所知觉到的变化是无法在我们的描绘中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用语言来表达出两次所见的不同。因此,格式塔把视觉印象看成一种稀奇古怪的摇来摆去的结构。[2](P234)这种关于作为一种意识现象的视觉印象的观念是空洞的,我们既说不出这种特别的意识对象为何物,也说不出我们同它的关系是怎样的;作为私人经验的视觉印象是哲学和心理学上的幻象。[3](P223)那么,我们可以说,在面相闪现时,不是视觉印象的特性在发生变化,而是我们对它的解释发生变化吗?比如,当我们突然把一个立方体的平面示意图看作一个立方体时,我们是直接知觉到一组线段,然后对它们作出解释吗?维特根斯坦指出,如果是这样做,我必定能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描述我的知觉经验。只有存在直接描述时,间接描述的说法才有意义。这就像我必定能谈论红色而不必把它作为血的颜色来谈论。而且,从概念的范畴类别上可以区分出:看见是一种状态,而解释则是一种活动。维特根斯坦说:“每次我都实际上看到的不同抑或只是以不同方式来解说我所看到的?我倾向于说前者。但为什么呢?——解说是一种想,一种处理。看是一种状态。”[2](P255)这就是说,在面相转变这种情况下,并非我们两次看见的是相同的东西,只是做了不同的解释,我们两次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东西。在面相转换时,两种视觉经验中的差异并非源自对象本身的某种客观改变,而是源自主体将这幅图放入不同语境的方式上的差异。我们不可能按照解释来看到一个东西。当教科书把插图解释成某个东西时,它既不是在对直接性视觉经验作间接的描述,也不是在强迫读者以特定的方式看这个插图,而是在表达某种基本的经验。
二、面相知觉依赖于生活实践
掌握“看见”的语言游戏需要学习和训练,“看见”这种能力标识着我们与事物、对象的实践关系和我们对它们的态度。
维特根斯坦在看兔鸭头这类双面图形时,引入“图画对象”这一概念。只有在存在面相转换的情况下,比如只有在我们把兔鸭头图有时看作一个兔子头,有时又看作鸭子头的情况下,“看作”这个概念的使用才有意义。在这里,我们所知觉到的兔子头图和鸭子头图是完全重合在一起的,引入“图画对象”这个概念来谈论我们的所见就很有必要。就我们与“图画对象”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强调了三点:首先,当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对象,我们看见的是它描画的对象——我们描述对图画对象的知觉时,谈的是它是关于什么的图画,而不是图画的符号。其次,我们把握图画对象时,我们毫无疑问地把图画对象与它描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比如,当别人需要我解释图画兔子事实上是什么,我们既可以指向别的兔子图画,也可以指向真实的兔子,谈到真实的兔子的行为,在这里我们不做区别。第三,我们对图画对象的关系有时就像我们与它们描画的对象的关系——比如,我们有时对待图画脸就像对待一张人脸,就像对人脸上的表情一样对它作出反应。我们对图画脸的阴险会反感,对笑脸会感到愉快。[4](P250)我们用图画对象所描绘的东西来描述它们,我们把图画对象与所描绘的真实对象归类在一起,我们对图画对象的反应类似于对它们所描绘的对象的反应,这些做法、态度显示出我们把图画对象的表现真实的作用视为自然而然的。
维特根斯坦强调,应当把“持续地看作”理解成一种特定的态度。当我们在画上看见一个动物被箭穿透,箭从喉咙穿进去,从脖子后面穿出来。我们不会说,画上的这两个线段表现一支箭的两部分,而是说我们看见箭。如果让我重新画出这幅画,虽然我会画得不准确,但多多少少会显示一只动物被箭穿透。“在我看来那是一只被箭穿透的动物。我把它作为那个来对待;这是我对这图形的态度。这是称之为‘看的一种含义。”[2](P245)因此,“看作”与“知道”不同。“看作”标识出我们与图画的对待关系。“我们把照片、把墙上的图画当作它们所表现的对象本身(人、物等等)来对待。”[2](P245)而仅仅“知道”图画表现的是什么的人,缺乏的正是这种对待图画的实践能力。“面相盲患者”就是这类人,他们并不缺乏知觉能力。“一个人把图形看作动物,另一个人只是知道它表现的应该是什么;我在这两个人那里所预期的会是相当不同。”[2](P245)看与知道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看时的直接性。我们以这种方式直接看到一个图形,总会倾向于这种描述。这是种直觉反应能力。比如,在画上看见一个动物被穿透这一点不会看错,尽管我们在识别这只动物是什么动物上可能会弄错,或者把箭错看成矛。总之,我们总会对图画作出某种方式的反应,总是在意义层面上看这副图画。
维特根斯坦指出,“看”“看作”这些概念标识的能力是与行为的精微层次相关的。在谈论画法几何学中使用到的图形时,维氏说,对图形的熟悉的操作能力是“看”的标准之一[2](P242),一个能以立体方式看这个图形的人在描绘它时的方式,是不同于仅仅知道它是立体图形的人的——比如,在图形中移动铅笔,就好像在一个立体模型中移动铅笔一样,或者用手势指示出图形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一个人要是仅仅知道这图形是代表这样的立体空间关系的,那么他在做这些动作时会很犹豫的,他的行为说明了他并没有把图形的三维性质看作是当然的,他与这图形的关系不像他与图形所描绘的事物的关系。
然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把“持续地面相知觉”这一个概念只限于图形对象的范围内,他还在这一概念下讨论了照片、绘画等。这些表现性的作品不像兔鸭头图,不具有两个以上的不同的面相。但是,这些图画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作用也预设了我们对它们的一种特别的态度,我们对照片、绘画的态度就像我们对它们表现的对象的态度。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常常以这种方式对待照片和绘画。比如,我们并不会一看见爱人的照片就去吻它,我们也不会在圣像的凝视下总是觉得羞愧。但是,这些行为正是依赖于一个普遍的事实:人们描述、对待绘画和照片时是把它们当作所表现的对象的。对于只能知觉到线条、色块并用它们来描述图画的人,这些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对我们来说最自然的是以立体方式表现我们所看到的,而无论通过绘画还是通过话语来以平面方式表现则都要求特殊的训练。”[2](P246)
三、语词是情境因素的结晶
“看到面相”和“经验语词含义”之间可以作类比。语词会唤起我们持续的意义知觉,语词不是被我们知觉为需要解释的声音或标记,我们直接就把说出的或写出的符号知觉为有意义的词语和句子。词语似乎在它的“面相”中携带着“含义”。但是,“含义”或者“意义”并不是我们在使用语词时精神上所意谓的东西。一个通常用于报道说话者意图的词语,实际上是用来表达特定环境中的经验。所以,我们不如不说“这个词有这个意义”,“我们用这种方式意谓这个词。”我们最好转向这种说法:“我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词。”“意义”这个词的原始用法是与使用和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与使用一个词的技术相联系,与在某个环境中某个说话者的特定意图相联系。但是,当我们孤立地不派用场地说出一个词语,它就不构成语言交流的一部分,但它也会似乎带有一种特定的含义。[2](P258)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语词视作某些情境因素的结晶,所以就会倾向于用“含义”或“意义”来谈论它。
我们这里并不是谈论语境主义。许多语用学研究者从语境主义的角度去阐释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词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这句话。这是望文生义地理解这里的“使用”一词。维特根斯坦关心的是使一个语词具有意义的那些一般事实,即生活形式,以及这些事实对语词使用的规定作用,即哲学语法。而语用学探究的是特殊事实。比如“张三上课去了”,我们对这句话中的“上课”一词的理解依赖于“张三是老师”还是“张三是学生”这些特殊事实。如果要用“语境”一词,不妨可以说,语言哲学关心的是一般语境,而语用学更关心特殊语境。“话语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带着自己固有的‘语境来的。并非语词是些死的东西,只有放到生活中才活起来;语词本来就是生活经验的组织。”[5](P382)在语言学习中,语词使用的恰切的周边环境就是使用的标准。P.M.S Hacker指出:“标准的改变也就引起意义的改变。”[6](P311)并不是我们的精神赋予语词以意义,也不是我们的随意使用赋予意义。意义是由语族的共同生活经验规定的。
正是由于某些生活情境结晶在语词中,语词才对我们呈现出某些面相。词语的声音面相似乎记录着我们知觉到它显示给我们的东西这样一种能力。当我们把词语当作有意义的东西来对待,也就是正确地知觉到语词中可以被知觉到的。这种反应能力或实践能力是“持续地含义知觉”的必要而非充分的前提。比如,在说出英语单词“bank”而意谓着河边,这里预设了我们对这语词有不只一种含义的感觉和区分这些含义的能力。我们也能把词语与邻近的词语比较对照,并比较它们不同的使用技术。经验语词含义的人不只是把语言看作以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各个元素在其中有特定位置的结构体,而且能感觉到语言中的精微变化。这种感觉渗透在语词正常使用时的现实环境中。这一点可以从英语学习者在听到英语中的一个大数字时的反应这个例子看出来。当我们听到英语中的大数字一时不明白,得先翻译成汉语数字才明白。当然,在英文中我们也理解,不然怎么能翻译成汉语呢。但这种理解是技术性理解,不是自然理解。在技术性理解中,我们只是知道,却没有感觉。我们对“two hundred thousand”往往要翻译成“二十万”才有感觉。
正是这种对语言、语词的精微层次的感觉能力,使我们能够选择、评价词语。一个词语是否是我们要寻找的,对这一点我们常常凭直觉就知道。但是要我们说出这些评判的根据往往就很困难。词语常常是迫人而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冒出来”。说到词语的这种细微的审美差别,我们有时也有很多可说。“这些词中的每一个都和其他词语句子盘根错节地联系着,而这些联系都是可以讨论的。事情恰不随着那个判断了结,因为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词的场。”[2](P264)对这些盘根错节的联系的判断力,对这种场的判断力,是一种直接的能力,我们往往不能说出清晰明确的根据。这种直接性说明了一种深度,语词使用的规则是被我们深深地同化了的。常常是这样,一个词与其他词的精微复杂的联系把我们领到直接的语言差异之外,把它们与非语言现象的联系也包含进来。语言与现实从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在语言游戏中我们学会使用语词,这种技术把语词置入、编织进非语言背景中。[5](P184)反过来,我们对这个背景的感觉也会被同化,这就有助于我们使用语词时能感觉到它合适不合适。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关键之处不在于我们对语言和非语言的环境的各种规定性的意识,而在于这种意识在我们心灵中的弥漫性和深度。仅仅对语词使用的各种规定性的意识并不能保证我们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语词。仅仅具有这种意识,我们还不能感觉到语词似乎“吸收进”它的含义。这就像面相盲患者,他们仅仅知道一幅画所表现的是什么,却不能对图画作出正常人会表现出的反应。比如,面相患者即使知道一个圣像是谁的画像,却无法理解有些人在圣像的凝视下会羞愧。在我们最初学习语词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明确的指示就可以理解语言。这是人类的一种自然能力。语言训练产生稳定的结构,意义按照那种结构逐渐呈现出来。[7](P92)人的经验、行为是在意义层面上显现的,这也就是说是在语言层面上显现出来的。语言就是经验的表达而不是描述。
(本文系昆明理工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语言分析与观念批判”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118262。)
参考文献:
[1]陈嘉映.无法还原的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M.麦金.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研究》[M].李国山译.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Stephen Mulhall.Seeing Aspects.Wittgenstein:A critical
Reader[M].edited by Hans-Johann Glock.Blackwell Publishers,2001.
[5]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P.M.S Hacker.Insight and Illusion(Revised Edition)[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7]约翰·希顿.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M].徐向东译.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5.
(赖成彬 张平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6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