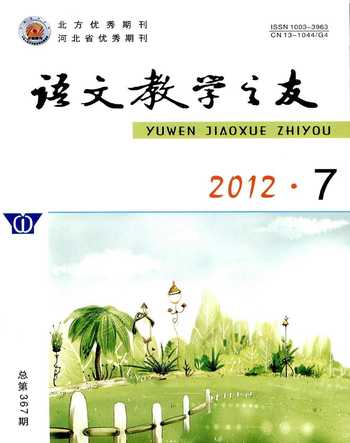《五人墓碑记》中的几处辨析
赵如刚
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对《五人墓碑记》中几处词句的解释略有不同,有的仍有疑点。笔者不揣浅陋,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家。
一、“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中的“社”指何“社”?
人教版、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将“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中的“社”都简单地解释为“应社”,而人教社的教参在翻译该句时却将之译作“复社”,到底是“应社”还是“复社”?值得一辨。
近人朱倓撰写的《明季南应社考》里说:“应社始于天启甲子(1624年),亦倡于常熟。”复社则是张溥与同乡张采等人集合郡中名士,联合南北诸省若干文社,于崇祯六年(1633年)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创立的爱国社团(参见《辞源》《辞海》中“复社”词条)。《明史·徐汧传》记载:“周顺昌被逮,缇骑横索钱,汧与廷敛财经理之,当是时,汧、廷枢名闻天下。”
由此可知,应社成立于天启四年,复社成立于崇祯六年。史载张溥是应社的创始人之一(杨廷枢亦为应社创始人,徐汧是应社成员),又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复社的成立比周公被逮时晚了七年。课文中的“社”处在“周公之被逮”时的具体语境中,当确定是应社。这样,作为“吾社之行为士先者”的杨廷枢、徐汧等人,在周顺昌被逮后“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才有了妥贴的注脚。
二、“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中的“今”指何时?
对于“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句,要辨其时间上的真伪。“今”指何时?文章写于何时?我们知道,张溥的文章写于魏忠贤自缢之后,这由《五人墓碑记》中“待圣人出而投缳道路”句便可断定,但若说为五人修墓是在“崇祯元年(1628)三月”(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则此说难圆了。据《明史》记载,明思宗朱由检于天启七年十一月即位。若明思宗即位后魏忠贤生祠即行废除,则自天启七年八月始,苏州士民便具备了为五人修墓的背景条件。况且,“崇祯元年三月”为五人修墓的说法又与别的史料内容相抵牾——据《张溥年谱》记载,张溥于“天启七年,丁卯十一月作《五人墓碑记》”。“崇祯元年三月”为五人修墓的时间竟然滞后于张溥为文的时间,问题便出来了:是先修墓后有张溥为文呢,还是张溥先为文而后才有苏州士民为五义士修墓的举动?不言而喻,应是修墓在前,而为文在后。
笔者案头资料有限,难以完全肯定或否定哪种说法合乎史实,但有一猜想,说出来供大家研讨。
假定《张溥年谱》所记《五人墓碑记》的写作时间(天启七年十一月)确为史实,又假定《周氏年谱》记五人之死的时间是“天启六年九月十二日”(“七”系“九”之笔误),则为五人修墓的时间恰巧就在明思宗即位的天启七年八月,其时间跨度也正吻合了张溥文中“十有一月”之说。依据这一猜想,“去今之墓而葬焉”中的“今”,乃指天启七年八月,而《五人墓碑记》则写于魏忠贤死后不久的天启七年十一月的某一天。
三、“敛赀财以送其行”中的“送其行”为何意?
课文对“敛赀财以送其行”句没有注释,大多数老师把这句话理解为“募捐些钱财来给周公送行”,“送其行”就是给他送行,募捐来的钱财是供他路上使用的。陈精康先生对此作了辨析(《语文学习》,1997年第11期),认为杨廷枢、徐汧等人“敛赀”是为了免除周顺昌在押时“旗尉于周公不利”,是在应付旗尉之敲诈勒索(即“经理之”),即敛赀财“非‘送周公之行”。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解都是片面的,值得商榷。
周顺昌官居吏部员外郎,被逮后须押至京城治罪。陈精康先生在文章中亦引用了旗尉的恶语:“不尔,则周某途中且不保……”对周公要被押往京城的情况,杨廷枢、徐汧等人是完全知晓的,故而敛赀财要保周公之“行”,钱财虽进了旗尉的私囊,却使周公之“行”安全了几分。这不正是“敛赀财以送其行”吗?关键是怎么理解“送其行”的含义。周振甫先生在其专著《怎样学习古文》(中华书局1992年版)中主张读古文须“立体的懂”,“立体的懂”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词的具体解释;一方面是一个词作为术语时,了解术语的理论意义;一方面是要读懂文章的用意。”对于《五人墓碑记》中的“送其行”句,不宜狭义地理解为在周公将被押解京城之际,杨、徐等人敛赀财当场为周公送行,而应根据“文章的用意”,达到对“送其行”之全体的、本质的、整体的把握,既清醒地知道周公之行的具体日子是在杨、徐等人敛赀财过后的第十天(即天启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又“立体的懂”得,杨、徐等人敛赀财以保周公安然之“行”的举动,是提前为周公送“行”了,是间接为周公送“行”了,也不排除把募捐来的钱财留下一部分供周公路上使用(甚至路上仍需“经理之”)。如此揣摩文章用意,庶可达到对“送其行”句的完整、全面的理解。
(作者单位:新沂市高级中学)
----论戴·赫·劳伦斯的哲学随笔《天启》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