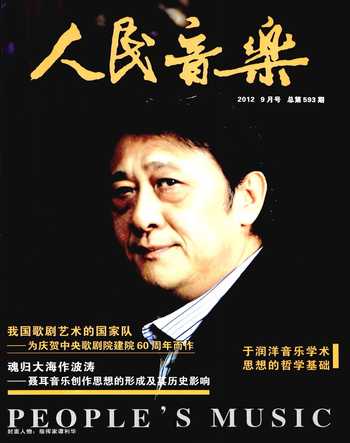魂归大海作波涛
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与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发达。换句话说,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任它怎样发达,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那末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
——聂耳
一、千岩万壑不辞劳——向着光明的前途上走去
少年时代的聂耳也曾幻想过“约得几个同志,盖点茅屋,一天研究点学问,弄点音乐,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辖”,结果受到批评,“青年志望宜远大,不宜作隐逸之想”。当然,作为一名有志青年,聂耳也向往着“以博爱互助的精神,为全人类谋幸福”,并为自己制定出八条“身心锻炼”的目标:1.身体健康;2.人格伟大;3.意志坚强;4.智慧灵敏;5.忠诚;6.友爱;7.互助;8.勇敢。在18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他还托物言志,满怀激越地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述志”诗:
渐放光明的东方,突起一轮通红的太阳;残暴怒吼的洪涛巨浪,一阵阵地拥上他的身旁。他知道这是他的穷途末路,只好挣开了他那柔弱的翅膀,预备着奔向他的自由之乡。
此时的聂耳已幻灭了迷梦,选择了积极的人生道路,“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为着要改变种种恶俗和黑暗现实,聂耳意识到必须“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同时他也“自己相信我稍有一点艺术天才,所以也要研究艺术”,可见聂耳之所以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开创新兴音乐道路,与其卓荦的早年经历及对自身个性充分认识并使之顺应时代需要密不可分。聂耳曾饱含满怀深情地呼唤——
光明之神哟,请你施给我们一部分的恩惠,放给我们一线的曙光,巩固我们的意志,从黑暗的牢狱里,达到光明的彼岸。
在1929年写给二哥的信中,他表达出“我的英勇,我的热血,还是继续地沸腾着,决意向着光明的前途上走去”⑤的坚定决心。同时,聂耳对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所谓左翼文学,也毫不掩饰地指斥其中充斥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蒋光慈先生的近著《冲出云围的月亮》,多么时髦的一部革命与恋爱的小说,多么适合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口味”,这对聂耳之后的音乐创作道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自觉抵制其中的低级趣味,并终其一生反对这种文艺创作中的不良倾向。
二、远看方知出处高——生活的苦闷与音乐创作思想的萌芽
1930年7月,聂耳来到千里之外的上海。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外省青年,“经过十天的奔走,结果,只得到一些滑头的答词或是访人未晤;换言之,可以说是绝望”。他只有暂时栖身于云丰申庄,无事时他一度将时间虚掷在一些无聊的闲事上。生活上的剧变,让心胸充溢着远大理想且刚刚步入社会开始独立生活的聂耳倍感困惑与苦闷,使得这位18岁的青年不时思考如何走向那光明的前途,“请您像以前一样相信他,他绝不会误入歧途”。他多次决心振作精神认真阅读进步书刊,继续学习外语和音乐。当革命纪念日到来时,他“企图在报纸上能见到应有的反应,更盼望在街头会出现动人的革命集会的场面”。同时,他潜心反思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久要想写我的年谱”。通过阅读革命文艺书刊,激发起他文艺创作的欲望,“看了几篇革命文学的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非集团的,不能和大众接近的是成为过去的东西了,它是现社会里所不必需的”。因此,“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改变了,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的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
1931年3月云丰申庄倒闭,聂耳为着生存四处奔走,屡屡受挫。虽然他的胸中充满忧愁,但心灵的火花,不熄的革命火花,却总是灼热地燃在心头——
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往往便是在这些杂乱的思想中挣扎出来的……若果他知道光阴的易逝而应该爱惜,不做无谓的伤感而只向着他自己应做的事业去努力,尤其是在青年时代一点也不把它滥用,那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他的将来必是成功的。
3月底,聂耳参加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即明月社)的招生考试,被取为练习生。聂耳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生活终于改换了,自从四月二十二号迁入学校以后,简直和以前两样了”。对于自幼喜爱音乐歌舞而又饱受失业困扰的“蚁族”而言,聂耳当时对明月社还是相对满意的。
聂耳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近来心理的变态,着实呈为异样的怪,常常会无由地忧虑、玄想。有时想入非非,好像前途非常光明;有时想到消极,感到人生无味”,他逐渐对黎派音乐感到怀疑与不满,“我替她们危险,我替这歌舞界的领袖团体危险,我可以猜想它是怎样地分散瓦解”。对黎锦晖的经营管理手段和在明月社的低薪待遇,聂耳更是牢骚满腹,“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赤膊露体的工人们大汗淋漓地在那高热的机械下苦作着……整整四天,通通便是拿了六块钱”,甚至直接将黎锦晖打入“资本家”的另册,“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是无微不至啊”,“物质的支配,给人感到不满时,在一相当时期,必然地是要使人对它发生怀疑,由怀疑便会产生一种需要。这几天我们这团里已经隐藏着这种需要的种子了”。此时距聂耳进入明月社不过两个半月的时间,其内心的不满和不同的人生观与艺术观早已决定了聂耳与黎锦晖的分道扬镳只是时间问题。
1931年末,聂耳满心希望地憧憬着来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不倦地保持着,努力地往前跑吧!”新年年初,聂耳收到了万茜“闯到革命的战线上”的诗篇,使他“内心的矛盾太厉害{好像有着不可解决的大事蕴藏在心里,忽而彷徨于十字街头,忽而凝想前途的可怖”。几天后,聂耳又读到《戏剧与音乐》创刊号上夏蔓蒂的名作《音乐短论》,主张音乐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是难以把握、神秘、超一切的艺术”,而是“绝对现实的东西”,这强烈冲击着聂耳的音乐思想,“现在我必须要这个来指导一下对音乐正当的出路,不然,自己想着有时的思想居然和社会、时代冲突起来,这是多么危险的啊!”此时的他,正在努力寻求新的艺术道路,与旧日之我作彻底了断——
我的出路问题在这个时候也好像随之动摇起来,所谓研究艺术,似乎不给你长远继续的可能,因为社会环境的决定,常常感到障碍和刺激。况且现在自己所重视的classic music是多么反革命的啊!
转机出现在这年的4月。聂耳结识了左联常委、剧作家田汉,这使得聂耳的音乐创作思路逐渐清晰起来,走向那光明的前途。自此,聂耳的创作思想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将学院派的古典音乐和流行着的黎派音乐作为其大众音乐理论的批判对象和革命音乐活动的突破口——
所谓classic,不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吗?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violinist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sonata,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
算是在这里面鬼混一年多了,前途茫茫,所谓“明月”,不过如此!算了吧!别想什么有望无望,另走他路吧……每到锦晖处一次,我总觉他着实有相当的麻醉力!无时不是在表现着他的个人主义、大湖南主义!难怪这般人的不会觉醒,诚然麻醉已深!
三、溪涧岂能留得住——感情危机与音乐创作思想的升华
就在聂耳苦苦追寻人生目标,逐渐形成其音乐创作思想的同时,在感情生活上他又经历着一场危机,这次冲击对聂耳之后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成为聂耳最终脱离明月社,走向光明前途的关键因素。考虑到感情生活的苦闷对每个艺术家创作动机的形成及其创作思想的定型都会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聂耳自然也未能免俗。
对真挚的恋情和生活事业伴侣的渴望,聂耳一直是心向往之,只是“没有多少功夫消耗于无聊,更没有时间谈恋爱”。这在聂耳看来“并不觉得是光荣、纯洁,我却以为是一种损失”,早年与袁春晖的纯真恋情一直深藏在聂耳的心底。来沪后,聂耳在明月社遇到与他一同考入的白虹,遂心生好感。他与白虹之间的恋情以精神恋爱居多,表现得既狂热又理性,“我这爱,也不过是一般的爱而已,并不会想到什么特殊的企图”,“在理智上,我并不敢有丝毫野心,她究竟懂得什么?使我讨厌又可爱!”这种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只能给自己带来痛苦的恋情,使聂耳既无法摆脱道德上的自咎,也无法忍耐白虹对他喜怒无常的态度,更无法将之与自己的革命理想相统一。1931年底,他写信给远在昆明的袁春晖,“报告我明年的新计划:1.多看英文书和社会科学书;2.努力做剧本和作曲的工作”。聂耳心里明白,他与袁春晖的初恋也就此无疾而终,因此,他暂时移情白虹,热切期望她“一切一切无形地进步,祝你的知识和年龄并进”。
然而,以白虹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阅历,与聂耳显然有着不可逾越的代沟,“说到真正的能同走一条路,同一思想性格,还是我的‘三人(袁春晖)好”。与白虹毫无进展儿戏似的感情纠葛,终于使为之心烦意乱的聂耳不得不考虑对此予以清算。1932年6月,聂耳压抑许久的感情终于决堤似地发作了——
我看现在要决定今后对她的态度很简单,便是赶快打断了爱她的念头。同时要根本推翻我一向所发表的爱的言论,这言论并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投机的漂亮话。事实已经告诉我,再不能拖延下去了!爽爽快快地拉倒吧!忘记过去的一切!
其实,正如“肖邦把他对康斯坦斯的爱不是理解为异性之间具体的个人关系,十分世俗地想要得到她,而是作为一个理想,作为乌托邦,把她看成一种艺术品”,对聂耳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1831年的波兰,正遭受着沙俄侵略者的蹂躏与摧残,华沙起义的失败,更使得远在异国的肖邦异常担忧祖国的前途与恋人的命运。而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中华民族不也面临着与当时波兰同样悲惨的命运吗?国将不国,何谈个人感情与前途?正所谓“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祗”,那些因现实受阻而难以宣泄的内心苦闷,便转移到艺术创作过程中,升华为创作动机的来源,肖邦如此,聂耳亦然。而当年五月武汉巡演的“绝大的失败”,促使他必须在革命道路上做出坚定的抉择,“忘了吧!过去的一切!从新开辟新的道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聂耳坚定地认为,“我对于我的婚姻问题似乎是一桩极平凡的事,而且是不需要在现在二十岁的我所应当去解决的事……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不管远在家乡的母亲能否理解游子的心理升华,已决心为人类社会做出伟大事业的聂耳终于要与旧的生活与旧的思想作最彻底的决裂!
7月,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上发表著名乐评《中国歌舞短论》,矛头直指明月社及其创始人黎锦晖——“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同时为新兴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贫富的悬殊,由斗争中找到社会的进步,这事实,谁也不能掩护。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
当然,聂耳与黎锦晖的冲突绝非只是出于私人恩怨和审美旨趣的差异,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聂耳二十年来音乐思想和人格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时代精神与革命情怀的自然流露。“聂耳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来批判黎锦晖及其明月歌剧社的活动,促使其改革,但字里行间表达出身为明月歌剧社一员的羞愧之情。特别是‘那么一群表演者正是感着不可言状的失学之苦,更是他心情的写照。也许是对于这些亲身经历的不合理遭遇的愤慨,使聂耳加入到左翼运动的行列之中”。对此,聂耳也坦言:“听了锦晖处新收的唱片,音乐却有很大的进步,嘴上虽在骂,心里却不安;自己实在浅薄,何敢去批评别人?!你骂他不对,你不但不能做出比他好的东西来,连你所骂的都做不出,这有什么意义?!”聂耳将其丰富的思想感情与艺术体验物化到音乐中,其所蕴含的精神内容与作曲家的情感体验是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的,使其作品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浪漫主义者肖邦不同,聂耳正是以深入生活的创造精神,用音乐的号角,鼓舞着大众开辟出一条通往光明与自由之路。大家莫叹行路难,聂耳以其实际行动给出了掷地有声的答案——
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
四、魂归大海作波涛——聂耳音乐创作思想的定型及其历史影响
1932年8月,聂耳主动退出明月社,来到古都北平。虽然他只在此逗留了短短三个月,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左翼文化战士,加入北平剧联,参与左翼戏剧、音乐活动,接触了党组织。正如他在此后回到上海时给于伶的信中所言,“是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汇注入正流的界堤”。现实固然残酷,却激起聂耳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为他此后光辉的新音乐创作与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时我曾对音乐抱过消极的态度,但读了一些音乐家的历史会即鼓起很强勇气。Wagner一生都是和苦痛奋斗着。
以后将更勇敢地去实践人生,在这里面取得伟大的材料,创造伟大的作品。
1932年11月,聂耳重返上海,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开始其音乐生涯的全新阶段。从此,聂耳专注于群众歌曲和电影音乐创作,其诸多著名音乐作品,都是为电影创作的插曲。1933年,聂耳完成处女作《开矿歌》,又为话剧《饥饿线》谱写插曲《饥寒交迫之歌》。同年夏天,聂耳结识报童小毛头(杨碧君),至今传唱不衰的《卖报歌》也在其笔下汩汩流出,算是他首次深入群众,为“生活的创作”。
1934年的春天到来了。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和努力,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终于成立,聂耳当选为负责人。4月,聂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英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后又升任音乐部副主任,1934年名副其实地成了聂耳的“音乐年”。
近代长期以来,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及其发展方向,始终困扰着每一个进步的音乐家,聂耳以多年的深思熟虑和毕生的创作经验,历史性地对这一难题予以解答,“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革命产生的新时代音乐家们,根据对于生活和艺术不同的态度,贯注生命”。聂耳正是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无产阶级新兴音乐的创作中,代替大众呐喊,谱写救亡乐章。
在1934年底撰写的述评《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聂耳除继续对学院派和流行音乐痛加声讨外,还充分肯定了左翼电影音乐自《渔光曲》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颇多溢美之词,“尤以《大路歌》、《开路先锋歌》的刚健新颖、雄烈悲壮为难得,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应该是一九三四年中国音乐不可多得的出产”,“歌词和曲调,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配合得很为恰当,决非一般善于抄袭者所能办得到的”。在文章的结尾,聂耳如预言家般宣告了革命新音乐的光辉前景——“一九三四年的中国音乐界虽不曾有过丰美的收获,但它的光明前途却已是预示了的,新音乐的新芽将不断地生长,而流行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
次年6月,聂耳在出席留日艺术界聚餐会时,应邀做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长篇讲演,除继续痛批学院派和黎锦晖外,还断言“《渔光曲》在电影中出现后,中国大众的音乐倾向便明显地转变了。《渔光曲》虽然替大众诉出一部分的苦痛,但它是悲观的、微弱的,不能给他们以满足,于是更前进、更有力的歌曲便应大众的需要而出现。自《码头工人歌》、《逃亡》、《开路先锋》等电影歌曲的异军突起,中国乐坛的新倾向具体地体现了出来。现在,中国新兴乐坛是天天在转变、在跃进,偕着革命的大众向最新的境域前进”。
在此,我们没必要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音乐家在文章和讲演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负情绪、宗派主义乃至左派幼稚病予以诟病,正是聂耳性格中这种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使他不断自我扬弃,追寻光明,从而成就了他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就在遇难的前一天,他还在为到日本之后没有新的创作而感到愧疚,觉得不该“欺人欺自己”,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在今天看来,聂耳音乐作品的时代已然消失,然而,他通过高妙的艺术技法和音乐手段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却如春风化雨,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民精神生活、感情生活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历程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在中国新音乐史上留下光辉的印迹,迄今仍引领着群众音乐创作的发展方向。而且,聂耳非常渴望创作能将西方音乐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有机融为一体的新音乐形式,为达成这一目标,聂耳有着强烈的愿望,“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而对苏俄音乐的学习与借鉴,更是聂耳创作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正是在中西音乐水乳交融的双重滋养下,才成就和奠定了聂耳作为人民音乐家和形式创造者的崇高地位,成为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楷模。
“聂耳呀,我们的乐手,你永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取着明天,作为你音乐的报酬”。百年岁月匆匆过,聂耳却如永生的海燕,穿梭于现实的黑暗与理想的光明之间,用昂扬的音乐激励我们在建设和谐中国的崭新道路上走向复兴,创造辉煌!
谨以此文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百年诞辰。
黄敏学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