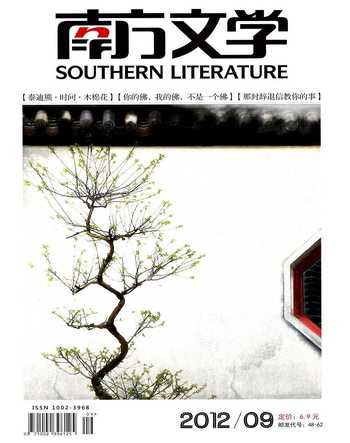诗人+农民+厨子+艺术家=潘漠子
谢湘南
头发有些自然卷,常及肩,爱穿背心,显摆出结实的肱二头肌;急性子,说话喜欢吼,笑声像大象的笑声,笑时的表情是欢快的狡黠,外溢出些许天真;爱吃干盐巴与绿色的菜叶,这个食草动物,命里似乎缺水,所以名字浸润着水,然而再多的水,也难以浇灌沙漠,所以,他炽热的情感,只能是自身孤寂的守护。
他叫潘漠子,他的家乡是海子的家乡,他的形象,总让我想起王小波笔下的王二,及王小波的那个裸体雕塑。
在我的印象或想象中,潘漠子与王小波有着几分神似。“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是李银河给予王小波的评价,我觉得同样适用于他,虽然他们是不同年代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履历,有着形体与思想方式的差别,但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强烈的艺术气质,那份智识、良善、醇厚、爽朗与幽默感,却有着相似性,甚至是同一性。
“走在天上,走在寂静里,而阴茎倒挂下来。”
“孤独,寂静,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这是王小波自喻式的三句话,我把它录下来,用来形容我的诗歌兄弟潘漠子及其生活。
其实,让我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前几年广州美院的一个搞艺术的学生做了个王小波的裸体雕塑,这个塑像展出后经媒体报道,变成了一个文化事件,引起热议。我觉得这个“王二”如果让潘漠子来雕,可能会更为出彩,因为他如同从王小波小说中出走的人物,与“王二”有着精神上的共通,他可以照着自己的嬉皮又认真、愤怒又嘲弄、荒诞又现实的形态,来“量身定制”一个“经典的前身”。而他学的就是绘画,日常工作就是做雕塑,他有着将“王二”定格为冲突性的自身的优势。
这种优势,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事实上,做雕塑与写诗一样,这两件表面上不十分关联的事,就是潘漠子的安身立命之本,并在他身上得以完美嫁接,互为肌理。这些年,他靠捏泥巴、刻石头、画草图、设计静止的园林、雕刻流动的时光来维持生计;而写诗,却一直是指引着他的生活,及一切行为的总指挥。可以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意的囚徒,诗歌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十多年前,他还在深圳时,曾也很是雄心壮志地开着公司,在深圳早年的豪宅区租下一幢别墅做办公室。那些年,他那里就成了深圳的一个诗歌据点,我们常去他的别墅聚会。那时我们一起办《外遇》诗报,在《外遇》上首推70后诗人作品展示。我们在草地上开诗歌Party,抱着吉它弹唱爱情,饮月吟诗,风骚得很。这种诗意的生活,后来因为他公司的经营不善,也就戛然而止了。
后来潘漠子去了北京。在北京宋庄,他租了一个农家大院,在院子里种四季时蔬,迎来送往各地的诗友。当着一群人的面,他一会是个艺术家,一会是个农民,一会是个厨子(就用自己种的菜,自己下厨,宴请一帮臭味相投的人。我曾带着孩子去到这个院子看望他,品尝他引以自豪的手艺),仍然活在诗意的景象里。而当他独处,他则回到一个诗人对生活的观照中,打磨词语,写下内心的锦绣。
他把自己在院子里种的向日葵、黄瓜、辣椒、紫苏、蕃茄等拍照发到博客上,引来朋友的一片羡艳,他自然也很是得瑟,更加来劲地传播着自己生活的好,或许这背后同样有着很多艰辛与不易。但在大多数人眼里,这就是他生活的常态与态度,他把美好的一面展现给朋友,把诗意的生活形象化到最大,他形容自己是“生于当下,活于魏晋”,这或许就是一个诗人在当下所需要的内心的荣光。
潘漠子的诗
雪Ⅰ
今天,我的身体漫天飞舞,披盖万物
今天,我洁白清远,照耀千年
今天,阳光远去,众生践踏
今天,漠子的莲花涤荡大地
今天,我的爱漫天飞舞,披盖心胸
今天,我纯净无语,缠绵千里
今天,星辰遍野,众生孤寒
今天,漠子的莲花独享大地
今天,没有异地,只有故乡
今天,我住进自己冰雪的内心
来慰藉和培育冰雪
雪Ⅱ
我不可能,用一朵盛开的花
来侮辱一朵凋零的花
我不可能,用一个人的大雪
来遮蔽一只乌鸦的大雪
我不可能,心里心外都是雪景
地上的雪可以赏玩
心里的雪只会蹂躏
我不可能,一生一世都在积雪
我不可能,让自身的苔原
侵占自身的戈壁
我不可能,被一场大雪遏制
但必定,被一场大雪消解或澄明
燕子
在天空徘徊盘旋的
一定是一只充满疑问的燕子
适用的房子在哪里?为什么
一扇扇光明的窗户都闪动寒光?
如此统一。一只被疑问挟裹的燕子
衔着一点点失望的泥土
在天空的包围圈里四处冲撞
看啊,它的眼睛闪动的一定是火焰
它一定是一颗黑色的弹丸
想把冷漠的门窗一一破解
如此郁结。一只燕子低沉地压低春天
向我们发出雄浑的嘶吼
我的出路在哪里?为什么
一张张光明的脸都沉溺于自闭?
如此凝滞。一只一定凝滞的燕子
一只被剥离墙壁的燕子
是我中的我,是即将生成的猛禽
在高楼的峭壁间展开巨大的尾翼
像展开巨大的尊严,俯瞰并消减
牵牛花
一枝牵牛花,在春天里,使劲地爬上春天
好像要拼命挣脱大地的束缚
她纤瘦的手指像伸入天空的钩子
她多想借助另一个身体把希望延长
仅仅有阳光是不够的,雨水也救不了她
一枝牵牛花的幸福应该是攀援的一生
而今她匍匐在地上像了无生机的蛇皮
她仅仅需要身边,有一个站立的物体
哪怕是一副已经冰凉的躯壳,只要站着,一直站着
她就可以为它输入绿色的血液
并促使这个躯壳重新说话
一枝牵牛花,只想把花开得和太阳近一点
只想把花开得和风雨亲一点
一枝牵牛花,使劲地向上爬向上飞
只想离浑浊的尘世远一点再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