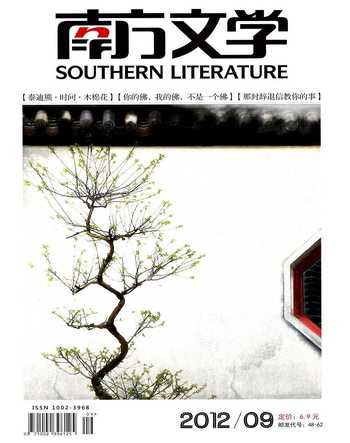知青妈妈陪我捡煤核
既然
给糖的阿姨愣了一下,很奇怪地哭了。
捡煤核的队伍好壮观
我的童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打小多见外婆少见妈。外婆对我很好,我知足得常常忘记自己还有一个妈妈。我一直闹不明白,电视剧里的那些看不见父亲或者看不见母亲的孩子,为什么个个都要问:我的爸爸呢?我的妈妈呢?天地可鉴,我当真是一次也没问过。
妈是知青,成分不好的那一撮,最早对回城绝望的一批。妈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当地农民,啥也不图,就图爹是三代贫农。我两岁的时候,一直病着的爹去了,妈抱着我,愁到不行。爹本来是孤儿,他一走,我们娘俩就成了孤雁,不知道如何是好。好心人劝她把我“处理”了,有一对不能生育的小学教师夫妇来相看过我,表示很满意。据说我当时生得颇不难看,他们愿意出六十块补偿妈。六十块不算少了,那时候粮店的米一斤才卖一毛多点,我居然也这么值钱过。
妈动了心。可是外公说:“拿了这个钱,你买什么吃都要肚子痛的。”看来肚子痛是一件比拉扯孩子还要恐怖的事,妈害怕肚子痛,我被留下了。
妈白天去出工,就灌我一茶缸米汤,将我锁在家里。大家都说我嗜睡得很,可以独自在屋内昏睡整日。我一直疑心,我后来之所以常常失眠,就是因为那时候睡得太多,把几十年之后的睡眠份额提前占用了。
外婆有时候会来看我,有一天打开门,看见我翻到了床下,脸被眼泪鼻涕糊得眉眼都找不着了,却依然是熟睡。小嘴巴鼓鼓囊囊,掰开来一瞅,嘴里含着一块生石灰做的墙皮——由此可见,我的吃货风范是与生俱来的,当时我大概把那块墙皮当做奇货可居的冰糖了。
外婆的眼泪刷地落下来,她对妈说:“不要造孽了,孩子我抱走。”
我就这样到了外婆家,没有户口,没有口粮,我成了黑人。查户口的来了,我知道要迅速钻进床底并且屏住呼吸,我还知道我吃的东西是外婆跟舅舅从他们的口粮里省下来的。捡煤核,是我唯一能做的减轻他们负担的事。
外婆家几公里之外有个很大的火电厂。巨大的倒渣场,成了附近居民的共同财富。那年月人人劳动,个个勤俭,捡煤核就是我们这帮小孩的任务。
大清早的爬起来,各自吃点东西,或者一个包谷饼子,或者一碗面片儿汤。七十年代,粮店买米是要搭杂粮的,不外是面粉和包谷。因此这两种食物不仅是我们的早餐,还会搭配到正餐里去,完全的白米饭不是天天能吃到的。
吃完放下碗,房前房后就热闹起来,我们开始呼朋引伴。张家的妞妞李家的姐,王家的弟弟刘家的妹,有的挎着篮子,有的端个破脸盆,三个一伙,两个一伴,一支以小女孩子为主的队伍就出发了。队伍里大的不过十来岁,小的只有四岁。但是不要小看我们这支队伍的劳动力,各家炉子里每天燃烧的,都出自这些幼嫩的小手。
扎着冲天炮发辫的谁谁;表情很严肃,身后总跟着一个淌鼻涕的弟弟的谁谁;作弄过我的谁谁;帮过我的谁谁……现在回想起我们这支队伍来,依然像电影画面一样清晰,只是再不知道她们如今怎么样。儿时的记忆就是这么奇妙,从不因时光久远而模糊,只为印象深刻而被铭记。她们成了划过我生活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永难忘记。
第一次跟着小伙伴们去煤渣场,我只有五岁多。有没有吸拉着鼻涕不知道,但是傻兮兮是肯定的了。
走到脚软,终于到了煤渣场。一望无际的黑色煤渣铺满眼睛,我当时就被震撼到了。
“煤好多啊……”
我大叫了一声,扔下篮子就扑过去,大把大把地往篮子里捧,小伙伴们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大点的姐姐走过来,教我分辨什么是煤渣,什么是能烧的煤核。她家离我家最近,奉外婆的托付照顾我。
电厂每天要耗费大量的煤来发电,产生的煤渣量也是巨大的。我们的宝贝煤核,就是那些没有完全燃尽的煤星儿,混在乌黑坚硬的煤渣里,等待我们去一一将它们辨别与发现。捡煤核的成功要领归结为三条:眼疾,手快,腿勤。用粗铁丝做的耙子把煤渣薅开,犀利的眼神瞬间发现煤核们乌黑而轻盈的身躯——煤核比煤渣有光泽,并且重量要轻很多——最后一步就是飞快地用手捡拾入篮。煤核抛入篮中的时候,熟练的姐姐们根本不瞟篮子,她们的眼睛已经盯住下一块了。而粗学的年纪小的我们,一边看着她们潇洒麻利的动作艳羡,一边在抹汗或者抹鼻涕的时候,把煤灰糊满自己的脸,成为姐姐们的笑柄。
不谦虚地自我表扬一下,这项技能我学习得相当快,并且不久之后就青出于蓝。我能左右手同时开弓,眼睛尖,脚步灵,效率远远超过同龄人。
挨饿的滋味不好受
捡煤核最振奋人心的时刻,就是倒煤渣的大卡车即将到来的时候。煤渣场再巨大,也架不住来自附近甚至不近的孩子们日日翻拣,本来就难以被发现的煤核日益稀少和难寻。有新的煤渣到来,无疑是一件大家都盼望的事。
倒煤渣的大卡车远远来了,我们全部呼啦闪到一边,判断它将即停留倾倒的位置。一双双眼睛溜圆,摩拳擦掌准备百米冲刺的劲头。刚倾倒的煤渣肯定是煤核最多的,虽然热气蒸腾,触手很烫,但没谁会顾及这些。卡车一开走,我们就飞快地冲上去,划定势力范围。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出煤的一块领地,让大家看见你捡出的煤核频繁入篮,是件很风光的事。有时候,会有不认识的大孩子过来欺负我们,妄图赶我们走,来自一处的孩子们就会互相照应,争取自己的地盘。打架的事不是没有,但很少。一般情况下,大家根据自身的个头与人数,很快就确定了是争还是让,然后相安无事。这是最原始的审时度势吧?没人教过我们,但好像一切得来就是那么简单。
早上跟随一大帮孩子去到煤场,捡到中午过后,我往往能捡满一个篮子。但那时候我确实太小,面对一个装满煤核的篮子,相当于面对一个巨无霸。我实在拿不回家,只有待在原地,等待外婆忙完了来接我。
等待的时光最是难耐,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因为饿,非常非常的饿。你想啊,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的饭食油水稀少,走路跟拣煤核又消耗体力,到了晌午谁不饿啊?
煤场附近的小山包经常被我们踏遍,饥饿练就了我们敏锐的眼睛和兼容并蓄的肠胃。小山上,我们可以找到好多入嘴的东西。春天最好了,满山是嫩嫩的刺梨枝条,我们叫做“刺苔”,剥了皮就入口,美味得很。夏天有茅草刚抽出的嫩苇子,包裹在叶片里还来不及舒展,就被我们囫囵塞进了肚子。那东西银白柔软,还有股香味。缺点就是茅草的叶片锋利异常,经常嫩苇子还没吃到嘴里,手就被划得血滴滴的了。秋天有刺梨,还有各种小而甜的野莓,那是一年中果实最丰盛的时节。最惨是冬天,平时葱绿的山包一片凋敝,我们只能刨茅草的根来解馋。
算起来好像有很多东西可吃似的,可这些东西就是解不了饿。有时候我们在山坡上忙活半天,其实入肚的东西不盈一握。搜寻的时间长了,还要冒着辛苦捡来的煤核被人顺手拿走的风险,实在悲催得很。
跟我年纪相当,必须等候大人来帮我们把战利品拿回家的,还有好几个,饿是我们共同的体验。饿得厉害的时候,我们集体躺着不动。“人是一盘磨,不动就不饿”,不知道是谁说的,这话我听一次就要抗议一次,只要没有东西吃,明明不动也是饿的。
亲爱的阿姨妈妈
有一天,外婆居然提前来接我,还带了一个面生的阿姨。那个阿姨看见我,很怜爱的样子,给我擦脸,理我的头发,还递了一块糖给我。糖在那时可是绝对的奢侈品啊,我看见附近的小伙伴眼睛都放光了。
我怯生生地说了一句:“谢谢阿姨。”
给糖的阿姨愣了一下,很奇怪地哭了。外婆重重地推了我一把:“叫妈!这是你妈。”
我茫然地看着眼前这个外婆让我喊妈的陌生的“阿姨”,突然想起来,是,我是有个妈妈的,虽然没有跟我住在一起。
妈妈上一次来看我是多久以前?我完全记不得了。好像久得让我忘记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六岁的我,记忆里难以搜寻到关于妈妈的印象。
论起没心没肺,我打小就是有目共睹的了。最经典的一次是,我到舅舅家去,舅妈说:“哎哟,没有煮你的饭。”我非常从容镇静地回答:“我吃面条。”一直以来,我竟然没有发现我跟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从来不觉得我的生活里缺少父亲跟母亲是一个问题……
这次妈留了三天,我猜测是那声阿姨刺激到她了,她决定陪我一起去捡煤核。
身边有一个大人,好像那几天我的嗓门都高亮了好多。妈不要我拣,她要我拎着小耙子跟着她。可是我看妈的动作实在笨拙,明显缺乏操练。照她的水平,我们拣到天黑也未必能拣满篮子。带点着急,也带点炫耀的心情,我在妈的附近开始动手,很有点为她做示范的意思。妈的眼神里却没有我想要的惊叹,我又看见她的泪光了。
煤渣场里,经常会有一堵一堵高高的煤渣山。说是山,其实就是积压已久的煤渣堆。大家都从底下往外掏,掏的人多了,煤渣山头重脚轻,极容易垮塌。有些力气大的男娃就用扁担拦腰击打,帮助将垮未垮的煤渣山彻底倒下。
那天我低着头正在翻捡,一座不远处的煤渣山轰然倒塌,伴随巨大的轰鸣声,煤渣洪水一般向我这边倾泻,有顷刻间要将我灭顶的架势。
一双手蓦地拽住了我,将我拖离险遭掩埋的境地。是妈妈。她拖开我之后,咆哮着冲向方才煤渣山伫立的地方。一个半大男孩直愣愣地站在那,手里的扁担上煤灰还在飞扬,一脸惊惶,估计他也被吓得不轻。
妈恶狠狠地推了男孩一把,扬手要打,但扬了一半又放下了,都是孩子。
妈跑回来,一把将我抱住,脚尖绊倒了篮子,拣好的煤核撒了一地,她看也不看一眼,只是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妈一只手把我的头摁在她的胸口,另一只手抚摩我的后背,嘴里不住地念:“三魂七魄回来啊!不怕,不怕,妈妈在。”
其实我才没有妈想的那么娇气呢,掉进河里再被捞起来我都没有哭过。可那一刻我哭了,哭得惊天动地的。
妈妈的怀抱是那么温暖,可以娇气的日子,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又这么少?
妈不能陪我太久,她与爹草草成就的短暂婚姻,让知青大返城与她无缘。当时她的情况属于另类,爹已经不在了,她连狠心离婚的机会都没有。妈后来说,狠心离了婚的,日子也不好过。看见回城的曙光,婚姻跟孩子根本拦不住知青向往城市的决心,可那些被抛下的孩子,终生都是他们心里的刺……
经过好些年的努力,后来我们娘俩的户口最终回到了城里。但妈妈韶华已去,健康日下——生命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在以后的日子经常会想,知青究竟是个什么群体?或许有人在这场所谓的磨难中出人头地,也有人在所谓的燃情岁月中志得意满,但事实证明,那只是小部分幸运的人们。大多数的家庭就如我所经历的一样,一路坎坷一路伤痛。
一转眼,妈去世快二十年了,我又想起这些事来,谨以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