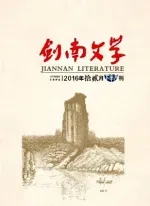红棉袄
◆ 闵凡利

许多日子了, 闵庆象心里总是魔魔乱乱的,布满皱纹的老脸木木讷讷的,常常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那双苦涩涩的眼睛,总是望着西南方向,流出的光也是让人不好捉摸的。
自从闵庆象大娘归了黄泉,闵庆象就成了这个样子,也不和人说话。这一天,闵庆象突然想起了闵庆方。
闵庆方打前年就病了,是胃癌。得癌症的人是活不长的,闵庆方二伯今年六十六了,刚吃过闺女送的六十六的长寿肉。看样子,二伯也没几天过头了。这天一大早,二伯一家人都到麦地里去了,就在院子里用油布搭了个棚,在棚底下放了一张床。闵庆方就躺在床上。床很老,木头都泛了黑,像被火烧过。二伯无聊,就看蚂蚁上树。蚂蚁们急急忙忙,二伯就笑,看破红尘似的。
门“吱呀”开了,脚步声唧唧踏踏,二伯知道是叔兄弟闵庆象。
两人就拉呱。闵庆象不拉东不拉西,只拉庆象大娘:“兄弟,你嫂走了一百二十八天了。苦命的,没那个福分!”说着,眼里泪汪汪的。
闵庆方就叹一声:“哎,哥,死了就享福了,你看我,活不活死不死的,多受罪!”
闵庆象就劝:“兄弟,别这么想,活着,有那个人。不孤单地慌。真的走了,摸也摸不着,喊也喊不着,心里空空的,苦呢!”说着就擦泪。
闵庆方见了就哎了一声说:“哥,人死不能复生,老挂牵嫂子,别毁了自己。”
闵庆象小孩一样地听话,认认真真地点头。“对,不想。我不想!”嘴说不想了,可一拉呱就又拉起庆象大娘。拉着拉着就掉泪:“我对不起你嫂子。当初我要不接她的红袄,她就不会被我害死了。”
闵庆方二伯说:“谁端谁的碗,谁刷谁的锅,哥,这是有定数的,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
闵庆象就点头:“对,不然,千里迢迢的,我躺在关外的雪地里,你嫂子咋就那么巧路过,用红袄救了我,哎,缘分,这是缘分啊!”
两人陷人了沉默。太阳白花花的挂在空中,丝丝拉拉的燃烧着。风偶尔千载难逢的吹来一丝,让你说不出凉快还是什么别的感觉。闵庆方二伯看着匆匆上树的蚂蚁,说:“蚂蚁和人一样……”
闵庆象悟出了,悠悠地点头说:“也是苦虫。”说这话的时候,他很内疚,声音低低的,仿佛别人听到似的。他说:“我把安眠药当成了胃药,她吃完就睡了,睡得很稳。那一段时间,她从没有睡过那样安稳的觉。我故意没喊她,想让她睡个好,谁知,她睡了就不醒了。”庆象大伯说得泪眼朦胧。闵庆方二伯就劝:“哥,你不识字啊。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你没听咱们街上的老娘们说你伺候嫂子像服侍老祖奶奶似的,真难为你了。嫂子是明白人,在天之灵一定会原谅你的!”
闵庆象就抹了泪。抬起头看了看日头。太阳把树晒成圆圆的一块,像个锅盖。闵庆象就起身说:“该吃午饭了,我走!”说完,就唧唧踏踏地走了!
五月中旬的夜,明朗新鲜,水洗了一般。麦子刚在场里打完,闵家庄乏了一个麦季的人们刚刚进入梦乡。可庆方二伯家的门被人重重的擂响了。把二伯一家人全惊醒了。二娘起来一看,天上月明星稀,是个好天气。莫非是场里发生了什么事。这时门外传来了声音说是我。二娘战战兢兢开了门,见是闵庆象大伯,方才把悬在嗓子眼的心放到肚里。闵庆象见门开了忙闯了进来,二娘问:“啥事,哥,这么慌,没明天似的?”
闵庆象说:“我来找兄弟拉个呱。”
闵庆方已在自己的床上坐起来,看是闵庆象,问:“哥,啥事?”
“我做了个梦。”闵庆象说:“我刚才做了个梦!”
闵庆方二伯的儿子清河也醒了 ,拖拉着鞋出来了,一看是闵庆象,脸上满是不高兴。问:“大伯,门拍的这么响。啥事?”
闵庆方见清河这样给闵庆象说话,很不高兴,就在床上骂开了:“小熊羔羔,别郎当着脸,你大伯找我拉呱,睡你的觉去!”
清河有点不服气,头勾着,烧鸡似的。
闵庆象就在一旁苦笑着说:“不怨清河,打扰你们休息了,我只说一句话,就走!”
闵庆方笑着。二娘问:“哥,啥话?”
“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嫂子了。”闵庆象说:“你嫂子在一座庙里哭。那庙就是我们从前住过的家。我想把她的红袄给她。你想夏天马上就过去了,入了秋,冬天也就到了。天就寒了。可我就是找不到进去的门。你嫂子哭得可惨了,我从没见她这样哭过。我的心都快碎了。”闵庆象说着泪珠子一个劲地往下滚。庆方二伯就跟着叹气:“哎!”
闵庆象抬起头,看着二伯。接着扑腾给闵庆方二伯跪下了。闵庆方慌了。二娘忙拉。闵庆方二伯说:“哥,你快起,快起,小弟可担当不起啊!”
“我求你个事!”
“啥事?”
“我怕你不……给办。”
“快起,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
“你一定能办到!真的,你能办到!”
“那……,那你说吧。”
“兄弟,你到那边去,见着你嫂,让她回来,你就说我想她。红袄我给她拆洗干净了。”
庆方二伯愣愣地望着庆象大伯。二娘也是。清河也是。
庆方就觉着有东西蛰着眼,用手一 擦,才知是泪。二伯想,流泪干啥呢?就很好地笑了。并且笑得很甜。他让清河拉起庆象大伯说:“哥,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捎到!”
闵庆象问:“真的?”
闵庆方说:“真的!”
庆象大伯还是不相信。就像小孩似的 伸出手指说:“咱拉个钩!”
庆方二伯就笑了笑,心想,他这是放心不下我呢。就忙把手伸开,把钩拉了。
闵庆象大伯很高兴,如释重负地长叹了一口气,然后笑着走了。
闵庆方二伯却苦笑着。他望着闵庆象的背影,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但他看到,老婆子和儿子的眼里早已长满了星星和月亮了。
天快亮的时候,二伯一家人都围到了他的跟前。族里的人围了圆圆的一圈。庆方二伯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了太阳。太阳湿漉漉的,很大,很红……”
大家都落泪。闵庆方二伯就笑。闵宪发就说:“庆方,你还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二伯指了指清河。宪发把清河唤到了庆方的跟前。庆方说:“我要走了。好好待你娘,啊?”
清河说:“你放心吧爹。你多保重,千万要走好!”
庆方说:“哎,难为你们了。我还有一件事,你一定给我办到!”
清河说:“爹,你说吧,我一定给你办到!”
庆方说:“对你庆象大伯说,让他放心,我一定把信给他捎到!”
说完二伯就长出了一口气,说:“我要走了……”说完就睡着了。就走了。
闵庆方走后,闵庆象天天抱着红袄往清河家跑。问:“兄弟来信了吗?”开始清河一家人还把闵庆象往家里让。后来就不行了。再后来清河一家人对他就横眉竖眼,比看到日本鬼子很眼红。
闵庆象就不去了清河家。就一个人抱着红袄去了闵庆方的坟前。先行礼,然后跪下,非常非常的虔诚。闵庆象轻拍坟堆,仿佛在拍睡觉的二伯。闵庆象问:“兄弟,信捎到了吗?你咋不回信了呢?”
这天,闵庆象不见了红袄,就发疯般地找。闵庆象想,别让老鼠拉去铺窝了。就满屋老鼠洞里掏。二儿子福禄问找啥?闵庆象就说:“找袄。你娘的红袄。”福禄说:“我拿去给小孩撕尿布了!”闵庆象听了一腚坐在了地上。他结结巴吧地问:“什么---什么?”福禄一看爹这样,忙说:“我扔在鸡窝上了,不知现在撕没撕……”
闵庆象就没命似的往福禄家跑去。百多米的路他觉得跑了整整一辈子。他恨自己咋不会像鸟一样生出翅膀呢,咋不能像鸟一样一下子飞到他要去的地方呢?
福禄家终于到了。闵庆象直奔鸡窝。吓得正在哄孩子的二儿媳连乳都忘了掩,只是定定地看着公公。
啊,红袄在。谢天谢地!红袄在!红袄在啊-……-闵庆象一把抓起,紧紧地抱着。惟恐别人在抢了去。
闵庆象天天抱着红袄,吃饭时抱着,睡觉时抱着。村里人都说:“真想不到啊,真想不到啊,老了老了,老成了 ……哎!”
闵庆象的大儿福寿和二儿福禄像偷人家被抓住,没脸见人了,自感觉在人前走路就像是老鼠过街。福禄问:“哥?咋办?”
福寿不吱声。默默的看着自己的黄胶鞋。胶鞋顶部露出了大拇脚指头,像分娩的胎头,蠢蠢地动。
福寿没言语,石头一样。只有嘴里烟头一明一灭,像只是灯似的亮。
福禄说:“哥,快入秋了,把红袄给咱娘送去吧,啊?!”
福寿掐灭了烟头,默默地点了点头。
夜里,福禄偷偷地把红袄从他爹怀里拿出来,弟兄两人去了庄东他娘的坟。月光很好。月亮像瓣橘子,谗得人直想流酸水。星星很神秘,调皮的把眼睛眨呀眨。像是眨住了一个什么秘密。树影款款地落下来,水草般地动。
弟兄两个跪着。福寿说:“娘,天凉了,不孝儿给你送棉袄来了!”
福禄起身浇了汽油,浇了很多。火着了起来,红红的,血一样的好看。火光中,弟兄俩猛然看到:娘在火中露出了脸,在对着他俩笑……
弟兄俩扑腾跪到,大喊一声:“娘啊……”
第二天,不见了闵庆象。
第三天,仍不见闵庆象。
闵家庄的人们就觉得这两天过得不踏实,就相互问:“闵庆象呢?怎么不见了呢?”
人们就摇头。
闵家庄的人就开始找。到了第五天,人们终于在庆象大娘的坟上找到了闵庆象。闵庆象扑在了红袄烧成的黑灰堆上……
闵家庄的人都说: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