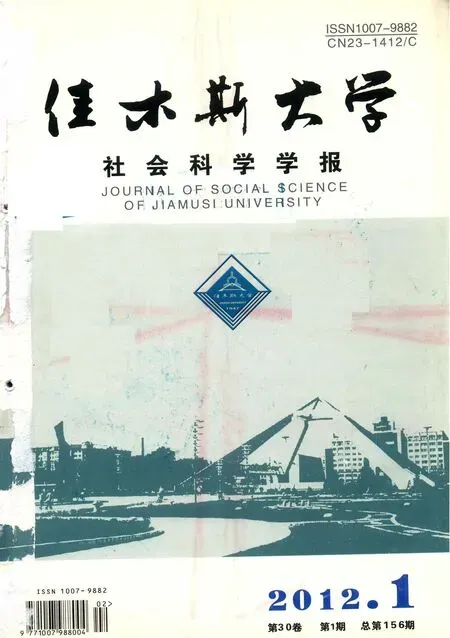《淮南子》的悲情①
邱 宇,刘秀慧
(1.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河北秦皇岛066000;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3.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陕西渭南714000)
《淮南子》的悲情①
邱 宇1,刘秀慧2,3
(1.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河北秦皇岛066000;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3.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陕西渭南714000)
汉初社会思潮主流是黄老道家思想,其无为政策使得社会形成一种思想兼容并包、开放自由的特色,同时文学艺术上深受楚文化影响,不仅有着丰富奇谲的想象和飘渺的“太清”“六英”“日月”“阊阖”“赤诵子”等浪漫意象,同时也有着浓重的悲凉之情;同时虽然汉初正值政体构建、政治秩序建立时期,为士人臣子建功立业、昂扬进取提供社会环境,但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他们感到失去了先秦士人的自由,个性受到压抑,对生命有着更强烈的理性认识,因此出现大量的悲情之作。而刘安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在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诸侯王倍受压抑和打击的历史环境中,其悲情自然更为浓重。
刘安;《淮南子》;悲情;理想与现实;生命
刘安把悲伤痛苦的生命体验用哲理思考和艺术浪漫方式寄托精神,平衡痛苦,消解悲情,使《淮南子》具有非凡的美和真实,使痛苦的生命体验提升到艺术和哲理的水平上,正如朱光潜说所有伟大悲剧里都有一种超自然的气氛,一种非凡的光辉,使它们和现实的人生迥然不同。刘安以“苍龙”“蛟龙”“八极”“六合”“九韶”“六英”“冥”“日月”“五星”“羊角”“阊阖”“赤诵子”?“太清”……充满浪漫色彩等意象,创造一个亦真亦幻、亦虚亦仙的境界,以开阔辽远,窈渺的意境寄托精神,表达出对宇宙太清境界的神往,宣泄出内心郁郁不得志的悲情。
汉初的多种文化因素决定了产生楚声兴隆的现象,汉初大一统,国家强大,君臣之序分明,士人从事政治文化活动,一方面其视野和胸怀比前人更开阔,如陆贾、贾谊的政治宏论,淮南王刘安综合百家的气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气概,张骞的探险精神,丝绸之路的开辟,国家的统一强盛,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士人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但另一方面在士人通经致仕之时,失去了战国士人的风采和自由,成为秩序井然的大一统政治中的工具,在皇权专制政治和帝王驭士之术中,士人的个性受到压抑,才能的发挥受到限制,“悲士不遇赋”的主题和情感萌生了,因此汉初文学的深情、张扬的个性和哀怨悲愁的时命之赋,是楚之悲情在汉代的延续,这对汉代文学自立意识有肇始之功。“汉初立国君臣多楚人,表现出对故乡与文学之热情浪漫、苍凉激越特色的追忆和倾慕,二是楚文化的艺术精神与汉初思想的符契,这充分表现为汉人一方面试图通过楚文化烂漫神奇的艺术想象来把握蓦然呈现眼前的地广物厚、生灵汇聚到现实世界,一方面又从楚人发抒浪漫情思间所寄寓的对大自然的惊愕与恐惧心态中接受了一种永恒忧患,并将此忧患从自然转向汉初战乱方息的满目疮痍、隐难未尽到现实社会。缘此两重原因,足可理解屈子激情与荆楚悲剧在汉初仍有震人心魄的力量和独占文坛的殊绝地位。”[1]汉初赋和仿楚辞之赋,表现忧患感、感伤之情。“众人莫可与论道兮,悲精神之不通。”[2]渴望社会环境是“贞士以耿介而自束”[2](P250)和“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2](P250)的理想化政治社会环境,以实现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但社会难以提供这样的现实,因此自然萌生悲意。贾谊《服鸟鸟赋》《旱云赋》《吊屈原赋》,严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皆悲戚,《楚辞集注》李维祯序:“凄郗紧豢,使人情事欲绝,涕泣横集。”贾谊《旱云赋》“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氵翁澹澹而妄止。”“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若飞翔之从横兮,扬波怒而澎濞。”“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照照而无秽。”“ 兮栗兮,以郁怫兮”,那种奇崛的景象,风起云涌的气势和 栗怫郁的幽思,都和楚辞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汉初时期对时间和生命的认识加深而且更理性化,实现生命价值的要求与阻碍其现实的社会矛盾,使士人悲从中来。严忌《哀时命》“往者不可扳援兮,亻来者不可与期”,是对时间流逝无法阻留的悲哀,面对此并非颓废,而是更激起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追求。“固将愁苦而终穷”[2](P231)“志浩荡而伤怀”[2](P231),“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侵辱之可为”[2](P231)。而现实却是如此的不如意,面对终穷的境遇只能是如屈原深深地哀叹生不逢时,但又不能像屈原坚持己见、追求真理,因此更是顿生悲意,并以大量比兴、铺排、对偶的形式应用于文中,形成韵律美感,增强悲情的抒发。“哀时命”和“不遇”成为汉初士人中流行的主题。东方朔《哀命》、严忌《哀时命》,“夫何予生之不遘时”[2](P231)。许结说汉初文学思想缠绕着士子的悲哀,通过“柔弱胜刚强”的心理转换超升、解脱,是汉初文学在黄老道家自然心态支配下的矛盾统一体。《服鸟鸟赋》表现失志者困踬落拓的情怀,《旱云赋》表现不平者忧惧愤懑的怨思,《吊屈原赋》表现伤今者览物吊古的深意,严忌《哀时命》:“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志憾恨而不逞兮……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广而无梁。”赞美“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於汨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表现愤世者捐累反真的意愿,《招隐士》表现凄清冷寂、幽美孤独的境界,贾谊辞赋“骚赋词清而理哀”[3](P1)。李炳海教授在《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中论及刘安《屏风赋》认为:“通过叙述山中乔木成为君王屏风的过程,表现士人遭遇明主的喜悦。……借屏风之口,盛赞君主招纳之恩,贤臣的推荐之功。由乔木变为屏风,由幽谷迁于宫殿,暗示人生命运的巨大变化,是由无人问津变为与君王遇合。”对此我是有赞同的一面,文中确实有此方面的流露,但我认为其中也有对自身身世的危机感。刘安的《屏风赋》有:“不逢仁人,永为枯木。”[2](P188)虽是颂世之赋,称颂自己的美玉之质。“巧匠不识……色比金而有裕,质参玉而无分。”[2](P191)但明言木,“孤生陋若……委伏沟渎。飘飘危殆,靡安措足”。其实也是隐喻生活于世上的内心真实感受和身世之悲,虽为诸侯王,如木成为屏风“近君头足”。但却近乎无地位时刻有着危机感,这都是继承屈赋的内在意蕴和精神实质。他们赞颂屈原精神,感叹自身,悲情无限,严忌《哀时命》“虽知困其不改操兮,终不以邪枉害方”。严忌《哀时命》:“愿至昆仑悬圃兮,采钟山之玉英。”以昆仑悬圃、钟山玉英比兴理想世界,以鸾凤蛟龙隐喻乱世贤才,感叹“志憾而不怛兮,路幽昧而甚难”。“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颇。”以整齐的对偶句式赞颂屈原精神,同时“巧佞在前兮,贤者灭息”[2](P262),“世从俗而变化兮,随风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毁败兮,虚伪进而得当”[2](P262)之两两对举,赞颂情感和对恶势力的批判寓含其中。还有为屈原鸣不平的,东方朔《七谏》《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仿《九章》,从题目看主要是独自悲伤感慨和幽怨,是代为屈原悲鸣,其中也如相如为武骑常事,非其所爱也,病免弃景帝客游梁,写作大赋其中也隐含着他内心对生活的不如意,颇有自怜之意。《初放》:“偃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浮云陈而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忠臣贞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信直退而毁败兮,虚伪进而得当 ……终不变而死节兮。”《沉江》:“ 处氵昏氵昏之浊世兮,今安所达乎吾志。意有所载而远逝兮,固非众人之所识。”《怨世》《怨思》以比干贤愚对比,“贤者蔽而不见兮,谗谀进而相朋。”渴望如凤皇远飞而高翔,《哀命》中有:“贤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党誉。邪说饰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直士隐而避匿兮,谗谀登乎明堂。”也是批判社会小人奸佞勾结,君王不识贤才。总之,汉之悲情有三:一悲生不逢时之时命志向难酬,二为屈原鸣不平,三代屈原而悲。但是所作无论思想还是取材全然没有超出屈原作品。但是一个是说明汉初模拟写作楚辞形成风气,同情屈原遭遇,赞美屈原精神。第二个是哀时命和怨思是继承楚辞之悲情和道家随顺时命和自贾谊《服鸟鸟赋》开始的对时命无奈之悲伤。第三是在大一统的汉初社会为文人提供贡献才智的历史舞台,文人积极进取,生命价值得以最大化实现,但是在此背景下仍旧有文人有着志向难以施展之哀怨。
那么,刘安的悲情是怎样萌生的呢?其特点是什么呢?“淮南国地处江淮间,古属楚地,老庄之学影响较大,与邹鲁文化则有一定隔膜,有歌颂和探索大自然的传统,流行古代神话传说,辞赋颇盛,习用楚语。这些对于《淮南子》一书的内容、形式、语言及色彩,都有一定影响,楚文化在书中的印痕是明显的。”[4](P156)淮南王君臣赋作,有刘安《屏风赋》,颂世感恩和自我悲伤的主题,四言韵文的体式,短制篇幅;有淮南小山《招隐士》要招归那些悲凉豪壮的隐士的诚挚之心,形成清幽、令人魂悸魄动的悲戚境界。在《楚辞通释》卷十二中王夫之评赞《招隐士》道:义尽于招隐,为淮南召致山谷潜伏之士,认为其音节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它辞赋之比。许结说汉初楚文化的浪漫和想象和疆域辽阔的现实社会结合起来,促进汉代文学雄浑壮阔气韵生动之风貌的形成,楚人宇宙观中怀疑精神触发了汉初文人对天命与人事双重疑问,揭示出汉初士子境遇冷落的悲哀。[2](P11)就连少年得志的贾谊也是悲情无限,《汉书·贾谊传》说:“意不自得”,正因为贾谊积极进取,所以才有重大的受挫之感,才产生浓重的悲情。《淮南子》作者刘安之悲是源于其身世和汉初要铲除异姓诸侯和以推恩方式削弱、打击同姓诸侯的政治斗争,是一个命运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汉初诸侯王的地位很是尴尬,在中央政权打击诸侯国势力的一系列举措中,他们一方面有以下几种方式应对:吴王刘濞反叛,被杀;景帝立太子,梁孝王因此怀恨,便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招延四方豪杰,成为诸侯国中无论是面积还是势力都是最大的,作兵器,府库金钱巨万,为诗作文,后因抑郁不乐而死;中山靖王刘胜吸取吴楚诸王的教训,耽于声色犬马之乐,不问政事,武帝时作《闻乐对》愁肠盈襟,悲思满纸,令人心恻,可见其也在矛盾中充满悲思;河间献王刘德多聚古书,与国家藏书相当,不问世事。
在强大统一的国家面前,如果诸侯王的反叛,只能是以卵击石,必然失败;于是就有诸侯王在压抑痛苦中选择或放纵自己,或另有寄托。如河间献王刘德聚古书,以远离世事,淮南王刘安在哲学中安顿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因此刘安的悲情一方面源自诸侯国在大一统的政治中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是历史发展中的悲剧.对刘安来说,就是因时代而形成的他个人命运的悲剧了,因此对于有才情、爱书、不喜游猎的淮南王来说内心是处于深深的痛苦中。还有汉初的悲情,受楚文化影响,同时也是源自于诸侯国士人中,他们渴望实现经邦济世的政治理想,还有臣子理想难以实现的挫折和受打击后的悲情,因此在汉初的刘安,不仅把觊觎政权的矛盾彷徨的心理也折射到《淮南子》著作中,映现黄老道家不争之争的权宜之计,同时写作中也必然染有时代的悲情色彩。但是《淮南子》中的悲情,不像刘安《屏风赋》中那样托物言志比较明显地表露,也没有严忌《哀时命》、贾谊《服鸟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等那样直接抒发悲情,而《淮南子》的悲情是内蕴于作品中,蕴藏于对天地宇宙之道的感悟中,融汇在祸福等对立转化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中,体现在对人间之事的淡然和清平无欲中,展示在对现实的批判方式的反抗中。
因此《淮南子》的悲情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理想与现实矛盾之悲情。
作为诸侯王的刘安,有才情,拥有雄心壮志,受着先秦士人精神的影响,在汉初时代精神感召下,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经邦济世,以旺盛的生命激情,作《淮南子》21篇,构筑治国的政治理想,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在削藩政治斗争中,他作为诸侯王的身份和其父为叛逆之臣的经历,虽为诸侯贵胄,却不如平民。平民尚且可以如贾谊、晁错等人通过对策等方式寻求到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刘安处在中央政权与诸侯国的矛盾中,处在贵胄子弟与皇权政治矛盾所形成的不可抗拒之悲中,现实与理想的激烈冲突,使刘安长期身处精神困顿中,他只能无奈、矛盾、痛苦、彷徨。虽然刘安积极参政,也曾谏伐南越,但也仅仅是得到武帝形式上的嘉许,后来把呕心沥血所作的《淮南子》进献给武帝,只是得到“爱而秘之”的结局。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赐淮南王刘安几杖,毋朝。这表明了武帝鲜明而坚决的态度,也决定了刘安必然的悲剧命运。因此《淮南子》必然染有刘安理想与现实冲突之悲情。
第二,淡然、豁达、无奈之悲情。
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的冲突矛盾中,在儒家思想立功、立德、立言与道家无为逍遥、因顺自然的融合中,刘安感受到深入骨髓的生命之悲情。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说痛苦则是生命力在其离心活动进程中遭受阻碍的结果。一切生命的活动都可以看作生命力的表现,任何一种情绪和思想,包括快乐的情绪,包括生命激情,只要得不到自由的表现,就都可能最终成为痛苦。在痛苦和悲情中刘安继承、发展老庄哲学理论,创造出自成体系的鸿烈之论,于是《淮南子》中刘安能够对个体生命、人生、宇宙等进行形而上的哲理思考与探求,主张自然的人性及本性复归,情意清平,淡然超然,以齐物论为原则,从宇宙天地的角度看待现实社会问题,从天道、地道推衍出人道,因顺自然,充满福兮祸之所伏的祸福辩证思想,拥有宇宙天下的视野和因时而变的转化观念。“在字句之间,不断提到祸福的问题,便开明白《人间训》一篇,反复于祸福利害的无常,即反映他们对此问题所感的迫切。心气平和,控制着人的七情六欲,血脉无郁滞,把精神及气志安顿于形骸之内,而不使其外驰,这是消极的不向外追求的人生态度。”这是悲情中的豁达、淡然,因此其理想难以实现之愁、之怅恨,消解在生命哲学的辩证与豁达的恬静的统一中,消解在天地与我为一的齐物、齐俗和对立转化的辩证之中。刘安把自我融入天地大我中,融入精神追求中,不执着于小我,虽然豁达,是内心欲求难以实现的无奈,在悲情之无奈中,内心的压抑、痛苦被加以哲理性升华,故精神淡然超脱,看透、看淡一切,在强大、矛盾的现实中寻求到了的自我心理平衡方法。朱光潜说悲剧的经验是一种兴奋,《淮南子》以豁达、淡然、超然,以想象、夸张把境界扩大,以铺叙、排比使情感宣泄,以辉煌的成体系的充满哲理思考的21篇,以超常的意象遨游于精神世界中,把绵绵的悲情最终转化为哲理的快乐,精神的快乐。刘安在《淮南子》所创设的飘渺、梦幻的世界中,求得心灵恬静的精神状态,获得超脱和自由的快感,以《淮南子》这部作品反映人生,即具体形象表现内心难以言传的悲伤感情和情绪。“不甘心像庄子一样,‘泄尾乎泥中’,却想沾溉由皇帝分下来的一份权势;又生当大一统的一人专制的大悲剧。我们可以从这种地方,看出在他们繁复而夸张的语言中,所透出的历史的真实意义。”[5](P150)徐复观所言的“这真实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可以说就是在中央政权和诸侯国的矛盾中刘安的无限的悲情。刘安的一种深沉的悲凄之情,是生命之悲情,弥漫于《淮南子》中并散发出淡淡的悲情意蕴。
第三,窈渺的意境之悲情。
刘安的好静,不喜游猎,爱书,思考,追寻世界本源,追寻道,寻本真,21篇的理论框架,欲求实施,其悲有源自诸侯国被打击的悲,也有汉代个体意识觉醒后的悲情,形成对“道”的追求的快乐和悲壮,以精神的深邃和逍遥,认识到茫茫宇宙中,悠悠天地间,人只是一分子,与宇宙自然万物“所归则一……终而复始,转无穷之源”[6]一样,人要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生存和消亡,顿悟之后,故采取“君子有能精遥摩监,砥砺其才,自试神明,览物之博,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以逍遥仿佯于尘埃之外,超然独立,卓然离世,此圣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及贤大夫,学问讲录,日以自娱”[6](P329-P340),形成一种内蕴的悲情,游的逃避之悲。刘安以游的精神和方式,消解悲情,因悲伤痛苦并把这种生命体验用哲理地思考构成精神寄托,平衡痛苦、压抑的情绪,转化为非凡的美和深刻的真实,把生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正如朱光潜说:“所有伟大悲剧里都有一种超自然的气氛,一种非凡的光辉,使它们和现实的人生迥然不同。”创造出美的意象、意境和《淮南子》这部艺术精品,以“苍龙”“蛟龙”“八极”“六合”“九韶”“六英”“冥”“日月”“五星”“羊角”“阊阖”“赤诵子”……充满浪漫色彩等意象,创造一个亦真亦幻、亦虚亦仙的境界,以开阔辽远,窈渺的意境寄托精神,表达出对宇宙太清境界的神往,宣泄出内心郁郁不得志的悲情。
同时在《淮南子》这部著作中,有大量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这是以寓言和神话的比类、象征、隐喻来完成的。如徐复观讲的“因汉代以法为治的本质,至景帝而益显,所以特别强调‘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而要求先本后末。这是对于当时政治实现的严厉批评”[5](P176)。如《淮南子》中对社会奢侈等风气的批判,究其实质这也是一种反抗,像《庄子》的谬悠之辞和逍遥齐物一样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抗,其实也是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热爱,是闻一多说的哭着喊着捉月亮的天真,也是在对道的本真追求中的一种源自精神深处的悲凉,这种悲情延续下去,形成悲情美,对司马迁《史记》以悲为美的美学风格的形成有所影响,“悲”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主题。
[1]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二十五[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M]//贾长沙集题辞.北京:中华书局,2007.
[4]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7.
[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汉]刘安.淮南子·说山训[M]//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I206.2
A
1007-9882(2012)01-0098-03
2011-06-10
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81026)
邱宇(1983-),男,河北秦皇岛人,硕士,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讲师;刘秀慧(1964-),女,河北新民人,陕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博士,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副教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