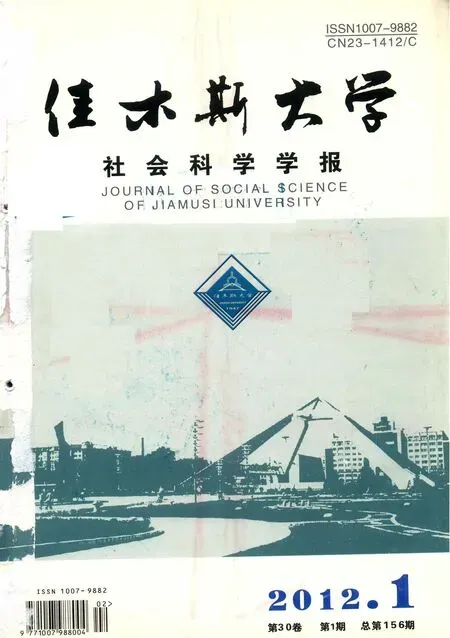试论陆机的“感物”说①
公沿海,王则远
(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
试论陆机的“感物”说①
公沿海,王则远
(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感物”理论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感物”说以《易经》的阴阳之学为哲学思想基础,并在《礼记·乐记》中以探讨音乐的产生方式被正式提出,随后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广泛应用。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感物”理论,并作了详尽阐发,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陆机;“感物”;继承发展
“感物”又称“心物感应”,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是一个重要命题,强调的是心物之间交感互构的活动,心和物之间反复触发,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与主观的心灵世界相互激荡,曼妙无穷的大千世界最终得以在内心世界中翻滚腾跃。下面着重探讨陆机“感物”说的内涵与意义。
陆机在文学创作论中明确提出“感物”理论,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将“感物”理论引进文学创作论的滥觞。同时说明在魏晋时代,自然景物在文学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凸显出魏晋文学对“感物”意思的总结。
“感物”理论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先秦时期的《易经》。《易经》第三十一卦《咸》,“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1](P2)感物意识已经萌发于此时,产生于战国年代解释《易经》的《彖传·系辞》解释地更为透彻:“天地纟因
,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世间万物,都是在阴阳相感中产生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以见矣。”[1](P2)天地万物各种情状均是物物、人人、物人相感而生。
荀子的《乐论》讨论音乐的巨大教化作用,有“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2]这里的“气”是人之气,与精神、性情有关的东西,荀子认为在“气”的作用下,通过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乐的强大的移风易俗、感染人心的作用。“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2]音乐感化人心,达到儒家从音乐欣赏方面宣扬其政治教化的作用,从而把乐提到“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礼记·乐记》中正式提出了“感物”理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口单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3](P61)这是《乐记·乐本篇》的开头,这段话用短小精炼的语言讲述了音乐是如何产生的,“感于物而动”这一命题也被思想界正式提出来,文艺创作的动因在《乐记》的“感物”说里已经有所体现,作为创作主体的“心”由于受到客体之“物”的影响,就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同时,《乐记》中的“物”不仅指客观存在的自然景物,主要的还有与人有关的社会事物,“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P63)无论自然景物四时变化,还是王道兴衰之变,都与政治教化发生着必然的联系。
汉代的《毛诗序》进一步发挥了《礼记·乐记》的“感物”理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3](P63)《毛诗序》的作者试图阐明情感的充沛与冲动会引发创作诗歌的欲望的同时,强调诗人的情感感动了天地、鬼神,最终起到“正得失”的社会作用。
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在文学创作论中明确提出“感物”理论,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将“感物”理论引进文学创作论的滥觞。陆机对“感物”理论的阐释,贯穿于艺术构思的整个过程之中。
首先是艺术构思的创作冲动阶段。陆机认为学识的积累和对世界万事万物的感知引发了文学创作的产生。《文赋》开端有:“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4](P20)杨牧对这一段话有如此的评价:“四时对于万物的触动和打击,于春秋迭代中明显可见,无论正面反面的效果都须能感动创作者的心志,向前推展,求其变化中体认人生的起伏和悲叹。”[4](P20)张少康对这段话的评价则更加明确地道出了陆机“感物”说的观点:“陆机在这一段中还提出了‘虚静’的精神境界,能使作者把主观和客观高度地统一起来,使心和物合一,借助于外物和四季变化的特征,来抒发自己的感情。陆机对创作过程的分析,具体地发挥了《乐记》中的‘人心感物’说。”[4](P35)“玄览”是通向“感物”的先决条件,“玄览”可以被解读为览冥,即居玄而览物,玄览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中应该保持一种虚无玄览的心境,达到用虚静的思维方式实现对人生、审美体验的超越。陆机于艺术构思之创作冲动的总结的最大价值是“感物”,即诗人有感于社会万事万物变迁以及四时变化而引发的创作冲动,“感物”理论也得以被陆机引入到文学创作中,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感物’最初的确只是关于文学本源的概念,但到魏晋时期,它愈益被限定在对创作过程的说明中,成为有关创作动机的概念”[5](P203),蒋寅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感物”理论最准确的评价。
接下来,陆机提出了“感物”应该具备的心理状态。“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这句是说要把用向其他方面活动的视听收拾起来,以得到精神的集中,即《西京杂记》谓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4](P37)徐复观对这一句话有着如此精准的阐发,在构思活动的开始阶段,进行广泛的思维活动要集中精力、排除外界干扰。这里实际上是承接前文“伫中区以玄览”的意思,将虚静引进“感物”理论,强调虚静在文学创作之艺术构思中的作用,认为这种心理状态是“感物”的必经阶段。
再有,“其致也,情日童日龙而弥鲜,物昭日折而互进”,程会昌释有“此谓宇宙物象,以虚静之心神驭之,则视焉而明,则焉而精,无复平庸杂乱之患。”[4](P40)当文思来临之时,内心的思维活动也随之展开,内心思绪由不清晰逐渐明朗,囊括进了自然万物,“情”与“物”相互感应,互相推进,“情”、“物”的这种循环往复、相互影响的特征,正是陆机“感物”理论的核心。
此外,陆机在艺术构思过程中还提出了“兴会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马及 ,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4](P241)
陆机的这种“兴会”说,实际上谈的就是创作灵感的问题,后世文人学者也都围绕创作灵感问题来阐发。
方 曰:此自述其思致通塞之情也。文之至者,多资神力为驱使。有若风雨之来,势不可遏。及其戛然而止,又复宇旷而天清。神之来也,虽率意而寡尤。神之往也,虽竭情而多悔。
王礼卿曰:进论文思通塞之故,亦申明妍媸厉害之所由也。首六句以通塞两义领起全段。下分两层承写:先言文思通利,则文辞泉涌,色盛音沛。继言文思滞塞,则理伏思涩,竭力亦难有成。顺结塞,逆挽通,顿住。末以通塞(不关)人力,其理难明作结,与前巧不能言相映
照。[4]P253,255
这段中心是讲创作灵感“,所谓‘灵感之会’,就是指灵感冲动,而‘通塞’即是说的灵感有没有的问题。陆机对灵感来和不来的两种情况作了十分生动的描绘。他指出,作家必须重视灵感,善于在灵感涌现时,抓住时机进行创作。”[6](P259)张少康的评价恰到好处,创作灵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思维活动,创作灵感可遇而不可求,当创作灵感来时,要及时捕捉,否则转瞬即逝,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创作灵感是一种非常随性的心理活动,常常是苦思而不得其解,却又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效果,显示出一定的神秘性,也就是“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意境。
感物理论在陆机之前就已经被应用于文学创作实践的过程中。《诗经》里有很多句子用自然景物比喻、起兴,来感叹社会变迁和人生遭遇。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6](P1)诗人以春天的柔嫩的柳枝和鲜艳的桃花起兴,联想到出嫁新娘的年轻貌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6](P242)以蒹葭起兴,展现一幅河上秋色图:深秋清晨,秋水森森,芦苇苍苍,露水盈盈,晶莹似霜,描写了对喜爱的女子执著追求以及渴望难即的焦虑心情。《诗经》中描写的自然景物,通过比兴形成了一种相互对应的感应关系。
陆机的“感物”说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陆机诗歌中涉及的景物有很多,不同景物在诗文中的引用也表明了诗人创作时的心情。陆机诗歌中有的景物具有凄冷、坚硬、隐晦的特点,带给人一种无限的忧郁、悲凉之感,如《驾言出北阙行》中有“长松何郁郁,丘暮互相仍。”《上留田行》中有“零雪霏霏集宇,悲中徘徊入襟。”同时陆机诗歌中常常出现风的意象,以“悲风”居多,还有“凄风”、“哀风”、“凉风”等。写云的意象也不少 ,如“阴云”、“玄云”、“庆云”,或者是云天蔽日的情景,如“曾云郁冥冥”、“油云豁高岑”。雨雪露水的景物也常常出现在陆机的诗歌中,如《梁甫吟》中有“零露弥天凝”。景物的色调多是寒冷、阴暗的。“坟墓”的意象甚至还出现在陆机诗歌中,情景悲凉:“长松何郁郁,丘暮互相承”,生命的衰败被长松的茂密反衬地淋漓尽致。
陆机诗歌追求对景物的动态描写,表现作家对时间飞逝的感慨。如在《折杨柳》中写有:“丰隆岂久响,华光但西阝贵”,描写雷响和日坠,字里行间却深深表达了一种悲怆。作家人的不安同时表现在描写动物的活动上:“鸣鸠拂羽相寻,仓庚嘈嘈弄音”,作家每当看到它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日月相追周旋,万里倏忽几年。”生命的飞逝使得作家变得异常敏感,作家诗文中处处体现着对日月变迁、生命飞逝无法掌握的无尽悲凉。
陆机受到个人学识以及时代的束缚,认识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张少康所评论的陆机“感物”说不足之处是“物”仅指“自然事物”,但“感物”说思想对后世影响依然很大。刘勰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继承和发展了陆机的“感物”说思想。
[1](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M].北京:中国书店,1984.
[2]杨柳桥.荀子诂译[M].济南:齐鲁书社,1985.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I206.2
A
1007-9882(2012)01-0090-02
2011-12-24
公沿海(1986-),男,黑龙江大庆人,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文艺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
[责任编辑:张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