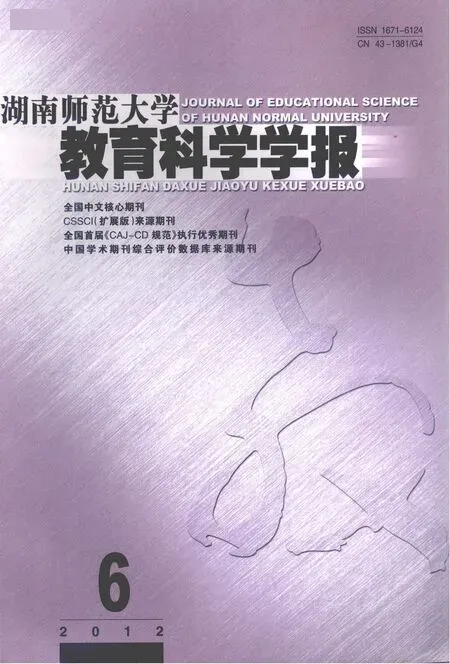务本的教育:兼论潘光旦先生的乡土教育观
海 路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教育学家。早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学校、美国纽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吴淞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潘光旦选集》(1~4集,光明日报出版社)、《潘光旦文集》(1~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乡土教育方面,潘光旦先生的代表作主要有《忘本的教育》(1933年)、《说本》(1947年)、《说乡土教育》(1948年)。
一、现代教育是“忘本的教育”
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现代学校教育制度[1]。1912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沿袭了这种西方式的教育模式。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的城乡大都建立起了新式的现代学校,教学内容多为现代科技和人文知识,很少涉及乡土知识。
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现代学校教育灌输的却是一种使受教育者与乡土中国相分离的价值观念。潘光旦先生认为,这种教育是“忘本的教育”,它脱离了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也脱离了乡土中国的实际。
30年来所谓新式的学校教育的一大错误就在忘本与不务本的这一点上。……20~30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是在教他们脱离农村,加入都市生活;这种教育所给他们的是:多识几个字,多提高些他们的经济欲望和消费能力,一些一知半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臆说,尤以社会科学为多,尤以社会科学方面的臆说为多;至于怎样和土地以及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离的关系,使85%的人口能够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3]。
潘光旦先生对现代学校教育的结果也做了论述:
85%的人口原来是在农村里长下很好的根了的,如今新式的教育已经把他们连根拔了起来,试问这人口与农村,两方面安得不都归于衰败与灭亡?[3]
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乡土性,决定了“乡村是本,市是末,农是本,工商终究是末”[4]。潘光旦先生认为,现代学校教育是一种“本末倒置”或“舍本逐末”的教育。
到现在总算还有人在那里大声疾呼“到民间去”、“到乡村去”。但就在这些大声疾呼的人中,也已经忘了他们的本源之地,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为什么不说“回民间去”、“回乡间去”,原来几十年的忘本教育,已经教他们忘记自己原是乡村里走出来的人,教他们把都市与城镇看做自己的老家。把都市看做老家、看做主体的观念一天不打破,农村的复兴,便一天没有希望[3]。
在这种城市本位的价值取向中,现代学校教育似乎暗含着这样一个隐喻:都市是文明的、先进的“中心”;乡村是蒙昧的、落后的“边缘”。在对乡村的“他者”的想象中,乡民被塑造成为愚昧、守旧、落后的一群,他们和他们的子弟需要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和“改造”。
李书磊认为,从1905年废科举以来的中国教育,主要是沿袭西方的成熟学制,“这种长期推行的学制对于乡村来说暗含着一种意义,那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将通过对已有的城市与工业的移植与照搬而实现。”[5]对城市教育模式的“移植”,成为近现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主流。
以追求“现代化”为目的的乡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的衰落和人才的流失。潘光旦先生指出:
如果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地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人之云已,邦国殄萃,试问,地方又安得而不凋敝,农村又安得而不衰落?[4]
在传统社会中,以“乡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不仅乡绅阶层出现了断层的危机,也导致了知识分子桑梓情谊的淡薄。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对此也有论及:
吴景超先生曾以我并不回乡的事实做例子说都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趋势,我是完全承认的。过去30年中长成的一代是在向都市集中。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在一个小学校里出来的学生中,在抗战前考取公费留学欧美的,依我所知道的,至少有7个。……但是这7个人没有一个回到本乡去,为本乡教育、政治、经济服务,是一件事实。都不回去了,而且也没有人想回去的了。
……我并不反对都市化,但是如果都市化会引起乡土的贫乏,不论是物质或人才的,我总觉得并不是一个健全的趋势。而目前的中国确正在表现出这种城乡隔离的恶劣现象[6]。
二、乡土教育的缺失
1905年,清政府颁布《乡土志例目》,以此作为全国编纂乡土教材的指导方案,由此奠定了官方所编乡土教材的基本格局[7]。中华民国政府在1929年的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改进全国教育方案》,其中“改进初等教育计划”的“课程”部分提出:“各市县可在课程中,斟酌本地状况,编制乡土教材,并施行细目,用来替代课程中的某部分,呈准教育厅施行。”[8]其后,1932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总纲》的“教学通则”第二条规定:“各科教材的选择,应根据各科目标,以适合社会——本地的现时的——需要及儿童经验为最紧要的原则。”[9]然而,在潘光旦先生写作《说乡土教育》一文的20世纪40年代,在乡土观念一向十分发达的中国,乡土教育竟然已经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境地:
近代教育下的青年,对于纵横多少万里的地理,和对于上下多少万年的历史,不难取得一知半解,而于大学青年,对于这全部历史与环境里的某些部分,可能还了解得相当详细,前途如果成一个专家的话,他可能知道得比谁都澈底。但我们如果问他,人是什么一回事,他自己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家世来历如何,他的高曾祖父母以至于母党的前辈,是些什么人,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最初是怎样开拓的,后来有些什么重要的变迁,出过什么重要的人才,对一省一国有过什么文化上的贡献,本乡的地形地质如何,山川的脉络如何,有何名胜古迹,有何特别的自然或人工的产物——他可以瞠目咋舌不知所对。我曾经向不少的青年提出过这一类的问题,真正答复得有些要领的可以说十无一二,这不是很奇特么?个人家世除外后,其余的问题都属于所谓乡土教育的范围[4]。
由于民国政府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需要,除了将国家教育体制统一化之外,教学内容也以西方现代科技文化知识为标准,乡土教育只能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正如潘光旦先生所指出的,“中小学的教科书既成为国定,标准题材既须全国一致,又怎能容许师生注意到某一个角落的个别情形呢?”[4]
潘光旦先生写作此文的时间是1948年。中国现代教育经过了60多年的发展,乡土教育的地位仍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国家知识的标准化、统一化、程序化;对中考、高考分数的追逐;“留学热”有增无减;部分青年学子对家乡疏离甚至逃逸。这“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当他们逃离土地,远走他乡与异国,就走上了永远的‘心灵的不归路’;即使不离乡土,也会因失去家园感而陷于生命的虚空”[10]。
城市化和现代化成了大多数人追求的唯一目标,桑梓之情的淡薄导致一部分民众对乡村的鄙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鄙视常常来自农村子弟本身。“走出农门”、“脱乡入城”成为大多数农村学子接受教育的主要目标——实际上,许多学校教师也是这样教导学生的。
有学者指出:“过去50年,我们的教育恰恰是过于强调国家整合教育的目标,而忽视了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个人生存教育的层面。我们的教育主要是为了5%的精英能够进入主流社会服务的,忽略了那些95%回归本土社区的文化边缘人。……我们单一的国家功能主义的整合教育造成的结果是,这95%的孩子既不能进入主流社会,又无法回归传统社区。”[11]
中国青少年一代在学校里接受的主要是国家认同教育。统编教材和应试教育使他们对自己家乡所在的县(市),甚至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难有太多的了解和认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国家认同教育缺乏牢固的乡土根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一类高而大的政治理念由于缺乏乡土认同为依托,只能是空泛的。换而言之,只有基于乡土认同、地域认同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认同,才具有更强大的绵续性和生命力。
对于青少年乡土认同的淡薄甚至消失,潘光旦先生称之为“轻去其乡”,并认为这种对乡土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是由于乡土教育的缺失造成的。
问题是在他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我们没有把家乡情形,包括广、狭义的史地在内,充分地介绍给他,让他观察、鉴赏,让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前途值得继续观察、研究的是些什么现象,值得维持兴革的是些什么事业,值得探讨解决的又是些什么问题,这又是回到乡土教育的话了。如今乡土教育既不存在,则此种印象自无从取得。及其为就学就业而暂时寄寓他方,他对于家乡的问题事物,也就不会再有心存目想的机缘,家乡对他也再无吸引的能力,而同时异地的风光情调却又不断的与以刺激诱惑,终于教他对于乡土的关系,由淡漠而忘怀,由忘怀而恝置。约言之,就地方福利而论,地方中小学不能运用乡土教材的结果,是断送了人才,驱逐了人才,决不是造就了人才,保养了人才。此种忘本而不健全的教育愈发达,则驱逐出境的人才越多,而地方的秩序与福利愈不堪问[4]。
乡土教育的长期缺失,不仅造成了乡村的边缘化和污名化,也强化了乡村人才不断向都市集中的倾向。最近10多年来,青少年回馈家乡、反哺故土的乡土认同情怀日益淡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越来越往都市集中,留学欧美也成为时尚。从教育方面追根溯源,乡土教育的缺失不啻为重要原因之一。试想,没有了乡土认同的精神之“根”,国家认同的大树何以枝繁叶茂?
三、教育的核心在于“位育”
潘光旦先生的乡土教育理念来源于他长期倡导并践行的“位育”思想。
何谓“位育”?潘光旦先生在《“位育”?》(1932年)一文做了阐释,“位”和“育”两个字的出处来自《中庸》,和“位育”对应的英文单词是adaptation或adjustment。
《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一位学者下注脚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所以“安所遂生”,不妨叫做“位育”。
西洋自演化论出,才明了生物界所谓adaptation或adjustment的现象。我们很早把它译做“适应”或“顺应”。适应的现象原有两方面,一是静的,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二是动的,指生物自身的发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便是“位育”。“生物,尤其是进入文化的人类,尤其是今日适当中西新旧之冲的中国青年,往往有不能安其位不能遂其生的,这种现象以前叫做‘顺应失当’,如今我们叫做‘位育失当’。助少壮求适当的位育,而避免失当的位育,或从失当的位育里解放出来。”[12]
在《忘本的教育》一文中,潘光旦先生就“位育”与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以前的人叫做适应,教育为生命的一部分,它的目的自然不能外是。我们更不妨进一步的说,教育的唯一目的是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3]。
“位育”的目的在于使每一个个体能“安其所遂其生”。潘光旦先生强调:“讲求本末的教育才是真正的位育的教育,也才是真正的教育,不求位育,不讲本末的教育根本就不配叫做教育。”[4]
在潘光旦先生看来,“位育的教育”应包括由本及末的3个步骤:第一步是关于人的教育;第二步是乡土教育,包括乡土历史和地理;第三步是一般的史地教育(这里的“史地”是广义的概念,“史”包括一切的人文科学,“地”包括一切的社会科学)。“以此绳目前流行的教育,无分中外,可知大病所在,即是本末倒置,或舍本逐末,目前最受关注的是第三步。”[4]从这3个步骤出发,“位育”应包括3个层次:一是个人的人性或人格的教育,它要解决的是人与自我的问题,属于自我认同的层面;二是乡土教育,即了解和熟悉自己所生长的历史和环境,传承地方性知识,属于乡土认同(地域认同)的层面;三是国民教育,即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属于社会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层面。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由亲至疏的“差序格局”[2]。在笔者看来,位育的教育也应以个人为本,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层层展开,首先从个体,其次为家庭,再到社区(地区),再后是大都市和国家,最后是世界。教育只有先从个人、从家庭开始,逐步延伸到周围的社区环境,才能上升到民族、国家这些层面。我们只有先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一类自我认同和地域认同的问题,然后才能回答“我要去哪里”、“我的民族和国家是什么”这一类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
因此,教育的核心在于“位育”,即使受教育个体适应其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于一个民族或群体而言,若要“安其所遂其生”,它也必须努力与固有环境达至“位育”。对于这种民族群体与固有环境相依相伴的关系,潘光旦先生称之为“绵续性”。“所谓民族性这样东西,可以说是生物的绵续性(遗传)与文化的绵续性(历史)所合作而成的一种复体的绵续性。”[3]
四、务本的教育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潘光旦先生重视务本的教育,讲求教育的本末,并不意味着他唯本是尊。相反,他在《说本》一文中对“唯本”进行了批判:
我一向认为任何带有唯字的思想学说是不健全的,是无法健全的。在主张他的人无论如何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总不免失之偏颇,失之武断,自己吃执一的亏,别人蒙抹杀的罪;唯本之论当然不是一个例外[13]。
潘光旦先生认为,要培植受教育者“本”的观念,适当的乡土教育是必要的,但这种教育不应是狭隘、自私的“乡土之私”,“乡土教育教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乡土有客观的认识以后,能够进而和别人的乡土作客观的比较以后,他的爱好也就容易成为有条件的、有制裁的、有分寸的,而不是一味的盲目的了。”[4]
在潘光旦先生看来,中国5 000年的文明,太注重传统,“过于重本”,“过于唯本”,吃了“唯本论”的亏。而20世纪初以来引进的新式教育,却将旧时教育视若洪水猛兽,一棍子打死,这也不是一种能使人“安所遂生”的教育。潘光旦先生指出:
要是旧日的弊病在唯本舍末,今日的弊病似乎在忘本逐末。革命的哲学,要是走上极端,一定是一个忘本的哲学。……二三十年来中国的教育,有能力把农工子弟从乡村里吸引出来,却无方法把他们送回乡村里去,从而改造农村,重新奠定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基础[13]。
潘光旦先生还认为,务本的教育需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所谓不忘本,就是要大家参考到固有的背景和环境,所谓务本,更是要大家在做事的时候,要从固有的事物做起,不要好高骛远,见异思迁。”[3]
由此可见,潘先生所倡导的“位育”观,乃是一种真正的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既非唯本是尊,亦非舍本逐末,而是本末兼顾。
中国乡村教育的出路何在?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向,如钱理群教授提出“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10];刘铁芳教授认为,乡村教育问题的出发点是“乡土价值的激活与重建”,乡村教育问题的中心是“乡村少年的健全发展与乡村社会健全生活方式的引导与培育”[14];袁桂林教授认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大力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15];滕星教授等人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学校教育中,应“建立一种尊重差异、和谐共生的多元文化课程”[16];杨东平教授认为,除了升学之外,农村教育还要满足“为城市化的教育”和“为农村的教育”这两种需求[17];陈敬朴教授认为,农村教育应把“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与能力”作为根本目的,从“功利性”回归“教育性”[18]。
在实践上,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中国许多省市、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包括天下溪、乐施会、福特基金会等NGO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多元文化教育中心等研究机构已因地制宜地开发了一些乡土课程(含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编写了一批适宜性较强的乡土教材(含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
这些乡土类课程及教材的开发,一方面在于传承地方性知识,使学生对本土文化和地方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和认知;另一方面与国家课程互为补充、相互融合,合力建构起受教育者对自我、对家园的认同。理想的乡土教育模式应是从培养受教育者的自我认同和乡土认同出发,“推己及人”,由珍爱家园、重视乡土开始,上升到热爱民族、忠诚国家、胸怀世界。
因此,要实现务本的教育,教人得到“位育”,就需要从家乡的一草一木开始,从“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培养学生对家乡的情感、对本土的认知,教育内容及方式也应循序渐进,由近及远、由浅至深。只有对家乡、对故土、对亲人爱得真切,对民族、对国家之爱才能根深蒂固,才能使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一类大而化之的抽象概念成为有根之木、有源之水。
(本文初稿曾在2009年10月召开的“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上交流,后经过修改和补充。致谢:本文的选题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女士的启发,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巴战龙博士对本文的修改亦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观察社,1948.
[3]潘光旦.忘本的教育[A].潘光旦.潘光旦选集(第 3集)[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4]潘光旦.说乡土教育[A].潘光旦.潘光旦选集(第 3集)[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5]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费孝通.漫谈桑梓情谊[A].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 5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7]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J].中国地方志,2004,(2):44-49.
[8]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改进全国教育方案[Z].南京: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1930.
[9]教育部中小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会.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Z].上海:中华书局,1933.
[10]钱理群.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A].钱理群.贵州读本[C].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
[11]滕星,关凯.教育领域中的国家整合与地方性知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33-37.
[12]潘光旦.位育[A].潘光旦.潘光旦选集(第 4集)[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13]潘光旦.说本[A].潘光旦.潘光旦选集(第 2集)[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14]刘铁芳.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起点与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5):23-27.
[15]袁桂林.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3):35-38.
[16]海路,滕星.文化差异与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一种教育人类学的视角[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6-7.
[17]杨东平.农村教育:“离农”和“为农”的教育[N].中国教育报,2005-01-14(6).
[18]陈敬朴.中国农村教育观的变革[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10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