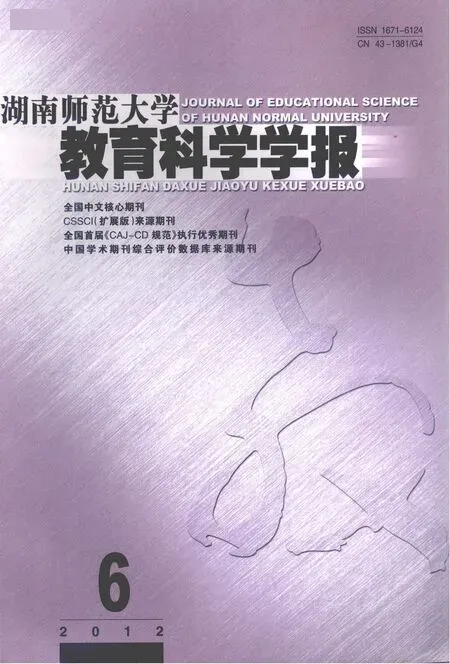从文化认知、文化自信到民族认同的转化与整合:壮族认同教育新论
杨丽萍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一、引 论
文化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是文化的创造和传承的主体。文化认知(Cultural Cognition)与民族认同或称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密切相关。认知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心理过程,认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特定的民族成员在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感知、注意、记忆、思维的过程中,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基本概念和认识,通过实现文化自觉,确立文化自信,进而形成对自己民族的身份确认、情感归属和心灵依附。
当前壮族认同教育呈现局部性、零碎性、片面性、表面化、功利性等特点。壮族人尤其是壮族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主要从家庭生活、村落文化空间、宗族的族谱和口头传说中习得。这种认知,客体不全面,贮存的信息支离破碎,只知道一些局部的民俗文化事象,甚至被一些假象所迷惑,造成文化的误读和曲解。
而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壮族文化认知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费支持力度不够,激励措施不完善,更重要的是缺乏宏阔的视野和学科理论的指导,教学内容肤浅,壮族学生不清楚壮族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发展方向,对壮族文化缺乏整体的有历史纵深度的感知,导致教学效果不明显。笔者重点调查的广西武鸣县各类学校,壮族文化教育侧重点是语言、民歌、民族体育和武鸣当地的风土民情,各学校往往以语言教育代替文化教育,过于功利地将壮汉双语教育目标简化为向汉语文学习过渡[1],忽略对壮族文化的学习;以局部的风土民情熏陶代替整体的民族文化认知;以无足轻重的风物介绍代替民族文化杰出成就的体认;以零散的当地历史知识代替系统的民族演进历程的传授。民族文化有限度地渗透到语文、历史、音乐、体育等课程当中,如一年一度的武鸣“三月三”歌节期间,让1 000名武鸣高中学生穿上舞台化的民族服装,参加跳属于“壮族”的竹竿舞活动,算是壮族学生对民间习俗的真切体验。
这种认知途径和模式的逻辑结果是造成壮族文化认知的片面甚至错误,造就“空壳化”“标签化”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强化壮族的文化认知教育,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将壮族的语言文字、历史、人文传统、乡土知识、壮族文化等内容整合融入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中,让壮族学生对壮族的历史文化由感性的体验逐步转化为有理性的认识,由此建立起系统的、理性的、全面的关于壮族文化的记忆,由文化认知支撑起民族的认同。
二、壮族文化认知教育的内涵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认知活动包括对外部信息的感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和思维的过程,信息的感受、输入、贮存、加工、提取、输出,都要依托于一系列的符号结构(Symbol structure),人的大脑通过对符号的感知,形成思维和情绪。外部的物体、声音、字符、图像刺激人的神经,在大脑中留下烙印,形成视觉模式、听觉模式、味觉模式和触觉模式的识别,“当人能够确认他所知觉的某个模式是什么时,将他与其他模式区分开来,这就是模式识别。人的模式识别常表现为把所知觉的模式纳入记忆中的相应范畴,对他加以命名,即给刺激一个名称。”[2]这种刺激是形成文化记忆、表象和心理认知的基础。
文化认知依托于特定的客体,离不开特定的素材。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认知的载体主要包括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壮族文化认知教育应当依托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结论,站在宏观的“多元一体化教育”的高度[3],将壮族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象征作为壮族文化认知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
首先,壮族文化认知教育要确认壮族是土著民族,壮族文化历史是源远流长的理念。
壮族祖先来自何处?壮族文化的根在哪里?许多壮族学生并不清楚,大多数对此没有认知,甚是茫然。壮族宗族的族谱大多认为本宗来自中原,来自“山东白马县”。这种说法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到封建势力的排挤和歧视,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攀附强势民族的心理体现。其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壮族先民是汉人南迁之前开拓珠江流域的主体民族[4]。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壮族地区自古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并且与当今的壮族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壮族的近源是有史记载的西瓯、骆越、乌浒、俚、僚、僮等,这些壮族先民创造了自成一体的从古文化、古城、古国到方国的文明演化序列[5]。壮族地区的古代社会经历了长期的自主发展的阶段,其历史进程与中原地区差不多同步,10 000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到6 000年前左右从氏族社会逐步向方国转化。
秦王朝统一岭南后,把壮族地区纳入中国的版图,壮族社会正式汇入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秦汉以后,壮族人民与迁居岭南的其他族群一道,以血与火的代价,拓展了祖国的疆域,推动着岭南社会朝着进步、文明、自由的方向演进,绵绵不绝地谱写岭南文化历史的壮丽画卷。
历史上壮族文化的演进历经沧桑,整个文化发展过程既有自成一体的线索,也同汉族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壮族文化认知教育应让学生知道壮族文化历史经历了仓吾瓯骆文化、乌浒俚僚文化、俍僮文化、僮族文化和壮族文化5个历史阶段[6]。
“仓吾”,或称“苍梧”、“仓梧”,是与中原尧舜部落同时存在的壮族先民。瓯骆包含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两大支系,瓯骆人以顽强的毅力,创造了花山崖壁画和壮族铜鼓,组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组织。学术界多认为乌浒是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在岭南的壮族先民,文化上传承着“巢居”、“击铜鼓”之俗。俍兵以英勇善战著称,瓦氏夫人曾率6800多名俍兵奔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出而九胜”,屡建奇功,受到明王朝的嘉奖。“僮”之名最早见于宋代史书,后多见于明清古籍中。晚清至民国时期,壮族意识逐步觉醒,壮族作为一个民族,逐渐引起世人的注意,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确立僮族文化的历史地位[7]。1949年以后,壮族作为一个民族,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承认,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壮族文化的演进从此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壮族的文化杰作与文化象征应当成为壮族文化认知结构的主体。
壮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3种形态结构的各个层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对于壮族学生而言,花山崖壁画、壮族铜鼓、壮族民歌、壮锦技艺应当成为文化认知教育的重点。
壮族崖壁画被誉为“悬崖上的敦煌”,其创作者是壮族先民骆越人[8],制作时间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位于宁明县境内的花山崖壁画长约100多米,最高处达40多米,最大的人物图像有3米高,画面气势恢宏,内在意蕴浩博精深,给人神奇朦胧的艺术美感,是壮族先民创造出的世所稀有的文化珍品。
铜鼓在壮族人的心目中犹如北方的鼎,具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被当作镇寨之宝,有“北鼎南鼓”之说,是村落财富的标志和地位的象征。目前发现的鼓面直径超过110厘米以上的大铜鼓都出自岭南地区壮族先民的居住地,都属于北流型。至20世纪90年代初,广西博物馆共收藏铜鼓344面,是世界上收藏铜鼓最多的博物馆[9]。
广西是“歌海”,“刘三姐歌谣”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三姐文化是壮族民歌的杰出代表,唐宋以来的刘三姐民间传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彩调剧《刘三姐》、电影《刘三姐》、电视剧《刘三姐》和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构成了一脉相承而又新意迭出的“刘三姐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植根于深厚的文化沃土,隐藏在民族记忆的深处,不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壮锦编织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壮族织锦工艺文化历史悠久,民族特色浓厚,结构方正,构图严谨,寓意深刻,朴质而瑰丽,庄重而典雅,凝结着壮族细腻的审美兴致,寄寓着壮族人民热爱生活、向往光明、追求幸福的美好理想。
三、依循认知规律,建立壮族学生的文化记忆
任何有意识的学习过程无不包括听、看、做三因素,可是研究不同的文化的学习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文化对听、看、做三因素的着重有不同,有些民族着重于听的因素,忽略看和做的因素,有些民族着重看的学习方法,而较不重听和做,其他民族则以“边做边学”为基本的学习方法[11]。
对壮族学生的文化认知教育,我们提倡教、学、做合一。通过讲授壮族历史文化知识、听讲故事、听唱民歌、敲打铜鼓、编织壮锦等形式调动所有的感官参与,体验文化的精妙;通过观摩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大型山水实景“印象·刘三姐”演出等民族文化活动感受壮族文化的永恒艺术魅力;通过对广西民族文化旅游、民族生态博物馆等场所的调研体验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空间和文化景观。这些感性、直观、丰富的认知教育形式,将教与学融为一体,使壮族学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耳濡目染,自觉或不自觉地习得特定区域族群的文化,由此萌生崇敬之心,自觉珍惜、传承本民族文化,构建、强化对本民族的“文化记忆”。
文化认知的教育,有赖于通过多次反复的视觉、听觉、触觉的刺激,形成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和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由表象系统的建构,形成概念,通过情感体验和心灵濡化,形成价值观。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
记忆在人的整个心理活动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不仅是知觉,任何其他一个心理活动和心理现象,从认知到情绪情感以至个性都离不开记忆的参与。记忆将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成一个整体,使心理发展、知识积累和个性形成得以实现[2]。
对于壮族历史渊源和杰出文化象征,壮族学生知之甚少,受到来自视觉、听觉等其他感官的刺激不多,没有感觉记忆(Sensory Memory)和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更加没有形成表象系统和言语系统。现代文化心理学认为:
儿童诞生在其中的具体习惯决定着儿童将从事的社会互动的类型,决定着儿童将要得到的东西,决定着儿童遇到什么样的学习经验好机会,也决定儿童从他们周围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得出什么样的推论[10]。
因此,当务之急是遵循人的心理认知规律,将壮族认知教育素材变成文字、声音和图像,融入教学过程,以纸质、数字化形式在学校、社会、家庭中广为传播,借助视觉模式、听觉模式、味觉模式和触觉模式,引发人们对壮族文化的注意,经过大量的信息加工、过滤、存贮,整合成记忆结构。李亦园先生认为:
四、实现壮族文化认知、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有效转化的对策
文化与民族如影随形,文化认知、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制衡关系,彼此之间一同消长,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文化的认知,就难以萌生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民族的认同也失去了根基,其逻辑结果是丧失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石,纵有民族的政治符号,也没有民族内在的精、气、神。
李富强认为,壮族的民族认同“呈现局部性、薄弱性、朦胧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12]。实际上,壮族文化呈现的“非整合性特征”[13],相应导致壮族的民族认同具有自在性、零散性、断裂性、表面性等特征。形成壮族这些民族认同特征的根源,除了壮族地区山岭连绵,交通不便,各支系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地理空间中的自然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导致壮族无法建立起统一的政治实体,无法完成民族内部的文化整合。壮族学子热衷以汉文化为主导的科举考试,有意无意漠视本族文化,未能形成对民族历史的深刻体认。相应地造成壮族文化认知、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之间的转化机制不能有效运作。
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壮族认同存在的局部性、朦胧性等特征,显然不利于壮族的未来发展。因此,很有必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加强壮族文化认知教育,建立起壮族人的文化自信,依凭壮族的自信心,整合本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激发民族内心深处的“家园感”和“归属感”,确立民族文化认同的根基和灵魂,创造一种壮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和谐共处的情境。
实现壮族文化认知、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转化以及整合,应采取的步骤和对策主要包括:
首先,通过认知壮族文化的杰出成就,克服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卑心理,确立民族文化自信。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壮民族基于水稻培育和种植基础上形成的“那”文化;基于诗性思维外化成果而创作的以《布洛陀》、《嘹歌》和刘三姐民歌为代表的歌咏文化传统;基于高超智能水平和工艺技术而制作的崖壁画和铜鼓,都是壮族创造活力外化的成果,是壮族本质力量的显现,充分体现了壮族的智能结构、进化程度、文明水平,成为壮族文化的象征,也是壮族人民对中华文化宝库的独特奉献。
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壮族文化认知提供了新的契机,为确立壮族文化自信并强化壮族认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壮族的布洛陀、刘三姐歌谣、那坡壮族民歌、铜鼓舞、壮剧、壮族织锦技艺、壮族歌圩、壮族铜鼓习俗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西初步建立起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这不仅为壮族文化认知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资源,对壮族文化表象系统的建构大有裨益,也有利于壮族学生改变“壮族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错误认知,克服自卑心理,进而借助壮族文化智慧濡化心灵,形成尊崇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实现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升华。
其次,建立学校体制内的壮族文化教育体系,保持壮族文化认知的连续性。
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壮族文化大多被排斥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未能变成课程资源而进入学校课堂。壮族学生极少或无法从教材及各种教学活动中获得对壮族知识的记忆。壮族的文化成就和文化象征,远未成为壮族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常识,因此,壮族学生也就无从对自己所属的文化和民族产生认同,更谈不上文化自觉,亦未能由此衍生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所以,建立不同学龄段的文化认知教育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应按照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3级课程体系的安排,组织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偕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教研员、一线教师、民间艺人等人士共同组成课程开发小组,逐级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壮族文化认知教育的教材编写要以“认识壮乡—热爱壮乡—建设壮乡”为主线,根据不同学龄阶段学生的认知特点,从内容到形式分序列编写,形成序列化的教材体系。在内容的安排上,学前教育阶段以壮族的歌谣、游戏、简单的民间工艺制作等体验式认知为主;初等教育阶段以《布洛陀》、《嘹歌》、《传扬歌》、神话、花山壁画、铜鼓、壮锦等感性的民族风情为学习内容,培养对壮族文化认知的兴趣;中等教育阶段以壮族的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等为学习内容;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是民族院校突出民族课程特色,更深层次地学习壮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与此同时,需制定与此相适应的课程管理和评价体系,建立壮族文化认知教育的长效机制,保证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文化课程的正常实施。
第三,通过壮族文化认知和文化自信教育,确立壮族认同,培养兼容壮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全球认同的新一代民族文化传人。
壮族文化认知和民族认同教育的更高层次是造就兼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全球认同的民族文化传人,让越来越多的壮族人,一方面能够切实体认壮族的历史文化脉络,感悟壮族历史文化蕴含的崇高感、神圣感;另一方面又不固步自封,以开放的心态包容中华民族文化和人类的文明成果。
1 400多万壮族同胞要通过文化认知教育,濡化民族的心灵,形成壮族历史文化的记忆,进而实现从文化认知到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转化。一方面系统感知并珍视壮族的文化身份,自觉肩负起实现壮族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实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认同的和谐统一,在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为实现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五、结 语
文化认知不是凭空生成,文化自信依赖于民族的辉煌历史记忆,民族认同植根于特定区域的民族共同意志。凝聚着民族智慧的传统文明是确立民族认同的力量之源。受到“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卑心理困扰的民族不可能建立起民族的自信,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必然弱化自身的民族认同。因此,唯有加强壮族文化认知和文化自信教育,方可支撑起理性的、清晰的、系统的、深刻的强有力的民族认同。实
现壮族文化认知、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有效转化、有机整合,促进壮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和谐统一,才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真正实现壮族的文化复兴与民族强盛。
[1]滕 星.壮汉双语教育的问题及转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4):9-14.
[2]王 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滕 星,苏 红.多元文化社会和多元一体化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1997,(1):18-31.
[4]张声震.壮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5]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6]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德清.壮族文学发展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7]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8]邱钟仑.左江岩画的族属问题[J].学术论坛,1982,(3):70-73.
[9]蒋廷瑜.壮族铜鼓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10][美]迈克尔·托马塞洛.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1]李亦园.人类的视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12]李富强.壮族认同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1):166-170.
[13]覃德清.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