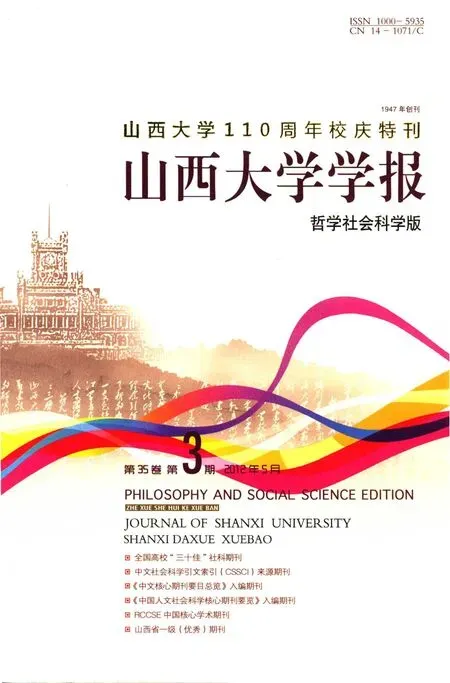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审美风范的规范与重塑
刘 培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理学对文学精神的重塑,其核心内容是理本的意识、思辨理性和理欲之辨。文学精神由体会人生转向体会道德境界,由重视政治教化、美刺讽谕转向重视心性义理、正心诚意,由教化目的论转向修养目的论。这种变化最终在文学创作的审美风范上表现出来,这是文学精神在美学层面的展示。南宋后期辞赋在审美风范上的表现主要有这几个方面:追求醇和淡雅恬静温馨的情调;趋向于严正庄肃的情感基调;行文拘谨,气势内敛,表现出整饬规矩的辞章特色。
一 远离高世之情,追求醇和淡雅恬静温馨的情调
从北宋后期以来,辞赋创作以理释情的倾向非常明显,文人们追求一种超越个人情绪的对社会人生的彻悟,南宋辞赋在理趣方面比较逊色,文人们在探寻一种祥和宁静的生活趣味,或优游山水园亭,或啸傲陋室草泽,批判现实的精神渐颓而情感自足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辞赋由表现深于学问才情转向表现深远道德修养,过去那种对情感超越的智慧被整齐划一的道德情怀和理学说教代替了。这种转变表现在辞赋审美方面,就是追求醇和淡雅恬静温馨的情调。
朱熹等以诗骚精神为其文统的源头,真德秀等以后的理学家则以此着眼,主张恢复《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们力求将托物言志的比兴原则与含蓄蕴藉的意趣风韵结合起来。在探索文学创作的美学风范方面,从朱熹到真德秀等,都力避豪放,强调中和之美,平淡而意味深长。其深长的意味便是对“理”的体会与把握。因之,古淡恬静之美不再指向对宇宙人生的思索,而是代之以理学的思想。真德秀是这样评价陶渊明的:“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陶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于庄、老,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源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从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秘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慷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遯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1]真德秀对陶渊明的阐释是从安贫乐道坚守节操着眼的。魏了翁评价陶渊明曰:“称美陶公者曰:荣利不足以易其守也,声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词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则未之深识也。风雅以降,诗人之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物观物,而不牵于物,吟咏情性,而不累于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谢康乐之忠,而勇退过之;有阮嗣宗之达,而不至于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岂小小进退所能闚其际邪?先儒所谓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者,陶公有焉。”[2]这同样是以理学思想来改造陶渊明,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门理义之秘的用意由此可见一斑。这方面,王柏对“风”的理解更具代表性,他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鼓天下而神变化之功者,莫疾乎风。起于空洞苍茫之中,而激越于山川,徘徊于草木虚徐,游泳于精神兴致之表,泠然而不可挹,倏然而不可留,其感人也深,其动物也力,有自然之妙,莫知其所以然者,其唯风乎!圣人观物察理,拟诸形容,喻君子之善,而名之曰德;风感歌咏之意而名之曰《国风》。曰风气之开以见造化之推移,曰风声之树以示治道之兴起,有曰风教、风俗、风范、风致,皆取其感人动物,有自然之妙故也。《烝民》之诗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传者以为清微之风,养万物也,盖其熏蒸披拂也,天地为之光华,如人之嘉言善行,流播传诵,后世为之振奋,顾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百世之下,闻者尚可以变化其气质,而况夫先世之流风遗韵,子孙所当观感服习,继继承承,要不失其气象,而忍遗响之不嗣乎!”[3]以风行水上来比况为文之流畅自然的气势是苏洵、苏轼等作文的法门,在宋代这种主张有巨大影响,王柏此论既强调了平易流畅的气势,又看重感化人心的作用,其概括当时的文坛风尚最为得旨。
自然流畅而正心诚意,落实到辞赋当中,就是追求醇和淡雅恬静温馨的情调,南宋文人的写作兴趣总的倾向是由宏大叙述趋于展示庸常生活。终南宋一代,辞赋表现庸常生活的嬗变轨迹较为明晰。初期以表现富家翁般的陶然为主;中期主要倾向于展示光风霁月般的襟怀、境界和心通万物的机趣;后期则趋于平实,展示生活中淳朴、和平、宁静的一面,其审美风尚具有“人间化”、写实化的倾向。在这种创作趋势的发展过程中,理学重视修身齐家的思想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北宋后期以来辞赋中的那种高雅脱俗隐僻幽峭的风格逐渐被淡化,而趋向于温柔敦厚的诗学精神,趋向于醇和淡雅恬静温馨的审美风范。这个时期表现乡居生活的辞赋创作相当繁荣,如刘宰的《漫堂赋》,洪咨夔的《老圃赋》,方岳的《茧窝赋》,胡次焱的《山园赋》、《山园后赋》,张侃的《春风赋》、《夏喜雨赋》,蒲寿宬的《古赋》等。这些赋除了大谈理学教义以外,其描写部分也多展示现实生活的醇和美好,借以反映作者渊雅冲和、清旷散逸的仁者境界。如张侃的《夏喜雨赋》这样描写雨:
弥天必降,彼其哕者欤!危虚直日,彼其会者欤!宝珠杂色,彼其具者欤!今日之瑞,不疾不徐。纷纷乎屋山之卷茅盖,沥沥乎岭腹之摇松株。使饶爽垲,不亦快乎。是能纳佣傁于清凉之区,脱佣傁于炎酷之墟。能释其倦局之躯,放荡于不谫谫拘拘乎。言未既,有东南而至者,飘飘若回雪之入太虚,来于绮疏。俛而谒之,封其姓,姨其字也。张子解带而揖之曰:其爽籁之裔耶?抑猎蕙之系耶?楚台扬腐之余致,谿谷土囊之奇异耶?小之萧萧拂拂之态,大之切切激激之类。尚与汝忘情乎胸襟之外耶?于是延以佳宾,酌以醲醇。微天际之故人,谁能滁我之世尘。宾复饮我,形骸尔汝。忽乎月皎星稀之不知,又焉知黑蜧之墐户,商羊之起舞!
作品通过与喜雨亲密无间的交流展示的不仅仅是天人相与的和谐美好,更是通过观物察己体现出理性的感悟和透脱洒落的仁者襟怀,洋溢着人间气息、生活气息。这不同于陶渊明笔下的结庐人境而心远地偏的出世,更不同于王维的空山不见人般的孤寂,而是表现着人与万物、我与外物共存共生和谐相处,这不是濠、濮之乐,而是曾点之境。
理学指向现实人生,受理学影响的辞赋创作,其旨归不是探索人生,而是以理学伦常来评判人生,其所体现的醇和淡雅恬静温馨之美,其核心是对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理”的发现、展示。这个时期的辞赋,表现生活场景的作品相当多,这延续了南宋中期以来辞赋的传统,但更重视对场面的描绘。比如董鸿的《奴戒》、姚勉的《嫉蚊赋》、方岳的《茶僧赋》、李曾伯的《逐蚤吟》、李龏的《诮暑赋》、洪咨夔的《烘蚤赋》、刘克庄的《白发赋》等。这些作品不再汲汲于发掘其中的深刻哲理,而是展现这些生活场面蕴含的恬静温馨的情调。如洪咨夔《烘蚤赋》:
麦送爽寒,梅迎溽阴,羸肌老干,败絮故衾。睡蛇甫蟠,跳虫倏临。无蜂虿材,有豺虎心。孕藁之奥,宅第之岑。质眇乎粟,觜饿也镡。其来施施,其进骎骎。假托茵凭,陵躐衽襟。躁跃如舞,潜行似瘖。左发右应,前却后侵。蛰其股锥,惕其毡针。据蒺刺刺,负芒森森。龟息正清,挠不可禁;蝶梦方栩,搅不可任。爬搔空疲,摸索曷寻。抚床以兴,子规夜吟。赤脚张灯,苍头炽煁。絮衾厌篝,烈于釜鬵。初而蠕动,如商望参。少焉纷纶,如发聚簪。或壮或穉,或纁或黔;或尾而丁,或腹而壬。龙跳虎掷,疑闻呜喑,星流雷激,惊逃沸浔。力穷势屈,骈搏旅擒。祈父爪牙,凯平绿林。
描写蚊子、跳蚤、苍蝇的辞赋多为讥刺之作,重在骂世,这个时期这类作品很多,但是骂世的成分大大减少。赋作把跳蚤之跳跃之态、人之瘙痒难忍把搔不已的窘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们几乎难觅赋中的骂世动机,我们从中能领略到的是作者对庸常生活的热爱和深刻的领悟,能体会到作者以“理”观物的那种透脱澄明。赋中焚被的场面和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立意相类,但是没有直白地揭示“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的人世间之营营的毫无价值,而是借此表现在群蚤骚扰下人的手忙脚乱慌不择法。刘克庄的《诘猫赋》也是一篇描写生活场景的富于情趣之作,赋曰:
余苦鼠暴兮,语之所亲,或致狸奴兮,稍异其伦。甚俊黯兮尤服驯,既咆哮而威兮,亦斓班而文。余乏精识兮,以貌而取人。阅一历兮,差良辰。栖以丹槛兮,藉以华茵。饭以香秔兮,侑以绚鳞。谓子苍辈之闻风兮,退避而逡巡。犹鳄惮愈而徙海兮,盗惧会而奔秦。始俘禽其一二兮,气稍振。意薙狝其族类兮,愤乃伸。俄伤饱而恋暖兮,复嗜寝而达晨。信半质之难矫兮,况驴技之已陈。彼瞷尔兮,柔而仁;汝视彼兮,狎不嗔。久遗毒于一室兮,寖旁及于四邻。尔尚施施而厚颜兮,嘿嘿而容身。余架无完衣兮,桉无完书,大穿穴于墙壁兮,小覆翻于槃杅。闯荐庙之鱼菽兮,伺享宾之牢蔬。将大嚼而后快兮,宁垂涎于馂余。彼蝶栩栩于栏槛兮,雀啾啾于庭除。嗅残花、啄弃粒兮,哀所营之区区。尔睥睨而袭取兮,之二虫又奚辜!余甚怜雪衣女兮,置诸座隅,譬之能言之流兮,绝代之姝。雨一旦窃发兮,掩其不虞,使果入朝而入宫兮,其不忮害也夫!
文章的立意和洪适的《弃猫文》相近,但更具生活情趣。作品描写与老鼠朋比为奸的“媚态的猫”的可恶,但是不像洪适的赋那样直白地将其比附现实政治,而是以饶有兴趣的描绘冲淡这种政治指向,这样的细致描写,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对生活中的林林总总所持有的包容态度和对平淡生活中的情趣的深刻体会。类似的作品刘克庄还有《白发后赋》、《蠹赋》等几篇,但是艺术成就相对来说要逊色些。这个时期的赋家对生活场景的描绘具有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一些咏物赋作也多刻画生活场景。如姚勉的《梅花赋》:
养竹于庭,所以标醉吟之清。滋兰在畹,所以风灵均之馨。君子好恬而乐素,不羡侈而慕荣。桃李华而近浮,松柏质而少文。未若斯梅之为物,类于君子之为人。今夫异离木而独秀,冠群芳而首春,是即君子之材。拔众萃而莫伦,立清标而可即,正玉色以无媚,是即君子之容。羌既温而且厉,寒风怒声,悄无落英,严霜积雪,敢与争洁,君子之节也。瑶阶玉堂,不增其芳,竹篱茅舍,不减其香,君子之常也。在物为梅花,在人为君子。皎茵璧之连接,莹壸冰其表里。既物我之通称,又焉得舍此而取彼。兹予所以内交于斯梅,而植之以为庭实也。方其林梢尽枯,琼萼孤出,霜风肃肃,庭有爱日,负朝暄于槛砌,而翻玩乎书帙。此时此花,味我闲适。又如残雪在檐,寒月侵室,浮云四卷,天宇寥阒,倚栏干而长啸,遇神人于姑射。此时此花,助我飘逸。嗟吾屋之半间,陋才止于容膝。惟此花之清绝,相娱笑以朝夕,开醉襟于酒觞,生妙墨于吟笔。使予舍此而他好,殆将丧志于玩物矣。
描写梅花是南宋辞赋的一大关目,一般多为表现梅格为主,像这样把梅花描写置于人的生活场景中,只有南宋后期才蔚然成风。这篇赋先多角度描写梅格,以比况君子之德,而在结尾处引入自己与梅花相伴的生活,展示自己的闲逸、自足,这里没有陆游笔下梅花的那种孤寂绝俗,而是在表现一种纯美祥和的生活情趣,道德诉求与生活情调融合得浑然无迹。这种比德与生活场景并存的结构模式在当时几乎被固定下来,比如吴龙翰的《古梅赋》这样描写梅花:“或横枝照水,如纫兰之湘累;或半树粘雪,如飱毡之汉使;或荒山击寒,孤根回暖,如采薇孤竹君之二子。烈士慷慨,羁臣顦顇。茹铁筋骨,镂冰肠胃。乃道引其形躯兮,如雾拥而云垂,如鸿飞而虎踞,故能曜其夜鹤之骨,而枯其秋蝉之蜕也。若余者,与伊纳交,庐其旁,诏弟读书,对亲奉觞,呼吸清寒,嚥嚼清香,而庶蔑泄吟笔之琳琅者乎!”在展示梅花的品格之后将自己和梅花纳入生活场景,人花交相辉映,展示出透脱的胸襟、恬静的生活情趣、醇和的道德人格诉求、恬静的生活情趣。
这个时期辞赋对生活场景的重视立足于理学人生观修身齐家的思想,在平淡自然而绘声绘色的描绘中蕴含着理学思想所要求的对生活应持有的态度和心境,正如王柏等所主张的,是要如风之动物那样,在自然而然中感化人心,移人性情。其辞赋中所体现出的醇和淡雅恬静温馨之美,正是“理”之人生境界的具体体现。
二 缺略娱乐精神,趋向于严正庄肃的情感基调
我们想用娱乐精神来指代辞赋创作固有的自娱娱人的内在冲动。其实,辞赋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和娱乐结下了不解之缘,[4]不管是对情感物象的铺张排比,还是就审察事理的辩驳滔滔,辞赋主要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尤其是对人情物态的传神描绘,多着力发掘其幽默风趣的成分。不单是那些俳谐赋、俗赋,即使是文人的抒怀言志之作,也包含着反讽自嘲等因子。辞赋整齐的句式、起伏跌宕的节奏,又平添了一种亦庄亦谐的幽默效果。可以说,娱乐精神,是辞赋的传统。展示和欣赏幽默,既需要才华、灵感和对生活的领悟力,又需要一定的素质和超然的心态。在南宋后期,理学道德观是功利主义的,是道德至上的,它更强调凛然正气和庄重严肃的生活态度。理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自身、对生活的揶揄反讽便失去了市场,肃容持敬成为流行的面部表情。因此,南宋后期以来深受理学洗礼的文人学士,逐渐失去了达观通脱和对生活揶揄的态度,失去了挥洒自如的风神,变得偪悃无华缺乏情趣。执著者走向敦厚迂腐,圆滑者走向猥琐庸俗。从辞赋创作方面来讲,严正庄肃成为这个时期的情感基调,娱乐精神黯然失色。
表现日常生活场景是南宋以来辞赋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这类赋擅长把生活中的感悟、机趣融汇其中,使人心领神会,解颐一笑。这个时期的这类赋仍相当多,描写部分多倾向写实,个人的感悟不是着力表现的对象,多流注着慎重持敬的生活态度。尤其是大多数作品结尾的谈论理学思想的部分,更增添了庄肃严整的格调。更有的作品把生活描写得大义凛然,了无情趣。如金盈之的《竹奴文》是描写竹夫人的,竹夫人又叫青奴,是一种圆柱形的竹制品。宋人喜欢竹席卧身,拥之以消暑。因其和人们闲逸的生活情趣相联系,对竹夫人的歌咏,辞赋中多从“夫人”“奴”着眼,如谢薖的《竹夫人赋》、洪适的《竹奴文》,收到了幽默风趣的效果。金盈之则以一副严肃的面孔出现:“非有《鹊巢》之德,《采蘋》之职,曷为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称汝,既以重诬,汝辄披襟,于汝安乎?夫金炯有清明之鉴,而袭彻侯之爵;毛颖以翰墨之勋,而掇中书之除。汝非有功有德,可与二君子为徒。今黜汝之僭号,而谓汝为竹奴。盍安名而谨分,顺主人之所驱。无沮怍以觖望,遂衔冤归憾于吾。”作者对小小的竹夫人也要辨名分,示等威,如果这也是幽默,那么这种幽默实在是太沉重笨拙了。幽默需要平和宽容的心态,而赋中折射出的作者之卫道热情和浩然正气,使得这一题材蕴含的谐趣荡然无存,让人有焚琴煮鹤之叹!也有的作品在可以表现风趣的时候倾注了过多的愤世嫉俗之情,冲淡了作品的娱乐性,如王迈的《蚊赋》:
暑风始至,天宇将昏。玉虫甫挂于明缸,银蟾突出于游云,有喧于室,有哄于门,讴如乱雅之俚曲,噪于不整之溃军。睨而视之,徐而听之,则藐乎小哉,其为蚊也。于戏!尤物之生,有徒是繁。大而猛者,则豺豹狼兕,貙貘麖麈;小而黯者,则蝮蛇蛭蝎,蝍蛆蠭蠜。彼惟肆恶放川陆兮,避之则易;汝独入于堂奥兮,去之也难。彼触之而后毒人兮,其罪犹可贷;汝求人而中伤兮,其情不可原。吾尝观诗人之伤谗,至援苍蝇而为比。蝇惟声之可憎,汝又兼之利觜。吾欲改“止棘”之章,独以汝为谗夫之刺。盖自古之小人,多不利于君子。将圣兮蒙毁于叔孙,大贤兮见沮于臧氏。管、蔡二叔兮,流言于国之硕肤。骊、戚二姬兮,欲摇乎君之家嗣。子椒之间行兮,恶草可掩乎芳兰;歌奴之潜入兮,白羽或移乎秋气。腹有剑兮伺人之可乘,笑有刀兮袭人之不备。盖此曹生则为嚣嚣嗷嗷之人兮,死则为缉缉翩翩之鬼。炙手附熟其故态兮,故多出于炎天;阴邪秽污其旧染兮,故每生于湿地。或被人以痏疮兮,如长庆三杨之流;或进身以纤巧兮,如熙宁十钻之类。吠尧之犬兮同声相呼,食月之蟆兮同恶相比。是何天宇之不肃清,使汝得以陆梁跳踯而为祟也?
苍蝇蚊子是辞赋常见的题材,且无一例外地将之与小人等同起来,多数作品对此二虫传神入画的描写中能唤起人们相关的生活经验,因为它们与人类的关系实在是非同寻常。将之与小人映照,若比附恰当,物我两不相丧,两致其意,的确能使人了然于心,解颐一笑。但这篇作品蚊虫在描写中几乎缺席,作者引经据典,主要是谴责小人,把蚊子视作小人所化,其疾恶如仇如此。这的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其所宣泄的对小人的切齿愤恨,也的确痛快淋漓,展示了赋体文学铺张扬厉的优长,但是给人的感觉是这几乎是一篇讨伐小人的檄文,含蓄蕴藉不够,缺乏使人会心一笑的韵味。在需要调笑揶揄的题材中,当时的文人们展示了严正庄肃的道德情感。在理学的规范下,文章中失却了幽默反讽,而变成一本正经的宣教文字。这其实正是理学所重塑的社会审美风范,崇尚敛情约性、慎重持敬、严肃庄重之美。
当然,也有的赋作在生活场景的描绘中包含着娱乐的成分,使得当时的辞赋不至于完全是一幅正义凛然的道学面孔。如姚勉《战蚁赋》描写了蚂蚁争斗的场面:
若乃柱础润流,浓于郁兴,潢潦虑及,邱侄思升,授兵于雷雨之堂,整旅于檀萝之国。列行伍而序进,势有类于征役。数越千万,陈分什伯。黍民肆腾翥之勇,元驹逞奔骤之力。初曼衍乎墙隅,旋围绕乎砌侧。登爽垲以屯集,养锋锐而待敌。缘阶历坎,负块依石,若创营而立壁也。交持兢啮,以力相格,若陷阵而纵击也。弱者散惊,强者攻克,若追奔而逐北也。利吻如钳,各啣所获,若献俘而斩馘也。方且围户之前,入穴之隙,军拔帜而汉胜,师馆谷而晋食,隳沙砾之楼观,空羶秽之储积。乃整众而还归,类志满而意得。一寓目而观戏,三重为之太息。
天下之区区,何以异于蚁穴之微;人心之好竞,何以异于众蚁之智!……驱万姓于锋镝,争一战之雌雄。竭民膏于中国,要边功于外夷。
作者以人间争斗的视角来审视蚁群的厮杀,甚至还有献俘斩馘告于成功的典礼。将蚁群人间化和将人间蚁群化包含着亦庄亦谐的审美效用,而“三重为之太息”则是点睛之笔,叹息人间的蜗角之争;也叹息蚁群竟然如人类这样残酷,从人到微虫,无不做着毫无意义的争斗,其根源就是“好竞”,就是争名夺利的欲望使然;更叹息时下边将为了邀功,轻启边衅,涂炭生灵。像这样既富于美感又给人启迪的作品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
赋有俳谐一体,专以诙谐戏谑为务。这类赋往往奇思妙想,笔触灵动,忍俊不禁,令人绝倒。要做到这一点,作者必须冷眼观世,方能深入人情物理,洞彻人世间司空见惯的事理中的荒谬悖论。俳谐之赋,虽然以调笑为目的,但是其对浮世人生的刻画相当深入。南宋后期的文人,尤其是受理学濡染的文人们,无法做到内心空灵,冷眼观世,便难以描摹人间的种种谐趣笑料。当时也有人在创作俳谐赋,但多是从理学的道德观出发,把“趣味”糟蹋得荡然无存。如陈淳的《祷黏蝇文》,祈祷苍蝇离开自己的居室。一般来讲,一本正经地做滑稽的事情,具有对神圣祛魅的作用,往往能收到滑稽的效果,但是作者的祈祷太过一本正经了,反而完全失去了喜剧性、娱乐性,如他写道:“况此之地,待圣对贤。天心之讲,王道之传。于赫有临,齐严庄肃。尤非尔曹,所宜厕足。云胡麾之,顽不肯归?天讨明命,岂容而已。咨尔让司黏,恪守乃职。”作者对着苍蝇大谈不得玷污圣贤的道理,此处是圣贤所居之地,苍蝇等微虫是没有资格混迹于此的,若不离开,就要司黏者恪守乃职了。这样的言论,除了流露着迂腐气以外,毫无娱乐性可言①陈淳的俳谐赋缺乏娱乐性,但是他那些严肃正经的文字因迂腐气息极其浓厚而不期然饱含了娱乐成分,如他的《上傅寺论淫戏札》,条陈八条理由主张禁止民间赛会表演,其中有“故簧人家子弟玩物,丧恭谨之志”,“诱惑深闺妇女出外,动邪僻之思”,并说“如此,则民志可定,而民财可纾,民风可厚,而民讼可简”(《北溪先生大全集》卷四七),实在让人大噱。理学思想已经使他的头脑麻木了,其滑稽性也缘于此。。还有陈淳《喻蚁文》晓谕蚂蚁离开自己的厨房,描写苍白,缺乏趣味。其实,当时的许多赋家创作俳谐赋时几乎没有娱乐的冲动,都缺乏娱乐精神,因此,煞风景之文比比皆是。如冉木的《古富乐山移文》:
方豫州置酒高曹于吾山也,升高延佇,虎视徜徉。沃野亘绵,郁乎苍苍。曰富乐哉,有德易王。其兴勃然,遂有一方。吾富乐名,于是乃彰。是时也,汝宅培塿之坂,亦闻之乎?……世道波颓,人情不美。务厌高而喜卑,或疑直而信伪。俄而山空谷黯,地是名非。骚客不吾赋,游人不吾归。川泽无光兮龙欲去,草木无色兮鹤怨飞。是故云英揶揄,宝蝉讪讽,罗浮遗笑,太康嘲弃。谓吾向也亦何丰乐,而今也亦何寂寥也。要之名虽应名,亦各有主,物理循环,名当复其故,于吾何伤,于彼何补?嶆峨兮月淡天低,变化兮朝云暮雨。上媲岷峨兮齐背拍肩,下瞰坵垤兮拳石撮土。是耶非耶,众目共睹。但将富乐,我别今古。
“移文”的俳谐赋通过小题大做来表现其幽默感。这篇赋写的是富乐山的山名发生了转移,以至于真正的富乐山门庭冷落。作者描写了富乐山显赫的历史以及世俗的重名不重实。作品除了替古富乐山愤愤不平外并没有调笑娱乐的成分,作者所关注的,是风俗之恶,而非滑稽幽默。可以说,这是一篇徒有其名的俳谐赋,而其实是一篇义正词严的刺世之作。
南宋后期,真正称得上俳谐赋的只有为数极少的几篇。林希逸《金天移文》是其中较为出色之作。金天指西方之天,佛教指在天竺国所在地,是极乐世界。此赋篇题指西天佛国发来的移文,因为赋中写的是一位友人丧偶后自号“在家僧”,但是写了好多淫词艳曲,因而招来了佛国的移文谴责,赋曰:
今有海滨俗士陈某者,窃其名而强自号。曾不逾时,迹与心背。破玄门之规,犯前修之戒。惟口是而心非,故前贞而后败。盖其始也,燕孤无偶,鸾只不双。粲虽不哭,岳实悼亡。霜寒冬瓦,月冷秋床。情凄凄而易感,哀绪绪以难忘。于是借说空无,纾悲寄意。期以玄机,祛此俗累。昧生天之因,窃在家之义。诱我云月,欺我松桂。虽驾言于双修,实撄情于秽翳。然且和铅舐墨,引类呼俦。私相标置,彼唱此酬。演长句,束短篇。为欺为诞,日颐日玄。自以证身如来,可同李白;思归兜率,何异乐天。使我龙象欢传,法筵瞻仰。以尔尘中人,能作如是想。奈何凡骨难医,欲流莫断。飞絮不沾泥,蒸沙求作饭。故七情作炎,五欲交起。见惑温柔,顿忘法喜。求卿卿之欢,忽如如之理。于是讴歌绕梁,粉黛列屋。主人之心,日且不足。何怀贝叶书,有意采莲曲。当尚子平毕婚娶之年,叹牧犊子雉朝飞之独。犹且绪宝瑟之鸣弦,粲洞房之花烛。昔兮同世界于浮沤,今兮忘泰山而逐鹿。此时此心,将玄将俗。嗟夫!禅关既键,火宅自焚。重将恩爱子,种此烦恼根。是岂不污我淄梵,辱我法门。使玄猿抱惭,白兔怀耻。恨斯人之我欺,嗅迷波之易靡。然诗案具存,前言在耳,亦乌得为无罪也已!我缘此误,惩艾永劫。遂敕禅关,具载玄牒。嗟尔后来人,莫造绮语业。
赋作的主要手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一个自诩为居士的朋友春情摇荡含讥隐讽地调笑。作品放笔铺排了朋友丧偶后的寂寞和难以自持心念佳人一心续弦的躁动,令人忍俊不禁。尤其让人大噱的是在寂寞难耐之际,这位朋友情不自禁把内心的冲动寄于翰墨,作下了绮语恶业。而这一切,又都打着在家居士的幌子。人们受欲望摆布的形状本身就是一种笑料,而如果笨拙地去刻意掩盖,那就更令人绝倒。作者一本正经地引经据典来地谴责,使得朋友的窘态活灵活现。特别是几个佛家典故的运用,就像戏剧里副末鼻梁上的一撮白粉,如文章说朋友假模假式的修行简直是“飞絮不沾泥,蒸沙求作饭”,①“柳絮沾泥”典出北宋道潜《口占绝句》:“寄语东山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絮之在天,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此即禅心所在。“蒸沙”典出《楞严经》卷六:“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饭,经千百劫,只名热沙。”骚动的欲望是“火宅自焚”②《法华经·警喻品》:“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若充满,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忧患,如是等火,炽然不息。”,以佛家语来揭穿礼佛人,把这种“矛盾”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③关于“矛盾”之法在文章中的运用,参看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76-1477页。这篇赋在立意和手法上基本上承袭了徐陵的《答周处士书》。徐陵在答复周弘让书中说:“承归来天目,得肆闲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无孟光之同隐。优游俯仰,极素女之经文;升降盈虚,尽轩皇之图艺。虽复考槃在阿,不为独宿。岂劳金液,唯饮玉泉。比夫煮石纷纭,终年不烂,烧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劳逸之相悬也!”[5]字面上写周处士修行得法,与他人相比,劳逸相悬,而暗指处士的修行其实是打着房中修炼的幌子在行纵欲之实。只不过此赋把这种贪淫与掩饰的窘态描绘得更具体形象了。
姚镕的《喻白蚁文》也是当时一篇优秀的俳谐赋,赋曰:
吾尝窥其窟穴矣,深闺邃阁,千门万户,离宫别馆,复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长亭,缭绕乎其甬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玲珑乎其蜂房。嗟尔之巧则巧矣,盛则盛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钻椽穴柱,不尽嚼而不已。遂使修廊为之空洞,广厦为之颓圮。夫人营创,亦云难矣,上栋下宇,欲维安止,尔乃鸠居之而不恤,蚕食之而无耻,天下其宁有是理。余备历险阻,抽事生涯,造物者计尺寸而与之地,较锱铢而赋之财。苟作数椽,不择美材,既杉椤之无有,惟梓松之是裁,正尔辈之所慕,逐馨香而俱来,苟能饱尔之口腹,岂不岌岌乎殆哉?虽然,尔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亲亲,无闺门同气之斗,近于仁;其行济济,有君子逊畔之风,近于礼;有事则同心协力,不约而竞集,号令信也;未雨则含沙负土,先事而绸缪,智识灵也;其徒羽化,则空穴饯之于外,有同室之义也。
“喻文”是官府中上对下发布的文告、指示,和“移文”一样,常被俳谐文采用。文中以人间生活来比附白蚁的穴居,以“性具五常”来调侃白蚁的生活状态,其对人间生活的反讽非常深刻。作者把人的生存状态和恪守的道德与白蚁做了一番比附,这样就把人类生活的一切价值观念都祛魅了,恢复神圣庄严的平凡状态,喜剧意味被蕴含其中。此外如董鸿《奴戒》也颇有风致。
总之,这个时期的辞赋,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普遍缺乏娱乐精神,不管是理学家之文还是文人之文,都崇尚一种大义凛然的道德宣泄。道德感冲淡了辞赋的滑稽幽默的特性,优秀的俳谐之作凤毛麟角。
三 行文拘谨,气势内敛,表现出整饬规矩的辞章特色
辞赋是古代文人展示才学的重要文体样式。相对于南宋中期,这个时期的辞赋作家的胸襟学力明显有所下降。这一方面表现为行文过于拘谨,缺乏汪洋恣肆挥洒自如的气势;另一方面是辞章法度过于拘泥,以至于千人一面,缺乏创新。辞赋艺术风格的这些变化与当时的理学有着甚深的关联。
科场是理学影响文坛最为便捷的途径。南宋以来的科场,尤其是深浸理学之泽的后期科场,代圣人立言的格局已经形成,对辞彩华丽逐渐排斥,昭示了律赋向八股文的迈进。理学所塑造的人文环境越来越倾向于摒弃诸子甚至集部,专以读经为务,在这一点上,科举的发展趋势和理学达成了共识,这也为塑造明清以来士人的群体特征埋下了伏笔。
在乾道、淳祐年间,理学在科场已经取得了绝对的地位,虽然庆元党禁期间对此大力打击,但是效果似乎不是很明显。淳祐元年(1241)正月,“理宗幸太学,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孔子),黜王安石。”①《宋史》卷一○五《礼志八》。诏文详见同书卷四十二《理宗纪二》。这等于奉理学为正统学术,理学以此完全占领了科场这块重要的学术阵地。②真德秀在给皇帝起草的《科举诏》中写道:“前者权臣崇饰私意,渊源纯正之学斥之为伪,忠亮鲠切之言疾之若仇。繇是士气郁而弗伸,文体浸而不古。肆朕更化之后,息邪说以距陂行,辟正路而徕忠规。四海之士,闻风兴起,既有日矣。今之大比,尔多士各抒所蕴,试于有司。贤书来上,朕将亲策于廷,以备器使”(《西山文集》卷十九)。他在《劝学文》中,劝学子系统地学习周、张、二程、朱熹等人的著作,以及《四书》等:“上、中二旬当课之日,则于所习之书摘为问目,俾之援引诸儒之说,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则仍以时文为课。”(《西山文集》)我们知道,作赋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知识积累丰富,尤其是对前人华章翰藻要广泛阅读。但是,理学主宰下的科考,士子的阅读范围被限定于古圣时贤的书籍,科场衡文以理学思想为准的。③嘉定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国子司业棐言:“南渡以来,嘉尚正学,中间诸老先生虽所得源委不能尽同,究析义理,昭若日星。……权臣误国,立为标榜,痛禁绝之,以《中庸》、《大学》为讳,所趋者惟时文,前后相袭,陈腐愈甚。夫积渐于数十年之久,其说之方行;大坏于数年之间,其论几熄。更化以来,崇奖虽至,丕变未能。……臣谓当此大比,戒谕考官,悉心选取,必据经考古、浑厚典实、理致深纯、辨析该通、出于胸臆、有气概者,理胜文简为上,文繁理寡为下。……从之。”(《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32,北京:中华书局,1957)又嘉定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殿中侍御史胡卫言:“近在淳熙,惟文祖嘉尚正学,粤有洪儒,所得益粹,熏陶渐染,一时学者,皆根柢乎义理,发明乎章句,文风三变……几至于道。而权杆不学,疾视善类,明立标榜,痛禁绝之,以务学为迂,以谈道为讳。……乞明诏四方,一新文体,俾小大试闱,自今以往,精于取士,其有六经之背于章旨,词赋之乏讽咏,议论之昧于趋向,答策之专于套类,芟夷蕴崇,望而屏去。则真才实学,或得于词语之间。……从之”。(《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40,北京:中华书局,1957)其结果是,场屋之文类同理学家的学术文字,失去了才学和辞藻的展示功能。周密在《癸辛杂识》所记“吴兴老儒”沈仲固的话说:“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膴仕,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气焰可畏如此。”①周密《癸辛杂识》绪集下“道学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9页;周密又记载道:“淳祐甲辰(甲辰四年,1244),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癸辛杂识》续集下“太学文变”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5页);《宋史》卷四二五《徐霖传》:“淳祐四年,试礼部第一。知贡举官入见,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奖再三。”“全尚性理”的文章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再三”,鲜明地体现出理学在帝王的提倡下,科举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罗大经曾感叹道:“近时讲性理者,亦几于舍六经而观语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6]由此可见理学对士子读书范围影响之深入。
在这种学术环境中,士人的腹笥塞满了道学书籍,满脑子性理之学,要去以才运学,写出锦绣华章,不亦难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期的辞赋除了储国秀的《宁海县赋》、洪咨夔的《大冶赋》和狂热的道教祖师白玉蟾的几篇赋外,鸿篇巨制不多。即使是应该长篇铺排的题材,如典礼赋,往往也是草草几句就煞了尾,像程珌的《壬申岁南郊大礼庆成赋》和罗椅、刘黻的两篇《明堂赋》等,草率得几乎是应付差事。又如,像黄山这样可写处多多,正需要赋家驰骋翰墨的题材,焦炳炎《黄山赋》却只有三四百字,潦草敷衍。才学不够,以至于无法表达完足,是这个时期辞赋普遍的现象,这与文人知识的积累只限于道学书籍大有关系。这从赋作中千人一腔地宣讲性命之际就可以看出来。而更为可怕的是许多人作赋毫无新意,只是堆砌滥熟的故实敷衍成文,如幸元龙的《梅花赋》除了堆砌一些与梅花相关的典故,竟无一以贯之的意脉,在梅花书写已经相当深入的情况下,这种赋的出现,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再如周文璞的几篇赋都是短短几句,但多不知所云,居简的辞赋也有类似的毛病。可以说,在理学的桎梏下,文人的头脑无法达到灵动自由的创作状态,加之腹笥空虚,无华彩辞藻可供精思傅会,赋作多行文拘谨,气势内敛,失去了挥洒自如的气度。这和当时的诗人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的赋作艺术上都不足取,而是就总体而言才力不够。在这种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一些赋家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创作风貌,这便是语言平易、流畅自然而冲和淡雅,行文不张扬,情感不外露,如王迈、王柏、方岳、刘宰等的赋作,把理学文风提升到一个艺术的高度,昭示着一种新赋风的形成。这个时期颇受后人瞩目的是刘克庄的赋作,他依然沿袭着杨万里等人对机趣的追求,不过才力所限,成就不高。如他的《白发后赋》、《吊小鹤赋》、《谴蠹鱼赋》、《蠹赋》等,或才气不足无以卒章,或拾人牙慧,类似于脱胎换骨般的偷意。
理学意在塑造道德人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时的社会环境基本上是理学的道德观占据话语霸权的地位。文人的情气才华受到规范、桎梏。但是,理学没有能力完全摒弃科举,摒弃他们看不上眼的文学,那就只能树立一种符合理学思想的文体规范,或者用赋格、辞章等来弥补圣贤书籍对文学创作的钝化作用。朱熹曾作《白鹿洞赋》在阐发白鹿洞书院的教育宗旨的基础上发挥张载的明、诚思想,以“开乎时习”,而且文风典雅渊粹,深得风骚之旨。这就为人们树立了一种为赋的规范,人们竞相模仿,如王柏的《宋文书院赋》、方岳的《白鹿洞后赋》、韩补的《紫阳山赋》都是模仿比较得法的作品。朱熹确立了一种以古文的声口、骚雅的情怀来为赋的原则,在当时影响很大。虞集说:“今此篇,辑录文公全书者以冠诸首,家传而人诵之,则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一《跋朱文公白鹿洞赋草》,四库全书本。又,周密《癸辛杂识》记载道:理宗端平二年(乙未,1235)省试,“是岁真西山知举,莆田王迈实之亦预考校。西山欲出‘尧仁如天赋’立说,尧为五帝之盛,仁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题为极大。实之云:‘题目自好,但矮些个。’西山默然。林居与王隔一岭,素相厚善,省试前,林衣弊衣邀王车,密扣题意。王告以必用圣人以天下为一家,要以《西铭》主意,自第一韵以后皆与议定,首韵用三极一家次韵云:‘大圣人之立极,合天下为一家’,四韵尧宅禹宫,大铺叙《西铭》。至是西山局于无题可拟,乃谓实之曰:‘日逼,无题奈何?’王以位下辞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题进,并题韵之意大略,西山击节”(《癸辛杂识》后集“私取林竹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6-107页)。王迈以《西铭》为省试律赋的“主意”,正与《白鹿洞赋》相合,由此可见该赋在当时的影响。它简直成了后来理学赋的范本。
赋格的盛行是当时弥补学识浅露的重要措施之一,赋格完全是为科场律赋服务的,由于律赋关乎士子命运,它的动向对整个赋坛会产生巨大的牵动作用。北宋末以来,《三元衡鉴》牢笼赋艺,这个时期赋格泛滥,郑起潜撰《声律关键》今存,书前有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札子,称“起潜屡尝备数考校,获观场屋之文,赋体多失其正。起潜初任吉州教官,尝刊赋格,自《三元衡鉴》、二李及乾、淳以来诸老之作,参以近体,古今奇正,粹为一编,总以五诀,分为八韵,至于一句,亦各有法,名曰《声律关键》”。[7]这实际上是总结两宋科场律赋格法。他的所谓“五诀”:认题、命意、择事、琢句、押韵等完全是辞章方面的功夫,他对文章布局方式点拨也比较多,如第一韵破题,有“八字包题”、“八字体面”、“贴第一句”、“贴第二句”、“贴第三句”、“贴第四句”、“贴两句”、“贴三句”、“四句分题”、“布置难题”、“一字包意”、“两字包意”、“四句见本意”。他还详细论述了赋的韵律安排与文章气势的关系,等等。李君瑞的《奇正赋格》则从文章的奇正相生出发来教学子如何结构律赋,是书已佚,但是从林希逸为该书作的序中可以窥得一斑,他说:
自退之为诗,正易奇之论,文章家遂有以此互品题者。抑尝思之,张说、徐坚之论文也,其曰“良金美玉,无施不可”,非正乎?其曰“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非奇乎?不妨为俱美也。前辈乃曰好奇自是文章一病,退之亦自谓怪怪奇奇,不施于时,祇以自嬉,然则奇固不若正矣。虽然,李长吉醉尚奇诡,而当时皆以绝去翰墨畦径称之。李义山受偶俪之学于令狐,及其自作,乃过于楚,非以其为文素瑰奇欤?长吉之奇见于歌行,义山之奇见于偶俪。偶俪云者,即今时赋体也。使今人之赋有若玉溪之奇,又何愧于古哉?莆阳同舍李君瑞以赋得名,屡荐于乡,优升于学,每以奇取胜,自谓之伏兵。盖前后见赏有司,皆以铺叙体得之。今集赋家大小诸试,自兰省三舍、诸郡鹿鸣,以至堂补巍掇者皆在焉。每题先之以正,继之以奇。铺叙之外,或以韵奇,或以意奇,或以句简古而奇,或以原头末三韵两韵混成构结。而谓之正者,人固知之;时出之奇,多有流辈思索所未及。譬犹孙膑之减灶削木,淮阴之背水囊沙,初不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自可扼敌吭而破敌胆也。以君瑞肘后之方,已效之剂,不自秘而传之人,得之者当万选万中矣。然唐人论,有“迷”者,有“至”者。其说则曰,以诡差为新奇,一迷也;至奇而不差,一至也。是必知其至而去其迷。以诗之病而验之赋,庶乎得君瑞所以传之法,而又尽其所以至之妙。[8]327-328
看得出来,该书也是教人写文章时如何立意布局的,其所谓“每题先之以正,继之以奇。铺叙之外,或以韵奇,或以意奇,或以句简古而奇,或以原头末三韵两韵混成构结”就是要在立意、句式、韵律等方面给人以新的感觉,这同样是辞章方面的功夫,与学术涵咏不相关涉。当时还有一部《李氏赋编》,欧阳守道为之作序曰:
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不为举业者吾见罕矣。苟为士,则学所当学,日孳孳以终其身,今移孳孳于科举,于身心则无得,于天下国家则无用,然而士不敢不为者,势驱之也。予昔时从事于此,未尝不自笑也。以予之心度他人之心,知凡为此者通病之也。况词赋之为技,视他文尤难精,旷旬月而不习,则他日抽思良苦,他人之已中选者不时取而读之,则无以熟有司之程度,常读常习,以侯一日之试,幸为有司所中,则缘一句一字可以取时名,享禄利。今之甄拔人才,固在一句一字之间也。古者人生八岁入小学,十五则入大学,士以此自进于圣功,而国家以此得王佐。今八岁则习读律对偶,十五则问场屋得失矣。呜呼!科举之害,千百年未易议其革也。士不能由科举,则所谓读而习之者亦安能自已哉?李君编所谓《集贤赋》,实以资同业者读习之助也。其编始放今成,推而上至端平甲午,继此皆以日月相次,凡省监郡邑学之所取皆在焉。[8]439-440
这篇序的看法甚有见地,指出科举之法实除了牢笼人们的心智外于甄别人才意义不大,对科举衡才的权威性提出质疑,这也是当时理学人士的一种论调,他们虽然主张恢复汉代的征辟荐举之制,但是到底拿不出可行的办法来,于是,在功名利禄的吸引下,举国之人都在课赋,作策论,读圣贤书。当时的赋格类书籍很多。其他如《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云:“《指南赋笺》五十五卷、《指南赋经》八卷,皆书坊编集时文。止于绍熙以前。”可见,此二书成书于绍熙年间以后。在文人腹笥贫俭的情况下,赋格的确是一条为赋的便捷途径,但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个时期的其他赋体独有律赋的影子,篇幅短小,讲究点题破题等法,除了立意布局的新巧外,真正反映才华和辞藻积累的作品不多,这就形成一种整饬规矩的文风。
形成当时辞赋行文拘谨、气势内敛、整饬规矩特色还有一个原因颇可注意,那就是当时古文评点的发达。儒道与古文有着亲缘关系,理学大兴,古文也乘势兴起,古文的法度也随着理学浸入到科场当中,以古文为时文,是南宋后期场屋之文的一个显著特色,时文的创作要模仿韩柳欧苏等古文家的声口、语势,学习他们的章法布局,文章学以此而确立,南宋中期陈傅良文章大行于世就是这个原因。吕祖谦、楼钥、谢枋得、周应龙等编选文章选集、评点古文的目的,除了要确立一种合乎理学思想的文风外,另一个用意就是为科场服务。因此,古文章法布局的训练以及古文语势的揣摩也是南宋文人的必备功课,这一点,今人多有论述,此不赘言。古文训练的另一个收获是,南宋后期的辞赋,语言风格更加平易流畅,更接近古文,亦更具有“文赋”的特色。
总之,理学确立了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它给古代文人崇尚的出世之趣注入了匡时济俗的内涵,塑造了一种醇和淡雅的情调,南宋后期的辞赋,则深受这种审美理想的影响,展示了一幅幅恬静温馨的社会图画。道德至上的理学思想排斥调笑和谐趣,这使得辞赋固有的娱乐精神被排斥,辞赋趋向于严正庄肃的情感基调。场屋诗赋格法,古文评点,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整套科考为文的规范。因此辞赋行文趋于拘谨,气势内敛,表现出整饬规矩的辞章特色。南宋后期,是辞赋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是辞赋行文上趋于古文、审美情感上趋于理学道德观的一个转变时期。
[1]跋黄瀛甫拟陶诗[M]//真文忠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2]费元甫陶靖节诗歌序[M]//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3]重改石笋清风录序[M]//鲁斋集:卷四.四库全书本.
[4]冯沅君.古优解[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5]全陈文: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8:3450.
[6]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3:302.
[7]郑起潜.《声律关键》卷首[M]//阮元,辑.宛委别藏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8]全宋文:第三三五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327-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