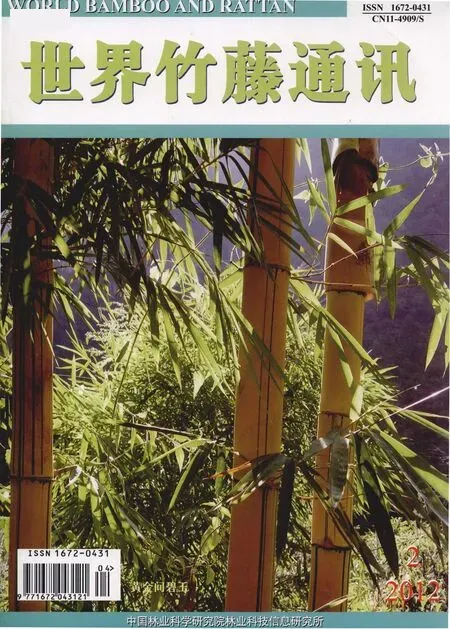日本竹文化的精神内涵
任敬军
(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日本竹文化的精神内涵
任敬军
(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壮美”与“悲哀”是日本竹文化的两重性内涵特征,“悲哀”是其基色,是日本“哀”特征文化的组成部分。
日本竹文化;精神内涵;壮美;悲哀;两重性
“悲哀”美是日本文化的特有特征,表现在包括竹文化在内的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竹文化的精神内涵在于由竹的旺盛生命力与顽强繁殖力的生物特征而视之为日本民族顽向上与坚忍不拔的精神象征[1],即“壮美”。自古以来,竹在日本文化中被神格化,被视为神圣之物、神灵寄居之所,作为大和文化的象征。但是,综观日本竹文化历史及其表现会发现,“壮美”只是日本竹文化内涵的一方面。“壮美”与“悲哀”共同构成日本竹文化的两重性内涵,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展现出来。
1 日本竹文化的“悲哀”之源
史前时期,!即出现于日本神话,并深深扎根于日本文化。天照大神躲进天之岩!,天钿女命取笹叶起舞,将天照大神引出来,此即神乐之始。有着向人类传达神意的魔力。巫女手拿!枝现身村里演奏神乐即为能乐,是舞乐之始。笹作为神的附体之物,最易于神灵附体、驱赶恶魔,几千年来笹一直保持着其神圣地位。
天钿女命取笹叶起舞之因源于天照大神隐遁导致世界光明不再的恐惧,竹(笹)的神圣化及其信仰则源于面对无所不在的万能之神以及恐怖恶魔时的无力之哀、祈望借竹(神之附体)之力驱赶恶魔带来的恐惧。可见,日本竹文化的雏形在史前神话中初现时,就与“悲哀”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日本竹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形成的朦胧期就与神秘、神圣、悲哀融合在一起,形成日本竹文化的原始基色。
史前时期的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日本就出现了竹编工艺文化萌芽,具有巫术的性质,是日本竹文化的前奏,是大和民族形成时期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公元三世纪卑弥呼女王及其后继者台与女王时期,竹笛作为除魔道具而使用,据载:“邪马台国有行鬼道之巫女卑弥呼女王……时有丧仪中丧主号泣,以琴、竹笛歌舞,饮酒之风俗。”日本竹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人们面对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感到无力、无助时,已经从神话传说转变为有意识的借竹之力祈祷神灵保佑的愿望,包含着发自内心的不安与恐惧。
九州隼人的竹编工艺品征收入宫是日本竹文化的开端,九州隼人是日本竹文化的开创者。隼人在臣服于大和朝廷之前,以鹿儿岛的宫之城为最后据点与大和朝廷对抗,被征服后开始了苦难的种族历程:沉重的竹编徭役,长达几个世纪的强制大规模畿内迁徙,充当当权者的护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悲惨生活,《竹取物语》主人公“伐竹翁”是当时隼人社会的一个缩影[2]。
可见,日本竹文化形成之始就在其胚胎之内注入了“悲哀”基因,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即先天性地奠定了它的悲哀基调。“悲哀”是融入日本竹文化内涵的特质性存在。
2 咏竹文学的“悲哀”内涵
在日本文学史上,以竹文化为主题的文学题材历史悠久而丰富。
《竹取物语》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因其浓郁的竹文化背景,主人公伐竹翁已经成为日本竹编工艺文化的象征,主人公辉夜姬是日本传统“美”的代表及日本竹文化的象征。
《竹取物语》是日本古典“竹”之物语,是日本竹文化的象征。根据数千年日本竹文化的神圣性、竹子3月成竹的生物性、竹工艺文化的悠久性、命名竹文化的广泛性等,小说勾画了一副神秘而神圣的日本千年物语图画,在日本竹文化的衬托下形成“壮美”的“化生”与“求婚”情节。然而,由于主人公辉夜姬生自竹筒的“非人类”身份特征,在故事开端之际就埋下“悲哀”伏笔,辉夜姬与伐竹翁以及求婚贵族与天皇等文中人物的“悲哀”结局,奠定了小说的全盘性“悲哀”基色,迎合了“让故事成为悲剧”的日本文化宿命。第3部分的“升月”情节又依借日本竹文化开创者隼人社会与竹的渊源性、日本文学中“竹之春”的文化性、伐竹翁一家悲痛欲绝的场面等,营造了一幅辉夜姬升月画面,表达了神仙面前人类无力、无助的绝望思想。使此日本式“悲哀”发展至极致的就是日本竹文化。前面的“壮美”与结局的“悲哀”相对照,更显此“悲哀”之重。《竹取物语》作为日本竹文化的象征同日本竹文化精神内涵一样有着“壮美”与“悲哀”的两重性特征,而“悲哀”是根本性的。然而,与《竹取物语》有诸多关联的中国《斑竹姑娘》故事则是“壮美”的基调、“大团圆”的结局。
《竹取物语》与《斑竹姑娘》的此种特质性区别,也是中日2国竹文化的重要区别。
《万叶集》21首咏竹歌中,借竹直述“悲哀”的歌有5首,约占四分之一[3]。平安时代文坛领袖菅原道真的咏竹诗大部分借鉴中国咏竹诗赞美竹子“壮美”的特征,而“雪夜思家竹”诗打破以往的咏竹传统,首创性描写了竹在暴风雪摧残下叶落枝断的衰败景象,抒发了自己蒙冤无助的悲叹[4]。作者以己比竹,以竹喻“哀”,表达了日本竹文化“悲哀”内涵的一面。这种“以竹喻哀”的文学手法在较之日本竹文化更悠久、更发达的中国竹文化中鲜有所闻。而川端康成更是在小说《竹叶舟》中,以笹舟文化为背景将战争造成的“悲哀”渲染至极致。
古典能剧《隅田川》、《鸟追舟》、《三井寺》、《樱川》中,狂女登场时手持的笹枝称“狂笹”,是“狂女”的象征。此!即寒竹,10月出笋,异于春夏出笋的其他竹(笹)类,取其悖于生长季节、不合时宜的“狂者”之意,与“狂女”相通[5]。日本传统艺能与竹文化相结合,赋予!独特的传统文化意义,“狂女”放荡不羁的“壮美”表面难掩其内心别夫丧子之“悲哀”。
独特的日本竹文化“壮美”与“悲哀”的两重性特征在日本文学、艺能领域有着明确体现。两重性是日本竹文化的特征。
3 竹文化传统节日中的“悲哀”内涵
以竹文化为主的传统节日是日本竹文化的重要表现。对一百多个以竹文化为主的日本主要传统节日的综合分析后发现,其共同的精神内涵除了娱乐、崇神之外,就是在恐惧恶魔、灾难频仍等“悲哀”基调之上,借竹之神力的防灾、祈福主题。广为流行的“左议长”本是皇宫中的神事活动,仪式用竹必须是金竹,燃烧时每节竹秆“嘭”的发出很大声音,被视为击退恶魔的神圣之物,可让神仙乘坐金竹爆音返回天国,因而金竹是日本传统活动的重要道具。而桂竹等竹秆燃烧时火势弱,并发出“噗”的低音,称为“竹屁”,这样不能使神仙返回天国,以后必受天责。可见,日本竹文化传统活动中的神明尊崇,对仪式用竹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其中展现的竹文化的特殊意义,体现了日本竹文化内涵的另一面,以对恶魔的恐惧之“悲哀”为基底,是借竹(神之附体)抑魔,而敬神不周的结果依旧可怕,仍未免“悲哀”结局。
古代御神体几乎全是竹,这是在交战中以竹枪为武器而感谢竹的思想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因为金竹最易为竹枪材料,所以古代神社中的御神体是金竹。以前,日本神以笋为神体,只有一个神殿。七夕神(星神)传说6-7世纪自中国传入后,没有祭祀场所,就请进祭笋神殿中共居一室共同祭祀[6]。以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为内容的七夕文化与日本竹文化相结合,给日本竹文化增加了一份悲情。天平时代,在宫中清凉殿院中开始七夕祭,立金竹幼株,供奉作物的初物,在纸片上写愿望,向牵牛和织女星祈愿。
日本祭祀的源流始于性崇拜,远古时代的部落当权者为确保自己地位,面临的最大烦恼是自身衰老导致的精力衰落之“悲哀”。在频繁的部落争斗中,胜利的最大因素是士兵数量,部落首领保持旺盛精力多生孩子是关键。因此首领们渴望精力保持。当时,没有比金竹笋生长更旺盛的生命体,于是认为竹是神的附体物。人们惊奇与敬畏于生命的不可思议,从男性自身性的急速膨胀与祈愿永不衰老的意愿出发,将抽象的“生命力”移入现实的笋中,作为御神体而祭祀,将金竹神圣化并以笋为神体建祠祭祀。此即神社的创设主旨。可以说,自太古代起,以哀叹精力不再和祈愿精力永驻为内涵的独特日本性文化便以金竹竹笋为载体,融入日本竹文化,形成了更深层次的日本竹文化双重内涵特征。
笋之于日本人,早生的“初物”之意义远大于笋本身的味道。这是数千年漫长年代里,日本人崇拜竹枪,爱竹、崇竹、祭竹而生的感谢之心的表现,也是日本人的祖先在漫长岁月里,从压制敌人的精神考虑而生发的抢占先机的心理满足感。对于寒风中的鞭笋,是日本人心中的“初物”珍品,备受早老者的喜爱。老人们作为心情料理聚而食之,共同祈祷已逝精力的恢复。鞭笋味道最下等,但价格最高,是“心情料理”的最高珍品。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日本民族精神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悲哀”意识在竹文化中的具体表现,而精力已逝之“悲哀”是祈祷的前提与基调。
4 竹文化传说中的“悲哀”内涵
日本民族有着神圣而独特的!舟文化信仰。新!地方,祭祀时用新生的千岛!制作“!舟寿し”。三重县山田地方,每年7月6日晚用“笹舟”迎接祖先神灵。后醍醐天皇(1288-1339)在海面波涛汹涌之即,制造“笹舟”放之入海告慰海之女神,此风俗一直流传至今。“笹舟”是日本人心灵的家园,是典型的日本民族传统竹文化信仰,是日本人民爱好和平的象征。“笹舟”被赋予特殊的文化内涵,构成其根底的是出于对海神的不安之告慰与救助“八百万神”于海难的日本式“悲哀”。
竹文化是日本门松信仰文化的主要载体。德川家康(1542-1616)在三方原之战中兵败滨松城,以竹束做成防御工事。当时民间仿效之,取“竹束”的“御敌”之意,用竹秆制成门松以防魔驱邪,出于方便将竹上端去掉,成为日本门松文化之肇始。二战以前作为祭祀神体的仅限于金竹。毛竹曾经写作“丧葬竹”、“妄想竹”,被视为竹子家族中不吉利之竹,与神仙全无关联。二战后门松习俗再现,当时由于运输条件限制以及年轻人竹文化知识不足,便将容易到手的毛竹作为门松,再加上毛竹耐干燥、不易枯萎的特性,用去梢的毛竹竹秆制作门松的风俗大流行并延续至今。日本门松文化的起源以及日本毛竹文化的历史内涵,使日本竹文化的“悲哀”基调作为门松文化的隐性内涵而广播于日本的家家户户。
民间传说中,日本竹文化的悲哀色彩同样浓重。奈良时代《日本灵异记》载:某人遇暗算后骷髅中长出竹笋,报恩于拔去眼中笋者并得以洗冤。“悲哀”是这则民间传说的基调,冤情借竹之神力而化解。在日本,“穷命”喻为“一根竹的命”,指沿街叫卖竹器勉强为生的命运。“笋生活”喻指变卖家当维持生计的困苦生活。这种文化现象是日本竹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日本竹文化“悲哀”内涵在日本人内心的生动再现。
5 竹枪:竹文化的血色象征
日本太古时代,特别是稻作开始后,部落间血腥争斗频繁,金竹竹枪作为战斗的最高武器广泛使用,是日本古代唯一的、最古老的武器。为保护竹枪材料(金竹)需要种植山茶为篱笆,并规定偷摘这种山茶花和果实的人处以极刑,因此山茶花被广泛认为是斩首之花、不吉之花。1582年发动“本能寺之变”的明智光秀单骑败走近江途中,命丧栗栖民兵的竹枪之下,如今还有称为“明智之丛”的竹丛。日向米良乡菊池藩,明治维新之前甚至有菊池千本枪的身份制度。
百姓起义又称“竹枪起义”。1834年岩手县竹枪暴动中手持竹枪聚集的饥民达8000余人。1871年福冈县“竹枪骚动”达30万人。竹枪的示威作用远大于作为武器的作用,在争议妥协时,用竹枪尖交换协议书或将诉状夹在竹枪上呈送,以示庄严。1918年日本各地发生袭击富豪与米店的竹枪暴动,饥民手持竹枪迫使米店方廉价售米,其中明石竹枪暴动酿成了流血大暴乱。二战末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强迫平民、甚至妇女参加竹枪训练,叫嚣“用竹枪战斗至最后一个人”,以至于产生了新语“竹枪精神”。此处“竹枪精神”是倡导平民百姓无辜送死的愚民手段,是让老百姓以血肉之躯给美军大炮状行色。所谓“竹枪精神”将日本竹文化的“悲哀”色彩推至无以复加的地步。1952年,吹田的全学联以及成田事件中仍有竹枪登场。农民游行中,用竹筒代替螺号作为发声器具以状威势。源自太古时代的竹枪在战斗、农民起义、战争以及示威游行等场合的运用,将日本竹文化的悲情内涵推至顶峰。竹枪文化给日本竹文化抹上浓浓血腥色,成为日本竹文化悲哀内涵的最沉重历史记忆。
6 小 结
日本竹文化具有“壮美”与“悲哀”的双重性精神内涵,两者相伴而生,“悲哀”是基调。此前为人忽视的悲哀内涵在日本竹文化的朦胧期以及产生、发展过程中,通过神话、文学、传统艺能、传统活动、祭祀、性文化、信仰、风俗等层面,多角度展现出来,成为日本竹文化的重要特征。其中,金竹以及金竹笋在日本竹文化中有特殊的文化意义。
源自太古时代的竹枪文化是日本竹文化的重要内容。竹枪文化与争斗、战争及政治运动的结合,增加了日本竹文化的“悲壮”色彩。具有浓厚“悲壮”色彩的竹枪文化,不但使日本竹文化的悲情色彩达至顶峰,更因其历史凝重感,已经成为日本竹文化“悲哀”内涵的血色象征。
[1]毕雪飞.日本竹文化现象及其内涵[J].浙江林学院学报,2008(3): 375.
[2]渡辺政俊.竹取物語の世界(一)成立の背景[J].竹(75),2001:14.
[3]山田卓三.竹笹と人間[J].富士竹類植物園報告(48),2004:28-33.
[4]後藤昭雄(著)、高兵兵(译).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M]. 北 京:中华书局,2006:133-134.
[5]扇千景.竹のおりふし(それぞれの姿[J].富士竹类植物园报告(47),2003:66-68.
[6]室井綽.バンブー·ノート(40)[J].富士竹類植物園報告(45)2001:186-187.
Double Connotations of the Japanese Bamboo Culture
Ren Jingj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Zhejia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Lin’an 311300, China)
“Magnificence” and “sadness” are the double connotations of Japanese bamboo culture, while“sadness” is the ground color, which is the component of grief-featured culture in Japan.
Japanese bamboo culture, spiritual content, magnif i cent, sadness, duality
浙江农林大学预研项目(2044010007)和日本竹文化的发展历程。
任敬军(1972-), 男,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