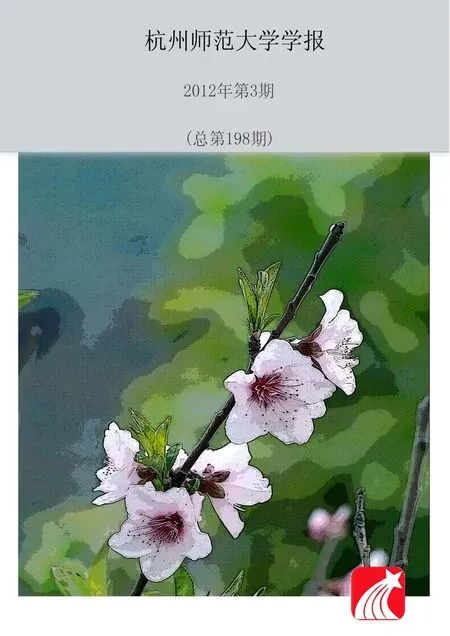人类语言的精神导航:汉语视角
——论洪堡特语言思想的时间轴和空间轴
申小龙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
人类语言的精神导航:汉语视角
——论洪堡特语言思想的时间轴和空间轴
申小龙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洪堡特普通语言学思想在空间轴上尊重和肯定人类各民族语言作为各自民族的精神观念形式,但在时间轴上认为不同的民族语言共同处在一个线性发展序列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具有丰富的纯形式的欧洲语言处在这个序列的最前端。一方面,只有形式化、精确化的语言体制,才能促进思维和观念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决定了思维逻辑的多样性。从汉语的视角审视人类不同的语言依不同的路径对精神的导航作用;其中,汉语的类比逻辑体现了以神统形、以意摄象、完整动态、时空全息的认知功能。
洪堡特;纯形式;类比思维;汉语视角
一 思想的活力与纯粹的语言形式
18-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是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洪堡特的普通语言学思想的一个特点,是在空间轴上尊重和肯定人类各民族语言作为各自民族的精神观念形式;在时间轴上,他认为不同的民族语言共同处在一个线性发展序列的不同发展阶段上,而发展出丰富的纯形式的欧洲语言处在这个序列的最前端。由此,不同发展阶段的语言“唤起”观念的活力是不一样的。洪堡特的思路是这样的。
(一)语言形成结构标志的目的,是为了借助语音来刻画人的知性行为
由此,形式越清晰丰富,语法关系的表达越明确,知性行为的刻画就越有效。一种语言,是在同“语音整体”即没有形态变化的单纯的音节打交道,还是在同“单个的分节音”即具有形态变化的词形打交道,决定了该语言语法的走向。后者引导说话人去层层辨析语法的形态标志,形成生动细腻的语言意识,而前者缺乏语言切分的意识,无法区分、限定、标记丰富的语法意义,无法形成清晰的认识。
洪堡特高度评价“切分”即形态屈折的作用,把它视为语言本质的表现。他认为语言中的任何单位都可以层层细分,它们既是整体又是部分。语言的功效在于各级单位在作为整体时是否易于组合,作为部分时是否易于分解,组合和分解是否精确,是否始终保持形式的一致。由于切分的细致品格直接关系到思维的细致品格,因此切分是语言形式最重要的手段,是语言逻辑功能的体现,同时也是思维逻辑功能的体现。人类一切言语行为的实质就在于“通过精确的分节音使飘忽不定的观念固定下来”。[1](P.113)“固定”,是通过形式标志实现的。因此,“凡是心灵中需要在语言上达到清晰明确的内容,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找到一个能够代表它的语言符号”。
(二)纯粹的语法形式才是真正的语法关系的表达
词序不是纯粹的形式,因为它表达的语法关系是依靠思维附加或者说补足上去的;实词的借用(或者说“虚化”)不是纯粹的形式,因为一方面它本身还有事物的含义,而语法标记只能具备形式意义,不能包含“质料”成分,另一方面它表达的语法关系是孤立的(例如汉语的介词“把”、“用”),不是在一个形式系统中相互关联的。真正的语法关系是体现在实词表达的形态上的变化,也包括一部分只有语法功能的词。
(三)精神的活动,观念的激发,思想的生成,都基于语言发展出的纯粹的形式
一种语言中观念的真正充满活力的发展,关键在于思维活动具有一种自始至终的纯形式兴趣。纯形式,是一种“敏锐的语言意识”,是“语言真正的精神特性和语音特性”。[1](P.94)语音的精细切分使思维因基本要素的凸显而充满活力,促进理性思维的发展,发展稳固的语法形式,因而能够激励整个语言社团。
洪堡特在长期对世界语言的调查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宏阔的语言视野。他完全认识到,并非每一种语言都有当时欧洲人所理解的那种“具有真正意义的语法形式”,然而所有的语言在表达效能上都是基本相似的。尽管这一认识使当时许多欧洲人感到吃惊。洪堡特承认,一种语言的语法关系不必都是有标记的(即可以黏附到词的形式上),无标记的语法关系通过语义的联系可以在说话人和听话人脑子里生成,“也能使语言的构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含混不清和引起误解”。[1](P.40)显然没有一种能够得到理解的语言是未能表达语法关系的,因为人永远不可能零碎地拥有语言,只能完整地(呈关系网络状地)拥有语言。“语言中不存在任何零散的东西,它的每一要素都表现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1](P.20)但是,暗示的——用洪堡特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真正的语法形式的”——语法关系并不能明确有效地促进观念的发展。当一种语言的语法关系不是标记在语言中,而只是作为质料(即作为一个表达事物的词)起作用时,这种语言虽然也能用来表达一切事物和关系,促进理智的认识和智慧,但它的观念“常常摇摆于语法形式之间,满足于实际的结果”。[1](P.42)例如巴西语中的一个词tuba,既是名词(“他的父亲”),又是动词(“他有一个父亲”),还可以类推为一个判断(“他是一个父亲”),实际上,这个词只是把“他”和“父亲”通过多种可能的途径联想在一起。这样一来,观念“混淆”了,语法的概念也“摇摆”了。在混淆和摇摆之中,这样的语言无法孕育形式思维,无法推动观念自由、纯粹地发展。因此,它不能满足观念发展的需要,它的观念活力是抑制性的,隐匿的。而只有“语法形式排序整齐,构成一个自足的整体”,“逻辑关系同语法关系准确地对应起来”,才能“强化观念的作用”,[1](P.43)引导形式化的纯粹思维,使思维敏捷起来。而当一种语言开始采用真正的语法形式时,它的纯形式兴趣就会“苏醒”,进而迈出语言改进的步伐。
(四)思维活动的纯形式兴趣,与习惯于非形式化的意义经联想而合成的语言,是格格不入的
纯形式兴趣不可能在这样的语言中产生,更不可能在这样的语言中安身。一种语言的特定本性,往往在它表达某种语法关系而未采用真正的语法形式时显现出来。的确,像汉语这样有着浓郁的意象思维、类比思维气质的语言中,任何无理据的形式,都不可能长久存在,它们最终会被理据性的形式替换。我们只在汉语外来词中看到极少数无理据形式历经“约定俗成”的历练而幸存下来,如“沙发”。
在洪堡特看来,任何语言都有“形式属性”,语言的发展阶段,视该语言对“形式属性”的重视程度而判分。形式属性越是成功地得到运用,语言越完善,通过语言而育成的知性也越完善。对一种语言优劣的判断不在于它能够表达多少东西(从表达上看,所有的语言都是合格的),而是这种语言能否凭借它的纯形式所具有的内在力量,使观念的表达清晰、准确和活跃。在这里,洪堡特高度肯定语言表达的精确性以及精确性的成因——形式化。精确性和形式化,成了洪堡特对任何一种语言的发展程度或成熟度、完善度进行判断的唯一标准。
我们很难质疑洪堡特的执著,因为他非常尊重每一种语言的结构差异,充分理解和肯定异文化语言形式的价值。他拥有一个西方近代以来一般(狭隘的)语言学家较少具备的在空间轴上看待语言的文化视角。虽然他断言那些没有达到纯形式思维的语言和欧洲最发达的语言之间存在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但他也肯定,如果不从时间轴的角度看两种语言的差异,那么即使是那些十分缺乏真正语法形式的语言,也可以采取“把少量的要素人为地、有规律地组合起来”[1](P.43)的方法,表达多种多样的意义和关系,并能取得言简意赅的效果。但这样一种在表意上可以与欧洲形式语言相媲美的方法,在洪堡特的语言理想中,还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语法形式对思维的重要且有益的反作用”。[1](P.44)洪堡特把语言看作一种精神活动。语言形式的巨大的功效,就在于能够促进思维更活跃、敏捷、精致和完善,而这一点,在洪堡特看来,只有纯粹的语法形式,或曰真正的语法形式,才能做到。而这种“优越的语法结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洪堡特将这种语法形式的产生比作金属的熔化,促其熔化的是强大的思维力量之火。强大的思维力量必然追求形式区分,促使语法形式化。在这里,洪堡特似乎进入了循环论证:语言的形式力量能够使精神习惯于严格区分语法形式,从而导向形式思维、纯粹思维,而思维的形式力量又能够使语言强化形式区分,融合分散的形式要素,产生新的真正的形式。我们当然可以把两者的关系看作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洪堡特最终把思维的力量归诸一个“优秀的”民族,显示出他难以超越的文化限度。他说:“毫无疑问,一种语言不论其命运如何,如果它未能有幸被一个具有丰富的精神或深刻的思维的民族哪怕只是一度所操用,就决不可能达到优越的语法结构。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能把一种语言从模棱两可的形式中解救出来,这类形式只是松散地相结合,不能满足思维力量对精确性的需要。”[1](P.56)洪堡特很难理解,这样的语言何以能使一个民族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变革语言。
二 语言形式系统的理想化
作为欧洲人,洪堡特很难突破在时间轴上看待不同文化发展的线性视角。文化这个概念,在空间轴上得到理解,尊重差异,这是相对容易的;而在时间轴上,要得到同样的理解和尊重,对于人类来说,尤其是欧洲人,貌似“不可能的任务”。这几乎是18世纪以来欧洲学者的根本局限。洪堡特是一个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看法是单一的动因、单一的路径,即一个朝着既定目标,在一个时间轴上从上帝创世的起点到世界末日(上帝审判人类的终点)的线性运动。这样一种发展观,在18世纪的欧洲衍化为一种基于“人类心理一致性”的文化单线进化理论;即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循着一个由落后到先进,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直至高度完善的直线运动;其深层逻辑是人类心理的不断完善导致心理派生物的不断完善,而完善与否的标准是理性。人类文化的差异就这样依“理性”程度的高低被重新排列为一个由低到高的时间序列。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上半叶,这是欧洲人的文化单线进化论逐渐形成的时期。而洪堡特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思想界热衷于按直线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人类各民族文明史的时期。在洪堡特之前,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Anne Turgot,1721-1781)基于人类经济形式发展的进步趋势提出了文明发展三阶段(神话阶段、思辨阶段、科学阶段);最早使用“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弗格森(A.Ferguson,1723-1816),基于从苏格兰高地原始公社制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文明”取代了“野蛮”的进程,提出人类对自然天赋的运用趋向完善,欧洲近代商业文明是文明发展的典范。尽管他在对商业社会的批判中认为即使最高度发达的社会也有退回野蛮专制的可能,并且对人类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既定路线”不感兴趣。另外,影响了19、20世纪欧洲思想家的启蒙经典,法国哲学家孔多塞(Jean Condorcet,1743-1794)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描述了“人类不断进步”及其线性历史进程的美好理想。欧洲思想家在时间轴上论证世界文明趋于完善,同时也在空间轴上论证了欧洲(尤其是西欧,即英法)是人类社会模式的最高典范,形成了欧洲中心主义。此后的文化进程理论,甚至按种族、地域而非文化的特点来划分发展阶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与洪堡特同时代的黑格尔按人类的童年、青年、成年、老年(完全成熟的)划分东西方的历史进程,其中东方在最底层,欧洲日耳曼国家在最顶层。可见,把欧洲文化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顶点,并以欧洲文化为尺度,将其他异文化放在不同的进化位置上有序排列,这是洪堡特时代的一种观念局限。
在洪堡特宏阔的视野里,人类的语言演进之途依形式的精确和明示与否而有“歧路”和正路、“顺利”和“不太顺利”之分。在他看来,“有些民族出于自身的独特个性而选择了类似这样或那样的歧路,或是片面地追求一条原本正确的道路;有的民族得以比较顺利地处理其语言,有的民族则不太顺利”。[1](PP.31-32)他赞扬希腊语那样的语言,是“命运之神”的“成功的一掷”。由此我们读懂了洪堡特对语言的真正兴趣:一种语言的魅力,不在于它的文学的灿烂,甚至不在于它的民族特色和历史内涵,而在于它“通过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基本成分的属性,以很不同的方式引导并束缚着精神和感知”。[1](P.8)洪堡特关注的就是人类语言引导、束缚精神的各种“不同方式”。而在丰富多样的“不同”之中,洪堡特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不同语言的很不相同的引导方式,对精神的引航作用有深浅正误之分。语言在这里就像一架乐器,表面上看乐器声在追随人的精神,实际上乐器“为精神和感觉指示了正确的道路”;而怎样的“乐器”才能为思维插上翅膀“随风而舞”呢?洪堡特的答案是:具有纯粹的语法形式的屈折语。他认为:“精神要求语言对事物和形式、对象和关系作出明晰的区分,避免把二者混淆起来。……而这种区分惟有在利用屈折形变或语法词的真正的语法形式构造中,才可能彻底地完成。”[1](P.58)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使人的概念清晰、表达明确、意识缜密,从而不断对思维和思维着的人产生反作用。
洪堡特并不把人类语言的符号形式(符号施指和受指的关系)如索绪尔那样看作是任意的,而是重视符号形式的精神内涵和民族性格。洪堡特在评价人类语言差异的时候,也使用“任意性”这个词。此时的“任意性”与索绪尔的“任意性”有叠合之处,即语言是一个形式系统。索绪尔在空间轴上将语言的形式系统普遍化,用“任意性”遮蔽了人类语言的文化差异;洪堡特则在时间轴上将语言的形式系统理想化,把“任意性”作为人类不同文化的语言演进的共同标杆。洪堡特将人类语言的表达形式大体分为任意性和自然性两类:前者“可能更多地表现出习惯用法和约定俗成的痕迹,带有更多的任意性”;后者在词的意义渊源上“可能更具自然属性”。[1](P.76)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都可以看作词语(表达认知的客体)和语法(表达概念的联系方式)两个部分的博弈。自然性的语言,其语法不发达,概念在心灵中的呈现方式是“生硬断续”和“杂乱拥挤”的,我们可以将之重新解释为“弹性实体”和“意象组合”。如果缺乏中国文化和语境的意会和诗化能力,这种疏朗的语法的确是“生硬断续”的。任意性的语言,其语法形式严密丰满,概念在心灵中的呈现方式是“轻松灵便”和“自然流畅”的。之所以“轻松”、“灵便”、“流畅”,就是因为繁复的形式在粗糙的现实之上建构了一个平滑的逻辑层面,说话人不必多做意会和默想,就可以在形式框架上滑来滑去。洪堡特十分赞赏这种“流畅”的感觉,尽管这样的“自由”在中国文化人的心中受到束缚,因此很不以为然。
张世禄曾经指出:“汉语和藏语未经分离以前,原来也是一种变形语(即洪堡特所说的纯形式语言——引者),后来汉语逐渐发展为现今孤立的性质。”“汉语演变的现象,正是由变形语进趋于孤立语。”不仅英语“到了现代已经大半成为分析语了”,而且“从前的梵语和较后的希腊语、拉丁语,往时的拉丁语和现代的法语、意语,两两相较,印度日耳曼语的变迁,无不有趋于分析语的途径”。印欧系语言演变的趋势“也是由综合进趋于分析,由变形进趋于孤立”。“各种语言里虽然进步迟速不等,而文法减省,形式单纯,实在为世界语言共同的倾向。凡有历史可稽的语言,都以应用便利、表现显明而日趋于简单化的。”对于那种认为古代语言形式周密,现代语言形式疏漏的说法,张世禄认为:“周密疏漏,必以意义的表现适可而止;现代语的疏漏,往往有他种较便利的方法来补救;两者比较,还是近代语比较合于实用。”张世禄反驳了将纯形式语言(综合语)视为语言类型进化最高阶段的观点:“语言由综合而进于分析,乃是进步的现象;十九世纪的学者所说孤立语最初等,正是适得其反。”[2]
汉语具有与欧洲语言气质迥异的文化特征。形式的弹性与刚性、结构的松散与紧密、功能的多元与一元、表达的灵活与确证,语言差异的两端中汉语与欧洲语言各据对立的一端,在洪堡特看来都是需要精神去拯救的。而只有欧洲民族凭借“丰富的精神或深刻的思维”才能做到这一点。洪堡特为他宽广视野中的人类语言差异下了价值判断。这样的价值判断值得商榷。
三 语言形式实现精神导航的汉语视角
每一种语言都完备地实现了它的思维和交际的功能,这一点我们和洪堡特没有分歧,而且非常钦佩和欣赏洪堡特的思想。但是否只有形式化、精确化的语言体制才能促进思维和观念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更多的是一种信念或信仰。
认定形式化、精确化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体制,其前提是形式化的思维是高级思维,而精确细致的语言形式有助于促进这种思维。在这一前提的更深层,是认定人类的思维形式、逻辑类型是统一的。否则洪堡特何以用能否促进形式思维的发展作为语言完善与否的标准呢?然而,洪堡特的这种逻辑一元论的深层信念,是和他的语言多元论的主张相矛盾的。“逻辑”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λóγοζ(logos),其本义就是“词语(word)”、“理性(reason)”和“言语(discourse)”,引申为词与物中蕴含的“思维”或“推理”,指世界的可理解的规律。希伯来圣经中记载上帝的语言是万物之源,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这种无上的智慧(即后来约翰福音书所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之“道”)被称为logos,于是语言和思维在“道”的层面统一起来。1902年严复译《穆勒名学》,将其意译为“名学”,音译为“逻辑”。我国古代的逻辑问题探讨被称为“名学”,“名”也是词语、概念的意思。可见,逻辑具有语言性,或者说它来自语言。只不过欧洲传统逻辑在其抽象过程中对自然语言的实际意义和关系舍弃得太多了,成为一种极其抽象的形式,使欧洲的语言逻辑看上去似乎是外在于语言、与具体的语言无关的。于是欧洲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这个从欧洲语言中走出的貌似“外在”的逻辑以人类普遍的属性,同时又很自然地将原是它的本源的欧洲语言(尤其是希腊语)看作最适合逻辑,最有利于逻辑发生的形式运作。当洪堡特歌颂希腊语的语法形式,歌颂语言中的纯形式思维时,他实质上依然是在肯定语法与思维的本质联系,只不过他误将他的母语系的形式化特征模铸的形式思维“非本质化”(非语言化),视之为最高级的思维类型,随后以此为标准,依不同语言形式对“最高级思维”的适应程度,为人类各种语言的完善程度排序。我们遗憾地看到,在洪堡特的“语言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命题中,“精神活动”的方式是有优劣之分的。张世禄在他的名作《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中对欧洲学者的这一看法提出了批评:
主谓结构才成为句子的观念,唯一的根据,是“主项和谓项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命题”这种形式逻辑。我们知道,语言是用来表示逻辑的。反转来,形式逻辑也一定要受语言习惯的反作用。“主项和谓项构成命题”这种西洋形式逻辑的形成,恰恰是受了西洋语言上主谓结构才成为句子这种习惯的影响。汉语的语法事实既然和西洋不同,那么,汉语的语法理论当然不应当受西洋的形式逻辑的限制。[3]
显然,形式逻辑来自欧洲语言注重分析、演绎的习惯。与中国语言文字注重意象、注重在上下文和语境中的意会相适应的,是另一种逻辑,我们暂且称之为类比逻辑。这里的“类”是说它的单位是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而非同一、抽象、普遍的;这里的“比”是说,它的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相关的、广域的,它的相关前提是松散的、高度依赖语境的,它和事象发展的脉络是贴近的,它的思维是灵动的、跳跃的。
类比使得汉语的单位(类比的项)不必依靠形式论证发生相互关系,而依靠自身的意象即可发生丰润且多义的相互关系。由此在汉语语法中呈现出浓郁的意象思维。从欧洲语法的视角来看,就是“读者往往不得不凭上下文去猜测,某个词应该被理解为名词、形容词或动词,还是语助词”(洪堡特转引阿贝尔·雷慕萨《汉文启蒙》的观点)。[1](P.60)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看来,问题不在于一个字(词)本身是否确证(自足地限定),而在于任何一个词在上下文和语境中都不是自足的,都需要“以大观小”地确证。对个体(小)在本质上离不开所处之境(大、众)这种东方思维,欧洲人是很难理解的。当欧洲人直观地看中国语言文化中单位的表现时,他们立刻就被“雷”(像雷慕萨那样)倒了。
类比又使得汉语的单位在描摹现实的时候,不需要一个游离于现实之上的抽象的、自成体系的形式框架,而是使用贴近现实经验的时间流组织,惟妙惟肖地“譬况”事理延展的过程。由此在汉语语法中呈现出流畅的经验性的事理思维。从欧洲语法的视角来看,就是“含混不清”,甚至“不连贯”(连贯的前提在欧洲语法中是连贯的单位在形式上的一致关系,而非意义上由此及彼的自然顺序),“几乎不具备任何通常意义的语法”,“语法关系仅仅由词序或独立的词来表达”。洪堡特质疑用这样的语言书写的古典文献(例如“孔夫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是否具有“真正的语法形式”所能影响并予以促成的优点,即像雅典人的散文那样,在“明确限定”的丰富多样的语法形式促进下,表现出雄辩、敏捷的特点。相对于汉语语法形式的经验性,洪堡特崇尚的欧洲语法形式实际上是先验性的。它在人与世界之间先验地设置了一个逻辑系统,人只能借助这个逻辑系统进行分析、聚焦,才能认识世界。哲学家李泽厚对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有一个深刻的解释:“中国是讲究经验的合理性,而不是像西方讲先验的理性,先验的理性是绝对的,而中国人则要根据经验合理地改变。”[4]这就是欧洲语言句法主谓二分、动词中心的框架和汉语句法事理铺排、意尽为界的差异之源。
类比还使得汉语的句子表达经常把一种观点放进虚与实、开与合、往与复、此与彼、先与后、问与答、景与情、主与客、纵与擒、兴与咏、名与实、叙与议、动与静、起与承……总之,是把世界放在一个两两相对的相互映衬之中加以感受。由此在汉语语法中呈现出诗意盎然的耦合思维。
类比还使得汉语的表达以深沉的体验放弃了形式的完备,将词句与上下文和语境互为生发,扩大联想,“人详我略”,拓展了丰富的言外之意。由此在汉语语法中呈现出语境通观的整体思维。洪堡特用“满足于形式”和“不满足于形式”来区别人类语言对立的两极。在他看来,某些民族(例如欧洲各国)热心经营完备的语言形式,力求用语言形式把一切语法、语义的差别标记明白,用“言内之意”穷尽所有的意涵。这些民族“显然更满足于它们的语言所勾画的世界图景,只不过还试着把更多的光明、联系和平衡赋予语言”。[1](P.75)另一些民族(例如汉民族)热心经营能够生发丰富的暗示和联想的语境,“仿佛一头扎进了思想之中”。它们对语言形式的表达有着深刻的不信任,只期望在语言的感性触发中(节律的开合回环,音调的抑扬顿挫,字形的画面感和情绪基调)让意义澄明。因此这些民族在洪堡特看来“永远不满足于现有表达,不相信能予以适当的运用,因此忽略了形式本身的自足和完善”。而洪堡特所谓的“忽略”,恰恰是中国文化“以神统形”而非“以形摄神”的追求。[5]
在人类语言和思维发展的进程中,语言的多样性决定了逻辑的多样性。[6]
研究中国文化源头之一《周易》的学者周山,对类比逻辑的产生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一种推理系统,如果是由“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建构的(例如拼音文字的字母符号是完全透明的“空壳”,可以参与字母之间的任意变换,造就反映一定内容的概念形态),必然具有演绎的性质;如果是由“属性明确”的初始符号建构的(例如表意汉字的符号是意象的生成、衍异和组合,它的每一步推理都是类比),必然具有类比的性质。
中国人选择类比作为主要思维形式,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无改,根本原因不是“内圣外王之道”,而是选择了一条由象形文字发展为象意文字的文化道路。象形文字是单体字,是远古先民对具体物象的描拟。随着思维活动的发展需要,先人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体字组合为一个复体字,便产生了象征某种意义的象意字(又称“会意字”)。每一个象意文字都有“本义”和“延伸义”;每一个象意文字的“本义”只有一个,“延伸义”往往有多个,这些“延伸义”大多是类比思维的结果。一个陌生的象意文字,你、我可能读不出它的音,但是从构成它的几个单体字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体悟出这个字的“本义”,甚至可以类推出它的“延伸义”。例如,“蛊”字由“虫”、“皿”两个单体字构成,可由此会意到器皿中出现了虫这个“本义”,并由此产生类比性的联想,得到了“腐败”这一延伸义。因此,用象形单体字和象意复体字表达思想的华夏先民们,注重类比思维、善于类比推理也就成为必然。[7]
表意汉字的构形方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假说。与类比思维异曲同工的,还有语言学家孟华提出的意指思维。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单位和所指对象建立了经验的直接联系,“人们在脱离系统的孤立状态下也可以明确所指对象和问题答案”。汉字的意指思维“使用可视、可感、有理据、非线性的方式表达客观对象”,在结构关系上更强调画面式、蒙太奇式、联想式的连接。孟华认为,这种编码原则“转移到汉语语法中,就是徐通锵所谓的‘字本位’性(由基本单位的理据性所决定的结构关系的语义性)和申小龙所说的‘以神统形’”。[8]当我们和洪堡特一起探索语言对民族精神的创造性活动的影响,引入一个独特的汉字视角,会有崭新的启示和阔大的视域。在这一视角得到深入之前,我们同样可以从汉语语法的建构方式认识中国文化的逻辑特点,汉语语法的建构和汉字的特点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前者深受后者的制约。
长期以来,精确化和形式化被树为语言形式的一个标杆,进而被树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标杆。但我们已经看到,语言首先是一个复数。迄今为止,语言形式分析的术语,究其实质,都有其文化的限度。换一个视角我们可以问:语言为什么必须形式化和精确化?语言学又为什么必须成为一门精确的学科?语言有自身的语音系统、语法系统,在人文现象中它的形式的确是“精确”的。从结构主义发源于语言学也可以看出语言结构的某些方面具有数学的性质。但这一切在本质上都是相对的,因而是表象的。语言系统本质上仅仅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人类语言形式的多样性深刻表明,语言的“精确”有其文化的限度,或者说语言的“精确”深刻表现了一种文化的限度!我们越是深入语言形式的“精确性”,也就越能揭示语言的文化差异。由此,“精确性”实际上是一个差异性的概念,造成其差异的本原是不可追溯的、具有多元结构的是文化世界。所以,不是“希腊语才达到了结构完善的顶峰”,[1](P.62)而是希腊语达到了结构精确的顶峰。而这样的“顶峰”,不过是人类语言文化群峰耸立之一隅。只有在发出“语言学为什么必须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的疑问之后,我们才真正能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树立起语言学精确研究的范式,使语言学真正成为一门领先科学。
[1]威廉·冯·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姚小平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张世禄.汉语在世界上之地位[J].大学,1933,1(3).
[3]张世禄.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J].复旦学报,1981,(s1).
[4]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M]//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75-299.
[6]申小龙.语法与逻辑[M]//当代中国语法学.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59-62.
[7]周山.中国究竟有没有“逻辑”[N].文汇报,2011-08-01.
[8]孟华.文字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334-335.
OnMentalPathfindingEffectsofHumanLanguagesfromaChinesePerspective——theSpaceAxisandTimeAxisofHumboldt’sLinguisticTheory
SHEN Xiao-l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Humboldt’s general linguistics research respects and affirms in space axis all kinds of human languages as mental concept forms of different nations, but believes in time axis different language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in which the European languages stand in the forefront. While only the formal, precise language system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and ideas, the variety of human languages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of thinking logic.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mental pathfinding effect, especially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Chinese analog logic such as governing forms through spirit, combining images through meaning, macro- integral dynamics, and space-time holography.
Humboldt; pure form; analog logic; Chinese perspective
2012-02-14
申小龙(1952-),男,浙江杭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史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
H0-06
A
1674-2338(2012)03-0086-07
(责任编辑: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