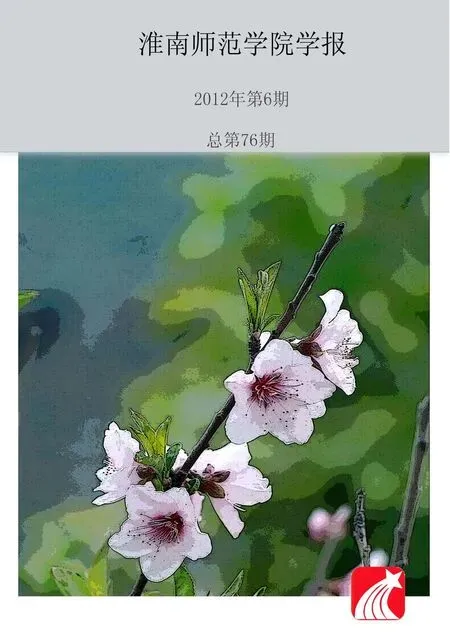沉思者的叙述实验——论卞之琳《山山水水》
杨培蓓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卞之琳于1941年初开始创作 《山山水水》,至1943年完成初稿。因觉得小说中涉及“政治问题”,日后不可能在国内出版,又为了让欧美知识分子更了解中国,卞之琳便一边修改初稿一边将作品翻译成英文。由开篇到最终搁笔,这部7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总共跨越了八个年头。他在1978年所作《〈雕虫纪历〉自序》中回忆道,写作前夕“特别是在昆明听说了‘皖南事变’,我连思想上也感受到一大打击……当时妄以为知识份子是社会、民族的神经末梢,我就着手主要写知识分子,自命得计”,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震动了英国,也震醒了我……”。解放后作者回到北平卷入“热潮”,对于这部作品的态度也随之变化,由而“反思”自己的小说“竟在那里主要写了一群知识分子而且在战争的风云里穿织了一些‘儿女情长’”,“蹉跎了岁月”。①卞之琳:《山山水水(卷头赘语)》,《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在50年代初期,作者将全稿烧毁,由于之前在杂志上发表过些零星章节,所以才得以存留一些片段。直到1982年,卞之琳凑齐了这些片段“自己重读一下”,“觉得还值得留痕”,故才有了如今的《山山水水》。这部小说的始末都与战时的政治事件相关,由“皖南事变的打击”开始,至“淮海战役的震动”而结束,内容上讲述了几位不同知识分子的战时经历,小说本身一波三折的身世也让我们对特殊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探究。
纵观四十年代文学创作,历史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战争观占据了主流文坛,主流文学的“典型”观强调要“集中地有意识地抓住要害(本质),删除某些偶然的表面的现象”②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页。,而卞之琳的小说《山山水水》在那个时代显然是不合潮流的,它是一个有着作者独特理论设计和丰富的个别、偶然象征的独立文本,是四十年代为数不多的实验小说。而卞之琳在三十年代以诗歌著称,四十年代其创作文体的大转变和对文本持续近八年时间的潜心译改,给这篇小说更添加了某种伟大的实验力量。他的诗歌中曾多次出现“沉思者”形象,“在荒街上沉思的年轻人”③卞之琳:《几个人》,《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页。奔赴战争前线之后,显然陷入了对某种更宏阔更深刻内容的沉思,如同他自己所说是要表现“狂妄想法”④卞之琳:《读宗璞〈野葫芦记〉第一卷〈南渡记〉》,《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1页。。令人遗憾的是,1950年作者因“悔恨蹉跎了岁月”,一把火烧毁了全稿,但从小说所残留的章节中依然可以窥见卞之琳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姿态在四十年代智性的留痕。
前后方战场及不同城市间的辗转经历让卞之琳——这位沉思的诗人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但其繁密思绪的背后自始至终仍保持着自我的坚持与反思,“其实来去都在我预定计划之内,纵然时间有了长短,路线有了出路,结果也有了歧异。可是我还是我。我坐既未改姓,行又未改名”①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初版前言)》,《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8页。。延安的参观之行并没有使卞之琳像何其芳一样选择留在延安,在他所作的纪实文章 《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1949年重版的序中卞之琳仍特意强调了自己当时(延安之行后)的“无党无派的身份”。他以在四川大学还有教职为由推辞了周扬等人的挽留,却在返回大西南之后“一鼓作气”地进行《山山水水》的创作。作者仿佛要一改过去在“时代风云面前,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悲喜反应”②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4页。的常态,他说自己“不满足于写诗,梦想写小说……诗的形式再也装不进小说所能包括的内容”③卞之琳:《山山水水(卷头赘语)》,《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小说的叙述化能力是群体在历史中定位自身能力,应对这一群体过去为历史所再现的必然性的能力以及想象一种对其 “命运”的创作性超越的能力的体现……而叙事化过程被认为是一种特殊人类机构的基础,它将必然性升华成一种可能性自由的象征。④[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01,202页。智性诗人卞之琳其文体转笔背后的深层诉求让我们注意到残篇《山山水水》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作者在《雕虫纪历》的自序中,也提及到小说创作的初衷“妄图以生活中‘悟’得的‘大道理’写一部‘大作’,用形象表现,在精神上、文化上、竖贯东西,沟通了解,挽救‘世道人心’”。在所剩几篇独立的叙述章节中,作者对于“世道人心”的小处敏感,捕捉到了现实社会的贫乏与人们心灵的落难;而在艺术抽象的“道”“悟”中,作者寄以了超验的存在哲学,他企图在混乱中追求某种秩序的建立,这种企图不仅体现在文本的艺术结构上,而且在思想内容上。无论这种抽象的思辨追求是否成功,但恰是在时代洪流里对于某种超验秩序的构建追求反映了独立个体对自我主体性的重视和强调,体现了一种内心潜在的自由时空预想,同时也反映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战争背景下其身份的社会性反思和时代参与的意义。
一、世道人心的蜕变:战争对于个体心灵的消解与侵蚀
作为诗人,敏感多思的性格特质让卞之琳在小说叙述中也表现出对于细节的高度敏感与关注。文本中故事的情节化叙述往往被男女主人公对于细微处的观察与体验描写所替代,这些细节的感触通过人物对话与心理独白被赋予“真实性”的展现。卞之琳在《评沙汀〈淘金记〉》一文中曾提出“小说家在小说里连篇累牍地作不相干的描写,不相干的议论,实是旁骛,对于小说本身有害无益”,可见担当“编造中心”的主人公们其视点的落脚处是作者精心构造和筛选过的人、物,富有象征意味就成了各处细节描写的共有特征。对于“世道人心”的丰富的小处敏感,则展现了作者在四十年代战时大背景中对人心独特而忧深的发现,这里可看作是其智性诗歌的“非个人”化手法的叙述衍变,作者以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民族的神经末梢”,通过男女主人公对社会现实的观察感受,分析思考,表达出个体丰富的心灵体验和战争认知。
在《春回即景二》这一章节中,女主人公林未匀起先对于空战场面的向往,竟颇带些诗意,“如今既亲自在场,她越发惋惜她不曾看见战斗的情形”,“可是她当时就感觉到十分难堪,竟不能瞥见一下招惹的飞机本身,只一任它们把声音穿织街上的一道蓝天空”。于是寻找战败的飞机在未匀看来似乎更倾向于是某种时事阅历的证明,当找到被打下的飞机之后,她对于敌机抱有一番惆怅的同情,“‘这是一架飞机的归宿吗?’未匀在心里感叹。‘你该让水塘只掠一下影子,留给它一个耐久的怅望。谁叫你动作得这么笨,糟蹋了风景,吹断了——你看,这不是你的笨翅膀干的?——一棵小柳树?”当得知飞机底下有一个死了的日本人,未匀竟眼前一阵黑而晕倒。与未匀同样“不合时宜”感性的蓝若冰,因为一张泥污的日本女子照片在流泪,此举也得到了一阵围观和哄笑。与此相对应的是,周围哄笑的众人们外出寻找飞机的目的在未匀看来也是奇怪的,“他们显得像出来春游呢”,“小店铺老板娘,自己怕走长路,就派一个学徒去看看掉下的飞机,回头好让她尽管饱不了眼福,也比较直接地饱一下耳福”。那些捞沉机的庄稼汉在女主人公看来“不像在捞东西,倒只像在玩。有的存心把水踩得重重的,一步拍上来一片泥浆的水花”,“未匀看见这么吆喝的一个小伙子正在跨骑着飞机翘起来的尾巴,就像一个人骑着一头泅水的海豚”。
作者在两者看似不同的战时心态的对比中透露出一种普遍的共性观,人们对于战争实质的认识往往都有一层恍惚的盲目与跟从,战争造成了现实生活的灾难和贫乏,而人们却在这种贫乏辛苦的生活中又反而将战争当成了生活的调剂和娱乐。小说中作者特意提及到一个细节,未匀看见一堆人挤在一起看电影的预告,放映的是当日的空战新闻片,战争甚至成了贫乏生活中另类的消遣。刚走出书斋的女知识份子会感伤战争带来的生命悲剧,而百姓们在战争胜利的刺激下将伤亡和残酷看成了一种理所当然。但往往只要通过像小说中立文这样的积极参战的演说家一番激动的雄辩——“血渍只有用血来洗涤;战争只有用战争来消灭”,就会让未匀开始对自己在战争面前的一丝迟疑和犹豫而感到惭愧,个体在群体的时代面前永远只能是无力的跟从者。
而在《海与泡沫》这一章节,男主人公梅纶年在参加延安的开荒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思考,在“海统一着一切”、“浪花消失于海”的意义总结中,梅纶年最终得出“文化人拿锄头开荒的意义:从行里出来的言又淹没在行里,从不自觉里起来的自觉淹没在不自觉里”,似乎是肯定了知识分子个体融入群体的改造。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海与泡沫”这番思考中,作者多次穿插了梅纶年对于自己潜意识的压制,所有个体自主的想法都被他归结为“想入非非,不伦不类,令自己讨厌”。开荒结束后梅纶年得知他们绕了许久来到的开荒地,实际只是在自己窑洞上面翻土种小米,面对这种回归原始的现实劳动,一切赋予开荒的深刻思考在这里受到了一种反讽意味的消解。
作者在小说中提出了一个人类局限在现实灾难面前的个性的心灵悲剧。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谈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倾向时曾说,“以外部世界为其舞台的灾难在这里屡见不鲜。然而最大的悲剧以人的心灵为其战场,甚至无需恶运的特殊的播弄的悲剧,却没有在同等程度上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四十年代的主流战争文学。结合卞之琳1949年2月在《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未刊行改名重版序)》中所说的有关观点①“这将近十年之间,正如大家所周知的,国家与人民不断受了多大、多深而多半是不必要的灾难”,“用我们读书人的眼光看来,可哀也可笑的是……如果不只会瞎着眼睛,倒行逆施的乱禁书刊,而相反的多少也学会读读书,因而也能够间或读到这一本一类的显然不是为某一方面作片面宣传而只让事实说话的记述,举一反三,而有所明晓,有所反省,有所启迪,进一步读些别的本来容易叫人望而却步的读物而更有所进益,那么,抗战就不必拖那么久而几至不可收拾,更何至有日后扩大的内战,迄今才渐进尾声的大规模流血、毁坏、消耗、建设进步的延迟?”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未刊行改名重版序)》,《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3页。,他认为恰是战争对人们思想行动的独裁才会造成战争灾难的拖延和更大的伤害,战争似乎成为了世间一切行动的指挥者,它仿佛在统一规划一切,而《山山水水》的创作可谓是作者当时用心良苦的一次精神启迪与挽救的实验,叙述文本中对“世道人心”的小处敏感,展现了在社会现实贫乏的状况下,人们心灵丰富性的萎缩与主体性的落难,由此小说也表达了卞之琳对于战争更深刻的一层认识——其对于人心灵的侵蚀。
二、抽象秩序的建立:“变”中前进,“变”中“不变”的守恒
由于对“世道人心”蜕变的敏感发现,卞之琳企图以其智慧的“圆宝盒”贯通相隔相接的时代山水,并在混乱的矛盾中寻找一种秩序的建构,通过这种超验的抽象秩序,作者力求在变化中寻求“前进”,并在不断前进中达到“不变”的守恒。文本结构上作者精心构建了“螺旋推进”的秩序:设置四个不同的地方为背景,人物之间互相推动而出场“每次再出场都有些不一样,在不出场的地方有的也会提到,不出场而无形中在场,因此也划了一道道旋进的弧线以至不同平面的圆线”,“总是一种旋进的态势”;叙述视角上作者“让一切人物、事物都是这一位局中人的耳闻目睹”,又“使她不只是‘观察员’、‘见证人’,而且又名符其实是局中人,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只是还顺了她观看的方向(角度)”,此谓“推前去一点”的叙述视角②卞之琳:《山山水水(卷头赘语)》,《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而在文学内容上作者认为“惟有表现时代的艺术品才有永久性,……可是也就在它表现到时代的深处,不在表现了瞬息万变、朝三暮四的浮面,而在表现现象,以意识到本质的精神”③卞之琳:《安德雷.纪德的〈新的食粮〉》(译者序),《卞之琳文集》(下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02页。。小说通过一定程度抽象化的叙事走向象征,意欲通过象征的方式摆脱具体事物、现象的限制而达到某种超验的本质认知。作者通过重复出现的意象和象征将零碎的主体经验连接起来,而这些重复出现的字眼与意象,在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与先一次更不一样,另带了新的关系,新的意义,且“大多是由无足轻重的地位,进到主要的地位”,这样,小说就显示出“一种批评的风格”,其思想的表达是通过反复逼近它本身来实现的④范智红:《现代小说的象征化尝试》,《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从而达到某种旋进秩序的生存哲学。
这种超验哲学集中寄托在小说对于艺术、绘画、书法、山水景象的抽象议论中。《山水·人物·艺术》这一章节,未匀谈到书法,认为“那实在只剩了早已成了规律的一些线条的变化,一些超过了形象的姿态的变化,可是这里如何容纳了执笔者各自个性的发扬——一如中国旧戏里都有固定规律的‘唱作’帮助了各有个性的演员”,这是一番对于个性与共性的探讨,涉及到抽象秩序的必要性,未匀肯定了在某种固定的规律中是可以表现不同个性的,甚至可以通过表面的固定而达到某种质的超越与发扬,问题在于这套手法不知如何运用到现实世界中。到了《雁字:人》章节中,纶年对于书法的讨论又在这一观点上向前进了一步,“我们的书法,我要说内容即‘姿’。可是写字上也最容易认得出人。那么,要写好字,还得先修好人;不然‘姿’就没有生命了”。由此可见作者认为只有个体的自我发展和提高到某种水平时才能形成一种普遍的 “姿”,在个性自觉形成的高水平共性下不同个性才能得以继续提高和完成自我的超越,不死的‘姿’恰体现了生命的寄托与价值,这是卞之琳超越现实经验而寄以的辩证贯通,是作者对于混乱的战争时局下有关生存的思考,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都可由此推导而出。联系卞之琳1949年4月后的政治表现,他一扫早期的“冷静”高蹈变得脚踏实地,似乎更是应证了此时有关“共性”力量的看法,但在那之前作者仍主要倾向于完善独立的自我发展,他这篇耗费巨大心血的叙述实验本身就体现了四十年代卞之琳作为一个智性知识分子强大的个人主体意识。
同时小说篇章中重复性字词“寂静”与“空白”在意义上的衔接递进,也体现了卞之琳“道、悟”的螺旋上升,“寂静”在第一章《春回即景》中意为“城市被攻占后的紧张”和对于战争胜利认识的一种“虚渺”,而到了《桃林:几何画》中,“静”却能表现最激烈的斗争;“空白”由笛子没有空就吹不响的“无之以为用”①李松睿:《时代·个人·小说——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0年第3期,第53页。的意思进步到赏析《秋江图》中能表现个性、让人与山水合一的力度,词义的层层递进也体现了作者对于现实的逐步超越,而无论是人与“姿”还是“空白”与个性,在小说文本中这种超验的思辨始终是定位于个体自主性之上的。
卞之琳就如同自己笔下的林未匀,“一看见这么多人,我就觉得有点眼花,多少副面孔在四面浮浮动动。幸而我想到了一个想像的匾额,上面写了‘川流不息’,大可以高悬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马上我就像站稳了脚跟”②卞之琳:《山山水水》,《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他将生活抽象化,赋予某种观念,转而在观念中形成存在的艺术哲学,以此重新审视现实投入生活,形成一种螺旋的前进。梅纶年的专业——交通史研究者——似乎就是作者赋予叙述文本深刻意义的暗示——展开“道、路”的悟解和秩序的追求认知。在动荡的民族危机下以旋进变化的视角看待现实,在变化中前进,求得某种“不变”的风姿和精神,而在守恒的精神追求之下方能体现生命的价值,这就是卞之琳赋予象征意义的“不死的姿”。而这种“不死的姿”以独特的叙述手法呈现,在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里则是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卞之琳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我们不能以是否有娴熟老练的文学叙事技巧或存在多少艺术成就的标准来判断要求,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作者给予四十年代文坛所带来的新鲜文学形象和深沉的文学思想价值。当智性诗人不满足诗歌略显狭促的理性表达时,叙述文本成为了他寄予沉思与智慧的最好方式。作者以一颗敏感多思的心感受到战时社会人们的贫乏,在个性心灵与共性感召的矛盾中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现实战争观,反映了战争的残忍与人们身心的陷落,以此提出了问题解决的警示。同时他力图进行某种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对现实的道路进行“道、悟”,企图以超验的存在认知达到某种精神秩序上的共通来追求生命的价值,体现了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社会可贵的责任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