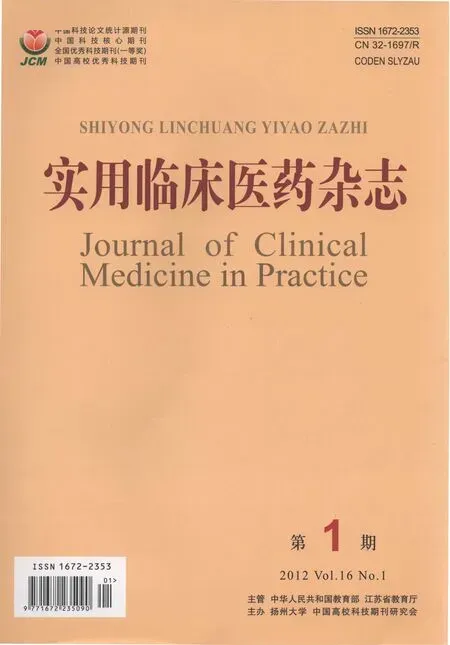转化医学指导肿瘤个体化治疗的现状与挑战
张西志,张先稳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江苏扬州,225000)
近年来肿瘤的治疗疗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在不同种族人群或个体间仍存在显著的治疗敏感性和不良反应的差异。目前常用的抗肿瘤化疗药物对患者治疗的有效性不仅低于70%,而且,由于缺乏化疗药物个体化治疗的遗传学分析,使20%~40%的患者甚至有可能接受了错误的药物治疗,同样病理类型、病期甚至分子表型相同的患者在接受相同方案治疗后可能产生“天壤之别”的结果[1]。临床医生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唯一能告诉患者家属的原因就是“个体化差异”,深入来讲就是基因表达的不同,导致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转化医学的出现有助于实现肿瘤的个体化治疗,有可能达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境界。
1 转化医学指导肿瘤个体化治疗的现状
转化医学[2](translational medicine)主要涉及基础医学与临床应用间的双向转化过程,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应用之间的桥梁,是循环式的科学体系即基础研究的新成果及时转化到临床应用领域(包括医疗、预防、护理等多个方面),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更先进的措施和方法(bench to bedside),并在临床应用中及时反馈、修正,再进一步转入相对领域深入研究(bedside to bench)的不断转化、提升,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转化医学的实现需要有综合性转化医学团队共同完成。这一团队由转化医学中心或转化型研究机构、医院、预防与保健机构、社区服务机构、医药企业等系统化的综合构成。广义上讲,转化型研究主要指基础研究与应用领域的双向转化过程的相关研究,转化型研究应用于医学领域就产生了转化医学[3]。由此可见转化医学是双向的,基础医学指导临床实践,临床实践为基础研究提高新的课题和方向。
目前已经在临床上实施或即将可能实施的肿瘤相关转化医学研究主要有:通过结构基因组、分子表型、临床表型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genomic complexity(CAAI)可作为乳腺癌的独立分子标志物[4];分别利用前列腺癌代谢产物化学图谱(三维彩色图谱)、前列腺癌中循环肿瘤细胞的定量自动成像系统,可用于检测处于早期阶段的前列腺癌[5];亚硝基谷胱甘肽还原酶(GSNOR)、雄性激素受体对肝癌形成的影响[6];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与肺癌等发病的关系[7];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肺癌等恶性肿瘤;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诊断和治疗靶点;药物dichloroacetate(DCA)治疗恶性胶质瘤的等[8]。
在临床实践中,现代科学的技术进步为肿瘤的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是由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加入使人类治疗Ⅳ期肺癌的中位生存时间提高到12个月以上,而人类为了将Ⅳ期肺癌的中位生存期有8-9个月提高到一年以上,耗费了近10年的时间[9]。人类从浩如烟海的基础研究中发现多个基因的表达与肿瘤药物化疗的敏感性和或耐药性有关,如:BRCA1的表达水平高提示对抗微管类药物敏感,表达水平低提示对铂类药物敏感;ERCC1表达水平低对铂类药物敏感,表达水平高表现耐药;TOP2A表达水平高对蒽环类药物敏感,表达水平低表现耐药;TUBB3表达水平低对抗微管类药物敏感,表达水平高表现耐药;TYMS表达水平低对氟类药物敏感,表达水平高表现耐药;RRM1表达水平低对吉西他滨类药物敏感,表达水平高表现耐药。通过检测肺癌细胞中EGFR基因的突变情况可指导该患者是否可首先使用TKI药物治疗肺癌,如存在19、21外显子的突变提示对TKI药物敏感,如为野生型提示该患者一线治疗最好首选化疗。笔者近年来,借助大型生物检测公司的平台,开展了对复发、难治性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化疗药物敏感性的基因检测,共送检20例患者,其中10例患者为治疗中进展,6例患者复发后进行治疗,4例患者一线治疗,初步统计结果表明总的有效率约80%,如此高的有效率的确令人兴奋,而且有5例化疗中进展的患者取得缓解。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共有4例患者出现Ⅳ度骨髓抑制,中位持续时间5天,20%(4/20)的Ⅳ骨髓抑制的发生率令人难以接受,这个结果初步表明基因指导下的个体化化疗的确可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同时由于肿瘤细胞和血细胞中基因表达的同源性,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敏感的同时可能也对血细胞敏感,从而导致了治疗效果与毒副作用上的“祸不单行”。
众所周知,肿瘤的治疗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手段难以奏效,目前多种肿瘤的治疗手段采取同步放化疗技术,就当前的发表文献来看,目前尚无人开展药物基因检测一线化疗联合放射治疗的前瞻性研究,笔者认为这种化疗方式可能不同于常规方案的联合化疗模式,因为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部分食管癌术后患者即出现淋巴结转移,在使用常规化疗并联合放射治疗后,患者的肿瘤控制较差,通过检测患者的肿瘤基因,发现存在原发性多药耐药性,由于肿瘤在化疗耐药和放疗抗拒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二者均涉及有肿瘤生存凋亡、分化转移等有关的信号转导系统,因此对可能存在放化疗抗拒的患者,积极进行基因检测,指导临床治疗,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这种思路对患者的治疗将大有裨益。
2 转化医学指导下肿瘤个体化治疗的挑战
转化医学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目前的研究方兴未艾,一方面转化医学的重头戏靶点治疗确实是整个肿瘤治疗中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基因表达“三维空间+一维时间”的特点,使得其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10],如何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患者,给合适的药物?肿瘤是一种系统性和全身性疾病,必须对多个细胞传导通路进行阻断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必须找出准确的分子标志物进行药物选择,同时还要考虑到患者的免疫状态、心理状态、内分泌及血液系统等因素,因此不能说有了转化医学这个桥梁,就能够从顺利的“从河这岸到河对岸”,正如笔者对20例患者的初步分析统计结果表明那样,出现4例Ⅳ度骨髓抑制的患者在后续的治疗中,面临着两个问题:患者能否继续化疗,如继续化疗再出现Ⅳ度骨髓抑制将对患者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按照肿瘤化疗药物减量的原则,减量25%~50%的化疗,是否还有抗肿瘤作用,因为无法保证化疗的疗效100%,但是任何剂量的化疗药物都存在100%的毒性,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为避免出现以后类似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检测患者肿瘤细胞内相关基因表达的同时,检测患者血液中相关基因的表达,而且以基因表达的绝对值来量化,采取“避轻就重”的原则谨慎实施,即选择在肿瘤中敏感基因绝对值较高,而同一基因在血细胞中绝对值相对较低的相应化疗药物。
从转化医学的发生发展来看,转化医学是实验室的产物,也就存在着实验系统的准确性、精确性、稳定性的问题,患者的基因检测结果是否是患者体内情况的真实反映,既然如此为何不能获得100%的疗效,这说明单一检测某个基因或某几个基因并不能反映肿瘤的真实全貌,转化医学的研究也是一把“双刃剑”,只有深入了解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才能真正将转化医学为临床服务。
[1] Janelsins M C,Kohli S,Mohile S G,et al.An update on cancer-and chemotherapy-related cognitive dysfunction:current status[J].Semin Oncol,2011,38(3):431.
[2] 杨春喜,殷 宁,戴魁戎.转化医学[J].中华医学杂志,2010,90(7):499.
[3] Geraghty J.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J].Lancet,1996,348(9025):422.
[4] DiGiusto D L,Kfishnan A,Li L,ct al.RNA-Based Gene T herapy for HIV with Lentiviral Vector-Modified CD34+Cell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plantation for AIDS Related Lymphoma[J].Science T ranslational Medicine,2010,2(36):36.
[5] Wu C L,Jordan K W,Ratai E M,et al.Metabolomic Imaging for Human Prostate Cancer Detection[J].Science T ranslational Medicine,2010,2(16):16.
[6] Wei W,Li B,Hanes M A,et al.S-Nitrosylation from GSNOR Deftciency.Impairs DNA Repair and Promotes Hepatocarcinogenesis[J].Scienee Translational Medicine,2010,2(19):13.
[7] Gustafson A M,Soldi R,Anderlind C,et al.Airway PI3K pathway activation is an early and reversible event in lung cancer development[J].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2010,2(26):25.
[8] Miehelakis E D,Sutendra G,Dromparis P,et al.Metabolic modulation of glioblastoma with dichloroacetate[J].Science T ranslational Medicine,2010,2(31):31.
[9] Uramoto H,Mitsudomi T.Which biomarker predicts benefit from EGFR-TKI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J].Br J Cancer,2007,96(6):857.
[10] 曾益新.肿瘤学转化医学思路[J].协和医学杂志,2011,2(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