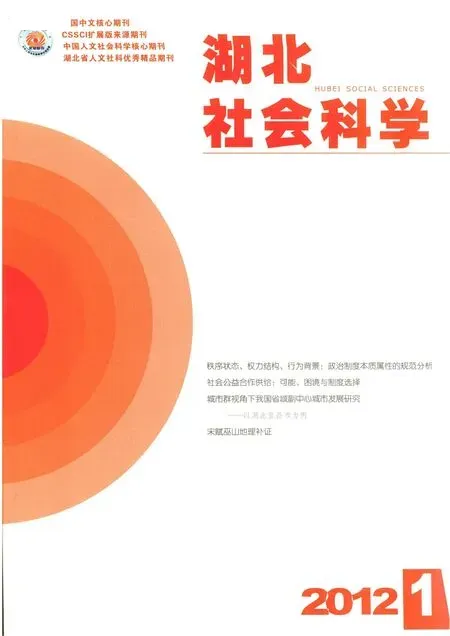论刑法中的危险
李金明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论刑法中的危险
李金明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随着主观主义理论的衰退,作为刑罚处罚根据的危险是指行为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将刑法中的危险区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并不可取;危险是行为的属性,而不是结果的属性;只有当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才能成立危险犯。危险是由一定的主体根据具体案件的客观事实,所做出的行为具有侵害法益或者造成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结论。关于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二者在处罚根据上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由于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危险才成立犯罪,其区别仅在于刑法对前者规定了“危险”的要件,而对后者没有规定“危险”的要件。未遂犯也属于危险犯,未遂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完全适用于危险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
危险;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未遂犯
一、引言
在刑法理论上,按照处罚根据的不同,可以把各种犯罪区分为实害犯和危险犯:实害犯是以对法益的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这类犯罪在构成要件上表现为,除了行为人实施一定的行为以外,还要求出现法益侵害的实际结果,行为才构成犯罪,例如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等;与此相对,危险犯是以对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这类犯罪除了要求行为人实施一定的行为以外,在实质上还要求出现侵害法益的危险,行为才构成犯罪。其中,刑法明文将行为发生侵害法益的危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明确予以规定的犯罪,被称为具体危险犯。例如,我国刑法第114条(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6条(破坏交通工具罪)等条文规定的犯罪属于具体危险犯;此外,刑法总则第23条规定的未遂犯也被认为是具体危险犯。[1](p315)刑法虽然未明文将发生侵害法益的危险,作为构成要件予以规定,但是,实施了某种行为通常就具有侵害法益危险的犯罪,被称为抽象危险犯。例如,我国刑法第125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6条(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等规定的犯罪就属于典型的抽象危险犯。
由于实害犯中的结果具有明确性、具体性的特点,例如行为导致他人死亡、重伤以及财产损失等,具有物质性、数量化的特点,所以,认定起来比较容易。而与之相对,危险犯中的危险,则十分模糊、笼统,更不具有物质性、数量化的特点,因此,认定起来非常困难,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于如何理解和判断危险犯中的危险,目前还是一个难题。本文旨在探讨刑法中危险的概念及其属性,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就如何区分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以及未遂犯与危险犯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二、危险的概念
刑法中的危险概念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行为人危险性说”,它是指性格的危险性,或者犯罪的品质、犯罪人的危险性及其反社会性。这种人的危险性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尚未犯罪者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和有前科者再实施犯罪的可能性。第二种是“行为危险性说”,它是指行为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性。[2](p270)“行为人危险性说”是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主张,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行为人的危险性格。主观主义刑法理论旨在贯彻特殊预防的目的,实现社会防卫,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特殊预防,即消除犯罪人再犯罪的危险性,故针对犯罪人的危险性格科处刑罚才具有意义;只有消除了犯罪人的危险性格,避免其再次犯罪,才有利于实现社会防卫。因此,犯罪人的危险性格是科刑的依据,外部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但由于受到认识手段局限性的限制,只有当犯罪人的内部危险性表现为外部行为时,才能认识其内部的危险性格,即只有借助于外部行为才能发现行为人的危险性格,所以,又不得不将外部行为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在主观主义看来,犯罪无非是行为人危险性格、犯罪意思的表现,通过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表现出来的危险性才是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无论是既遂犯还是未遂犯,其可罚性的根据都是行为人的危险性。
在涉及危险判断的领域,“行为人危险性说”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如何处理迷信犯的问题。按照主观主义的理解,迷信犯的行为人同样通过其迷信行为表现出人身危险性,因此就应当定罪处刑。然而,迷信犯无罪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只要认为迷信犯不可罚,就会与“行为人危险性说”的基础理论相矛盾。
随着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衰退,以“行为人危险性说”作为定罪根据的见解已经被彻底放弃,作为处罚根据的危险是行为的危险,即行为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问题是,如何理解危险的性质?这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危险是行为的属性还是结果的属性?
国外许多学者基于行为无价值论或者结果无价值论的不同立场,将危险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行为的危险是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因而也可以称为行为的属性;作为结果的危险是指行为所导致的对法益的危险状态,是“原因行为后所产生的危险,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说,指行为的作用已经进入到被害人的法益范围。”[3](p222)因而也可以称为结果的属性。
笔者认为,将刑法中的危险区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这一做法并不可取,很容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按照这一分类,行为的危险是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作为结果的危险,是行为所造成的一种可能侵害法益的危险状态,因而属于结果。[1](p154)这一分类的最大缺陷是混淆了“危险”与“结果”这两个概念的界限,把本来没有造成法益侵害、仅仅是对法益造成某种危险的状态也视为一种“结果”,这就违背了人们对结果的基本认识,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首先,根据哲学上的基本概念,结果是与原因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它是指由另一个事物或现象而产生、引起的事物或现象,这一事物或现象与原来相比,其在形态和本质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状况。这就说明,结果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实际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一种现象,结果必然具有现实性。而危险是行为导致法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因此,危险不属于结果。其次,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一致认为,危害结果具有因果性、侵害性、现实性、多样性等特点,[4](p85-86)据此,行为只有对法益造成了现实的侵害事实,才属于刑法中的危害结果。而危险只是行为对法益造成了侵害的可能性,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当然不等于“侵害性”与“现实性”。因此,危险不等于结果。第三,如果将危险视为结果,那么,既遂犯和未遂犯的区分将变得毫无疑义。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我国有学者认为,犯罪未得逞是指犯罪人所追求的、受法律制约的犯罪结果没有发生。[1](p317)如果认为危险也是结果,所有的未遂犯就都变成了既遂犯,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的区分就会失去意义。第四,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是严格区分“危险”和“结果”两个概念的,法律并未将“危险”视为“结果”。例如,我国刑法第116条规定:“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并不属于本罪的犯罪结果,否则,“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无法理解。
既然危险不是结果,就不能从结果的角度来理解危险概念,所以,从行为的角度来理解危险概念就是当然的结论。而且,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危险显然指的是行为本身的危险。例如,前述刑法第116条规定的“破坏……足以……发生……危险”,这一表述显然告诉我们,是行为足以发生某种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而不是指行为已经造成的危险状态。因此,危险是针对行为性质而言,而非针对结果来讲的。结论是:危险是行为的属性,而不是结果的属性;只有当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才可能成立危险犯,否则,行为不构成危险犯。
(二)危险是一种“判断”还是一种“状态”?
与前述危险的属性问题相联系,在刑法理论上还存在着究竟应当把危险看作是一种“判断”还是一种“状态”的争议。
行为危险论者主张,对危险应当作“判断”的理解。以特定的行为及事态等等作为对象来判断行为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从而认定“危险的”行为或者“危险的”事态。例如,以布利(Buri)为代表的主观的危险说认为,危险是人类无知的产物,它是由各个判断者根据自己的主观观察来决定的。因此,危险的有无取决于判断者的主观认识,而不是取决于客观事实。与此相对,结果危险论者认为,应当将危险理解为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例如,以克利斯(Kriss)为代表的客观的危险说认为,危险是出现有害事实的客观可能性,也可以说是一种状态。所以,危险的有无取决于客观事实。[2](p273),[5]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在具体问题的结论上,并不一定截然对立。判断说是站在判断主体的立场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因为,危险的有无及程度的高低,都是由人(判断主体)做出的。对于同一种行为,可能有人认为它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有人却认为它不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因此,危险的有无,当然取决于判断者的主观认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判断危险可以脱离客观事实,因此,判断说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再从状态说来分析,该说认为,危险是出现有害事实的客观可能性,危险的有无取决于客观事实。这显然是站在判断资料的立场上所得出的结论。因为任何主体的判断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判断,都必然要依据一定的事实资料来做出自己的判断结论。但是,依据一定的客观事实得出有无危险的结论,并不意味着客观事实本身就能说出有无危险的结论,而是必然由一定的判断主体,根据客观事实才能得出有无危险的判断结论。因此,状态说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但是,上述两种观点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在吸收二者的优点及克服其缺陷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危险是由一定的主体根据具体案件的客观事实,所做出的行为具有侵害法益或者造成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结论。
三、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区别
在刑法理论上,一般把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两种类型,但是,对二者如何进行区分,目前尚无定论,概括起来讲,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构成要件说,认为具体危险犯是以发生危险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而抽象危险犯是不以发生危险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根据这种观点,当危险既是立法者设立处罚规定的根据,同时又是司法实践中定罪的条件时,便是具体危险犯;反之,虽然危险也是立法者设立处罚规定的根据,但仅此而已,危险既不是构成要件,也不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证明行为存在危险,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便构成犯罪时,就是抽象危险犯。换言之,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构成要件,因而需要具体判断;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不是构成要件,因而不需要具体判断,也不允许反证,即便行为人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危险,也不妨碍抽象危险犯的成立。
第二种观点为认定标准说,认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都是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的根据,但是,前者的危险是需要在司法上具体认定的,而后者的危险是立法上推定的;其中,有人主张,对于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不允许反证,有人则主张,在有反证的情况下应承认没有危险。据此,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都存在危险,只不过前者是有具体证据证实的,后者由立法推定、毋需证实。
第三种观点为危险属性说,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具体危险犯的危险是“作为结果的危险”;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是“行为的危险”。如日本学者松生健指出:“具体的危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的区别是,在具体的危险犯中,要求有构成要件上的‘危险’这样的‘结果’,而抽象的危险犯则没有这样的要求。着眼于这种法文规定的形式上的差异,二者的区别应是:具体的危险犯=‘作为结果的危险’;抽象的危险犯=‘行为的危险性’。”[5]
第四种观点为危险程度说,认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都是以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但二者的危险程度存在差异。关于危险程度差异的表述并不完全相同:有人认为,两种危险的差异在于对事实的抽象化的程度的差异,即具体危险犯要求在具体范围内考察有无危险,而抽象危险犯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考察有无危险。有人认为,抽象危险犯是具体危险犯的前一阶段,即“侵害意味着发生实害,具体的危险意味着侵害的可能性,抽象的危险意味着具体的危险的可能性。”有人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紧迫的、高度的危险,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较缓和的、低度的危险。我国学者张明楷赞成以对事实的抽象程度来区分二者的观点。[5]
对于以上四种观点,笔者均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应当从刑法的目的以及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形式上的差别来对二者进行区分。由于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危险犯,其在客观上都是对法益造成某种危险的行为,刑法是不会把对法益没有造成任何危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因此,立法者把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规定为犯罪进行处罚的理由都在于,二者对法益造成了危险。这是二者的共同点。二者的唯一区别,表现在构成要件的形式上:对于具体危险犯,刑法明文将发生侵害法益的危险,作为构成要件予以明确规定了下来;但是,对于抽象危险犯,刑法并未明文将发生侵害法益的危险,作为构成要件予以明确地规定下来。刑法之所以没有明文规定抽象危险犯的危险,是因为抽象危险犯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危险性,只要实施了特定行为,通常情况下就会对法益造成危险。例如,我国刑法第125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非法制造、买卖枪支行为,通常情况下,就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危险。因此,基于立法简洁性的考虑,刑法条文就不必将危险规定为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但这绝不意味着就不要求行为对法益造成危险。
前述第一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是以发生危险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而抽象的危险犯是不以发生危险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构成要件,因而需要具体判断;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不是构成要件,因而不需要具体判断,也不允许反证,即便行为人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危险,也不妨碍抽象危险犯的成立。显然,该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既然承认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一样,都是把发生危险作为处罚根据,那为什么允许对完全没有任何危险的行为,也认定为抽象危险犯进行处罚呢?这明显违反了刑法处罚危险犯的目的。第二种观点也没有充分说明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根据,同样可能出现将现实上没有任何危险的行为认定为危险犯的情况。第三种观点立足于危险的不同属性来对二者进行区分,其区分标准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危险是行为的属性,而不是结果的属性,将刑法中的危险区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这一做法并不可取。因此,不能认为具体危险犯的危险是“作为结果的危险”,抽象危险犯的危险是“行为的危险”。第四种观点立足于危险程度的不同,对二者进行区分,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因为,无论是认为两种危险的差异在于对事实的抽象化的程度上的不同,还是前后阶段的不同,或者是危险的紧迫性程度高低的不同,在司法实践中都很难对这些差异作出具体评价。例如,如果以对事实的抽象化的程度上的不同来区分,就会导致抽象危险犯中危险认定的恣意性。正如论者所述,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为根据或者说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5]但是,什么是“一般情况”、“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必然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最终沦为完全的臆断。
笔者认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二者在处罚根据上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由于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危险才成立犯罪,其区别仅在于刑法对前者规定了“危险”的要件,而对后者没有规定“危险”的要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具体危险犯的认定,司法机关必须根据相关证据查明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了具体的危险,如果控方根据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了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危险,法院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具体危险犯;反之,如果控方只是证明了被告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但是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危险,那么,法院就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具体危险犯。相反,对抽象危险犯的认定,司法机关只需要查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行为方式,即可推定其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危险,而无需证明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危险。但是,应当允许反证的存在,即如果被告人一方能够证明其行为没有危险,则可以推翻危险推定的成立。
四、未遂犯与危险犯的关系
关于未遂犯与危险犯的关系,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未遂犯是否属于危险犯?二是如果未遂犯属于危险犯,那么,未遂犯中的危险与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否属于同样的危险?二者在判断方法上有无区别?
(一)未遂犯是否属于危险犯?
关于未遂犯是否属于危险犯的问题,目前,在中外刑法理论上尚未达成共识。否定论者认为,未遂犯不是危险犯。例如,日本学者如冈本胜认为,“未遂犯中的危险意味着实现既遂犯构成要件的盖然性,而不一定直接对法益产生危险。故对未遂犯的危险与危险犯中的危险不可等同看待。”。[6]笔者认为,如果从实质的观点来理解,实现既遂犯构成要件的盖然性,就意味着行为对法益产生了危险性,因此,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国也有学者支持否定说的结论,其理由主要是:首先,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危险犯是一种基本构成要件的危险犯,即以单独犯的既遂为模式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危险犯是既遂犯。其次,通说认为无论是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都存在未遂形态,即存在危险犯的未遂犯。这时未遂犯中的“侵害的危险”明显不同于危险犯中的危险。再次,未遂犯的规范构造与具体危险犯的规范构造相去甚远,而与抽象危险犯有类似之处。具体危险犯在规范构造上是有描述的,即刑法对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相反,未遂犯的危险性问题刑法则没有作出任何的规定。最后,未遂犯也不是抽象危险犯。未遂犯与抽象危险犯在规范构造上的相似点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同一概念。抽象危险犯的成立仍然取决于分则条文的明文规定,而未遂犯则是由总则作出的规定。[6]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这些理由都是有待商榷的。首先,上述论点混淆了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既遂条件的区别。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即犯罪构成要件,而非犯罪既遂的条件。这一点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中,处罚未遂犯以刑法分则的明文特别规定为限,也就是说以处罚既遂犯为原则,以处罚未遂犯为例外;但在我国的刑法中,处罚未遂犯并不以刑法分则的特别规定为限,而是在刑法总则的第23条做了概括性规定。因此,不能说我国刑法分则也是以既遂为模式的,我国刑法分则对危险犯基本构成要件的规定,是就其成立犯罪的条件所做出的规定,而不是就其既遂犯所做出的规定。其次,以危险犯存在未遂犯为由,来否定未遂犯属于危险犯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危险犯与未遂犯是根据不同标准划分得出的犯罪类型,前者是根据处罚根据的不同,将犯罪分为危险犯与实害犯;而后者是根据犯罪停止形态的不同,将犯罪分为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与既遂犯。根据不同标准划分得出的犯罪类型之间完全可能存在交叉与重合。第三,以未遂犯的规范构造与具体危险犯的规范构造存在差别为由,否定未遂犯属于危险犯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危险犯包括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两种类型,未遂犯的规范构造虽然与具体危险犯的规范构造不同,但是,却与抽象危险犯的规范构造完全相同,二者在刑法分则的规范内容上,均没有明文把“危险”规定为构成要件。第四,以抽象危险犯由刑法分则规定,而未遂犯由刑法总则规定为由,否定未遂犯属于抽象危险犯,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是刑法总则还是刑法分则,都是刑法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某一概念是在总则做出规定还是在分则做出规定,完全是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而与未遂犯是否属于危险犯没有关系。
与否定论的观点相反,肯定论者认为,未遂犯属于危险犯。例如,在日本,多数学者认为,未遂犯属于危险犯,只是对未遂犯属于何种危险犯存在争议。我国学者张明楷认为,“未遂犯属于危险犯,这应是没有任何争议的结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法处罚既遂犯也好,处罚未遂犯也好,都是为了保护法益;反过来,犯罪是因为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才受处罚:既遂犯是因为行为侵害了法益而受处罚,未遂犯则是因为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而受处罚。不难看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与危险犯的处罚根据完全相同,这说明未遂犯是危险犯。”[5]笔者认为,肯定说的结论完全是正确的。在此前提下,未遂犯究竟是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对于此问题的回答,笔者基本上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即应当联系与未遂犯相对应的既遂形态的犯罪性质来决定:侵害犯的未遂犯是具体危险犯;具体危险犯的未遂犯也是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的未遂则属于抽象危险犯。[5]
(二)未遂犯中的危险与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否属于同种危险?未遂犯中危险的判断与危险犯中危险的判断是否相同?
既然未遂犯属于危险犯,那么,未遂犯中的危险与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否属于同种危险呢?从而,未遂犯中危险的判断与危险犯中危险的判断是否相同呢?
关于此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7](p235):一种意见持肯定态度,认为,危险犯中的危险性判断同未遂犯与不能犯相区别时的危险性判断在原理上完全一样,并将后者危险性的判断方法直接运用于前者的危险性判断。[8](p74,80-88)另一种意见持否定态度,认为,不能犯学说(即区分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危险性判断的学说-作者加注)所涉及的危险性判断是就行为本身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而言的,也就是说,这种判断归根结底仍然是对行为属性的判断;而危险犯中的危险状态的判断则是就行为是否造成了法益侵害的危险而言的,也就是说,这一判断实际上是对存在于行为之外的客观事实的判断。因此,将不能犯的学说不加任何区别地直接适用于危险状态的判断,是一种理论上的错位。[9](p60)
笔者赞同肯定说的立场,认为否定说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无论是未遂犯中的危险,还是危险犯中的危险,作为危险,都必然是行为的属性,而不是结果的属性;危险是由一定的主体根据具体案件的客观事实,所做出的行为具有侵害法益或者造成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结论;仔细分析起来,无论是未遂犯中的危险性判断,还是危险犯中的危险性判断,都是由一定的主体根据具体案件的客观事实,就行为是否具有造成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做出的判断。因此,这两种判断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判断。正由于此,否定说一方面反对直接将未遂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直接适用于危险犯中危险的判断,另一方面,却又实际上在其关于危险犯的危险状态的判断方法方面,直接套用了未遂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9](p60)这不能不说是其理论自身自相矛盾的必然结局。
从更本质的理由来说,笔者之所以主张未遂犯中的危险与危险犯中的危险属于同种危险,是因为,在立法上,危险犯是未遂犯的转化形式。由于刑法中的危险犯集中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侵犯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中,因此,探讨危险犯的立法理由,对于正确理解危险犯的危险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我国台湾学者黄荣坚的研究,“侵害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 (超个人法益)和侵害个人法益犯罪类型间的差异是,侵害对象的范围,换句话说,二者之间是量的差别。超个人法益犯罪之立法,之所以有其必要性,在于技术上的考量。”[10](p114)“对于行为时不确定法益侵害范围的行为,一个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对于未遂责任的追究。”“由于行为人的故意里头,他也知道自己在技术上没有办法控制实害的范围,因此其实害范围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就已经实害的部分还可以论以杀人或伤害既遂罪,但是就其他同属不确定范围的(虽然未受到实害的)人还是有杀人或伤害的故意,其未遂责任的认定即有困难,亦即,要论以几个杀人或伤害未遂罪?”[11](p225)“刑法尊重每一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一个人的利益。行为人侵害一个人的法益,和侵害十个人的法益,法律上就应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11](p226)“如果行为人除了针对一个人或数个人的实害故意之外,另外有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实害故意,那么除了追究其针对特定一人或数人所负的刑事责任以外,应该另外就其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实害故意并着手事实的部分,追究其相当的未遂罪的刑事责任。所以简单的讲,行为犯的立法理由是在不法意志的完全评价。”[11](p227)“既然被害人范围不确定,无法确定要论以几个未遂罪,因此立法上必须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此一问题,亦即超越以个人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单位的角度,直接以不确定的多数人作为利益主体的单位。公共危险类型的犯罪是如此,其他超个人法益的犯罪也是如此。对于这一些犯罪,由于本质上就是未遂犯类型的形式转化,因此自然并未以实害结果的发生为要件。”[10](p115)
按照上述观点,危险犯的存在本身就是按照未遂犯的模式来立法的,因此,危险犯中的危险当然与未遂犯中的危险属于同一种危险。从而关于未遂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理应当完全适用于危险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
[1]张明楷﹒刑法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M].北京: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7﹒
[3]张明楷.未遂犯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7.
[4]陈兴良.刑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5]张明楷..危险犯初探[J].清华法律评论,1998,(1).
[6]陈家林.论刑法中的危险概念[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2).
[7]何鹏,李洁.危险犯与危险概念[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
[8]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9]王志祥.危险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10]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M].台湾: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3.
[11]黄荣坚.刑罚的极限[M].台湾: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0.
DF611
A
1003-8477(2012)01-0154-05
李金明(1969—),男,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本文是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创新计划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法治关系的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3230012210902
责任编辑 劳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