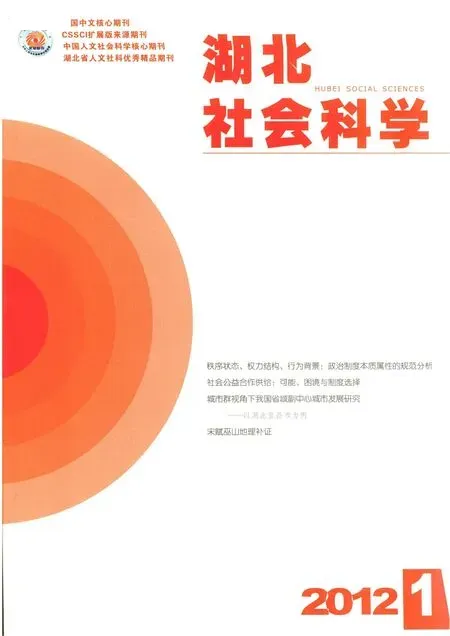何所谓慢,又何所谓快
——米兰·昆德拉《慢》带来的生活
钟利平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外语学部,湖北 武汉 430074)
何所谓慢,又何所谓快
——米兰·昆德拉《慢》带来的生活
钟利平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外语学部,湖北 武汉 430074)
米兰·昆德拉《慢》全书只有100多页,但是它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无限的。“何谓慢,何谓快?”从《慢》里,我们看到了速度,看到了真正的生活,也给我们当今社会带来一些启迪和启示。也许里面的内容太现实了,但是,让我们看到真实的社会景观。
慢;速度;生活;社会景观;思考;
忽然的一天,忙忙碌碌一下子都没有了。片刻的宁静下来,想写一首诗,吃完早饭就呆在桌子前。但很久感觉都找不到,在纸上乱涂乱画。不想写了,——也无法再沉浸到诗思里。顺手拿起一本书翻,书的名字就叫《慢》。书是两年前买的,却一直没想完整读一下。
哦,两年前应是2009年,那时的我可是天天在忙,天天在高压之中,时刻想找一个逃避的处所。到书店买书,也是突然想起来的,于是就去了。坐公交汽车去,于我有时亦是乐事。坐车,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却什么地方都恍然到过。还可以看车里很多的人在一起,我与你互不认识,但却走到了一辆车上,那感觉就像被“裹”了起来。“万千人海一身藏”,就是这种感觉。这比呆在屋子里要好,会使自己觉得“我”还是人世里的人。至少,还在自己的国家,而《慢》的作者却没有那么幸运——可怜的米兰·昆德拉。
中国的人们最初提到米兰·昆德拉,脑海里浮现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这部让无数的人们内心受到震撼的名著表面好像离我们远去,其实不然。旧千年将尽时,旅居法国几十年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接连用法文出版了三部小说《身份》[1]、《慢》[2]、《无知》[3]以及一部论说集《小说的艺术》。这位早年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因政治问题逃离当时的祖国前“捷克斯洛伐克”,客居他乡,并凭借多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事隔多年,再次为世人所瞩目。
笔者赞同这样的评论:“小说不同评论的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评论只是给读者提供一种论点,你只能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而小说,则提供了无数种可能,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或者几种可能。”我想,《慢》就是如此。
《慢》篇幅很短,全书仅有一百余页,在篇幅上虽比不上《玩笑》、《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米兰·昆德拉前期的作品,但该作品延续了米兰·昆德拉作品的一贯风格,在该书中作者运用幽默的词句,刻画出一幅幅生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场景,对人们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虚伪、虚荣、势利等阴暗面进行了嘲讽。维旺德农的《明日不再来》是作者一个很重要的联想,并由此引发深思。T夫人和陪送她的青年骑士的旅行,本身就是很浪漫的过程,先是在马车上的一段颠簸,然后进入花园的相持阶段,到最后的水乳交融,很像慢的艺术过程。但是我们马上读到,青年骑士充当了可笑的假情人,他们在凌晨就分开了,这变化太快了,回过去看这整个事件也就转眼烟云间,真的是明日不再来,下一刻不会重复彼时。
这就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到底何所谓慢,又何所谓快,而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文中出现“舞蹈家”一词,他们是一类只想占据舞台、发扬自我,要把自己的生平做成艺术品的人。谁都知道人能站在舞台上,不是不论什么时刻,在聚光灯下的时刻是非常短暂的。那么在现实的宝贵时期,我们该如何把握呢!在我看来,恰恰不是匆忙地完成自我展现,是以慢的技巧,微分每一个瞬间,dance to the time,演绎最出色的有条不紊。“慢的极致,慢慢消受黑夜的光阴,把它分成互不相连的不同板块,将一小段一小段的光阴烘托出来,像一幢精致的建筑物,像一个形态,使时间具备形态,这就需要美,也需要记忆。 ”[4](p2)
捷克学者在昆虫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段自发的感情抒发,可能他已沉浸在慢给他带来的真实乐趣中,当所有在座者都惊呼于他忘了科研报告,他骄傲地走回来了自己的椅子,全然不知自己闹了一个多大的笑话。三件套男人的出现对于文森特来说,如同侯爵之于青年骑士,在三件套男人和侯爵眼里,他俩都是一个笑话。文章最后文森特和青年骑士跨世纪的相遇,让他们有了共鸣,他们都过了一个美妙无比的夜晚,可又都是前后矛盾的,他们该在意的究竟是什么。文森特选择了快,忘却;青年骑士选择了慢,把玩。这样的结果给我很好的启示,我们应该享受被遗忘的欢乐,同时抛弃没有意义的自我纠缠。[5](p43)
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慢》的结尾处说:“明日不会来,听众不再有。朋友,我请你做一个幸福的人。而且我隐约觉得,我们唯一的希望取决于你有没有能力做一个幸福的人。”读到这里,笔者猜想:如果我们能够慢一点,也许就能够记得自己关于幸福的最初想象,大概就会变得幸福一点。
那么,何谓速度?速度,这个年代一切的东西都讲求速度。不论是上网的速度、计算机的速度、上菜的速度、工作的速度。什么都要越来越快。跟以前同事聊天的时候,聊到他的近况。他说:“过去需要一到两周制作的网站美术,现在公司要求必须在两天之内完工。其实我很怀疑这样赶工之下,究竟能维持多少水平。”但是这个年代就是这样。过往的画家可以花五年十年完成一幅作品,而现代的ART做上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被嫌动作太慢,尤其在网络慢慢融入生活之后。信息更是呈现爆炸的情况,所有的人都要求更多,也要求更快更好。虽然不见得花的时间长,东西就会比较好,但是精致度绝对会有明显的差别。也许这个年代已经不再追求极致的完美,只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就是好现象。就像快餐也许不好吃,但是方便、快速。或许这就是现代人需要的。从某些角度看起来,这是所谓的进步。不过笔者总觉得有点可悲……甚至可怜,可叹。
从《慢》,我们知道: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比,身上总有自己存在,总是不得不想到脚上水泡和喘气;当他跑步时,他感到自己的体重、年纪,就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岁月。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候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人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捷克有一句谚语用来比喻他们甜蜜的悠闲生活:他们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6]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那些不再凝望的人对上帝彻底失望,不再对上帝的拯救和恩宠抱有幻想。我见过真正丢弃信仰的人,他们绝不再向上帝的窗户望上一眼。他们回归到人所以为人的天性即动物的本性中。这种人很快就会成功,无论置业还是仕宦。他们很快什么都有了,但就是没有上帝。但他们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没有上帝的人是快乐的,因为此时动物的本性得以最大化张扬。如果一只熊或是一只猴,有吃有喝,还没病,性欲得到最大满足,你说它会有什么烦恼不爽?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他幸福。在我们的世界里,悠闲蜕化成无所事事,这则是另一码事了,无所事事的人是失落的人,他厌倦,永远在寻找他所缺少的行动。[7](p183)
慢,真的是世界的本质。曾经我认为“快”才是世界的形式,因为“快”才痛快。生活,要“赶快生活”。时间,也是匆匆。学习,要“一寸光阴一寸金”地去珍惜。年轻,可是一辆满载能量飞速向前的大轿车!慢一点,你就落后啦……
在“快”的后面,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钟情“快”的人,似乎都曾充满了“希望”。而我,这时,已无所谓“希望”。如果“快”是一青年,那么“慢”就是一老年。而这个世界确实总是趋向“老年”的,比如:公元一年一年地加长,而今年你又刚长大一岁。年轻的脚步随着岁月趋于沉重,人生的“希望”总不免落空。没听人欢喜地说:“过了今年,我的年岁就减少一岁啦”。当“慢”的时候,才会注意到什么悄悄已变化。“快”,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它,总膨胀着“希望”。因此,“能把自己变慢点”,是我如今的希望。
追赶的脚步令我太累!而我一直追赶不到前面。停下来,我才发现自己真是“慢”的,而不是像人们那样认为的。慢慢地,我才思考有关“自己”的一些事情。悠闲,是慢的特征。人生,本应该把自己分给“悠闲”,谁说“悠闲”是罪恶!也许“快”是人类的一种毒素。我发现真正的艺术是慢的,满溢着宁静和谐的美。而人们的生活,总那么的 “慢条斯理”,“不慌不忙”,脚踏着生命的乐章。
在“快”中,艺术渐渐地消失,诗人退缩到屋角一隅。
为了准确全面地对滑坡位移特征进行研究,本次选取滑坡监测初始的约2.5个水文年作为代表性时间段(见图3)。分析该滑坡位移与库水及降雨间的相关性发现,该滑坡的位移明显增加现象并非发生在强降雨时期,而是库水位强烈波动时期。由此可知,该滑坡的主控外因是库水位波动,即在后续数值模拟研究中,忽略降雨对滑坡变形的影响是合理的。
昆德拉站在窗台前,想起了德农小说里伯侯爵夫人和骑士一晚的浪漫,——那爱,是“慢”的。自己身体在衰退,昆德拉深刻地感觉到了。似乎可以从巴黎游泳池边文森特身上看到他的影子。而那年高的捷克学者,对于被勒去建设劳动和“快”年代中锻炼起来的发达的肌肉,余年里仍为自己感到自豪。
有时,真只有在“慢”里体验一种被我们忽视了的乐趣。我也早放弃了那篇所构思的“慢”的小说。生活乐趣的丧失,我已无法沉浸到自己的空间里。因为人们,我希望把这空间粗暴地推到了生活前面,被世纪的裸狂病鼓噪着再也回不去。
在文化工业盛行的年代,评论家们的嗅觉通常是敏锐的。就在如上作品发表的不长时间里,文评界就形成了相对一致的口径,即一再宣扬昆氏著作中“性与政治”的普遍主题。然而,由于这些文评者们的“媚俗”(昆德拉的自造词)通病,在解读作品时只是从直观上去把握作者的思想,却往往忽略了文本的深层意向性——即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的内部自我内部衍生的根植于德意志文化母体赫尔德式[8](p231)的或尼采式的精神道统,以及胡斯式的或卡夫卡式的、来自捷克波希米亚民族自我认同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
如果说在昆氏早期著作《告别圆舞曲》、《好笑的爱》中仍旧在普遍伦理意义上对人性进行探讨的话,那么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始,无论是《不朽》、《笑忘录》,还是新近的作品,以“人”为中心的、对现代性的洞鉴恰恰成了作者有意遮敝的主题。这个主题的隐身与呈现无疑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反讽:思想自身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张力成了人类自我悬置的必然条件;任何意义上的自我反观都将落入诠释与再诠释的循环罗网之中,看似一场游戏,却正是一场宿命。而在这场西绪福斯式的宿命背后,站立的,竟是一个身着海德格尔披风的人!
正像黑格尔署名《逻辑学》的著作里却大讲辩证法一样,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的论集的开始,通篇谈起了现象学以及胡塞尔对欧洲精神危机的隐忧。有意思的是,昆氏宛如海德格尔终结传统形而上学一样,他对哲学和哲学家宣称了这样的审判:当代的哲学把探讨存在的责任让给了诗人和小说家。他断言,“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
在小说《慢》中,昆氏不再掩饰他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而是光明正大的借助存在主义探讨“存在与遗忘”。他写道:“在存在主义数学中,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成反比”;这似乎又是他在《笑忘录》开篇的那句“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的延续。更为戏剧性的是,昆德拉在小说的尾声竟真的如存在主义一般:当实存的思维碰诸现实时,自由价值的思辩立即化作事实伦理的诉求;存在哲学的行动意义,全部成了浪漫式的冲动,一次让上帝发笑的喜剧。而小说也不过是一篇“逗你一乐的大傻话”(昆德拉自语)。
在《身份》、《无知》这两部小说中,昆德拉再次将主题深化,或许和他年已耄耋的缘故,或许和海德格尔晚年《林中路》的写作有关,“家园与故乡”成了小说的绝对主题。其实,早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就已经不自觉应用“田园牧歌”式的旋律开始了小说的创作;而此时的他,对此的认识更为感同身受。这位客居他乡几十年的老人,从来不曾忘怀自己的祖国,也不止一次赞扬布拉格的美丽。“家园”(法语:chez-soi;捷克语:domov;德语:das haim;英语:home)之存在主义神秘,在他身上得以极致的发挥。他说:
“祖国的概念,从这个词情感意义而言,是与我们相对短暂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生命赋予我们的时间少得让我们没法去依恋另一个国家,另一些国家,另一些语言。”
“尤利西斯离家二十年,在这期间伊塔克人保留了很多有关他的记忆,不过他们对他没有丝毫的思念。而尤利西斯饱受思乡之苦,却几乎没有保留什么记忆。”
TRAHIR:“可到底什么是背叛?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
在这里我们仿佛隐约可见海德格尔“林中路”中农夫脚上的那双鞋子,那双浸透了大地之精神的,依托凡高的那幅油画而得以彰显的鞋子之伤,人之伤。
然而,不幸的是,“人”的主题却是一个早已被超越的主题。自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分别断言了上帝在哲学与文学的“死亡”之后,卡夫卡与福柯也分别断言了人在文学与哲学的“死亡”。
这又使我不得不想起了青年卢卡契的著名断言“小说是无神世界的诗史。”[9](p73)按照阿多诺的理解,这个摆脱了眷顾的先验预设的世界里,不仅使世界中的一切皆坠入了不稳定状态,万事万物似乎都可臻完善,因而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也不再成为可能,人随时受到“事”的束缚,人不再依赖自我的行动来实现自身;而客体的优先地位被社会的先在性而得以确定。[3]
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米兰·昆德拉的这些著作都是迟来的,那个以大地为教堂、以疏林(即“澄明”)为圣坛、以自我内在意向性为认识起点的时代已然消逝在灵光隐没的时间深处,历史之流从不会允许同质的观念重复两次出现——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已经终结,一去不返。
或许,我们可以改写昆氏在《笑忘录》[10]中借助那位哲人说出的那句 “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历险即历险的不存在”,为“自祁克果(基尔凯郭尔)以来、自海德格尔与萨特以来,世上生活的每一个“人”的最真实的存在,就在于这种存在的不存在”。只有如此,我们才确信福柯的话,“人”不过是一个近代的“发明”,人不过是沙滩上的一张脸谱,浪击即逝。
他用最细腻真挚的文字,最鲜明震撼的观念,让您深切体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本《慢》被某些人评论为“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我不知是否恰当,但这部明显反现代倾向的小说技巧玩得倒是真不赖。既嘲讽了知识分子,又把知识分子那套文本互涉的游戏玩得精熟,玩到让人眼花缭乱,是一本好玩的书。
也许里面的内容太现实了,不过还好,这就是他,让我们看到真实的社会景观。
想想中国字真是非常有意思的:“盲”,从目从亡,眼睛死了就是盲;而“忙”呢,从心从亡,心死了就是忙;只是不知是因为忙而令我们心死了,还是因为心死了只剩下忙了呢?于是开始渴望又那悠闲自在幸福满足的慢生活,这样的慢显然不单单是外在生活节奏的放慢、事务欲望的减少,它更是一种内心的状态:悠闲自在,不被外物所累,也不被情欲所役。“慢”,从心从曼,曼,柔美也,心温柔优美就是慢。可是,心又要怎样才能柔下来美起来呢。于是又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慢》。
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他幸福。
[1]米兰·昆德拉.身份(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米兰·昆德拉.慢[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米兰·昆德拉.无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付强.“主编荐语”[J].洪渡河,2011,(3).
[5]刘苇.“在戏谑中深嵌着严肃的意图——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慢》” [J].游吟时代,2011,(2).
[6]杜浩.“在‘快生活’中慢下来”,第 C1 版:时尚周末[J].山西日报,(19).
[7]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出版社,1993.
[8]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
[9]孙甘露.“上海流水”[J].游吟时代,2011,(6).
[10]米兰·昆德拉.笑忘录[M].王东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I106.4
A
1003-8477(2012)01-0130-03
钟利平(1970—),男,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外语学部副教授,硕士。
责任编辑 邓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