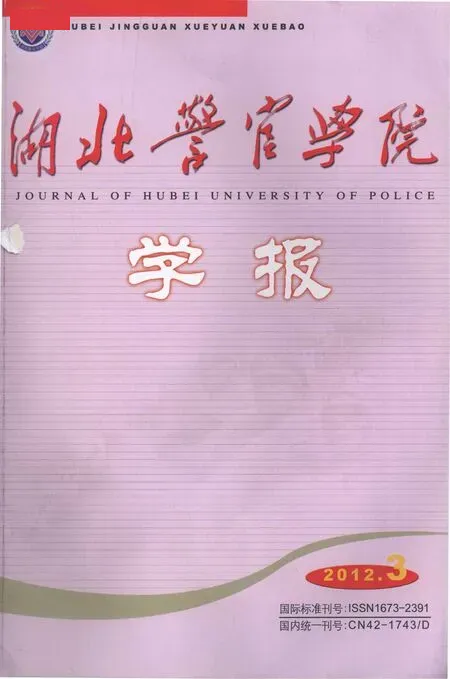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反思与解构
——以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为视角
冯骁聪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400031)
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反思与解构
——以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为视角
冯骁聪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400031)
学术界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诸多批判建立在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的认识之上。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标准”。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虚拟的冲突,是一种过时理论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冲突。从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的视角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进行解构。
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
随着我国1997年《刑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理论界出现了对于社会危害性的各种批判。这些批判的基本理由是: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在内在精神上相互抵触,因而二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冲突。重新审视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社会危害性理论自身的命运,更与我国刑法学体系进路之选择息息相关。
一、当前理论上关于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之观点
综观理论上关于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阐述,一般认为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是相冲突的,具体表现在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在此,分别称之为“价值层面冲突”论和“技术层面冲突”论。
(一)“价值层面冲突”论
该论所主张的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是社会危害性所表征的实质合理性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蕴涵的形式合理性之间的价值层面上的冲突。该论以德国著名学者韦伯在分析社会结构时所提出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二分法为出发点,来分析二者在价值层面上的冲突。持该论者认为,在刑法领域存在着韦伯所说的“法逻辑的抽象的形式主义和通过法来满足实质要求的需求之间无法避免的矛盾”[1]。因为“法是用来满足社会正义的,但法又有自身的形式特征”,刑法规范只可能是抽象的、一般的,而社会生活则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形式的法律永远不能满足实质的社会需求”[2]。持该论者进而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意味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犯罪”[2]。而“如果要处罚一个行为,社会危害性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为此提供超越法律的根据”,因而,“社会危害性所显现的实质理性与罪刑法定原则所倡导的形式理性之间存在着基本立场上的冲突”[3]。
(二)“技术层面冲突”论
该论所主张的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是由社会危害性所决定的实质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形式犯罪概念之间的技术层面上的冲突。对于形式概念,持该论者认为,它“是从罪刑法定原则引申出来的,亦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逻辑延伸”[4],因此,它“使犯罪行为限于刑法的明文规定,对于刑法典来说具有封闭的功能,能够发挥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从而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作用”[4]。对于实质概念,持该论者则认为,它“以社会危害性甚至阶级危害性作为判断犯罪是否成立的标准,而完全摈弃在犯罪认定上的法律标准”[4],在这种犯罪概念之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认定的标准,没有刑法分则条文对各种具体犯罪的规定,甚至也没有法定刑的规定”[4]。显然,在持该论者看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应仅从其法律形式上进行定义,实质概念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二、当前理论上关于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之误区
仔细考察以上关于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两个观点,实际上存在两个重要误区。
(一)误区一: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不具有实质合理性的内容
论者一般仅从形式层面认识罪刑法定原则。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以形式理性为特征”[2],“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应当倡导形式理性”[5],而否认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层面的内涵。罪刑法定原则果真不具有实质层面的内涵吗?这需要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起源进行分析。
1.关于罪刑法定的两种立场
罪刑法定原则发端于西方法律思想中,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的理解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形式主义立场和实质主义立场。形式主义立场将“罪刑法定”之“法”理解为由有权立法机关创制的成文制定法,因此在法律渊源上坚持法律主义,“强调只有立法机关通过合法程序制定的成文法才是刑事法律存在的惟一形式”[6]。实质主义立场则突破了对于法的形式化的理解,在制定法之外探寻法的真谛。从罪刑法定的思想源流来看,其滥觞于复兴的自然法思想对于封建刑法罪刑擅断的批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主义立场正是从自然法观念出发,认为除非有法律明文规定,某种行为纵然对社会生活造成了某种危害也不得认为是犯罪。显然,罪刑法定的实质主义立场是与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追求背道而驰的。
2.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之解读
形式主义立场是基于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追求的必然选择,它蕴含了形式合理性的诉求。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不仅有赖于清晰明了的成文刑法,更需要将成文刑法所承载的内容在司法中实现。现代法治视野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再机械地固守形式合理性观念,而在形式合理性的框架内注入了实质合理性的因子。在实质合理性观念的渗透下,罪刑法定原则也衍生出了新的内容,即“法定的罪与罚应当在实质上符合民主人权的要求,即使在罪刑法定实质要求中的秩序状态,也不仅是秩序的存在本身,而是要求这种秩序是符合民主、人权要求的秩序状态”[7]。成文法本身的实质内容必须符合人权保障的要求,这种思想即被称之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化。
(二)误区二:认为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存在社会危害性标准
有论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存在社会危害性标准,即“罪与非罪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否达到应受刑罚处罚为标准,也就是说,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决定罪与非罪的唯一因素”[8]。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的社会危害性标准必须通过类推制度来实现,正如批判社会危害性的论者自己所指出的:“与罪刑法定相背离的‘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存在’所确立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定义界定标准是其运作的基础”[8]。而为这些学者提供口实的正是我国1979年刑法所规定的类推制度:对于《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危害行为,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类推制度意味着,只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就可以绕开《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罪刑条款,依法官的主观判断使之入罪,实际上就以合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危害性标准。然而,时过境迁,类推制度随着我国1997年《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而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罪刑法定原则蕴涵之一的法律主义要求犯罪圈的划定必须依据《刑法》分则条文,单纯以社会危害性作为入罪根据的现象既失去了实现机制又缺乏原则支撑,社会危害性标准在现行刑法的框架下没有了存在的空间。
三、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之解构
既然否定了社会危害性标准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存在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所谓的“冲突”其实“并不是我国刑法中的一种实然冲突,而是一种虚拟的冲突,是现有立法规定与一种过时理论的冲突,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中心论的冲突”[8]。因此,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排他的关系,两者完全可以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共存。
(一)对于犯罪圈外的行为,罪刑法定原则为社会危害性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当某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却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时,罪刑法定原则为社会危害性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当立法者制定出刑事法律,将犯罪圈划定之后,对于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裁判也就交给了司法者。在这一过程中,判断主体是人民法院,判断对象是被审理的行为,判断根据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各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判断目的是得出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以及符合何种犯罪构成要件。可见,判断过程涉及三个方面,即司法机关、对象行为和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将导致判断过程无法继续进行。要判断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符合刑法上并未规定的犯罪构成,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我证成的。因此,一个行为即使具有相当的甚至是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立法者没有将这种行为纳入犯罪的视野,司法者要认定这种行为成立犯罪也就缺乏了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只能将这种行为作无罪化处理。
(二)对于犯罪圈内的行为,社会危害性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化提供了实现手段
1.社会危害性为实现明确性原则发挥了解释论的机能
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蕴涵之一,它表示了这样一种诉求:“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9]。因此,承载刑法规范的语言必须尽可能清楚明了地将立法原意表达出来。然而,“现代社会内部矛盾百出,连专门的法官都难以弄清其真实含义的法律多如牛毛这一残酷的事实,使人们无奈地看到启蒙思想家力求建立的以内容完整、逻辑严密、表述清晰的法律为基础,人人都能做法官,让法律的适用成为一个自动过程的理想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乌托邦”[6]。刑法规范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刑法典的稳定性与现实生活和人们认识的变易性,决定了刑法的具体适用需要解释,通过解释克服刑法规范自身存在的模糊和歧义,达到拾遗补缺的效果。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确知行为是否属于某一刑法规范的适用对象而需要对之加以解释时,能否抛开表征实质合理性的社会危害性,而在形式合理性的范围之内寻求解释的依据呢?回答是否定的,脱离了实质合理性,形式合理性本身无法担当解释的根据。
从形式上看,具备了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行为就成立犯罪。但当《刑法》分则具体条文对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规定得相当模糊,而这些模糊用语又是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时,就需要对之进行解释,然而,此时面对的悖论却是,仅仅依据形式的犯罪定义无法得出解释的结论。因为判断的目的是要看某种行为是否达到了依法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但是否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却无法从应受刑罚惩罚性自身得到说明,否则就会形成这样的逻辑推理:因为是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根据依法应受刑罚惩罚性,所以行为应受刑法惩罚。这无疑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有违形式逻辑规律。形式合理性自身根本无法解释一行为是否具有形式合理性,判断的标准只能在罪刑法定所体现的形式合理性之外的实质合理性去寻找。而犯罪的实质合理性正是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承载的,某种行为是否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只能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进行判断。没有了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惩罚性将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而失去其判断的标准和实质的内容。
2.社会危害性为实现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原则提供了出罪的机制
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要求“不得处罚不值得处罚的行为,或者说不得处罚轻微行为以及缺乏处罚的必要条件的行为”[10]。较之于西方国家刑法,我国刑法所划定的犯罪圈较为狭窄,国外刑法中的众多轻微犯罪行为大抵相当于我国治安管理违法行为,被排除在犯罪圈外。我国刑法处罚的对象不是泛指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而特指那些在相当程度上危害社会,为社会民众所无法容忍的行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作为认定犯罪标准的犯罪构成诸要件必须作实质性的理解,即形式的犯罪构成要件背后体现着行为对社会的严重危害程度,它是“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的统一,形式要件以实质要件为基础,实质要件的排除意味着形式要件的否定”[11]。某种行为,即使形式上暂时地“符合”《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由于缺乏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从实质上看并不符合刑法的犯罪构成,从而被排除在犯罪圈外。因此,对那些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实质上缺乏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果从形式上将其认定为犯罪,完全没有科处刑罚的必要,也违背了犯罪的应受刑罚惩罚性这一特征,因此,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犯罪的实质条件,发挥了出罪的机能。而为这一机能得以实现提供法律根据的是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使犯罪的实质内容受到了规范内的关照,既可保证一般公正,又可实现个别公正[8]。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01.
[2]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68.
[3]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
[4]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进一步的批判性清理[J].中国法学,2006(4):6.
[5]陈兴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刑法学的反思性检讨[J].法学研究,2008(6):111.
[6]陈忠林.刑法散得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5,164.
[7]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45-146.
[8]储槐植,张永红.善待社会危害性——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说起[J].法学研究,2002(3):93,94.
[9][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4.
[10]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8.
[1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68-69.
D926
A
1673―2391(2012)03―0121―03
2011—11—10
冯骁聪,男,湖南长沙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校:陶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