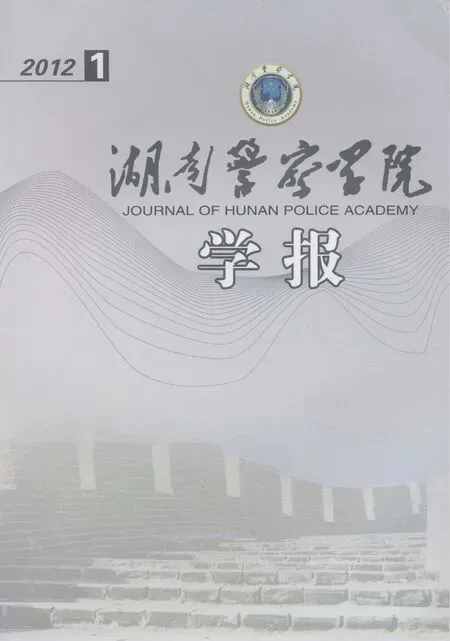也许已经发生:刑法学的深刻转变
刘旗胜,陈英铨
(1.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广西 桂林 541001;2.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检察院,广西 贵港 537110)
也许已经发生:刑法学的深刻转变
刘旗胜1,陈英铨2
(1.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广西 桂林 541001;2.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检察院,广西 贵港 537110)
以97刑法修订为分水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刑法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刑法学研究重心发生根本转变,即刑法学的研究重心从面向刑法立法、服务刑法立法向面向刑法司法、服务刑法司法转变,刑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刑法学对待刑法典态度的根本转变,即刑法学由批判刑法典向捍卫刑法典转变,刑法学的意识形态色彩隐退,规范色彩凸显。转变之所以深刻,是因为这一转变意味着刑法学转型大体已经完成,规范刑法学已基本确立。
立法刑法学;规范刑法学;西体中用
97刑法颁布至今,十余年光阴如烟逝。十多年之前,就已经有刑法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转换论述或者重新切块组织并不是刑法理论的发展...我们的刑法理论研究是不是总体上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偏差,才会出现这种刚刚起步就已经到达了理论终点的感觉?司法实践为什么会对如此发达的刑法理论充耳不闻?”[1](P2)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有学者认为:“新中国刑法学经过30年的研究发展,已初步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理论体系”;[2]有学者呼吁:“如何完成我国刑法学的现代转型,是摆在我国刑法学者面前的迫切任务。”[3](P717)有学者则埋头苦干,贡献出沉甸甸的刑法学研究成果。众说纷纭,然而中国刑法学到底处于何种状态?是需要转型还是不需要转型?是将要转型还是已经转型?中国刑法学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便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本文认为,以97刑法修订为分水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刑法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刑法学研究重心发生根本转变,即刑法学的研究重心从面向刑法立法、服务刑法立法向面向刑法司法、服务刑法司法转变,刑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刑法学对待刑法典态度的根本转变,即刑法学由批判刑法典向捍卫刑法典转变,刑法学的意识形态色彩隐退,规范色彩凸显。转变之所以深刻,是因为这一转变意味着刑法学转型大体已经完成,规范刑法学已基本确立。
一、立法刑法学①对立法刑法学的深入研究于我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此仅提出意见,深入的研究有待将来展开。
立法刑法学是泛指围绕中国刑法立法为中心展开的形形色色的刑法学理论。立法刑法学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刑法立法现代化,从而追求刑事法治。由于我国刑法立法自清末修律至97刑法修订经历了漫长的刑法立法时代,曲折艰难的立法历程使得我国刑法学的研究长期滞留在立法中心阶段,而迟迟未能实现向规范刑法学的转变,终于积淀为这异常厚重的立法刑法学理论。值得注意的是,97刑法修订完成,刑法立法的百年历史行程暂告终结,但是立法刑法学②限于篇幅考虑,本文对立法中心刑法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和国时期部分,对共和国之前部分暂时不予以研究。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根本调整其理论立场以适应刑法学发展的需要,而是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延续至今。如今,表面上看,似乎立法刑法学依然占据刑法学的主流地位,但是立法刑法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已经失去,其自身严重缺陷日益暴露,相信为时不久,其必将为新兴的刑法学理论所完全取代。
(一)立法刑法学与刑法立法:百年风雨同路行
中国刑法学与刑法立法有着不解之缘,现代刑法学在我国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刑法立法这一历史主题密切相关。清末变法修律,立法刑法学应运而生,由此直至97刑法典修订完善,将近一百年历史里,中国刑法人需要完成刑律向刑法转变,帝国刑法向民国刑法转变,民国刑法向共和国刑法转变的艰巨历史任务。期间,清末修律,新刑法立法成功,现代刑法学勃兴;民国立法将刑法立法与现代刑法学发展推向高峰;旋即共和国尽弃民国立法与刑法学包括刑法人,另起炉灶,共和国刑法立法和刑法学耗费几近五十年才终于恢复到今天的水平。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与腥风血雨中,中国刑法立法与刑法学共同进退,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风雨同路。在这样的历史行程里,进行刑法立法研究、服务刑法立法,推动刑法立法的现代化理所当然是刑法学的绝对研究重心,也是我国刑法学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由此,将这一百年的中国刑法学称为立法刑法学或许没有言过其实。
(二)立法刑法学的基本成就
从宏观视角看,立法刑法学的基本成就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基本成就是完成了刑法学的恢复重建历史任务,刑法学从文革之后的一片废墟开始恢复发展到97年的初步繁荣。期间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相信每一个刑法人都深有体会,在此无须赘述。第二个方面基本成就是完成了刑法立法恢复重建的历史任务,97刑法即刑法立法恢复重建成功的标志。至此,我国刑法立法大体上已经恢复到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的水平,这当然有立法刑法学不可抹杀的贡献。
(三)立法刑法学的学术价值
对于立法刑法学而言,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走向社会,热情展开思想启蒙活动,争取自身学术价值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是走进立法机关,热情参与国家立法活动,致力于追求自身学术研究成果的立法实现。事实上,立法时代,刑法学者的成就往往体现为参与立法的成就,而非纯粹意义上的学术成就。沈家本,王宠惠,因为主持刑法立法而被载入史册,甚至连名不见经传的日本人冈田朝太郎也因为参与了清末修律而在中国刑法史册占得一席之地。
此外,一方面,由于对实在法持强烈批判否定态度,刑法学对司法实践的认同感较低而且立法研究成果并不追求直接面向司法实践适用,导致刑法学对获取司法认同感的热情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初衷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功利取向,过分沉溺于实际立法过程中的人事倾轧,刑法学研究对纯学术的真理与知识探索的兴趣较淡。真正以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就跻身史册的学者难得一见。
当然,严格来看,也许立法刑法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学术分量,然而也不必过分悲哀,虽然造化弄人,但是毕竟“我们上一代刑法学者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可供批判与发展的基础”。[1](P3)足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贡献,立法刑法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做出了它的贡献。
(四)立法刑法学存在的基本问题①
97刑法颁布之后,我国刑法立法已经基本完善,因此短时间内再次大规模刑法立法事实上已经不必要也不大可能。97刑法颁布标志着刑法立法时代暂告终结。刑法立法时代虽然已经终结,但是原来适应立法时代需要,围绕立法时代展开,与刑法立法如影随形地发展起来的刑法学并没有随之终结,而是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延续至今,在后刑法立法时代里其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
第一,刑法学理论与刑法典的关系问题。立法刑法学理论以自然法理念或者法律工具主义理念(社会危害性)批判实在法,推动刑法立法的发展,其与被批判的实在法之间是相互对立的批判与被批判的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在立法时代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应当存在的。问题是,刑法立法终结之后,由于立法刑法学巨大的惯性,无法及时转换理论立场,于是原来针对旧刑法典的批判态度无意识地指向了新的刑法典,旧的刑法学理论与新的刑法典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97刑法颁布不久,刑法学理论研究便出现大量对新刑法典批判的声音,原因或许正在于此。刑法学理论对待刑法典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刑法典的地位。在立法时代,刑法学的基本立场是质疑刑法典的合法性,追求的是废弃刑法典,制定理想的新刑法典,此时的刑法典是众矢之的,人人得而“诛”之,而刑法学则高举自然法或者社会危害性旗帜,脚踏刑法典,俨然一副我即正义法律的神态,此情此景,莫说让刑法学去维护刑法典的地位,甚至要让刑法学消极认可刑法典的法律地位都有困难。然而,试想,如果刑法学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新刑法典,将会给新刑法典的实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第二,立法刑法学研究忽视司法实践,刑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缺乏良性互动。刑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关系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对此,刑法学理论要承担相当的责任。首先,正是刑法学理论有意无意地把司法实践边缘化,才导致实践反对理论①有学者认为,刑法学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在于“实践反对理论。实践反对理论的第一个表现是立法上频繁修改刑法,不考虑理论上关于罪刑法定主义以及刑法稳定性的呼吁;第二个表现是法院解释而非法官解释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理论发展,不借鉴理论成果;第三个表现是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在所谓的司法改革上耍一些‘小花招’,完全不考虑相关问题上刑法理论的成熟性;第四个表现是司法上权力技巧的过度使用,以及意识形态影响刑法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实践并非单指司法实践。参见陈兴良、周光权著《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0页。或者理论反对实践局面的出现。立法刑法学的主要理论关注在于刑法立法完善,其主流的理论诉求是刑法立法推动刑法发展。因此,绝大部分的注意力被集中在刑法立法相关问题研究上,以至司法实践极少进入研究视野,造成司法实践事实上被边缘化。其次,比边缘化更严重的问题是,刑法学往往以对司法实践的强烈批判否定作为刑法立法理论根据,而不对司法实践抱以基本的同情理解以期与司法实践者共同努力寻求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方法,长此以往,造成司法实践界对理论界的普遍抵触,影响双方的沟通。由此带来的恶果是,一方面,刑法学对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把握不准,学术批评常常大而无当,对司法实践并无实际价值;另一方面,司法实践在理论界得不到有效支持,对理论界失去信心,最终造成了今天刑法实践我行我素,刑法学研究自说自话各行其是、“法人”相轻的不良局面。对此,单纯把责任归结到实践界不但不公平,更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刑法学理论有必要重新检讨刑法学与司法实践的关系。
第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问题。为适应刑法立法任务的需要,立法刑法学大量运用社会危害性、人权保障、自由民主、法治理念等非规范的政治理念、自然法理念作为批判现实的基本理论依据,刑法学理论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刑法司法实践过程中,这往往容易引发人们的朴素道德激情,加剧中国本来就有的泛道德主义倾向,极容易造成直接超越实在法而寻求诉诸意识形态途径处理问题思维方式对司法实践的严重冲击,最终背离法治的追求。80年代初“严打”严重扩大化造成的惨烈后果便是深刻的教训。
第四,刑法学理论的纯粹性问题。立法刑法学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理论体系,究其实质,其实不过是多年来,在不能照抄照搬的口号下,以苏联刑法学为主体,广泛吸收英美德法意日俄等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刑法学理论,拼凑而成的“应然与实然、形式与实质、规范与事实,各种刑法学知识成分相混合”的大杂烩式刑法学理论。这样的理论怎么可能达到学术理论体系所要求的纯粹性呢?这样的理论连消除自身相互矛盾,自相冲突的理论困惑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可能指望用它来正确指导司法实践?第五,刑法学的未来发展问题。立法刑法学历史任务的特定性导致立法刑法学全神贯注于刑法立法目标的实现,而刑法学自身的发展长期处于被冷落的状态。97刑法修订完善,使立法刑法学顿时失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陷入迷茫状态。刑法学的未来发展问题日渐突出。
(五)结论:功成自然身退
立法刑法学适时而生,与中国刑法立法相互促进,至今已经完成了中国刑法立法和刑法学恢复重建的两大历史使命。立法刑法学也由此发展到顶峰。但是,立法刑法学在本质上是面向刑法立法而不是面向刑法司法的,而且由于长期沉溺于立法这一现实政治的功利算计和人事倾轧,积淀了大量的妨碍司法实践走向法治的毒素,它已经无法承担面向刑法司法,服务刑法司法,通过司法实践落实刑事法治的新历史使命了。正如刑法学者所指出:“这个理论的观念、基础、方式与结构已经失去了它存在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基础。换言之,它可能基本上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刑法学了。一个在理论基础上偏离规范学原理的刑法学研究,不论它在数量上是多么地浩瀚,也不论它覆盖的范围多么广泛,它就不可能是成熟的,更不能有效地服务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的时代与实践要求。”[1](P3)立法刑法学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规范刑法学
(一)规范刑法学的历史使命
立法刑法学随着历史使命的终结逐渐退出刑法历史舞台,应运而起的是规范刑法学。规范刑法学的历史使命早已为刑法学者所指明:“年轻的刑法学者,可以脚踏实地写十万二十万字,切实解决一个规范理论上的难题,使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中同行们还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司法实践中可以直接援引作为认定或者判决成立的根据、立法机关因为理论的逻辑性和适用性(不是因为作者的社会地位或者职称)在立法中纳入逻辑体系。这是一个刑法学者的最大的光荣和满足。如果我们没有弄懂,我们首先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刑法理论中,还有许多理论问题,是近百年来各国刑法学家共同努力仍未能基本解决的。刑法研究和任何科学领域要取得一点成绩一样,需要辛勤与脚踏实地的劳动。中国刑法学界对于‘到头论’的批评是正确的,刑法理论的发展远未到头。在有的地方,我们也许还未入门;有的地方之所以有到头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就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1](P17)
(二)规范刑法学的确立
本文以“也许已经发生”为题目,所指其实也就是规范刑法学也许已经确立,只是尚未为刑法学界所充分认识而已。在此,本文并不打算长篇大论地论述规范刑法学的确立,而是试图从刑法学的微观和宏观两方面进行“实地”考察。
从微观方面考察,以《罪过形式的确定——刑法第15条第2款“法律有规定”的含义》[4](以下简称《罪》)为典范的刑法学论文高水准地表现了规范刑法学的品质,充分表明规范刑法学已经确立。
1.刑法学的研究重心从立法研究转向司法实践研究。刑法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意味着其研究基本上应当围绕刑法典规定的刑法规范进行,重点研究刑法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问题。《罪》一文紧密围绕刑法典所规定的“法律有规定”这一刑法规范展开,研究意图正是在于澄清刑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对罪过刑法确定这一问题的模糊认识,“使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中同行们还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司法实践中可以直接援引作为认定或者判决成立的根据”[1](P17)。
2.刑法典地位高扬,刑法学由批判刑法典转变为捍卫刑法典,刑法学理论与刑法典关系得到理顺。在《罪》一文中,尽管刑法典在“法律有规定”这一含义以及具体犯罪的规定中可能确实存在模糊不清之处,但是作者不仅没有象立法刑法学那样以批判的方式大肆批判刑法典,随意提出所谓的立法建议,甚至没有流露出丝毫对刑法典不满或者遗憾的心态。如此高远的行文意境,说明作者已经进入了“位我上者,巍巍法典;正义理念,在我心中”的极高境界。刑法典不再是肆意批判的对象,而是高高在上的巍巍法典了。刑法学的研究也相应地由批判刑法典转变为解释刑法典。刑法学向神圣的刑法典低下高傲的头颅,虔诚地臣服于刑法典之下,“当解释者对法条难以得出某种解释结论时,不必攻击刑法规范不明确,而应反省自己是否缺乏明确、具体的正义理念。所以,解释者与其在得出非正义的解释结论后批判刑法,不如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得出正义的解释结论;与其怀疑刑法规范本身,不如怀疑自己的解释能力与解释结论。”[5]
3.刑法学理论与刑法司法实践的对接。刑法学的研究重心从立法研究转变为司法研究是刑法学理论与刑法司法实践的对接的前提条件。而刑法学理论与刑法司法实践的真正成功对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关键在于刑法学理论能够向刑法司法实践提供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的高品质理论产品。《罪》一文,作者针对现实刑法司法实践与刑法学在确定具体犯罪罪过形式的困境,通过对刑法规范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法定标准和实质理由,这些标准和理由可以直接为刑法司法实践所运用。一旦司法实践遇到类似的问题,这些标准就可以得到实际应用,而实际应用的效果和所出现的新问题将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回刑法学理论,进而刑法学理论可以再次作出回应,由此,刑法学研究与刑法司法实践之间即可逐渐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4.刑法意识形态的合理处置。立法刑法学留下了大量的意识形态遗产,在新刑法典施行过程中,如何合理处置意识形态问题,发挥其积极意义,限制其冲击刑法典的消极作用,是规范刑法学必须解决的历史遗留任务。《罪》一文,意识形态(实质的理由)的讨论被安排在法定的标准之后,而且意识形态的使用被作者严格限定在法定标准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才非常谨慎地探讨意识形态对罪过形式确定作用的问题,并且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消极的,即用来限制过失犯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而不是用来扩大过失犯的处罚范围。由此,作者一方面发挥了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限制了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合理地处理了意识形态问题。
5.刑法学理论的纯粹性问题解决。规范刑法学追求法的纯粹性,强调“语言之外不存在法”[4](P101),自觉以分析哲学①分析哲学是一种以语言分析作为哲学方法的现代哲学流派或思潮。主要包括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也包括批判理性主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不属于这些支派的分析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基本思想最初见于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G.弗雷格的著作中,正式形成于20世纪初的英国。创始人除弗雷格外,主要有B.罗素、G.E.摩尔、L.维特根斯坦等。其共同特征是:①重视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把语言分析当作哲学的首要任务,甚至当作唯一任务。②普遍重视分析方法。③反对建立庞大的哲学体系,主张在解决哲学问题时要从小问题着手,由小到大地逐一解决。分析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之一,在30年代以后的英美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分析法学②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分析法学,是19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法学流派之一。分析法学强调法学研究的对象为实在法,即对现行法律规范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分析法学把道德排除在法学研究范围之外,也不顾及法律在具体应用中的千差万别,认为恶法和良法都是法。但作为一种法学研究方法,分析法学一直延续至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立场和方法,匡正、消除当前刑法学普遍存在的直觉式思维方式,缺乏严密论证,不注意概念、命题的精确性等等弊病。《罪》一文,作者引用“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法律语句’的语句形式表达出来。可以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达、记载、解释和发展法”,以及“一个刑罚法规的目的,必须在它实际使用的语言中去寻找,根据它明显的和清晰的含义来解释”[4](P101)来论证其理论立场,说明作者已经进入了分析哲学、分析法学所要求的“走进语言”的佳境,经过了深刻的“语言的洗礼”。由此,规范刑法学在理论立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各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纯度。
6.刑法学独立学术研究价值的确立。立法刑法学阶段,刑法学的学术价值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学术水准本身,而是更注重作者的社会地位和职称。规范刑法学的学术价值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刑法学理论研究水准本身。学者也更多地靠学术水准而不是社会地位和职称获取学术价值。从而,在立法刑法学阶段,一篇完美的刑法学立法建议论文完全可能因为得不到立法认可而沦为废纸一堆,而真正有水准的规范刑法学论文却不必因为外界的不认可而失去其学术光芒。或许,在消逝了立法之争的意气纷争和现实功利的巨大诱惑之后,刑法人终于有可能心平气和地安坐书桌,凭案挥毫,做一点真正的学术研究。如是,则立法终结日或许就是学术开始时。
从宏观视角来看,规范刑法学已经为刑法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一个可以批判发展的基础,因而事实上已经跻身刑法学舞台,占据一席之地。张明楷在接续立法刑法学的基础上,以外国刑法学的研究为新起点,引入规范性的法益理论“乾坤大挪移”式地置换了立法刑法学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明晰了规范刑法学的刑法基本立场,消除了立法刑法学的某些理论混乱,以《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奠定了刑法解释的立场和方法,最终以规范性的刑法学教科书奠定了规范刑法学的地位。陈兴良自觉告别既往的立法刑法学立场,以《本体刑法学》开始了向规范刑法学的“朴素回归”[3](P733),走向似乎日益与张明楷先生协调一致。立法刑法学论者则茫然追问中国刑法学研究向何处去,分明已经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危机,尽管他们可能尚未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来自规范刑法学。
种种迹象显示,在刑法学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中,历经十年的磨砺,以张明楷为灵魂人物的规范刑法学已经成为事实。刑法学的历史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地转向了规范刑法学。
三、中国刑法学的未来走向展望
(一)立法刑法学逐步衰退,规范刑法学逐渐跟进
在刑法立法时代,作为立法刑法学主流,以苏联刑法理论资源为基础,以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为理论基地的保守派立法刑法学因其作为推动中国刑法立法的主要力量而占据主要理论优势。但是,随着刑法立法的历史任务基本终结,其痛失主要理论舞台,理论影响力将有所下降,日益式微,退居次要地位。
在刑法立法时代,作为立法刑法学重要组成部分,以近现代自然法理论资源为基础,以北京大学为理论基地的改革派立法刑法学对保守派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体系发挥了强大的解毒功能,为中国刑法立法现代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但随着刑法立法的终结,刑法实在法地位凸显,自然法地位衰落,该理论同样也痛失主要理论舞台,理论影响力全面下降,日益式微。
顺应刑法典实施的时代发展要求,规范刑法学由于获得刑法司法实践这一广阔的理论舞台而有可能日益占据刑法学主流地位,取得对立法刑法学的全面胜利,完成刑法学理论的改朝换代、推陈出新。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立法刑法学的理论可以较快被取代,但是肃清立法刑法学对中国刑法实践的错误影响(例如批判刑法而不是解释刑法)将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中国刑法学进一步发展
进入规范刑法学时代,中国刑法学如何发展呢?规范刑法学由于其鲜明的面向司法实践特征,因此上述问题需要从中国刑法实践认识上来回答。
当前我国的刑法司法实践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在架构上是照搬苏联的政治化的司法体制,政治因素对司法实践影响异常明显;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可能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国刑法司法实践不可能不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最后才是现代刑法文化的影响。概而言之,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可说是基本处于政治刑法文化搭台,传统刑法文化唱戏,现代刑法文化看戏的尴尬局面。针对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这种状况,中国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应当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中国刑法学必须重视加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刑法司法实践的影响。虽然形式上我国传统的法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逐渐积淀成了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识的指引规范,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惯、心理习惯中。中国人不管识字不识字,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意识到没意识到,其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均渗透着这一传统精神。即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刑法学中的影响必须予以清醒的认识,十分值得研究。例如,我国刑法中的“数量较大”,“情节严重”以及“情节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等等中国特有的刑法规定里有没有传统文化的精神,或许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其次,中国刑法学应当深入研究如何淡化刑法的政治化色彩,凸显刑法作为共同生活规则“社会契约”的法律色彩,针对当前弊端,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再次,中国刑法学应当研究如何进一步吸取现代刑法文化养分,继续发展壮大现代刑法文化,提高现代刑法文化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最终落实刑事法治。
(三)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路径:西体中用
可以肯定的是,在刑法学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将不得不长期学习吸收先进国家的刑法理论成果,但究竟应当如何学习这恐怕至今仍然是困惑中国刑法学的大问题。
“新中国刑法学经过30年的研究发展,已初步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理论体系,完全照搬、抄袭他国刑法学理论的做法并不可取。德国、日本刑法学理论固然精密,但其本身也存在固有的缺陷,在借鉴时应有所扬弃。立足本土,充分认识和了解中国国情,尊重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法律制度,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理论,进而实现刑事法治正义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理论,才是当代中国刑法学研究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段出自谢望原先生之手的话,基本上代表了当前刑法学界相当一大部分人的观点。对中国刑法学既有的刑法理论基础的过分自信与对认真学习西方刑法理论的反对两种思潮在当前中国正大行其道。
对于我国既有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理论体系,笔者并没有谢先生的自信。但笔者倒是愿意大体赞同谢先生“完全照搬、抄袭他国刑法学理论的做法并不可取”的说法,当然在笔者看来,这不是可不可取的问题,而是可不可能的问题。“全盘西化”的努力由来已久,此路至今尚未走通。该是时候另觅新路了。
既然不能“全盘西化”,原样照抄西方经验,也不能“中体西用”,倘期待我国当前的刑法实践和理论自身开出现代刑事法治之花,那么,“西体中用”似乎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新路。李泽厚先生指出,“自五四以来,西化派从康有为、严复到胡适、陈独秀,强调的是普遍性,国粹派从章太炎到梁漱溟强调的是特殊性。一派要求‘全盘西化’,一派强调‘中体西用’。只有去掉两者各自的片面性,真理才能显露,这也就是‘西体中用’”。[6]所谓“西体中用”,是指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结合中国传统,将西方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政治经济理论的“体”(社会存在的本体,以及“学”,即对这个本体的意识)应用于中国。[7]当然,既不完全认同“全盘西化”,也不苟同于所谓“中国特色之路”的当代“中体西用”,那么,处在两面夹击之下,“西体中用”绝对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
从研究进路考察,张明楷先生在接续立法刑法学的基础上,以对外国刑法(成果表现为《外国刑法纲要》)的研究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经由《犯罪论原理》、《刑事责任论》、《刑法的基础观念》、《法益初论》、《刑法的基本立场》、《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等文批判性地引入外国刑法学理论,最终到达《(中国)刑法学》,完成了“西体中用”(张明楷先生称之为“洋为中用”),所遵循的正是“西体中用”这一发展路径。至此,中国刑法学发展的路径之争可以休矣!
值得注意的是,张明楷先生的西体中用(洋为中用)思想存在严重缺陷。他缺少了李泽厚先生“转换性创造”这一重要概念。张明楷先生似乎把“中用”仅仅当作策略,视为用完就扔的手段,而没有意识到“中用”应成为某种对世界刑法学具有重大贡献的新事物的创造,即由“中用”所创造出的“西体”,不止于符合普遍性的现代刑法准则或原理,而且将为刑法的发展增添新的具有世界普遍性的东西。张明楷先生在“骨子里”是全盘西化论者,却无奈地身处在立法刑法学尚未被清醒地认识的保守落后的“苏式”中国刑法学时代,他只好采取渐进的方式从内部掏空立法刑法学的根基,以经过他吸收消化的现代德日规范刑法学取而代之。张明楷不够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文化在刑法中的地位,越来越走向刑法理论的形而上学化体系构建,说明他的“洋为中用”未得“中用”三昧,没有认识到“转换性创造”之特别重要,未注意吸收消化中国既有的刑法文化。所以,张明楷先生的刑法学成就虽然已为中国规范刑法学奠定基础,却仍然需要进一步批判和超越。
(四)简短的结论
中国刑法学将通过大洗牌最终实现从立法刑法学到规范刑法学的转变。以张明楷先生为杰出代表的清华刑法学出色地完成了中国规范刑法学的奠基任务。未来的中国刑法学发展,应当在继续大力引人规范刑法学这一西学的基础之上,大胆进行转换性创造,解构重建中国传统文化,消除中国刑法司法实践政治化的弊端,最终实现中国的“刑事法治”。至此,如何在“西体中用”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好,或许才是中国刑法学的真正出路。
[1]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谢望原.中国刑法学研究向何处去[N].检察日报,2007-07-31.
[3]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张明楷.罪过形式的确定——刑法第15条第2款“法律有规定”的含义[J].法学研究,2006,(3):98.
[5]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
[6]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169.
[7]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杂著集)[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158.
It M ight Have Happened:Profound changes in the Crim inal Law
LIU Qi-sheng CHEN Ying-quan
(Th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in Guilin,Guilin,Guangxi,541001)
Taking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97as a watershed,after ten year's development,China's criminal law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the focus of the Criminal Law Research had a fundamental change too:the focus of criminal law is from facing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serving criminal legislation to facing criminal justice and serving criminal justice;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criminal law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and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Penal Code.This mean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riminal law has generally been completed and the basic norms Of criminal has been established.
criminal law;norms of criminal law;using west system in China
D903
A
2095-1140(2012)01-0085-07
2012-01-10
刘旗胜(1973- ),男,广西桂林人,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陈英铨(1980- ),男,广西桂林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王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