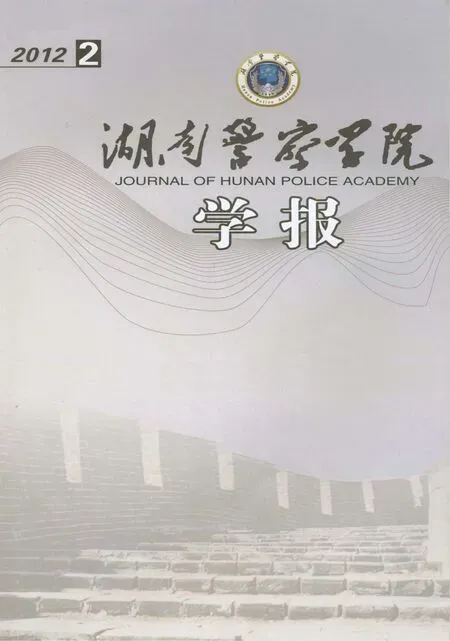论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中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
白思敏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论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中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
白思敏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虽然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具有当事人的地位,但被害人的权利常常在“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中被忽视。之前的“量刑制度改革”为被害人之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化”提供了契机,本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该将被害人的保护由司法解释的层面提升到立法的层面。对此,在分析被害人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具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正当性后,提出保障其能够有效参与的权利,以期达到保护被害人和量刑公开、公正的目标。
被害人;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地位和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幕幕人间悲剧的发生使人们重新开始关注个人的价值。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中兴起了一阵“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权利得到了加强。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但在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没有根本转变、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法律中规定的当事人的地位和现实中仅仅发挥证人的作用相比,就有些“名不副实”了。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其与案件的结果有利害关系。被害人也许不会专注于正义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但他却关心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实际利益,学术上称之为“复仇意愿”和“求偿意愿”①此概念参见房保国:《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5页;陈瑞华教授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主要利益总结为“寻求刑罚的正义”和“充分的民事赔偿”,参见陈瑞华:《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此二意愿为被害人参与诉讼之动力和评价诉讼活动之标准。而在我国过去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方式中,是以定罪为中心,在定罪程序中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可能实现,只能沦为证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作为民事原告,不能参与和了解量刑,并且囿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和执行情况,造成了赔偿不到位、量刑又满足不了其复仇的欲望的现状,所以上访必然发生。为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实现量刑公开和公正,从2009年6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进行试点。经过了大概一年多的经验总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签发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文简称《意见》),自2010年10月1日起试行。《意见》规定了在原来一体化的审判程序中保障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这一改革也为被害人之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化”提供了契机。
一、量刑程序中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正当性
当我们准备将“被遗忘的人”从司法的边缘状态(marginalized status)拉回到诉讼活动中,并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和权利赋予来真正落实其当事人地位时,我们也应审视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当事人地位的正当性,笔者认为,其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的在刑事诉讼中有独立的个体利益,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为维护其个体利益提供了程序保障
在除了被害人和被告人达成和解的案件外,双方在量刑程序中存在对抗,有时还会很激烈。这就需要加强法院的司法控制,包括程序上的控制权(《意见》第15条)、证据的调取权和核实权(《意见》第12、13条),但控制并不等于“专断”,法官需要在判决中说明量刑的理由(《意见》第16条)。在英美法系定罪和量刑分离模式中,定罪程序中将对抗发挥到淋漓尽致,而在量刑程序中也体现出一种“职权主义”,也从事实上证明了量刑程序中司法控制的必要性。
在传统犯罪观的影响下,被害人的利益往往被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或被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所掩盖。大部分国家从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不承担诉讼职能和不承认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存在独立的个人利益出发,不认为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如英国1994年《皇家检控官守则》中规定:“皇家检控署基于公共利益而活动,不单纯考虑任何个人的利益。但皇家检控官在确认公共利益之所系时应当非常慎重地考虑被害人的利益,被害人的利益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利益因素。”[1]而把被害人的个体利益作为一项公共利益因素来考虑,是基于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是统一的、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利益即实现了个体利益的理论假设,但“事实上,被害人利益不是完全融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中。公益维护主要是站在国家和社会的立场上,更注重于从全方位上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而被害人利益的维护主要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侧重于个人的人格、尊严、名誉、财产等利益的维护”[2],如果二者发生冲突,被害人的利益很可能成为牺牲的对象。并且,检察官在被害人在因犯罪遭受损失时,也没有追索赔偿的欲望,而我国又没有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所以,被害人只能依靠个人的力量参加一个自己对案件结局影响力极低的诉讼程序,其结果可想而知。在相对独立的量刑阶段中,被害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和同被告人达成刑事和解来实现其“复仇意愿”和“求偿意愿”,这是原来在以定罪为主的检察院承担主要控诉职能的一体化模式下被害人不能充分实现的。所以,通过参与量刑程序、提交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书进而影响量刑,被害人的意见才能有机会表达出来,被害人才有了和被告人谈判的“筹码”,其利益才有可能被重视,其当事人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二)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以真正确立
要成为刑事诉讼主体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刑事诉讼主体必须是刑事诉讼基本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和刑事诉讼主体的活动决定着诉讼的产生、发展、运行方向和结局。[3]在传统的一体化审判方式中,虽然法律规定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具有当事人的地位并有一系列权利,但其证据收集规定的阙如和有效参与庭审能力的限制,并不能承担起控诉的诉讼职能,只能依附于公诉方,造成了被害人在法律上具有当事人的地位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找不到充分证据来表明其具有诉讼主体的地位,也造成了我国刑事诉讼主体理论为了“迁就”被害人而导致的混乱和分歧。①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将刑事诉讼主体和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等同,认为享有一定诉讼权利、承担一定诉讼义务的人就是刑事诉讼主体。参见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3页。其他把刑事诉讼主体限定为基本诉讼职能的承担者,则一般不认为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主体。但在这次的审判方式改革中,相对独立的量刑中为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发表量刑意见的机会,这与过去的被害人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有四个不同:1.性质不同。被害人的量刑意见是被害人就量刑问题从自身出发的一个纯粹的意见表达,没有约束力;被害人陈述是法定证据的一种,其实质是一种证据资料,需要经过法院的认定才有效力,而且一旦成为证据,则对法院产生约束力。2.内容不同。量刑意见是被害人根据被告人对其的侵害程度和影响(具体内容见下文)所作出的一个量刑方面的意见,是一种评价;被害人陈述是被害人就案件事实做的一个陈述,不涉及评价问题。3.证明标准不同。被害人量刑意见以及各种量刑情节固然要承担证明责任,但证明标准并不需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甚至就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也不需要,而至多达到民事诉讼上的“优势证据”标准即可。”[4]但在死刑案件中,证明标准还是要达到最高标准,是为特例。4.对判决的影响不同。《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量刑理由。”其第3款又规定:“量刑理由主要包括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发表的量刑建议、意见的理由”。据此,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必须说明是否采纳被害人的量刑意见的理由,客观上保障了被害人量刑意见对判决的影响力;而法院是否采纳被害人陈述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这四个不同中,我们可以看到证明标准的降低和影响力的增强,量刑意见书都为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承担诉讼职能、发挥主体作用提供了途径,为诉讼中的“四方构造”真正发挥应有的结构作用提供了可能,被害人可以实现由与案件结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向承担一定诉讼职能的诉讼主体的真正转变。
(三)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被害人的地位的提升不会打破诉讼平衡,反而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机会
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增加,国外有许多学者担心,“恢复被害人的权利动向有使司法正义崩溃的危险,导致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制度毁于一旦”[5],更何况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还极不完善的我国,被害人的参与将使被告人面临双重压力。但是,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都是围绕定罪和平等对抗赋予被告人的“武装”,在量刑程序中,在法官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确信,这些特殊保护权利完成了“使命”,法官需要全面衡量各方提出的量刑情节和建议,作出一个明确的量刑判决。正因此,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是必要的,尽管有时被害人可能带有非理性的因素,但在检察院、被告人的制约下和法院的司法控制下①在除了被害人和被告人达成和解的案件外,双方在量刑程序中存在对抗,有时还会很激烈。这就需要加强法院的司法控制,包括程序上的控制权(《意见》第15条)、证据的调取权和核实权(《意见》第12、13条),但控制并不等于“专断”,法官需要在判决中说明量刑的理由(《意见》第16条)。在英美法系定罪和量刑分离模式中,定罪程序中将对抗发挥到淋漓尽致,而在量刑程序中也体现出一种“职权主义”,也从事实上证明了量刑程序中司法控制的必要性。,维持诉讼的平衡,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另外,在量刑程序中,作为诉讼主体的被害人,可以选择和被告人进行交流、和解。此时被告人已经没有了被判无罪的侥幸心理,出于真心悔过或为了减轻刑罚而取得被害人谅解的目的,更可能倾听被害人的心声和满足被害人的要求,在诉讼程序内就尽量满足被害人的“复仇意愿”和“求偿意愿”,而不是通过诉讼外的申诉、上访。恢复性司法的目标是“对犯罪产生的危害进行修复”[6],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是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目标之一。虽然对被害人的保护并不是恢复性司法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刑事司法程序开始对人进行关注的表现,是犯罪观和刑罚观发生改变的表现。更多地关注因犯罪受到伤害、因诉讼受到忽视的处于弱势的被害人,就是人权保护的一大进步,为将来整个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机会和一次宝贵的尝试。
(四)在相对量刑程序中被害人的参与是程序正义的要求,实现诉权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
在定罪量刑一体化审判模式下,量刑程序是封闭的、不公开、不透明的,再加上实体法上对刑种和幅度的规定跨度很大,为法官在量刑上滥用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可能,造成了量刑的公信力不高,损害了司法权威。就最近轰动全国的“药家鑫”案件来看,对司法的不信任,加剧了舆论对司法的影响;舆论对司法的影响越大,反而给人们的感觉是司法的公信力更低,走进了一个互为因果、逐步恶化的“怪圈”。要想做到“公信”,就要做到“以理服人”,这“理”来自于实体和程序。实体上的“理”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程序中的“理”就是程序正义。表现在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是:“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到诉讼中,并得到有利于自己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和证据的机会”[7]。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就是要通过参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来实现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也要求法院给予双方提供量刑证据的机会,并围绕其展开充分的辩论,最终影响判决,实现诉权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就是提高司法公信力最好的途径,也是保护法官不受外界干扰、保持独立的最好途径。
此次的量刑程序改革是要保障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这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被害人具有不依附于检察院的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地位决定着权利,权利保障着地位,失去权利的“支撑”,多高的地位都是“空中楼阁”,所以下文将对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的被害人的具体权利展开讨论。
二、被害人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的权利
在已有的有关被害人保护的著作或文章当中,已经对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程序上,从侦查阶段一直到执行阶段;地域上,从英美法德一直到联合国的公约;时间上,从古罗马一直到新世纪。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中规定了受害者具有知情权、表达意见权、获得法律帮助权、不受伤害权和获得赔偿权。我国有学者将被害人的权利分为三类:(1)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性权利,包括控告犯罪的权利、参与诉讼的权利、获知诉讼信息的权利、诉讼性程序的申请权和执行程序参与权;(2)被害人的救济性权利,包括获得补偿的权利、获得赔偿的权利和救济性程序请求权;(3)被害人获得援助以降低对其伤害的权利。[8]也有学者提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核心应是加强并保证他的程序参与权。”[9]本文拟结合2010年10月1日起试行的《意见》,就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被害人的权利展开规范基础上的超规范研究。使被害人能够“有效参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则是被害人享有各种权利的总目标。下列权利是对被害人能够有效参与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权利:
(一)聘请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被害人聘请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是其主体地位的体现,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翻译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是不需要诉讼代理人的;被害人聘请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是诉讼对抗性加强的表现,有助于实现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权利的平衡。在诉讼代理人的具体权利上,《意见》没有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大的突破,只规定了具有提出量刑意见和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量刑证据材料的权利,没有赋予诉讼代理人像辩护律师一样的阅卷权,这其实是被害人知情权缺失的体现。尤其在量刑程序中,被害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这其中对情节的选择、影响的陈述和最后具体的量刑意见都需要专业的人士来辅助,诉讼代理人对于被害人,特别是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就非常重要了。
(二)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上文已经分析了诉讼代理人,尤其是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对被害人的重要性,而且被害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遭受犯罪带来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后,由于很难凭借自身力量开展诉讼活动,很容易在诉讼中受到“第二次伤害”,这是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现实依据;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也适用于法律援助中的“接近正义”理论、律师使命理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论和正当程序理论等一般原理。[10]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也在联合国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得到确认。但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了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在这次的《意见》当中,同样也没有赋予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只是强调了对被告人指定辩护(《意见》第6条)。明确规定了被害人具有获得法律援助权的是国务院2003年7月16日通过、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该条例规定了被害人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两种情况:一是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二是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尽管《法律援助条例》在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但限于条例的效力和实践中的不足,应该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确立并完善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三)量刑意见表达权
如果说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是其权利保障的核心,那么,在参与的过程中的意见表达则是程序参与的核心,有可能最终影响判决则是“有效参与”之有效性的体现。但在以往“一体化”的审判中,存在着参与和意见表达的诸多矛盾:一是如果被害人在被害人陈述中发表自己关于量刑意见,则违背证据的客观性,不符合我国“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量刑标准,法院不予也不能采纳;如遇有怜悯之心的法官,则只能影响自由心证而不能作为理由写到判决书中,法官还要面对被告人不服上诉的风险,影响其业绩考核。二是如果被害人不出庭,采用书面方式表达其意见,则无法当堂质证和辩论,证明力大小不能保证;如果被害人出庭,其被害人陈述的提出和补充则可能被其他证人证言和证据所“污染”,同样证明力也会受影响,最后被害人辛苦、漫长的诉讼参与只能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作用,得到的判决还可能遇到“执行难”的问题。这些矛盾的法律根源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赋予和被害人有作证义务在“一体化”审判中的冲突。立法者既要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又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初衷错了吗?反观只把被害人作为证人的英美法系国家,“被害人保护运动”正是发源于此,并且在审判中也越来越重视被害人的作用,通过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来对法官量刑施加影响。在混合诉讼模式的日本,也有学者提出,“如果不建立刑事诉讼中反映被害人意思的制度,则《刑事诉讼法》便会因游离于国民之外而失去信任”。[11]所以,可以看到,我国赋予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地位,是“引领”世界潮流的,但由于无法解决在“一体化”审判模式下的上述矛盾,实际效果并不好。但这次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改革,为解决上述诸多矛盾、落实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提供了契机。被害人的参与,在定罪阶段,表现为与被告人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可以举证、质证、申请新的证人到庭或调取新的物证;在量刑阶段,则最突出的表现为量刑意见表达权。被害人通过量刑意见表达权的行使,来满足其作为犯罪受害者和诉讼主体的“复仇意愿”;通过法院在量刑时必须考虑被害人的量刑意见,即影响量刑的可能性,来作为和被告人谈判的“筹码”,满足其“求偿欲望”,最终达到打击犯罪的同时又平息了纠纷的目的,达到激烈对抗后的“和谐”,这也正是西方恢复性司法所追求的。
以上论述了在量刑程序中被害人意见表达的重要性。被害人量刑意见书具体内容包括量刑的意见和理由及依据两部分。但《意见》对被害人量刑意见权的行使,仅仅规定了“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并说明理由”(第4条)和“在定罪辩论结束后,审判人员告知控辩双方可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辩论,发表量刑建议或意见,并说明理由和依据”(第9条),并没有像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一样做具体的操作上的规定。在参照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和英美被害人影响陈述的相关内容后,笔者认为,被害人量刑意见表达权具体实施包括下列五个问题:(1)以何种形式行使?可以参照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的规定,如果被害人出庭,可以制作被害人量刑意见书;如果不出庭,那么不应强制被害人出具量刑意见书,因为求刑权本为检察院代表国家追究犯罪之公诉权的一部分,不能放弃;而被害人之量刑建议权乃为权利,作为诉讼主体,被害人可以放弃行使。(2)在量刑意见的幅度上,是采用“概括式量刑意见”、“相对概括式量刑意见”还是“明确式量刑”?《意见》规定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具有一定的幅度,但被害人的量刑意见可以更加灵活,即在其自己可以熟悉法律或在诉讼代理人的帮助下,可以提出“相对概括的量刑意见”(提出明确的刑种,并具有一定幅度);如果自己不了解法律且没有诉讼代理人的帮助,则选择“概括式量刑意见”(不具体提出刑种和幅度,只是提出“从重”、“从轻”、“减轻”的意见)。这样设计的出发点是最有效地使被害人的意见影响判决,增加法院对被害人意见采纳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正义。(3)被害人提出量刑理由和依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里我们可以参照英美被害人影响陈述的相关内容,采用被害人量刑意见表格。表格的内容除了对量刑的意见外,还要有理由和依据,主要包括身体和精神是否伤害、是否需要医学治疗、治疗及其他的费用、该事件造成的其他损失、该事件对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是否还会有后续的影响?如果有是什么?被告人是否采取行动弥补损失求得原谅?是否达成刑事和解?通过被害人量刑意见表格来对被害人提供一些指引,一来意见的理由和依据更加明确,有利于被害人操作;二来可以避免重复陈述同一或相似的事实,提高诉讼效率。(4)如果被害人出具了量刑意见书,是否要在开庭审理前送达被告人?笔者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首先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书和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书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如果公诉案件没有检察院的起诉法院是不能主动审理的,所以检察院的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意味着检察院代表国家追诉犯罪,是一种权力的行使,有义务将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移送法院,作为发动诉讼的标志;法院也有义务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送达被告人,一是通知其已被追诉,二是起到辩护准备的作用。而被害人量刑意见书是其作为诉讼主体权利的行使,法律上没有通知被告人的义务;从被告人辩护准备的角度来看,由于量刑意见书已制成表格,还是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辩护对象的,并不会对被告人造成明显不利的影响,所以不必要将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书提前送达被告人。(5)刑事和解书和被害人量刑意见书的关系。如果在审判前达成刑事和解,则表明被告人积极悔过并赔偿,被害人也认可,此时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书可以选择已与被告人达成刑事和解,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这种概括式的量刑意见。
综上所述,这次的“量刑制度改革”是通过保障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来达到量刑活动的公开和公正,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兼顾的思想观念的体现。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独立诉讼主体地位的正当性,又从《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解读中,提出了几个对被害人能够有效参与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的权利,以期能使被害人走这“名惠而实不至”的尴尬境地。但实践的情况如何、是否需要完善?这还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而本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可借加强对被害人保护的理念而将刑事和解、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融入到现有的程序当中去,为程序的局部改革提供刑事司法理念上的支持。
[1][英]迈克·麦康维尔.英国刑事诉讼法典(选编)[Z].岳礼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46.
[2]高德道,孙付.被害人在刑事公诉中的地位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1,(10):72.
[3]卞建林.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42.
[4]陈瑞华.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J].中国法学,2009,(1):178.
[5][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419.
[6][英]詹姆斯·迪南.解读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3.
[7]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9.
[8]周伟.刑事被告人、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245-303.
[9]陈光中.诉讼法论丛[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8.
[10]杨正万.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从诉讼角度的观察[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87-380.
[11][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09-310.
On the Status and Right of Victims in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entencing Procedure
BAI Si-min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100088)
Although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provides that the victim has the status as one party,the rights of victim is often neglected in the defendant-centered trial.The previous reform of sentencing procedure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victims to become the real party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nd have the right of a party.This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hould put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from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level to the legislation level.After the analysis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victim’s status as a subject in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entencing procedure,it should be proposed to protect the victim’s right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effectively.
the victim;relatively independent sentencing procedure;the status and right
D924.13
A
2095-1140(2012)02-0071-06
2012-02-17
白思敏(1987- ),男,山西五台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0级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左小绚)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