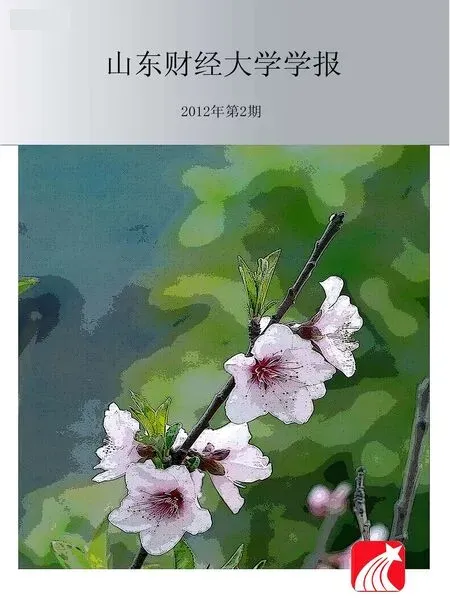论灵性资本视野下企业价值的内化与提升
陈 颐
(1.闽江学院 管理系,福建福州 350108;2.海西地方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引 言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误读“市场经济之父”亚当·斯密的著作与思想,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已经彻底断绝了文化上的血缘联系,这种将精神价值判断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肢解无可挽回地成为了事实。更不幸的是,这种肢解和误读,随着经济学帝国的建立,已经将理论外化为现实,造成市场经济道德血液的稀缺。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1]这一语便言中了公平与道义的重要性,否则社会经济的安全稳定便难以实现。我们也亲见了包括金融危机中资本主义的贪婪,也包括中国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矛盾,其中道德缺失是导致各种矛盾与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这个世界看似充满了二元性,然而犹如一种幻觉。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亦是如此。只有当我们有能力让头脑和心灵从理性的贪欲中解脱出来,我们才算获得真正重要的资产——“灵性资本”。“灵性资本”这个字眼近些年来日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她是人在信仰、宗教、终极价值目标方面的素养,关系到企业家、员工奋斗的原动力,以及人们在内心深处应对变迁与危机的能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企业之余迫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经典文化不仅对个人“身”、“心”、“灵”修养的提升有极大的帮助,对企业的管理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对此,本文将以企业为分析主体,从三个方面对投资“灵性资本”展开探讨:一是在管理过程中净化文化环境,探寻“灵性资本”;二是让管理文化回归人本经济,投资“灵性资本”;三是在实践中担当起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累积“灵性资本”。
二、探寻“灵性资本”,净化文化环境
文化作为一种行为规则而存在,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历史表明,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包含着关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每一种经济制度都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经济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发展过程。通常所说的“文化”概念大体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人类全部创造物,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第二个层面,人类精神领域的创造物,主要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等;第三个层面,人的主体精神世界,即文化是作为一种匡正人类行为的内在整合力量。这第三个层面的意义却又是最重要的。就像不同的自然资源会形成不同的市场一样,不同的文化资源也会形成不同的市场。在通常情况下,非物质文化要落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这就造成了文化滞后现象;文化在不断变迁过程中,其各部分变化的速度并不相同,有的部分快,有的部分慢;文化滞后的这部分通常在群体价值中的地位很高,例如道德、风俗、思想意识、社会制度等常常成为滞后部分,并通过群体压力迫使人们趋同,当这种情形出现时,滞后部分对于整体所发挥的功能是非整合的负向功能。况且,在文化总体中总是存在着许多亚文化,有些亚文化是负文化,如非道德行为等。这些负文化所发挥的功能,对于整个文化来说,是反方向的、非整合的。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种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为其提供指导和奠定基础。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的因素。”[2]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其生存和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哺育。现在许多企业开始高度重视文化管理,企业的文化管理除了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软约束力外,还可以在生产中提供更多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企业道德文化管理也应与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的步调相适应。但问题是许多企业的文化建设还是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当企业发展又上一个台阶的时候,就急需新的文化与之相适应,这种转型带来的陌生感使得原有的文化制度无法适应企业当前的新发展。这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使文化与管理实现耦合,主要是要及时调整,将新的文化理念替代旧的不适应企业发展的文化。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些企业由盛而衰的末路也说明了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全员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的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永久强大的企业。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今日新月异的变迁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呢?“灵性资本”①我国学者张志鹏(2010)将灵性资本理解为:为了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持续收益,个体从宗教和其他信仰中接受的有关人生意义、目的、使命和价值观的认知。来源于文化,其形成或许给我们一些启示。灵性资本具体来说就是主体为了使有限的生命实现收益最大化,必须确立一系列有关人生意义、目的和使命的认知,这些认知是个体进一步选择的基础,也直接决定了选择的质量、机会和范围。这些认知并不能从科学实验中来,而主要来自于宗教或其他信仰。灵性资本来自于文化的提炼。而文化又是凝聚和激励人心的重要力量,文化建设离不开一种基于心灵自性的灵性资本的培养和酝酿;文化是智慧与文明的集中体现,而智慧与文明来自于灵性资本的不断累积。用灵性资本整合经济资源,再将文化转化为凝聚力、吸引力、竞争力,便会产生强有力的经济推动力,所以灵性资本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内在凝聚力的支撑。
我们认为,外在资本短暂、愚昧、痛苦、卑俗且变化无常;灵性资本恰恰相反,其因具有自由意志,可自主选择其存在样式,且具有长久的智慧力量,所以又称“边际能量”,比如,懂得人生的目的、了解人生的机遇、有集体感、有很强的家庭观和劳动观、有自信心等等都是拥有灵性资源的表现,灵性资本是一个企业所真正需要的一种内在力量,也是企业文化得以随机应变的保障。企业需要做的就是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市场参与者提供新机会,这样才能更好地通过理解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适应经济增长的文化模式在吸收各个方面的文化精华中形成。对于一个企业,不断圆满的“灵性资本”可以通过对企业员工心灵的升华而形成一种永不变迁的内在约束力、内在强大的凝聚力、内在和谐的进取力,从而实现企业文化理念与管理目标有效衔接。
三、投资“灵性资本”,回归人本经济
当前,传统的物本主义经济增长反复撼动着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约束,经济增长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终极目的、以效率为中心的泥沼,其后果便会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忽略人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忽略物质财富分配格局对经济增长主体——人的影响。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总以“经济人”作为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假定,从逻辑上注定了经济主体的无限贪欲之本性。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经济道德的恶化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发生的。2008年风靡全球的金融海啸足以引起我们对社会诚信的深思,并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同样的状况反复发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是以人为本!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将理念付诸于行动实践。
我们企业管理中所谓的“人本经济”并不应该以经济效率指标为其评价衡量的主要标准。“人本经济”的回归需要在人的“灵性”提升中实现,否则会陷入无限的“物欲”之中而难以自拔。企业管理过程中企业家应该带头自己当好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被所谓的财物所控制。自我本性的改造或者说自性的清净则源自“心灵”的修养,因此,企业家更需要投资的是灵性资本,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融,在管理中回归人本经济。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些管理政策在某个企业团体能够取得成功,却不一定适应于其他文化背景的群体。那么移植文化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呢?灵性资本中的“灵性”一词看作是“意义、价值观和基本目的”,因而灵性资本也可称为信念资本,在福格尔看来,灵性资源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但又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灵性资源并非只局限在宗教领域,而是涵盖了所有的非物质资源。这种资源时常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私下进行转移,而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来进行。灵性资本主要是来自于传统的文化资源,在扩展人们选择的范围和质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3]。
灵性资本有利于将文化“内化”成人们内心的一种自信力,作为一条“纽带”,灵性资本能发挥文化对企业系统发展的推动、凝聚、润滑和整合作用,通过不断的潜移默化,化解企业发展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实现健康、有序、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同时灵性资本也是人们在内心深处应对变迁与危机的能力,她可以使企业系统从封闭式转向开放式,从自信式转向反省式,从分析还原式转向系统综合式,从纵向传递式文化转向多维沟通式;灵性资本作为信仰层面的素质,对经济活动的发展有着莫大的作用。
真正地实现企业管理运作需要从每一个人自身做起,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微杜渐而不要亡羊补牢;管理细节中无不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灵性资本的不断酝酿中不断累积起真正属于企业自身的特色文化。
四、累积“灵性资本”,担当社会责任
对于经济学中最难回答的“公平”问题,其最合理的认定来自于社会认同,而认同感的培育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缺乏认同感的社会对经济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而效率最大化作为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其超常实现的前提在于公平与正义,其核心在于诚信。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学说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出发,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就是“公正”、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基石就是“公正心”——他称之为“合宜感”;斯密还揭明了“公正心”的内涵和要求——学会从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并约束利己心。[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也曾说过:“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公正、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上述精辟之言都阐明了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必须建立信用文化。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信用经济论坛”上也指出,信用是经济生活中对交易者合法权益的尊重与维护[6]。信用体系的崩溃与瓦解将对经济生活造成巨大的损害,对社会生活带来灾害性后果。所以,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应当肩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在追求效率的时候也不忽视公平与正义。
社会道德基础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活动的质量。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本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树立企业道德是比开发高新技术和改善企业体制更重要的事情。因此,企业的管理与经营运作都必须围绕诚信道德展开,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秩序的需要,也是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腐败行为之土壤的根本利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要把企业经营管理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唾弃。同时,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企业道德风尚。
那么,如何从管理的角度真正实现企业道德理念的内化呢?我们从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到,个体因人生目的认知上的差异,所面对的选择范围是不同的,选择范围的差异本身就限制了个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如果企业能够注重灵性资本的投资与累积,那么这种心灵上的磨合和提升便会形成一股融合的力量,强有力地聚合力使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互谦互让,在互助中共同为着企业阶段性的目标而努力。《礼记.学记》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7]若欲形成企业全员良好的文化氛围、累积灵性资本,必先从“灵性”教育入手;精神上的启迪和教育除了能提高学问,令人明白事理外,更能改变个人之修养及道德,加速社会道德化,防止罪恶,改变整体员工质素,不损人利己,奉公守法、公平贸易。对于充斥世间刚强难化、冥顽不灵之辈,却非普通教育所能感化,因此实践化莠为良,整固文明,“灵性”教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引导作用。
企业可持续性发展需要企业自身能不断累积灵性资本,担当起自身应有的社会责任并实现其社会功能的超越。如果说取得良好经济效益是管理效果的表面评价,那么,灵性资本因地适宜的累积所产生的无形资粮则是管理效果的真实体现,也是企业道德提升的有效路径,更是企业价值的内化与超越。
[1]新华网: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全文)[EB/OL].[2009 -02 -03].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 -02/03/content-10755604.htm.
[2]范玉刚.“文化创意”驱动中国未来[J].人民论坛,2011(13):72 -73.
[3]张志鹏.灵性资本:内涵、特征及其在转型期中国的作用[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7-33.
[4]崔宜明.市场经济及其伦理原则——论亚当·斯密的“合宜感”[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19-24.
[5]朱永亮,俞瑾,林丛.市场经济、契约经济与制度变迁[J].统计与决策,2005(1):98-99.
[6]厉以宁,郭凡生,沈明等.中国信用经济论坛[DB/CD].北京:朝阳国际商务节组委会,2001.
[7]礼记正义(卷三十六)学记(十八)[EB/OL].[2011 -07 -03].http://ssjdd.snnu.edu.cn/show.aspx?id=303&cid=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