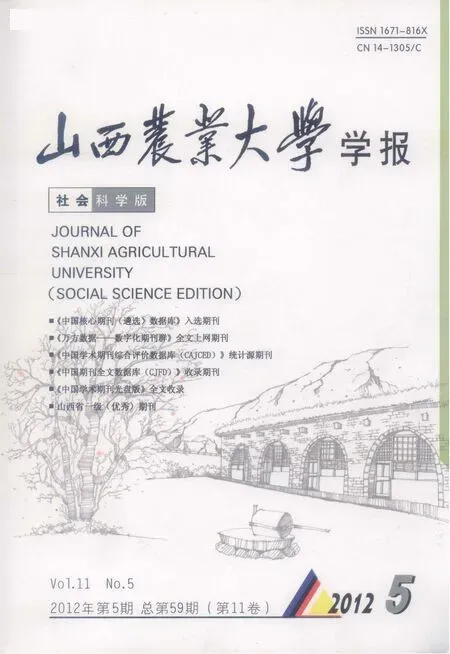论生态伦理的时代自觉及其实践路径
周松峰,黄旺生
(1.中共泉州市委党校,福建泉州362000;2.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论生态伦理的时代自觉及其实践路径
周松峰1,黄旺生2
(1.中共泉州市委党校,福建泉州362000;2.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生态是自然的状态,人类生存于自然环境中,有史以来就应是生态的和谐存在与发展。在农耕时代,人类虽然不自觉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却是敬畏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而符合生态伦理的。然而,近代以降,人类的工具理性大加凸显,自然生态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遭受严重的破坏,人类也在破坏过程中觉醒生态的意义与生态责任的承担。而实践生态伦理的路径或者说发展生态伦理的指向应是全社会的责任担当,特别是公共政府的责任担当。
生态伦理;时代自觉;实践路径
生态环境的维护与优化关键是生态文化的建设。而生态文化建设的关键又在于生态价值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就是确立物自有情的生态观,也就是给予人类主体之外的自然体以主体性的人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树立新的生态伦理道德。伦理本是作为万物灵长之理性的人类才具有的义理,之所以阐释于生态,就在于赋予自然价值的存在,表征人对生态生命体系的自觉。鉴于此,人们面对自然的惩罚,当反顾一下生态伦理的辩证发展过程,更深层次地关照一下生态应有的人格意义,并现实地对生态伦理以时代的凸显,有效地从公共路径抉择上走进生态伦理的和合。
一、生态伦理的意蕴与初期的自然融和
生态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命体的自然是宇宙主体的非意志的系统存在,不管是无机物还是有机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就其个体来说,既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上帝”既创造了其自我的价值,它就有存在的内在理由,从而生物个体间复杂的辩证统一系统就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状态,既使是其间个体在适者生存条件下的灭亡也应是自然态的无怨。而人作为思维的动物,单就物自体来说,也是宇宙存在的一个细胞,假如以自然的形式而存在,本身也是生态的。问题是,人是一根会思维的芦苇,我思故我在,人因思维而有意志、有力量,从而能够化成天下,改造自然,创造出与自然相对立的文化一面。当然,文化体与自然体如能天人合一,遵从自然内在的本身规律也就罢了,可怕的情形是文化以人的自我意志为表征,以经济人的自利为实践的出发点,不断地以自我为中心,张扬着自身的存在价值,而毫无顾及他者的平等利益,就此导致生态系统生命体的平衡破坏而危及人类存在之自身。
就此,生态伦理应运而生。伦理本是关于善、恶价值判断,是与人相关的范畴,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内在地以种群的利益为参照,内在地意识群体的秩序,只有人才会以价值为导向进行多方思维,才会以类的利益为基础共怀世界整体的有序愿景,但是,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的意义使人的理性得以升华,人离不开自然的他物存在,人应该从自我中心突破出来,把生命的意义推进于自然宇宙的全部个体,并赋予自然宇宙以情感,进而维护其生存价值,形成一种生态伦理的道德观念。这就是说实践的理性升华使人类伦理观产生新的飞跃,形成现代生态伦理观念。传统伦理是“以人为中心的,把道德、伦理限定为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故而传统伦理不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承认人对自然有某种道德关系。”[1]生态伦理的产生本身就是伦理范围的历史性拓展,其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意识形态,把一般的传统伦理扩展到整个宇宙,珍视人以外的生命和世界的自然伦理价值。利奥波德在其巨著《沙乡年鉴》中对生态伦理学作了这样的描述:“最初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来所增添的内容则是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处理人与生态的伦理观,生态伦理是人类伦理发展的第三步骤。”[2]而在当今时代,要在传统伦理背景下树立生态伦理观念,需要人类重新认识和审视自己——人并非外在于自然,并非具备理所当然的那么多对自然征复的权力。人类应该用真心、精神、力量和思维去关爱自然中的每一事物,就像关爱人类自身一样。进而在实践中把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的相对平衡当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在初期的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相和谐,生态伦理由人类自我的感怀而引发。孟子于《孟子·离娄上》就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自然的生态存在与人类诚意相待本是天道在理的事情。荀子也在《荀子·不苟》中说:“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西汉大儒董仲舒正式提出“行有伦理副天地”的天地伦理观,其间,“天地君亲师”,人类意识着自然生命的存在。内在之道在于,作为类存在的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作为动物,作为脆弱的理性动物,要生存,就要吃穿住行,要生产,就要处理与自然的能量转化,就要联合起来,以群体生存的形式展开与自然的生命共存。特别地,在农业社会里,社会的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其主要地依托于自然的个体的生命体的自然供给才保证人的十分有限工具理性条件下的生存,当然也依托群体类的共同联合,借以形成强大的与自然相均衡的力量。这里,人们在生存过程中意识到两大威胁的同时形成两个方面的伦理意识。一者,在自然农业社会里,家庭是主要的个体生产单位,其在当时有限的工具水平下,物质成果是十分有限的,既是有限的,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族群与族群间、村落与村落间、区域与区域间、阶级与阶级间就存在争斗,而且每每是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内残。这样,为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首先,就在人群自身中形成伦理的意识,以维护类的秩序。二者,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肢体力量与自然相比,往往相形见拙,人也时时处处受到太多自然体的侵害,但是,在自然经济为主的家庭生产中,主要的劳动成果依靠自然条件,甚至主要地直接来源于自然的恩赐,更多的是感恩于自然的主导力量,从而感性的人往往把自然个体神性化,赋于人格的力量,就此也感性地形成自然生命及其伦理的意义。当然,其时的自然生命力量处于主导地位,人的生命力量的处于弱势状态,生态伦理主要是人类以关爱人的生存为前提条件而感恩大自然的各种生物体,进而自觉地与自然相融合,处处体现着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二、人类工具理性的彰显与现代工业化背景下的生态伦理的缺失
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但人的性质是经济人、社会人与文化人的多样统一,并且,文艺复兴以来上帝之死给人们自由利益的凸现,首要地表现为个体的自利性。有了这种自利性,人才会创造历史,也就是说人类创造历史本质上是为自身利益而创造的。当然,一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由于这种利益的驱动,人的需求总是刚性向上的,就像马斯洛所言由生存需要到自我实现需求的渐次提升,而人之生物体力量的十分有限,人需要一种外在的借力,需要通过规律的认知,利用器物的自然力量延伸人的肢体力量,这样就促使人借助理性的特长,撑开工具理性的天空,成就了以电力与电子信息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工业文明,造就了胜过以往几千年还要多的200多年的工业辉煌。可就在这种工具理性条件下,生态伦理却没能沿着启蒙的状态良性地成长,倒是在工具理性及其工业文明下越加式微、越加缺失而表现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可以随意地支配和掠夺大自然的财物,人类的价值是最高的唯一目的,大自然中其他价值只有在人类使用它们时才能表现出来,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们对自然界索取的一切行为都是应该的、合法的。”[3]据联合国环境署做出的最新评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亿多人受到荒漠化的威胁。目前,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相当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国土面积的总和,其中有1.35亿人在短期内有失去土地的危险。究其缘故,主要为三个方面:其一,是现代工具理性的历史逻辑。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下,在自然与文化的矛盾统一体中,自然物生命体处于绝对的上位,人的意志外显相对地球、宇宙绝对是一种微不足道甚至可勿略不计的力量。而人虽然有感恩自然生命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可怜自我的俾微与对自然的恐惧。对此,人作为理性的动物首先的价值意旨是怎样增进自我的力量,在文化与自然的矛盾统一体中强化自我,实现自我、征服自然、凸现文化的力量。逻辑上推演也就是自我关照而淡化自然的生命意义。其二,是知识文化的自我加速增长。文化,特别是知识文化,虽然是人化自然的成果,但作为历史的存在,本身具有自我发展的内在冲动。而工具理性作为理性,它属于知识文化的范畴,内在地具有加速发展的本能,也正由于这种本能才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使其在人类面前体现出一种巨大的功利价值,人类越来越离不开其存在与发展。从而,与其过于亲密的关联促使人类关爱工具理性而相对地淡化自然生态价值及其生命。其三,是社会伦理的更加凸现。伦理本是在工具理性低微的景况下,在社会财富十分有限的情形下,在人之类的内斗下形成的概念,按理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历史的现实是,在工具理性得以突进的现代社会初期,社会的矛盾更加剧烈,就此,人类更加注重类自身的伦理而无视于自然的伦理。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科学技术对人类的负面影响。科学的产生伴随着抨击宗教权威,破除宗教迷信,宣扬人文精神。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尊严价值以及权力都是传统伦理所关心的。科学技术也就成了关心和满足人的欲望的工具。根据就在于只有人类才有资格成为价值主体,因而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对人有直接的道德义务。而对自然界及其间的大部分生物价值被大加忽略,人有恃无恐地利用科技向自然掠夺,奴役自然。自然在人的面前失去了神圣性。可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得人成了科学技术的奴仆,产生了异化。因为,人可以不信神,但决不可以不相信神圣。想通过科学技术奴役自然的人,也是相互作用的自然的一部分,在与自然相互联系的过程中最后异化为科技的奴仆。
这种生态伦理的缺失反过来给人类造成恶果——自然生命在人类面前式微的情况下,终于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得以觉醒而反抗式地予人类以反击,而人类在自我陶醉于工具理性的同时,终将被自然惩治。就历史地实现地观察,先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曾经承受过巨大的自然环境与能源压力,现在有所意识,但仍然是“每天犯罪而又每天赎罪”,这也是对生态伦理缺乏的佐证。就区域地看,人类的文明起源于自然的恩赠,凡是自然资源丰富之地,近水傍海之所都是现代文明都市所在或富裕之所在,然而,今之观来,这些处所也正是生态缺失最为严重,面临险境最为直接之地,如几近断流的黄河流域、环境严重恶化的沙尘肆虐之北方、还有那已逝的楼兰大可作一例证。
生态恶化也好,自然对人类报复也好,都说明工业时代,人类没有给予生态系统及其个体应有的关注与价值认可,都说明生态文化的落后与缺失。
三、生态伦理的觉醒与公共路径的时代抉择
面对工具理性下的现代器物文明,人类却得到自然之有力的不断打击,人类生态伦理就不能不加以觉醒。觉醒之一,人类只能与环境友好相处,人离开了自然的环境,离开了整个生态系统,那么人类本身也不得生存。恩格斯就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也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还是少些。”[4]既然人类天然地具有兽性,人类就整体也好,就个体也好,总千丝万缕地与自然界的生物与植物相关而存在,人类需要自然给予恩惠,也需要对自然尽些责任,需要一种必然的伦理存在。当代西方著名的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就人类对自然的依存进行跨文化和跨时空的思考,提出“生态纪”学说,把人类物种、地球放到宇宙的过程中进行一种相互平等的思维,指出“生态纪”是整个宇宙共同体的新生。“作为人类整体的我们身处一种具有毁灭性影响的现代工业技术文化之中,[5]这种文化正将地球历史的新生代送进历史博物馆。我们时代的伟大工作是呼唤生态纪的到来,在生态纪中人类将生活在与广泛的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在这里,人类不仅要以平等的主体地位尊重自然界一切的价值存在,而且越加清醒地意识到自然界本身所蕴含的诸多价值,诸如净化空气,生物链和谐,夏华秋实,这些自然本身的价值并不因为人类的意志或存在或消亡。既然人类无法离开自然而单独存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就注定是绝对性的,那么,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时候,人类就必须正视自然本身的价值,不管它本身的价值是不是对人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人类都有责任维护自然自身的价值。人类要生存并生存得更好就要保护好自然环境,以人类的智慧优化自然环境。觉醒之二,人类在文化与自然的辩证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先进应是与自然的均衡之中才得以彰显,如以工具理性的单一形式追求自身生命价值而缺少一种自然生命的关爱与价值认可,将不得以造就一种真正的幸福,并势必遗患于子孙后代,人类就此应有一种理性的消费,不能一味地追求消费的增长而追求生产的增长而无视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的过度消耗而影响下一代的生存,这既是对人类代际间的责任与伦理,也是人类主体与自然间的和谐与协调性的伦理秩序。觉醒之三,人类从自然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自然的付出太多太多,人类缺失生态伦理的征复也太多太多,届此21世纪,人类工具的理性已有相当高度的文明,人类有能力也应该反过来对自然的生命体有所回报,有所修复,并创建适合自然生态系统要求及其人类生存与发展价值的新生态系统,以全社会的力量加上现代高科技的发展造就自然破坏的修复与生态伦理强化下的自然环境良性发展。这种积极的以现代高科技修复与优化自然环境实际上是人类主体的事后责任,也是生态伦理的一种自觉表现。
生态伦理既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扬弃了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摆脱了将自然界纯粹工具化的思维方式的奴役之后,所实现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境界。”[6]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实现这种修复,如何寻找一种生态伦理的实践路径。一方面,人类作为整体,在自然生命的报复性强势冲击下,得以生态自觉,但这种自觉本身是整体的自觉,就社会个体的人来说,受制于囚徒困境的限制,在自利的强势内在驱动下,仍然陶醉于自我利益的追逐之中,市场经济经济人假设的理由在现有的经济制度下绝对地存在着。另一方面,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与辩证统一,在当今世界竞争的情形下,各个民族国家都在为各自的生存与发展强调着效率,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就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国家来说,既然是实行市场体制,内在的主要社会主体就是企业,企业在本质上是盈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其经营的内在经济与外在不经济定然客观存在,其对外的生态伦理与环境道德有时为其力不及,有时不在其利益的视域之下。这正如政治家甘地所曾经指出的那样,“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就如赫胥黎所得出结论,“人类就是要满足某些欲望,如果得不到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外部毁灭。如果得到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内部毁灭。”在此情况之下,既然,社会个体的生态伦理的觉醒转化不了普遍的生态关怀之实践,那么也就只能寻求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公共实现。
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与社会公共的服务者,体现着社会财富的权威、政治资源的权威与意识形态的权力。既然现代国家是民主国家,政府从专治型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要依托于三个方面的权威实现生态伦理的强制实践。一者,政府作为社会财富的转移分配者,通过经济的再分配手段,限制社会企业主体的环境不经济,以实现生态伦理的提升;二者,“对国家来说,无论是哪方面的调整,政策和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的调整更直接和有效”,[7]政府通过法治的强制性外在约束,从强制性外力上限制社会主体的自利而不义的生态伦理行为,从而规约人们的心路渐渐走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道途;三者,政府通过社会主流意识的强化,激活现代生态价值意识,推动人们从单纯的工具理性迷信中走出,展示与引导人们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就十分突显这种生态伦理的政策导向。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8]
实际上,社会公共力量实践生态伦理的路径,也是生态文化实践的切入点。文化的核心是思想道德,生态文化的内核是生态伦理。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生态伦理不可能自然而然生成,只有通过社会公共权力及其派生的力量加以社会的规约,才能给予生态各子系统以及各元素以真正的价值,只有通过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树立起普遍接受的正确生态价值观,才能导出正确的生态思维、制度,才会有社会共同认为与自觉遵循的生态维护,也才会有美好的生态环境。
而更深层的途径是人们消费误区的突破。就表层来说,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经济活动和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类自身,造成当今环境恶化与全球生态危机。但真正深层次的原因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是由于人类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造成的,或者说是人类消费需求增长而引起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而造成的。长期以来,人们把社会发展直接等同于经济发展,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偏离,即重物尺度,轻人尺度,而对经济价值、消费享受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人类走入消费误区。在西方国家,一度受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人们把能够高消费、多消费和超前消费的行为视为时尚,在道德上给予肯定性的评价。那些消费大量物质财富的人,受到社会的尊敬和羡慕;消费能力的大小、水平的高低成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高消费不仅象征了消费者本人的体面和经济地位,也表明他们拥有的荣耀、价值和尊严。因而人们不是为需要而消费,而是为地位、为虚荣而消费。“他们在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9]人们简单地以物质欲望的满足为生活内容,从而成为“拜物主义”的“单面人”。近代社会虽然赶走了禁欲主义的魔咒,却打开了享乐主义的潘多拉魔盒。消费上的盲目攀比、竞争、物欲横流使“文明”的社会积重累累。要使人类形成生态伦理的意志,首先要使人类自觉地定位为生态系统内平等的一员,意识自己没有任何理由高高在上地统治自然生态系统内其他分子,自觉地走出以过度消费并以此为荣的误区。当然,这一过程也同样需要政府公共服务的政策及其实施过程的正确规约与引导,比如无损生态环境而有利人类可持继发展的绿色消费的社会导引,比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比如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下的文化新兴产业的支柱性强调。
当然,生态伦理自觉历程既然是辩证的过程,历史地发展必然是从隐到显,从理论到实践,从局部到全局,从责任的小到大的渐进过程。就如伦理本身从历史上最初的小范围的家庭关系逐步扩大,最后“扩大到一切种族的人、低能儿、残废人以及社会上其他无用的人,最终扩大到低于人类的动物”。[10]更何况生态伦理从时间的维度上更关切的是长期历史发展中代际永续,“人类后代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体的当然成员,是伦理关怀的重要对象。代际伦理就是重视远距离伦理,通过伦理关怀的对象扩展到后代,使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延续性特征充分地展现出来。”[11]生态伦理的实践将是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持续艰难的过程。生态伦理的公共实现之路也必然是路漫漫而修远地循序渐进地开拓,但只要有积极的作为,最终定能以历史辩证法的方式走向自然生命体系的和谐相处,求得生态伦理的共识与坚守,实践生态环境的优化。
[1]韩跃红,张云莲.可持续发展伦理能够取代生态伦理学吗[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0):58.
[2]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167.
[3]刘振亚.基于江苏沿海开发生态实现的生态伦理原则研究[J].生态经济,2010(3):160.
[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86.
[5]赫尔曼·F·格林著.王治河译.托马斯·柏励和他的“生态纪”[J].求是学刊,2002(3):6.
[6]张志丹.论伦理生态[J].伦理学研究,2011(2):138.
[7]郭思哲,侯明明,黄晓园.论生态文明视野下技术的生态伦理调控[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1(3):12.
[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07-10-16)[2011-12-30].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content_6938568_3.htm.
[9]刘京.异化消费和生态革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5.
[10]Ch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151.
[11]廖小平.可持续发展的两个伦理论证维度[J].中南林业大学学报,2007(1):13
(编辑:佘小宁)
On the Awareness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Ethics
ZHOU Song-feng1,HONG Wang-sheng2
(1.Th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Municipal Committee Quanzhou,FuJian Qanzhou 362000,China;2.College of Marxism,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Fujian 350002,China)
Ecology is natural environment where human beings are supposed to exist and develop harmoniously.In the agrarian age,human beings,though unaware of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held nature in awe and lived with it,so it wa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hilosophy of ecological ethics.However,with human's grow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ince modern times,there has been a serious damage to natural ecolog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during which man has become conscious of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y and his commitments to it.Thus,it is the obligation of whole community,especially the governments to practice the philosophy of ecological ethics.
Ecological ethics;Awareness;Practice
B82-02
A
1671-816X(2012)05-0525-06
2012-02-26
周松峰(1964-),男(汉),福建屏南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化哲学方面的研究。
福建省科技厅重点课题(2009R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