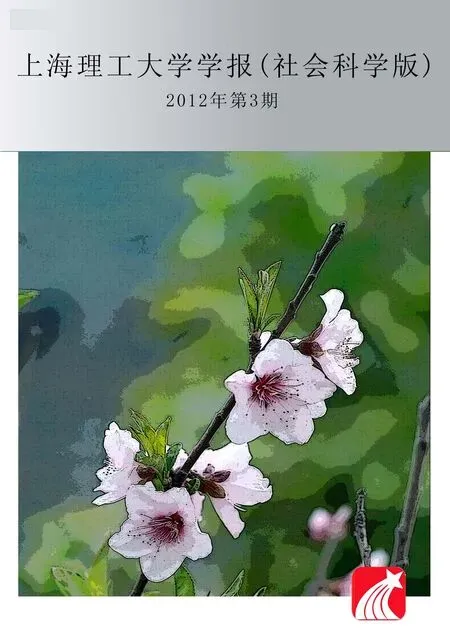形而上学二分法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理论
陈蓓洁
形而上学二分法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理论
陈蓓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433)
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理论常常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当人们提到法兰克福学派艺术理论的时候,“审美乌托邦”几乎已经成为它的代名词。然而,通过对隐藏在“审美乌托邦”这一评价背后的那种普遍信念的存在论基础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表明,这一公认的评价是值得商榷的。这一评价的得出与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对日常生活的统治紧密相连。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为法兰克福学派艺术理论之基本性质的进一步认定和研究澄清前提。
审美乌托邦;艺术;现代性批判;形而上学二分法;相互作用
一、重新审视“审美乌托邦”评价背后的普遍信念
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理论常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当人们提到法兰克福学派艺术理论的时候,“审美乌托邦”几乎已经成为它的代名词。
“乌托邦”一词,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空想和不切实际。尽管它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望,但却由于无法在社会实践中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从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责难。也正因为如此,“乌托邦”一词在现代这样一种讲究实效的社会中极具杀伤力,它拥有意义终结之权能,总能咒语般地让人羞愧难当。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洛文塔尔在1980年的一次以“乌托邦主旨的中止”为主题的谈话中就这样说道:“也许(思辨的——乌托邦的时期)是个累赘。因为一谈起这些事情,我就感到有点迂腐和背时。毕竟,一个人不可能只是生活在某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希望之中,一个人的希望只有在可能的王国里才能得到实现。”
一般来说,如果将某个人的理论指认为“乌托邦”,也就基本从总体上否定了它所可能具有的积极的社会意义,以及对此进行过多研究的必要性。而之所以还有学者不断地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十分恰当地将自己的研究意义限定在美学领域自身的批判和推进上,从而获得了研究的合法性。于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乌托邦”一事就显得极其明了,在给它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将它归结为这样的主义,从而将之定为人类精神的一次失败性尝试之后,似乎也就该言尽了。
但是,对这个已经尘埃落定的问题再作反思,将会是一次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尝试。只不过,这一反思并不意欲将自己的视阈仅仅限定在美学的范围内,也不意欲在下述方面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证明,即,并不想就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乌托邦”理论之内容和意义进行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区分,然后为自己提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任务,以此显示自己更为辩证的处事态度。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更为公正和严肃的做法,这种区分对事情的解决也毫无益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蒲鲁东辩证法的借用;而这种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言,乃是“小资产者”的方法:当它“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时,它就“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并使得企图消除坏的方面的人们“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却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然而,对法兰克福学派艺术理论的这种处理并不少见,比如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指出的一些学者对于阿多诺美学中的断片的拯救就属此类:“耀斯和伯勒尔拯救着审美体验的颠覆性特征,这种审美体验是‘对客观上具有约束力的意义的否定’,这种否定因素已经包含在审美体验之中;伯勒尔拯救的是审美乌托邦的绚丽光彩;比格尔拯救的则是艺术对真实的需求。”然而,在不触动整个理论视阈前提的基础上,断片被完好地从整体中分离和拯救出来将如何可能?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本质上恰好是浪漫主义的吧。
为了能与问题的真相靠得更近些,下述问题必须被提及和深思:我们究竟立于何种基础而做出了这种判定?这种基础的可靠性和确定性是否先已得到了内在的澄明?因为,唯有确保自己已经处在坚实的基础上时,对别人的评判才是公允和有效的。通过这一提问,那一直隐身于“乌托邦”评价背后的普遍信念便最终显露出来,这一信念正是本文要加以反思的对象。然而,若要真正阐明人们在这一信念上所持有的复杂而隐秘的心理,必须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主旨谈起。
二、对形而上学二分法的初步克服:“相互作用”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始终以对“现代性”的批判为其总任务。但是,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展的对“现代性”的资本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的主要对象乃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又常被称为“意识形态批判”。
“批判理论”采取“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有其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一方面,他们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即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卢卡奇),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掌握乃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葛兰西);但更为主要的方面,是为了应对当前的时代状况,这一时代状况被哈贝马斯很好地概括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一表达中,即,生活世界作为基础领域为意识形态所渗透和遮蔽。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使得这一工作——对当下时代的各种文化意识进行批判,从而使生活世界的本质得以呈现——变得十分迫切和艰巨。为此,法兰克福学派将之置于“现代性”批判的首要地位,正如阿多诺所说,“意识形态的批判不是某种边缘性的和科学内部的事情,不是某种限于客观精神或限于主观精神的产物的东西,而是哲学的核心的事情”。即使是洛文塔尔,在1980年的那场以“乌托邦主旨的中止”为主题的谈话中也依然强调,“现在放弃意识形态批判就是犯罪”。
然而这一“转向”(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转换)的性质如何,它到底是一种对马克思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还是一种背离和放弃,却历来颇有争议。这一争议,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在问:“意识形态批判”的真实效力如何,这一批判能不能使现代性在现实生活中趋于瓦解并最终消亡。说得更加确切些,人们的顾虑在于:在意识的领域内发生的对于意识的批判,真的能够冲破双重意识的阻拦,将自己批判的力量作用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和斗争中吗?事实上,这一顾虑因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深刻的指向性而一直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正像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其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全面理解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认为,“意识形态批判”是对远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批判,这种批判由于没有深入到这些精神特征由以形成的社会基础之中,从而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观念论批判,换言之,这种批判无论在批判的对象上(作为社会的“观念论副本”)还是在批判的形式上(采取理论批判的方式,否认马克思革命实践的可能性),都将自己保持在理论的范围之内。因此,相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它的革命性以及现实意义就变得极其有限,它并不具有摧毁现实的真实力量。比如佩里·安德森就一直这样认为:这种转向“与政治实践相脱离”,“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结果是“沿着一条离开一切革命政治实践的永无止境的曲折道路前进的”。
不过,在将两种“批判”进行了长时间的对峙之后,人们的态度已经有了缓和。现在,虽然仍不时地要表示一下对法兰克福学派将全部热情倾注在意识形态批判上的稍许不满,以表明自己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但却于总体上不再倾向于将两种“批判”尖锐地对立起来,而是试图理解并接纳“意识形态批判”中的真实意义和现实力量,努力地在两种“批判”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比如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而两者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等等。毕竟,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上层建筑也是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对于上层建筑的批判,只要是一种真正的批判,就不应当是纯粹观念性质的,它可以按照它的方式来触动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于是乎,对上层建筑的批判和对物质基础的批判之间的对峙,就以这样的方式,即相互作用的方式,得到了缓解。
必须承认,这一态度的转变标志着某种进步,即我们已经认识到世界并不是以主客对立的形而上学的二元建制为其存在之基础的,意识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上层建筑与物质基础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具有某种亲密关系,它们是相互作用的。由此,近代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由于是对世界存在的一种虚构便成为我们一致批判的对象。
这一认识的取得固然可喜,然而对这一进步保持谨慎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在竭力要与这一被海德格尔称之为“真正的哲学‘丑闻’”的虚构行动保持距离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思考,这种距离的取得是否意味着对这一虚构行动的真正超越。因为,即使是如海德格尔这般的哲学家,也深深为“超越”之艰难而殚精竭虑,就像伽达默尔指出的:“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解答,比人们习惯于轻率地援引的海德格尔所谓对形而上学的克服,更为坚强有力。而海德格尔也一直防止把形而上学视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被克服和可以轻易地被弃之不顾的东西。”
因此,必须对我们的“进步”加以如下追问:那种使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峙”,以及使对经济基础的批判和对上层建筑的批判之间的“对峙”得到缓解的“相互作用”到底是怎样一种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对“对峙”的真正解决,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折中、调和?因为就问题的实质而言,这一“相互作用”在其存在论基础上的真实性质,将最终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否是一种本质性的进步。
三、艺术与现代性批判:超越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可能契机
若要真正澄清上述问题,绝非一件易事。然而庆幸的是,发现自己根本无须在理论上提出各种论证来准备一场论战,事情的实质很快在这样的现象中得到了决定性的展现:当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在晚年纷纷转向艺术领域,并不约而同地将审美、艺术看作唯一能够对异化的现实起到批判、否定之功效,并因此成为人类获得拯救和解放的最后基地和希望的时候,争议再度爆发。只是这一次的“争议”演变为众口一词的责难:用艺术反抗现代性的统治,并试图以此实现人类的解放,这实属幻想,是“审美乌托邦”。比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理查德·沃林就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之所以转向美学研究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把进步的解放置于历史现实中”,因此“被迫到审美领域去查找否定力量的替代性源泉。但是总而言之,艺术无力承受在他们的体制中必须承受的沉重负担。结果,留下来的只是某个‘全面受到主导的世界’的观念窘境和历史上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计划”。
暂且撇开法兰克福学派艺术理论内部是否存在观点的偏颇,引人注意的是我们在“艺术”与“现代性批判”之关系上的这种集体意识。当我们激烈地反对对这一关系的肯定性见解、并将之斥责为“审美乌托邦”的时候,这对于我们在物质与意识之关系问题上所取得的进步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艺术”为什么无力承担“现代性批判”之任务?因为在通常的看法中,艺术只不过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领域,而且是离物质基础最遥远、关系最不密切的领域,因此,现实世界之反抗“现代性”统治的斗争怎么可能通过艺术这样一个领域而获得胜利呢?!当然,还是要指出,即使在艺术的问题上,那已取得的进步也并没有被我们完全抛弃,因此,“艺术”与“现代性批判”之间的关联依然得到承认。只是这种关联被置于意识与物质之间之亲密性的最遥远的边缘,它对于物质领域中的反对“现代性”的斗争来说是作用最小、最微不足道的。它充其量只能进行艺术领域中的反抗现代性的斗争,比如对现有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的批判,从而实现一种主义向另一种主义的转换。而法兰克福学派恰恰在现代性批判的视阈内为艺术设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寄予了如此深切的希望,那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了。由此可见,促使人们作出“审美乌托邦”这一定论的乃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待艺术的这种态度,这种态度极大地触怒了人类理智对于“艺术”的一贯见解。
然而,关于“艺术”的一贯见解是否是一种正确的见解?这一见解是否真正地摆脱了“乌有之乡”的束缚而获得了颁布“乌托邦”这一殊荣的资格?在此尚无法三言两语地作出回答,但是,这一被人们坚信不疑的关于“艺术”的传统看法,却首先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证明:建立在“相互作用”基础上的对于形而上学之二元对峙的超越乃是一种虚假的超越,而且,只要人们对艺术的见解仍停留在传统美学的视野中,那么对于形而上学建制的任何超越都将被证明是不彻底的和虚妄的。因为,当把“艺术”当作一种对象来欣赏,一种使心灵摆脱俗事缠绕而获得愉悦与宁静的途径,并因此将艺术视为离现实斗争距离最远的领域时,“相互作用”便从来没有在它那本应具有的意义上,即超越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被领会过。相反,对艺术的这种看法证明,“相互作用”并没有击穿原先的形而上学之二元基础,它只是被保持为两极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它不过是两极之附庸;在比较好的情况下,“相互作用”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也不过是成为第三者而与它的两个端点一起保持着权力的均衡而已。
可见,虽然一直努力地将形而上学的两极拉近,甚至有时声称这两端是融合的,是零距离的,想以此揭示形而上学建制的虚假,但艺术之被顽固地拒斥在社会革命的现实作用之外的事实却无情地将我们的声称撕碎,它表明形而上学对我们头脑的统治依然如故。正是在这种统治之下,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作审美乌托邦的评判,并且无须反思,无须论证;才会那么普遍地按照“意识形态批判”的各种对象(即各种意识形式)与物质基础之间的距离远近来订立它们各自的价值和等级。比如,认为对科学技术及启蒙精神的批判是最重要和最有现实意义的,对权威和纳粹的批判居其次,对艺术的批判又次之。因为毕竟,按照这一二元对峙的基本架构,意识“总是不得不排在健康的肉体能力与特性之后”的(海德格尔语)。而在面对当代思想语境中的一些关于艺术的断语时,才会那么容易地就无所措手足,比如:海德格尔居然认为“艺术为历史建基;艺术乃是根本性意义上的历史”;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认为,“现实的基础条件的性质是审美的”,这是“现代思想自康德以降,久已认可”的“见解”;杜威说“人类经验的历史就是一部艺术发展史。科学从宗教的、仪式的和诗歌的艺术中明确地突然显现出来的历史,乃是一种艺术分化的记录,而不是与艺术脱辐的记录”;尼采谈到悲剧诞生的问题时,他居然认为这是“严肃的德国问题”,是“德国希望的中心”、“旋涡和转折点”。
也许,还是会有学者疑虑重重:上述论断之得出是不是太卤莽了?在对艺术的传统见解和对于形而上学之超越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无法构成本质的对立啊!然而,海德格尔的下述论断或许有助于打消这些疑虑:在形而上学支配下的时代,艺术进入美学的视界内,成了体验(Erleben)的对象和人类生命的表达,这正是这个时代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换言之,艺术进入纯粹精神的领域,成了表达,成了第二层的东西,然而海德格尔却相当肯定地指出,“我们既不能把艺术看作一个文化成就的领域,也不能把它看作一个精神现象。艺术归属于大道(Ereignis)”。
面对与日常的艺术思考如此不同的立场,到底该怎样抉择和自处?是闭上眼睛挥挥手,将它们归于思想家过于敏感的神经,从而将之视为没落的艺术之神在当代上演的一幕小小的喜剧,还是拿出心灵的真诚和勇气,将自己重新置入并立身于这一冲突和斗争的漩涡之中?也许这不是本文应该过问的事情。但显而易见的是,“审美乌托邦”人类理智关于“艺术”的一贯见解,作为这一评价的始作俑者,与我们一直致力的哲学努力(即对形而上学二元建制的超越)之间,是关系密切却南辕北辙的。因此,艺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该如何解开艺术之谜,对于现代性批判之历史任务而言,便也同样是亟待加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了。因为现代性批判,就其本质而言,若不意味着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克服与超越,那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当然,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将是任重而道远的。本文在这里首先要做的,正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之后记中所说,不是解开这个谜,而是认识这个谜。一切有意义的工作,都将首先奠定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
[1] 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10-111.
[2]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145-146.
[3]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5.
[4]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145-146.
[5]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 2006(2): 1-8.
[6]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45-65.
[7]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118.
[8]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集[M].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449.
[9]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47.
[10] 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61.
[11]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11.
[12] 杜威.经验与自然[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246.
[13] 尼采.悲剧的诞生[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 2.
[14] 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J].学术月刊, 2006(2): 46-52.
Dichotomy of Metaphysics and Frankfurt School’s Theory of Art
Chen Beijie
(,,,)
We often think Frankfurt School’s theory of art is romantic. “Aesthetic Utopia” has almost become the synonym for art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when we talk of it. But this accepted evaluation is still open to discussion through reexamining the appraisal of “Aesthetic Utopia”, and especially indicating the ontological basement of the general conviction on which the appraisal is established. This opinion relates to the Metaphysics’ rule to our life. By this means we can further clarify and recognize the basic nature of Frankfurt School’s theory of art.
;;;;
B089.1
A
1009-895X(2012)03-0238-05
2012-02-20
陈蓓洁(1975-),女,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E-mail: beijiechen@126.com
① 衣俊卿教授将这两种观点总结为“激进的否定性评价”和“温和的批评或消极性的评价”。参见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② 在理查德·沃林的这种言论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在他看来,“审美领域”乃是不属于“历史现实”的,至少两者之间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在实际的生活中是十分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