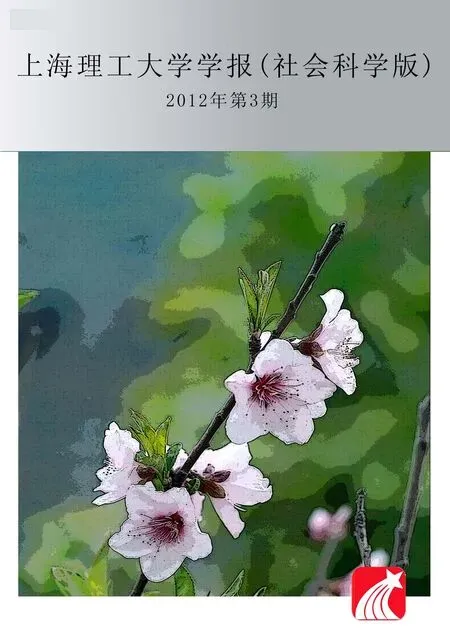关于“语言生态学”
蔡永良
关于“语言生态学”
蔡永良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20世纪70年代初Haugen提出了语言生态学,这是一门有别于传统语言学的新兴语言学科,研究环境与语言的相互作用。由于它与语言接触、语言衰亡等研究之间的渊源关系,使它更多地关注环境对语言的作用。Haugen把这一作用分成十个方面,为语言生态学确定了研究范围;Mühlhäusler提倡综合分析影响语言存在和发展的因素,批判语言帝国主义,将维护语言多样性作为语言生态学的主要关怀;Tsuda在继续深入批判语言霸权主义和语言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引入语言平等、语言人权思想,加深和拓宽了这一学科的内涵与外延。
语言生态;语言霸权;语言平等
“语言生态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A.L.Kroeber、M.B.Emeneau以及D.H.Hymes等著名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3],而首次系统提出语言生态学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Haugen,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语言生态学提出初期,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但是,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学科交叉研究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对加速进展的全球化给民族语言文化造成强大冲击的深入思考,这门学科被推到了前台,成为国际上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从研究方法看,语言生态学本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综合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甚至人口学、民族音乐学、病理传播学等学科的方法与范式,探讨人类语言的动态;从理论本身看,这门学科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研究人类语言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涉及相关的语言、社会、文化、民族、历史、政治、经济、人口等各个方面;从发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看,这门学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同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学科所关注的不仅是语言文化的微观联系,而且是紧系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关系。学习、理解并参与这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准确认识和把握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有助于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背景
(一)语言生态学起源于语言接触的讨论
20世纪70年代初,现代语言学处在从结构研究为中心逐步转向结构与语义同时并重的时期。Chomsky在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推向顶峰的同时,显露出了纯粹从语言结构研究语言的缺陷,引发了对语言意义的探讨,不仅语义学,而且社会语言学,甚至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线,特别是在后面几个领域里,涌现出一批知名学者,如U. Weinreich、C. A. Ferguson、W. A. Stewart、W. Labov、J. Gumperz、J. Fishman、D.H.Hymes、J. Rubin等。他们把眼光投向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各种联系,探究其规律与意义。语言之间的接触及其关系是他们研究的核心。例如,Rubin研究巴拉圭的双语现象,提出了“语言地位”(status)—“亲密程度”(intimacy)的模式,指出西班牙语是拥有地位的语言,用于一切正式的场合;而当地原住民用的瓜拉尼语属于没有地位、只能在非公众场合、亲朋好友之间使用的语言。Stewart在研究加勒比海地区语言接触时提出了类似的模式和理论,指出标准语处在“公众—正式”(public-formal)一端;标准语与当地原住民语言混合而成的克里奥语处在“非公众—非正式”(private-informal)一端,双语的选用受到这一模式的支配。
其实,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焦点就是语言接触,双语及多语现象是他们的切入口,涉及类似“语码转换”、“语言选择”、“语言更换”、“语言标准化”、“语言地位”、“语言使用区域”等问题。在Ferguson、Fishman、Gamberz、Hymes、Labov等人的著说中都能看到这些方面的研究。Haugen本人也是以语言接触研究而成为国际著名学者的,他是研究美国挪威移民语言的专家。无论是Haugen的研究还是Rubin、Stewart、Fishman等人的研究,其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研判和界定语言所处的坏境。
率先使用“语言生态”这一术语的是C.F.Voegelin等人,他们把这一体现语言与外界错综复杂关系的“语言环境”视作“语言生态”。很显然,这是语言生态学的源头和前身,依Haugen所言,语言生态学是这些研究的自然延伸。
(二)语言生态学的发展与人类语言急剧衰亡联系紧密
虽然那一时期的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兴奋点在于探究语言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对语言衰亡的关注并不多,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语言接触的不平等现象,而语言的不平等接触恰恰是语言衰亡的主要原因。因此,语言接触的进一步研究促使语言衰亡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从而使语言生态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人类语言的衰亡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然而,最近数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大量语言急剧灭亡。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指出:“当今世界,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语言学家D. Crystal告诫人们:世界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中只有600种暂时还处在“安全”状态,至21世纪末,整个世界将被少数几种语言所统治。美国SIL的最新资料证实了这一说法。
原住民语言是语言衰亡的重灾区。近数百年来,几乎所有大陆上的原住民语言都在急剧地衰败。以北美洲为例,欧洲白人登上这块大陆之前,分布在那里的原住民语言不下300种,有的甚至认为有500种左右,但是至今幸存下来的不到一半。20世纪 50年代末,美国语言学家W. L. Chafe受美国哲学学会和美国史密森学会委托,对北美原住民语言作了首次比较详细的调查,结果显示,北美原住民语言数量为286种,其中分布在美国境内的有251种。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要求,时任美国原住民语言协会主席、阿拉斯加原住民语言中心主任M. Krauss博士对北美原住民语言作了更为详细确切的调查,结果是:北美原住民语言的数量减少到了190种,其中美国境内的数量为155种。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幸存的语言在不久的将来都将一一灭亡。即便像目前尚有近15万语言人口、能说该语言的儿童数超出北美说其他原住民语言的儿童的总和、如此强盛的纳瓦霍语,似乎同样难逃厄运18]。
语言的大量急剧衰亡一次又一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如同生物种类的不断减少,语言种类消失对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所构成的危害将是十分巨大的。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自然就落到了语言生态学的肩上。因此,语言生态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相继出现了关于语言殖民主义、语言帝国主义、语言霸权主义、语言战争、语言人权等讨论24],通过揭示语言不平等接触的原因,倡导不同语言的合理共存与和平相处,维护语言生态的平衡,确保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三)语言生态学与语言相对论密切相关
就理论渊源而言,语言生态学与语言相对论关系十分密切,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率先关注语言衰亡的是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早在20世纪初,F. Boas、E. Sapir以及 L. Bloomfield等人,深切关注了美洲原住民语言的衰亡。这些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深入到美洲原住民的部落,做了大量的收集和记载工作,为研究那些现已灭绝的北美原住民语言积累了珍贵的原始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收集、记载、研究濒临灭亡的原住民语言的过程中,发展形成了系统的“语言相对论”思想。他们指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习惯”或“模式。他们以此作为前提,肯定语言的多样性,并揭示语言多样性影响并导致文化的多样化关系,从理论上阐述语言多样化的合理性。其实,Kroeber、Emeneau、Hymes以及上文提到的Voegelin等人的研究实际上是在语言相对论范式中进行的。Kroeber以北美原住民为研究对象,提出“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s)和“自然区域”(natural area)的理念;Emeneau在研究印度诸语言时,提出了“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思想;Hymes以民族学角度研究语言接触的规律和特征;Voegelin等人也是如此,在亚利桑那这一文化区域中研究原住民语言的环境。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的本质特征是,在肯定语言多样性(包括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提倡不同语言文化的合理共存。因此可以说,语言生态学是从语言相对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关理论。
二、内涵与外延
(一) Haugen的语言生态学
Haugen是美籍挪威人,其父母在他出生前七年移居美国。Haugen亲身感受了斯堪的内维亚语言与英语接触的不平等,研究挪威移民语言成为他的终生追求,而且因此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他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以及美国多所著名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的语言学教授。由于研究美国移民语言的境遇,使Haugan具备了国际眼光,能够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观察语言接触的规律和特征,从而使他能够系统地提出了语言生态学的理论。
Haugen借用了“生态”这一隐喻,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相关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学问。Haugen所指的“环境”,其概念与“语境”有类似之处。不同的是,他所强调的不是语言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指代关系,他把后者称作“词和语法的环境”。他所指的语境是语言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他指出:语言真正的环境是使用这一语言的社会。由于语言存在于人们的大脑里,同时又在语言使用者之间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发生相互作用,Haugen又将语言生态一分为二:心理学意义上的语言生态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语言生态。前者指双语者或多语者大脑中语言间的相互作用,后者指语言同将此作为交际手段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Haugen 认为:语言生态的决定因素是学习、使用、传承语言的人。
显而易见,“生态”这一术语属于生物学用语。19世纪语言研究领域里受到达尔文主义影响,普遍将语言比作有生命的物体,有诞生、老化,直至死亡的生命周期。但是到了20世纪,大部分语言学家摒弃了这种简单的生物类比,不再相信语言如物种一样具有生命。但是Haugen并没有完全抛弃这一比喻,认为“只要把语言当作人类的行为来看,语言就拥有了生命、目的以及形态”。Haugen指出,生物学家研究植物、动物与整个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此称为“生态”;社会学家研究人类与他们的整个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此称为“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那么,研究语言与语言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称此为“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这一术语岂不是那些科学术语的自然延伸?
在Haugen看来,语言生态学研究语言与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其内容不仅包括心理语言学、民族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学长期关注的语言变化、语言接触、双语现象、语言标准化等,而且还可以包括所有关注类似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维护等一系列语言与使用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科学。在这基础上,Haugen列出了语言生态学所关注的十个问题:
语言属于哪一类?(历史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
使用者是谁?(语言人口学)
语言使用范围是什么?(社会语言学)
语言使用者目前使用的语言是什么?(双语研究)
语言内部的变体是什么?(方言学)
语言文字的性质是什么?(语文学)
文字的标准化程度如何?(规定语言学、传统语法学、词汇学)
获得什么样的机构或制度性支持?(语言政治学)
语言使用者对所用语言的态度是什么?(民族语言学)
语言在整个语言生态类型中所处什么样的地位?(语言生态类型学)
上述十大问题既是语言生态学的核心内容,同时又是这一学科外延。虽然Haugen把语言生态学定义为语言与使用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但很明显,他的兴趣点在于环境对语言的作用,而不在于语言对环境的作用。
(二) Mühlhäusler的语言生态学思想
从Haugen 为语言生态学确定的内涵与外延看,语言生态学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它所涉及的面几乎包括关于语言的所有一切,研究的范围也几乎包括了语言学所有分支。语言生态学刚提出之时,响应者不多,继续深入研究Haugen所提出的十个问题的语言学家寥寥无几。然而,当另外一部分人将注意力放在语言的衰亡上面时,语言生态学出现了转机,逐渐为人们关注并接受。这一方面澳大利亚语言学家P. Mühlhäusler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Mühlhäusler主要从事语言维护、语言规划、皮钦语、克里奥语以及太平洋地区语言研究,其学术背景与Haugen相似,因此,他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Haugen 的语言生态学观点,同时也能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这门学科。
Mühlhäusler语言生态观主要体现于他的代表作《语言生态学: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变化与语言帝国主义》。Mühlhäusler是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的语言学教授,长期从事太平洋地区的语言研究,对这一地区的语言变化情况十分了解。语言变化的传统解读是自然现象。Mühlhäusler另辟蹊径,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分析研究了语言变化的情况,认为历史与文化诸多因素才是语言变化的真正原因,而造成语言变化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总和就是语言的生态。
Mühlhäusler认为,语言生态学之所以没有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主要原因在于Haugen没有完全摒弃传统语言学若干核心理念。比如,Haugen相信“某种特定语言”(a given language)的存在;又比如,Haugen认为,语言的描述、历史、以及内在的演变等问题应该同语言生态学分开来并由相关专家进行研究。Mühlhäusler指出上述两个观点的主要问题是,实际上,语言生态系统中没有特定的标准来确定语言到底有多少种,也就是说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界限是极其模糊的,因此“某种特定语言”的概念是传统的语言学概念,并不是语言生态学所能接受的概念。如果把同语言生态问题关系如此紧密的语言历史、语言描述以及语言演变排除在外,由其他专门学者专家研究的话,语言生态学便重蹈了传统语言学的覆辙。与此同时,这样做实际上承认了传统语言学将非传统语言学,包括Haugen提出的语言生态学本身边缘化的理论依据。仔细分析Mühlhäusler这一段对Haugen的批评,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除传统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之外,Mühlhäusler把这一概念之下的语言单位,比如方言以及可能比方言更小的语言现象,如“社区语”(communalect)等统统纳入了语言生态学的视野;另一方面,他提出了综合研究语言生态的所有相关因素的观点。不难看出,Mühlhäusler不仅在理论上进一步廓清了语言生态学,而且在方法论上明确了该学科与传统语言学的界限。
从综合的和生态的观点看待语言这一点出发,Mühlhäusler将研究重点从语言种类问题转向人类社会交流本身,从语言周边发生了哪些会对语言产生作用的事件或因素转向是什么样的过程使语言得以存在和演变,以及这些过程的本质特征是怎样影响语言生态的等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些问题,Mühlhäusler 认为,“语言多样性”问题是一个关键。这不仅是某一地区有多少语言的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一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态度。相信语言进化论思想的语言学者,一方面将语言多样性视为落后的象征,语言多样性是人们不愿交流,与世隔绝,不善合作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有些语言进化先进,而另一些语言进化缓慢,因此一些语言成为先进的语言,而另外一些语言成为落后的语言。相反,语言统一是人类社会勤于交流、合作团结的结果,同时又是交流与合作的必备条件,所以语言统一势在必行。在语言统一的过程中,落后的语言让位于先进的语言,既顺理成章,又符合发展规律与需要。无论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这一理念是体现人们语言态度的意识形态。在思想意识层面,上至达官,下至平民,几乎人皆认同;在实践操作层面,大到语言政策制定,小到家庭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为其左右。但是Mühlhäusler认为,这恰恰就是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语言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
语言统一理念的典型是语言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ühlhäusler指出,我们离真正理解和把握语言多样性的本质特征及其意义作用还很遥远,但是毫无疑问,近200多年来欧洲帝国对外扩张与殖民行径给语言生态构成了灾难性破坏。语言多样性的消失并不是自然结果,而是历史造成,即人为所致。帝国主义原初的定义是指某种政治制度,与帝国侵略和殖民有关。随着殖民制的不断瓦解,帝国主义的定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比如经济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帝国主义定义有两个关键词,“入侵”和“强加”,外来强势将某种经济制度、政治理念以及文化价值观强加于被侵略的弱势社会。首创“语言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Phillipson 认为,目前世界范围英语的广泛传播是一种语言的入侵和强加。Mühlhäusler接受了Phillipson的“语言帝国主义”理论,把它融入到语言生态学理论框架中间,并且指出其定义还须包括“入侵性语言”(imperial languages)这一概念。他认为入侵性语言不止英语一种。当然,Mühlhäusler的兴趣并不 在于完善语言帝国主义理论,而是在于语言入侵(imperializing)过程如何对语言生态所构成影响。他的研究结论就维护语言多样性而言是负面的:外来语言的入侵过程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语言生态,致使那一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大幅度急剧衰微,众多原住民语言让位于少数几种外来的强势语言,并从此走上几乎不可逆转的衰微之路。
(三) Tsuda的语言生态观
当Mühlhäusler把语言生态学研究与当下维护语言多样性这一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发展研究生院国际交流系教授Yukio Tsuda(津田幸雄)将焦点集中于关于世界范围内语言接触不平等现象,主要是“英语霸权”的研究和讨论。Tsuda是当今语言学界反对“语言霸权”,提倡语言生态平衡比较活跃的学者之一,长期从事语言交际中不平等现象的探讨和剖析,对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及其对其他语言与文化所构成的影响,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丹麦语言学家T. Skutnabb-Kangas称他为“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尖锐的批判家”。
Tsuda在其代表作“英语语言霸权与语言多元策略——提倡语言生态学范式”一文中,分析批判了英语语言霸权,陈述了他的语言生态学思想。
Tsuda在文章中指出:英语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泛、运用最普遍、势力最强大的语言。全世界说英语的人口超过15亿,60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科技领域主要用语是英语,全球80%左右的学术出版物是英文,大多数国际组织事实上的官方或工作语言也是英语,而且英语还是世界上教学最广泛的外语。Tsuda认为,英语在世界范围构成的语言强势实际上是另一种霸权,一种语言霸权,英语的传播已经成为“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文章认为,这一霸权不仅构成国际交流的不平等和语言歧视的蔓延,将非英语国家人们推至极为不利的境地,使他们因不说英语或英语能力较弱而遭受歧视,而且影响甚至控制了世界上非英语人群生活的许多方面,奴役他们的思想,培植非英语人群对英语语言、文化,甚至英美人士的语言、文化和心理依赖。这是对非英语语言和文化的严重威胁。通过引用Pennycook、Phillipson、Skutnabb-Kangas等人的语言殖民主义、语言帝国主义以及语言人权学说,Tsuda进一步分析研究了英语语言霸权的本质特征,指出,英语语言霸权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是全球范围内语言文化“英美化”(Anglo-Americanization)的特征。Tsuda把它称为伴随经济贸易全球化同行的“全球主义”(globalism)。全球主义是以英语语言文化为核心的新的国际关系,同时又是英美文明同化其他语言文化、控制世界意识形态、垄断国际政治经济、最大限度地扩大其物质利益和发展空间的过程。显而易见,这是人类文明的畸形发展,不仅对其他非英语语言文化构成伤害,而且对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因此,Tsuda认为,提倡语言生态学范式是应对这种威胁、遏制英语语言霸权、维护语言多元局面、确保非英语语言文化的生存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的良策。
全球主义是建立在语言同化、文化单元、意识统一等相关理论基础之上的,其中最重要的命题是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因此Tsuda 认为,提倡语言生态学,首先必须打破“语言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的束缚,确立“语言是文化、语言是人们认同的源泉”的思想。Tsuda说,语言不仅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而且是造就和影响人们不可或缺的环境,甚至可以认为“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language is people and people are language)。因此,“语言的不平等就是人的不平等;语言的灭亡就是说该语言的人们的灭亡”。在这个基础上,Tsuda指出语言生态学提倡语言权利、交流平等、语言文化多元,促进和维护非英语语言文化的安全和发展。
语言权利是指任何个人在任何情况下自由选择认同、使用某种语言的权利,这是一项基本的人权。这是Tsuda从Skutnabb-Kangas等人那里借用过来的语言人权思想,其核心是对母语的认同和使用,因为世界上许多地方存在的母语由于种种原因被排斥在边缘地位,被人遗忘直至灭亡。语言人权思想认为,这是语言人权的剥夺。语言人权的剥夺是导致语言接触不平等、目前世界语言格局的单元化趋势,即语言生态失衡的根源。
交流平等的前提是语言的平等,为实现语言及其交流的平等,应该打破英语一统国际交流的局面。比如,在法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工作语言理当是法语;在中国召开,那么汉语是工作语言。Tsuda将此称为“语言地方主义”(linguistic localism)。通过倡导语言地方主义,不仅能够保障语言及其交流间的平等,而且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甚至国际外语教学,开拓了极为广泛的前景。当然,维护国际交流的平等,本质上是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Tsuda的语言生态学观同时吸纳了“语言多 样主义”(multilingualism)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两个思想,用以提倡语言文化多元,维护语言生态平衡,遏制语言文化的单元化趋势。过去的历史显示:由于片面追求交流的效益,出现了以语言标准化为核心的语言单元化,导致语言等级和语言歧视的强化。当下的全球化正朝这个方向发展,已经形成的以英语为核心的语言文化单元化趋势正在构建一个以英语以及英美文化占居统治地位的“全球阶级社会”(Global Class Society),致使世界民主、自由、平等无法得到保障。因此,Tsuda认为提倡语言文化多元不仅仅是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化的单元趋势,遏制英语语言霸权的蔓延,维护语言生态的平衡,更重要的是确保国际交流的民主和平等。这是语言生态学除语言本身之外更为重大的关怀。
三、结束语
总结归纳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生态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语言之间、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学科,关怀的不仅是语言本身,而且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看,生态语言学突破了以结构主义为核心的传统语言学,在语言的定义、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关系以及语言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对传统语言学提出了挑战,展示了语言及其研究新的观点与意义。从实践层面看,语言生态学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语言的本质与特征,理解语言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修正语言态度,完善语言规划与政策,更为科学合理地处理语言与语言、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国家民族以及语言与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学界普遍认为语言生态学有两个范式,一是Haugen范式(Haugenian Dogma),一是Halliday范式(Hallidayan Dogma)。英文术语也有两个,language ecology和ecolinguistics,前者通常译为“语言生态学”,后者为“生态语言学”。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研究社会环境对语言的作用,生态一词为隐喻;后者研究语言对生态的直接影响,生态一词取其实意。本文所讨论的是语言生态学,即Haugen范式,关于被称作Hailliday范式的生态语言学,笔者将另外撰文讨论。
[1] Kroeber A L. Cultural and Natural Areas of Native North Americ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9.
[2] Emeneau M B. India as a linguistic area[J]. Language, 1956(32): 3-16.
[3] Hymes D H.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4]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5] Rubin J. Bilingual usage in paraguay[C]//Fishman J.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1968: 512-530.
[6] Stewart W. Creole languages in the caribbean[C]//Rice F A. Study of the Role of Second Language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1962: 34-53.
[7] Voegelin C F.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arizona as part of the southwest culture area[C]//Hymes D H, Bittle W E. Studies in Southwestern Ethnolinguistics. The Hague: Mouton, 1967: 403-451.
[8] Campbell L.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Th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f Native Americ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蔡永良.从文化生态视角解读语言衰亡[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 43(1): 75-83.
[10] 加利.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2, 39(3): 8-10.
[11] Crystal D.Language Death[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M]. Dallas: SIL Internation, 2009.
[13] Mithun M. The Languages of Native North Americ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 Chafe W L. Estimates regarding the present speakers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62, 28(1): 162-171.
[15] Krauss M. The condition of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the need for realistic assessment and action[J].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98 (132): 9-21.
[16] Spolsky B A. Navajo language maintenance: Six-Year-Olds in 1969[C]//Pialrsi F. Teaching the Bilingual.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4: 138-149.
[17] Holm A, Holm W. Navajo language education: respect and prospect[J].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1995 (19): 141-167.
[18] Lee T, McLaughlin D. Reversing navajo language shift, revisited[C]//Fishman J A. Can Threatened Languages be Saved?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evisited: A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1: 23-43.
[19] Pennycook A. English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M]. London: Routledge, 1998.
[20] Phillipson R. Linguistic Imperial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 Tsuda Y.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and strategies for linguistic pluralism: proposing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paradigm[M]//Asante M K, Mike Y, Yin J.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New York: Rout- ledge, 2008.
[22] Calvet L. Language Wars and Linguistic Poli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 Lakoff R T. The Language War: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Making[M]. California: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24] Skutnabb-Kangas T.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Over- coming Linguistic Discrimination[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5.
[25] Gumperz J J, Levinson S.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 vity[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6] 蔡永良.重温“语言相对论”[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6): 73-76.
[27] Mühlhäusler P. Linguistic Ecology: Language Change and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the Pacific Regio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8] Skutnabb-Kangas T.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0.
[29] Bang J C, Door J. Language, Ecology and Society: A Dialectical Approach[M].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30]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C]//Fill A, Mühlhäusler P.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175-202.
Language Ecology:Thesis and Theories
Cai Yongliang
(,,,)
Initiated by Haugen in the 1970’s, language ecology as a branch of learning is the study of the mutual effects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play in the course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structure oriented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With its close relations to the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decline and the like, the subject renders more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environment plays upon language, which Haugen classifies into 10 aspects as its major concern. Mühlhäusler advocates that linguistic ecology can achieve its purpose only with its involvement with a profound criticism of linguistic imperialism which undermines language ecology in Pacific region in specific and that of the whole world in general, and an adoption of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the effect taking al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Meanwhile, Tsuda pushes the subject matter further with his in-depth criticism of linguistic hegemony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ideology of language equality and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
H313
A
1009-895X(2012)03-0211-07
2012-06-25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1BYY30);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0YJA70005);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资助项目(10ZS100)
蔡永良(1955-),男,教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与政策、语言与文化。E-mail: cyl0715@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