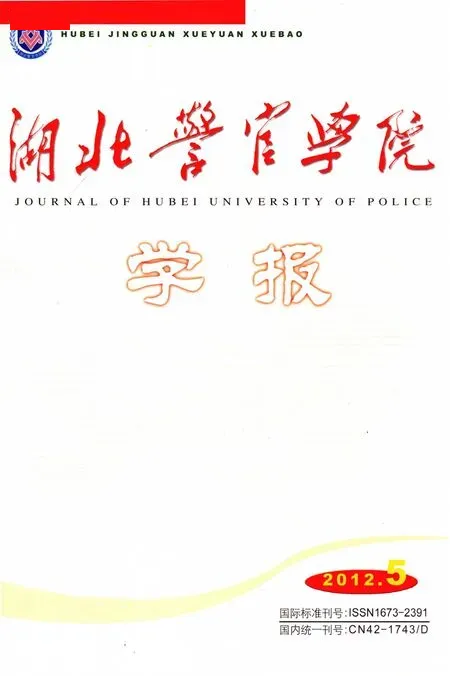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之理性解读
边慧亮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之理性解读
边慧亮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实体性规则是对非法证据的实质性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排除和法官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程序性规则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所采用的程序、步骤和方法,主要包括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程序模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修正案草案》;专门性审查;附带性审查
作为国际通行的刑事司法准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功能在于规范证据的证据能力。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由于该规定过于抽象、笼统,且对于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等问题没有具体规定,因而缺乏可操作性,难以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虽然随后相关司法解释有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规定①“相关司法解释有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规定”是指:(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一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事诉讼法》之不足,但由于规定过于粗疏,不切实际,且没有涉及非法实物证据排除问题,遏制刑讯逼供的功能微乎其微。”[1]鉴于当前司法实践的现实必要性,为从制度上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2010年“两院三部”的“两个证据规定”②“两个证据规定”是指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前者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后者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司法解释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的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制度。这是我国司法机关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框架下,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司法实践需要,在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成熟的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基础上所确立的相对具体、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进行大量科学考察、理论论证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当然,由于其法律效力等级低、证明标准过严等问题而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被虚置或者有意规避。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契机,“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2]”,国家立法机关于2011年8月30日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简称《修正案草案》)从法律原则和具体制度层面,分别规定了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第49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从法律原则的高度明确了严禁非法收集证据的立法精神导向。同时,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明确规定了对不同种类的非法证据的实质性处理方式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步骤和方法,以增加其在立法司法实践中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总体上,在我国立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分为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一、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性规则
对于非法证据的实质性处理方式,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立法模式。目前世界各国的通常做法,主要是将非法证据区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三种,并基于此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总体上,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主要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两方面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毒树之果”,则未予明确。
(一)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实体性规则
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多数国家采用绝对排除的做法,禁止法官自由裁量。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2条采用绝对排除的做法。在立法上,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未作规定,但是《修正案草案》第53条第1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这表明,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处理,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认同绝对排除的做法。
(二)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实体性规则
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实质处理,多数国家原则上仅做相对排除。在司法实践中,通常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情裁量确定非法实物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对此,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借鉴国际通行做法,采用了相对排除的做法。具体而言,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模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4条的规定采用了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的相对排除做法。但是《修正案草案》第53条第2款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表明,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立法者取消了备受争议的瑕疵补正制度和合理解释制度;同时基本采用了理论和实务界普遍肯定的相对排除的做法。即由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决定是否排除涉嫌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实物证据,从而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权衡,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合理分配和理性平衡。
(三)法官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
对于由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即“毒树之果”的实质处理,多数国家采用法官自由裁量的做法;只有少数国家绝对排除,但也通过判例规定例外情形。我国主要采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一般可依其职权主动调查核实有关案件情况。对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法官可以依职权裁量决定其证据能力。总之,对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问题,在我国现有司法体制框架下完全可以解决,因而在立法上确立“毒树之果”规则没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性规则
(一)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修正案草案》在法定证据种类的基础上,对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专门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进行了笼统的概括规定。
1.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
根据《修正案草案》第56条的规定,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分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上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承担初步证明责任,而且要达到“足以引起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另外,在审判阶段,侦查人员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就其所收集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出庭说明情况。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涉嫌非法收集证据的,其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问题,《修正案草案》未予规定。有学者认为,非法排除规则的制度目的在于遏制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将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纳入,不符合国际惯例。
2.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
根据《修正案草案》第57条规定,对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举证方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最低标准。同时,根据第53条的规定,在审判阶段,法院根据确实充分的证据,“确认属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无论是非法言词证据,还是非法实物证据,只要无法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可能性而存在重大疑点的,法院都可以进行排除。需要说明的是,在举证方没有确实、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如果要排除非法实物证据,还必须考虑违法行为的严重性程度,在司法公正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之间进行权衡。因此,总体上,举证方对其所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的最低证明程度,至少要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检察机关不能提供证据排除重大疑点,从客观上排除非法收集证据可能性的,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所提供的证据要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这种力图通过降低证明标准的做法,恐怕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反而可能引起新争议。对此,有学者建议删除第57条中“存在重大疑点,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可能性的”的规定。这种做法或许是一种倒退,不妨将其修改为“较大优势证据”标准。早在《修正案草案》出台前,陈光中教授就曾主张,“为了能够真正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适度降低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要达到的程度。笔者认为宜采用‘较大证据优势’或‘明显证据优势’的标准。”[3]
(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模式
在《修正案草案》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嫌非法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的方式,采用专门性审查和附带性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其中,专门审查具有司法审查的性质,附带审查则不必然。相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而言,《修正案草案》扩大了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范围。首先,专门性审查的范围,从审判程序扩大到审判前程序;附带性审查的范围,从审前阶段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扩大到包括侦查程序、审查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在内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其次,专门性审查的主体范围,从法院扩大到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在内的司法机关;附带性审查的主体范围,从检察机关扩大到包括法院、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在内的所有公安司法机关。这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科学化、理性化和民主化的重要表现。
1.专门性审查模式
《修正案草案》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专门性审查程序,不但包括法院在审判程序中的法庭调查程序,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所没有规定的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调查核实程序,这两者都有中国特色司法审查的性质。即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所进行的专门性的司法审查。
第一,法院在审判程序中的法庭调查程序。根据《修正案草案》第55条的规定,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发现可能存在以非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可以依职权主动启动专门的法庭调查程序;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依法申请法院启动专门的法庭调查程序,即提出有关线索或者证据请求法院就有关证据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同时,根据第57条和第53条的规定,对于经法庭调查,查证属实确属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或者“存在重大疑点,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可能性的”,法院应当依法排除有关涉嫌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能将其作为判决依据。另外,为确保法院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专门性审查的有效性,《修正案草案》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这是遏制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有学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有利于排除非法证据,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4]
第二,检察机关在审判前程序中的调查核实程序。根据《修正案草案》第54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自行发现侦查人员涉嫌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经调查核实,确属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提出检察意见要求侦查机关予以纠正;必要时,可以提出检察建议,要求侦查机关更换办案人员。对于侦查人员涉嫌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此,樊崇义教授认为,这是《修正案草案》在侦查阶段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具体表现,尤其是其中关于检察意见和检察建议的规定,加强了侦查监督,同时也是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八条中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的具体化。[5]因为草案规定实际上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即不但加强了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程序中对于侦查机关侦查活动合法性的事后监督,而且加强了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对于侦查机关调查取证行为合法性的事中监督。这种做法表明,立法者力图加强对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时的、动态性的法律监督,不再局限于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事后监督。这从制度上保障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进行事中法律监督的可行性、有效性和权威性。这些保障性措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立法目的的有效实现。
2.附带性审查规则
所谓附带性审查规则,就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其据以定案的所有涉案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依法进行必要的一般性审查的程序性规则。该规则没有相对独立的专门审查程序,也不必然具有司法审查的性质。具体而言,根据《修正案草案》第53条第3款的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只要发现确有依法应予排除之证据的,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而不得将其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根据。这从总体上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这就意味着,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其据以定案的所有涉案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必须依法进行必要的附带性审查。同时,根据有关立法精神,这种附带性审查还必须贯彻全面审查原则。首先,公安司法机关对据以定案的涉案证据进行审查时,在审查阶段和审查主体范围上,不但审判阶段的法院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检察院必须依法对其据以定案的所有涉案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且侦查阶段的侦查机关也必须依法对其据以定案的所有涉案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其次,在审查对象范围上,公安司法机关不但要审查言词证据,还要审查实物证据;不但要审查公安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还要审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交的证据;不但要审查控诉证据,还要审查辩护证据;不但要审查有罪证据,还要审查无罪证据;不但要审查定罪证据,还要审查量刑证据。总之,在刑事诉讼中,所有办案机关在作出侦查终结决定、起诉决定或者判决时,都必须依法对其据以作出处理决定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凡经查证属实确属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就应当依法排除,不得将其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根据。
[1]陈光中,肖沛权,王迎龙.我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之探讨——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视角[J].法学杂志,2011(9):1-7.
[2]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EB/OL].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2011-08/30/content_1668503.htm,2011-08-30..
[3]陈光中.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之探讨——以两院三部《两个证据规定》之公布为视角[J].中国法学,2010(6):5-16.
[4]邓瑞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探索[EB/OL].http://ww w.chinac ourt.org/html/article/200903/12/348166.shtml.
[5]樊崇义.博士研究生集体指导课讲义[Z].2010-10-08.
【责任编校:陶 范】
D915.2
A
1673―2391(2012)05―0071―03
2012—03—07
边慧亮,山西曲沃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