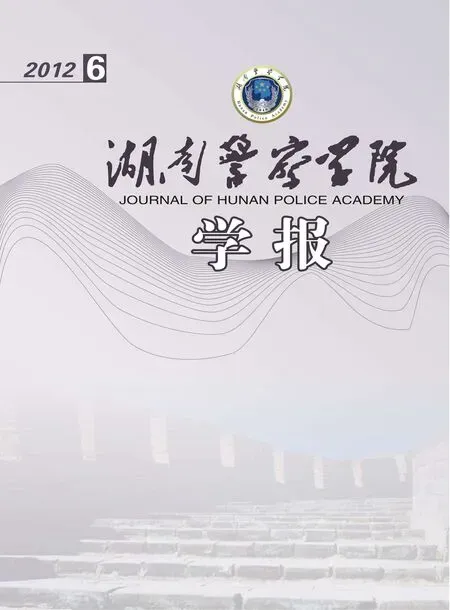信息化侦查视阈下公民隐私权保护研究
李宝字,廖剑聪
(1.公安海警学院,浙江 宁波 315801;2.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湖南 长沙 410006)
信息化侦查视阈下公民隐私权保护研究
李宝字1,廖剑聪2
(1.公安海警学院,浙江 宁波 315801;2.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湖南 长沙 410006)
信息化侦查作为一种新型的侦查模式,已在侦查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信息化侦查中缺乏对公民隐私权的必要保护,从而导致信息化侦查过程中公民隐私权容易遭到肆意践踏。因此,必须通过加强信息化侦查的法律规制、建立侦查机关内部防控机制、建立信息化侦查中公民隐私权的救济机制、增强侦查人员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意识等途径,实现信息化侦查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赢。
信息化侦查;公民隐私权;动态平衡;保护路径
信息化侦查是在公安信息化建设整体推进的大背景下,依托网络化警务信息技术,以信息化破解刑事犯罪活动出现的新规律、新特点、新手段等难题,进一步提升侦查机关侦查破案能力的一项重要的、带有前瞻性的新型侦查模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犯罪手段的高智能化,传统的侦查模式已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信息化侦查作为一种新型的侦查模式,正是顺应了信息化时代和犯罪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然而,信息化侦查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够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另一方面又容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如何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信息化侦查与公民隐私权之关系考量
(一)信息化侦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依赖
“侦查破案和防控犯罪需要准确、丰富、全面的犯罪情报信息,侦查人员必须在全面占有与犯罪有关的人、事、物等情报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侦查决策,制定出防控犯罪和打击犯罪的规划、措施和具体行动方案,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精确打击和防控犯罪。”[1]由此可见,信息化侦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海量的信息资源和智能的应用软件研判系统是信息化侦查的两大核心内容。以情报资料为主的信息数据资源是信息化侦查的基础,如果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案件、人员、车辆、物品、轨迹以及社会信息等资料,那么信息化侦查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信息化侦查,突破了“从案到人”的传统单一侦查模式,形成了“从人到案”、“从物到案”、“从事到案”等多元化的侦查模式。在多元化侦查模式之下,人、事、物等要素的相关信息都可能成为信息化侦查的触发点,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对相关情报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对相关数据进行碰撞比对以及对关联信息进行拓展,并通过多方面的查证工作,往往可以获取侦查破案的重要线索。
目前,与传统的侦查方法如摸底排队、阵地控制、追逃并行的网上侦查手段,比如网上摸底排队、网上阵地控制、网上追逃等现代侦查措施在侦查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公安内网信息应用技战法、手机通话信息碰撞比对法、同类案件串并关联追踪法、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览踪法、依托社会卡类信息寻踪法等技战法已经逐渐形成体系,并在侦查破案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从而实现了侦查效益的最大化。然而,各种技战法的有效运用,需要依托海量的信息资源,否则信息化侦查的功效就难以实现。
(二)公民隐私权保护对信息化侦查的制约
随着诉讼文明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保护程度已成为衡量一国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隐私之大敌是政府机关对个人自由神圣性的侵犯,他们更倾向于担心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免受公权的侵扰[2]。侦查权作为一项国家公权力,为了侦查犯罪的需要,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的价值追求,依法可以侵入个人私生活领域,必将威胁着被侦查对象及其相关人员乃至无辜的其他公民的隐私权。为了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恣意践踏,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侦查权予以遏制。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隐私权已从独处的权利发展到控制私人资料的权利。公民个人信息在侦查犯罪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信息化侦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信息化侦查必将对公民隐私权造成一定程度的侵扰。根据“权利制约权力”的侦查权控制理论,随着国家对隐私权保护的不断深入,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会不断加大,这必将制约着信息化背景下侦查行为效能的充分发挥。
(三)信息化侦查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动态平衡
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如何有效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力求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是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9· 11”事件后,即使是一向重视保障人权的英美法系国家,也开始逐渐关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问题。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之下,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随着犯罪的职业化和高智能化,传统的侦查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当前犯罪的严峻形势。信息化侦查主要是围绕侦查工作目标,利用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优化和完善侦查业务,是适应犯罪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但是,信息化侦查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有效侦破刑事案件,维护国家公共安全,同时也会侵扰公民私生活的安宁,践踏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高利润意味着高风险,也意味着对不同诉讼价值的追求,同时也考量着一个国家司法文明进步的程度。
如果把公民隐私权保护看作是侦查成本,把有效控制犯罪看作是侦查效益,侦查机关要想追求侦查效益的最大化,必须通过不断缩减侦查成本来实现,但是,一味减少侦查成本的投入,势必影响侦查效益的产出[3]。因此,为了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赢局面,必须努力寻求两者在法律制度规范空间内的动态平衡。
二、信息化侦查视阈下我国公民隐私权保护之现状考察
(一)我国公民隐私权保护之立法考察
我国的隐私权保护制度研究起步比较晚,尚未形成完整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总体上呈现出“内容少、法律散、手段弱”的特点。对于隐私权的保护散见于我国的宪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之中。
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条规定可以看作是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之基石。第三十七、三十九条是对公民人身自由和住宅权的法律保护。第四十条是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法律保障。在民法中,对隐私权保护主要体现在对人格权、名誉权的立法条文中。比如,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我国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方式对隐私权给予正面立法保护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此条充分体现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隐私权保护问题,必须制定一部关于隐私权保护的专门法律。在此背景下,我国正在起草《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标志着我国隐私权的保护已进入全新的阶段。
(二)我国信息化侦查中缺乏对公民隐私权的有效保护
1.从法律层面上看,信息化侦查中公民隐私权保护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而只是散见于宪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之中,不仅没有形成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系,而且规定也比较粗略,可操作性不强。
信息化侦查需要海量的信息资源作支撑,因此,侦查机关为了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必须广泛收集各类情报信息资料,建立侦查情报信息系统。按照侦查法治化的要求,侦查机关收集、保管、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但是,由于我国没有专门关于公民个人信息收集、保管、使用的法律规定,致使侦查机关在情报信息收集、保管、使用过程中难免会侵害到公民隐私权。
2.从机制层面上看,信息化侦查中侦查机关缺乏隐私权保护的内部防控机制
信息化侦查需要海量的信息资源作为支撑,否则,信息化侦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侦查机关聚集多方力量广泛采集各类信息。信息来源的渠道相当广泛,不仅有侦查机关在工作中收集到的,还有来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以及金融、电信、交通、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将各类社会信息纳入公安综合信息查询系统,直接服务于公安实战,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前,公安机关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构建大情报信息系统上,对这些数据信息的内部安全防控方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表现在尚未建立对这些数据信息的内部防控机制上。比如现在的综合信息查询系统,只要有公安数字身份证书就可进入系统进行查询,公安机关内部并未建立关于对这些数据信息的查询、储存和使用的一系列严密制度,以防止这些数据的泄露、外传和非法使用[5]。
3.从观念层面上看,信息化侦查中侦查人员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意识淡薄
由于我国对隐私权制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公民(包括侦查人员)对隐私权的认识比较肤浅,隐私权保护的意识不强。我国信息化侦查萌发于1999年开始的“网上追逃”,时间不长,侦查人员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聚集多方面力量尽可能多的采集各类信息资源,充分发挥信息化侦查打击犯罪的效能,几乎很少考虑到收集、保管、使用信息资源会对公民隐私权造成侵扰。正是因为侦查人员对公民隐私权保护意识淡薄,致使在信息化侦查中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在侦查工作中,时常出现侦查人员在没有履行审批手续的情况之下,利用其与电信部门相关领导的私人关系,轻易获得公民个人的通信数据信息的情况[6]。
三、信息化侦查视阈下公民隐私权保护之路径
基于以上考量,笔者发现由于信息化侦查带来的巨大侦查效益,容忍公民隐私权对国家公权力的适当让渡是必要的,但是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是现代法治和司法文明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应当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寻求一条最佳的公民隐私权保护路径。
(一)加强对信息化侦查的法律规制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信息化侦查中,既要追求控制犯罪之目的,又要实现保障人权之要求,因此,必须加强对信息化侦查的法律规制。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对侦查机关收集、保管、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和共享社会信息资源的相关问题予以法律规制。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1.对侦查机关收集、保管、利用公民个人信息予以法律规制
侦查机关在信息收集、保管、利用方面应该严格控制,坚持分级授权、严格审批、严格管理等原则,只有负有相关案件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为侦查犯罪之必需,经过批准后方可查阅、利用相关信息,对于在收集、保管、利用信息过程中有泄漏公民个人信息和侵扰公民隐私权并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的行为应当追究相应责任。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强制采样,经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即可。对无辜的人或者涉嫌人员的强制采样除非案情需要,一般不允许采样,如需采样,需要得到被采样人的同意并遵循严格程序方可。对于一般采集行为由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即可;对于重大采样行为,比如涉及面广、涉及人员多、影响较大以及对人体血液、精液、尿液、指纹、毛发等的采样,需要提高审批级别,有学者建议由检察院批准[6]。
2.对侦查机关共享社会信息资源予以法律规制
信息化侦查中,侦查机关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需要共享社会信息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以及金融、电信、交通、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可能存有大量的对侦查有用的信息。如何在信息化侦查中共享各个社会领域的社会信息,是侦查机关亟待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息资源共享的问题,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搭建起社会信息交换的平台,只有这样,不仅可以解决社会信息资源的引入和共享问题,还能解决当前比较严重的信息安全和公民隐私权保护问题。因此,应通过立法形式为侦查机关共享社会信息资源提供法律支撑,使信息化侦查的运行合法化。
(二)建立侦查机关内部防控机制
当前,侦查机关正在构建“大情报”系统,聚集多方面力量收集情报信息资源,大大提高了情报信息系统的使用效能和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对信息资源的内部安全防控方面,尚未引起侦查机关的足够重视,对侦查人员如何妥善收集、保管和利用获取的信息资源缺乏必要的规制。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下,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保管、利用缺乏系统的、可操作的法律规制,在此背景之下,侦查机关应尽快出台信息化侦查的规范性文件,对侦查人员收集、保管、利用个人信息进行严格规范,以加强侦查机关对信息资源的内部防控。
侦查机关制定信息化侦查的规范文件时,要严密细致,并且具有可操作性。侦查机关可以设置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信息的收集、管理工作,并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对情报信息的使用情况进行严密的跟踪监控,并将侦查人员使用情报信息的情况进行记录。同时,侦查人员对信息的使用要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防止其滥用侦查权力,侵扰公民隐私权。
(三)建立信息化侦查中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救济机制
信息化侦查犹如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有效侦破刑事案件,也会侵犯公民隐私权。在信息化侦查中,侦查机关如果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公民应当依法获得相应救济。俗话说:“无救济即无权利”。因此,侦查机关应当建立信息化侦查中公民隐私权的救济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民隐私权得到有效保护。笔者认为,建立信息化侦查中公民隐私权的救济机制,应当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应当充分保障公民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侦查机关应当将收集、保管、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情况及时通知其本人,当事人有权知道其信息的保管、使用以及遭受侵害的情况。只有充分保障公民享有知情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另一方面应当保障公民隐私权遭受侵害时的依法求偿权。信息化侦查中,公民隐私权一旦遭受侵犯,当事人有权依法寻求救济。公民可选择的救济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非法证据为由进行法庭辩护,请求法官予以排除,用以对抗侦控机关的指控;另一种是以侦查机关侵犯公民隐私权为由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通过诉讼方式获得相应赔偿或救济。
(四)增强侦查人员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意识
继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行大规模修改之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次进行修改,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这充分体现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近年来,侦查机关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加强侦查人员人权保护意识的培养,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侦查办案中,侦查人员能够比较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犯罪手段的高智能化,信息化侦查在侦查办案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侦查人员往往过多关注信息化侦查的侦查效能,而忽视其可能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随着公民隐私权保护意识的增强,侦查人员在侦查办案中应当增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意识。侦查机关应加强侦查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使其认识到公民隐私权保护的重要性,使其认识到只能在职责范围内使用公民个人信息,不得用作侦查犯罪之外的其他用途,否则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徐海霞.侦查学原理 [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121-122.
[2]刘琼,郭建军.西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价值取向及借鉴[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3):34.
[3]汤纪东.网上侦查视阈中的公民隐私权保护研究[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3):103.
[4]吴兰.信息化时代的隐私权保护[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27.
[5]曹文安.论信息化侦查与公民权利保障[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1,(4).
[6]毕惜茜.侦查信息化的法律困惑与前瞻[A].陈刚.信息化侦查大趋势[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103.
Research on Protecting Citizen’s Right to Privacy from the View of Information Investigation
LI Bao-zi1,LIAO Jian-cong2
(1.China Maritime Police Acedamy,Ningbo,Zhejiang,315801;2.Yuelu People’s Procuratorate,Changsha,Hunan,410006)
Information investigation as a new investigative mod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vestigation practice,but due to the lack of necessary protection of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information investigation,citizen’s right to privacy is likely to be violated.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investigation,establish investigative organs’inter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establish relief mechanism of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information investigation and enhance investigators’protection awareness of the right to privacy,so as to realize the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crime control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investigation;right to privacy;dynamic equilibrium;protection path
D918.2
A
2095-1140(2012)06-0040-04
2012-09-20
李宝字(1982-),男,山东临沂人,公安海警学院船艇指挥系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刑事侦查学研究;廖剑聪(1973-),男,湖南邵阳人,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诉讼研究。
(责任编辑:王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