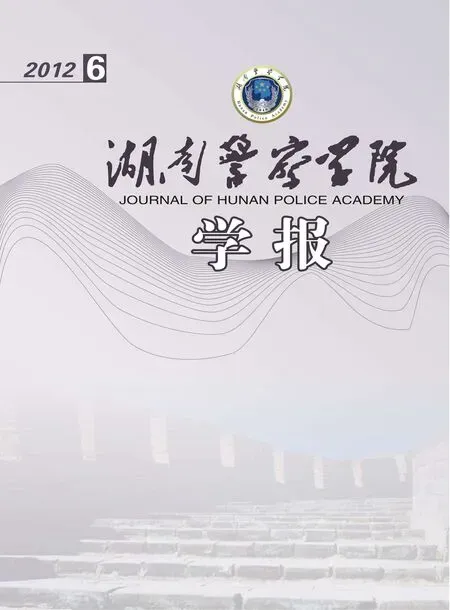习惯法研究的概念谱系
王 彬,杨丹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习惯法研究的概念谱系
王 彬,杨丹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目前国内的习惯法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概念混乱,为澄清概念混乱,在习惯法研究中应慎用“民间法”概念,并应对习惯法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正确区分。立足于事实与规范二分的研究立场,可将作为默会性知识的习惯与作为事实性规范的习惯法进行区分。在理论上厘清习惯法研究的概念谱系,有利于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提供习惯法的识别标准和适用方法。
习惯法;习惯;惯例;默会性知识;事实性规范
目前,学术界习惯于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范式来研究民间法问题,从而将运行于社会层面的非正式规范与国家机关颁布的正式规范区分开来,而民间法则属于非正式规范的范畴,然而,国家与社会范式是西方学者立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语境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语境而进行的理论裁剪。中国的社会形态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并不具备市民社会所具备的契约精神,并无从产生现代法治的内在社会土壤,所以,国家与社会范式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先天不足”的局限性,通过对西方社会现实的理论裁剪来分析中国问题,无法真切地发现中国本土的“日常生活世界”,所以民间法这一概念是充满歧义的语汇,我们应当慎用“民间法”这一概念,故应以习惯法称谓形成于社会层面的社会规范。概念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悖结不利于研究的展开与深化,正如陈金钊教授所说,“一般来说,某一学科的基本概念,对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我们能够定义得当,就能在理论体系中显现基本概念的巨大穿透力或影响力。我们如果不能发现一个适合某一学科的核心概念,就很难建立起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1]同样,对于习惯法研究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在逻辑上澄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具体的理论语境,我们也很难进行深入的理论展开,更无法构建习惯法研究的学科体系,所以有必要对习惯法研究的基本概念进行学术清理。
在学术界,存在着对习惯与习惯法严重混淆的情况,或者虽然对其做出区分但区分不合理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在讨论民法典与民事习惯的关系时,不论是‘习惯’还是‘习惯法’,其所指称的对象是同一的,即未予法典化的不成文规则。我们认为,在这一层面上理解习惯与习惯法的关系就够了。”[2]正因为在这一观念的误导下,我们无从认识习惯法的规范属性,以至于在司法过程中无从正确地识别有效法源从而达致司法判决的合法性与妥当性的有效统一。所以,我们又必要对习惯法与习惯等核心概念做出区分。
一、作为默会性知识的习惯
习惯作为人们惯常性的行为方式具有重复性、自发性等特征,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因此,对习惯这一概念进行考察,可以通过对比这一概念的日常语境和法学语境进行语义分析。首先,对习惯进行语义学分析,习惯是一种重复性的惯行。比如《辞海》中对“习惯”的定义:习惯是“由于重复或多次联系而巩固下来的并且变成需要的行为方式,如良好习惯、坏习惯。”[3]在日常语境中,习惯可以分为个人生活习惯和作为特定共同体共同遵守的社会习惯。如果不对习惯的主体做出界定,无法凸显习惯这一概念的法学意义,即法学中所称谓的习惯只能是为社会上某一共同体共同遵守的共同习惯而非个人
生活习惯。通过对习惯的语义学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法学意义上的习惯具有社会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习惯是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规范形式,个体习惯是构成群体习惯的基础,所以,习惯是个体性与群体性行为或生活方式的混合物。
其二,从发生学意义上对习惯进行考察,习惯是人类长期行为的结果。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梅因认为,我们对法学概念的考察必须基于人类早期的社会生活而进行,“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任何方法,断定法律概念的早期形式,这将对我们有无限的价值。”[4]在初民社会,习惯作为早期的法律形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淀而成的,其存在样态是一种无意识的重复性的社会行为。正如德国历史法学家萨维尼所认为,法律象语言、风俗一样是民族的普遍精神自发的、直接的产物,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个性的消亡而消亡,“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旨所孕就的。”[5]可见,习惯向法律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非人为理性的建构过程。习惯作为民族精神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习惯往往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中,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群体进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地方性知识”。
其三,从经济学角度对习惯进行考察,习惯作为集体行动的结果,是公共选择的产物。按照霍布斯的理论,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象狼与狼一样,个人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集体行动往往陷入困境。由于人类在集体行动中无法具备全知的知识,无法对集体行动的计划做出理性的设计,“只能依据常常表现为习惯法(习俗、惯例)的抽象知识建立假想的模型,以理解和适应外部环境。”[6]经济学对这一人性假设进行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趋利避害符合人的本性,在这一本性的预设下,人们之间很难展开合作,所以在公共选择的过程难以避免“牧场悲剧”。然而,长期的博弈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与人之间需要合作,通过合作可以实现更大的效益,习惯成为人们通过反复博弈而形成的“默会性知识”。与法律相比,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趋利避害、自然选择的结果;习惯是通过博弈行为而逐步形成的,具有自发性的特征;习惯并非是个人理性建构的产物,而是引导集体行动走向合作与一致的默会性知识。自发性的习惯与建构性的法律相比,习惯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而非理性的结晶,习惯并非通过明确意识和特定语言文字进行表述并为特定机关公布的明确性知识,而是为社会公众广泛认可进行心理确认的“无言之知”。
所以,从语义学、发生学、经济学对习惯进行定义,习惯是一定群体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习惯是特定社会群体通过长期社会生活而形成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通过反复的博弈行为而逐渐形成的“默会性知识”,法学语境中的习惯具有社会性、重复性、地方性与默会性的特征。
二、作为事实性规范的习惯法
习惯法这一概念无疑在民间法研究中具有核心概念的地位,但是,习惯法的复杂性也是任何概念无法加以比拟的,人们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对习惯进行界定的同时也为习惯法这一概念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另外,习惯到法律的演变过程往往是一个动态化的演化过程,我们很难在学理上将这样一个量变的过程进行定性分析,因此,即使是基于同样的学术立场,学者同样会产生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混乱使用。对此,笔者认为,只有基于规范法学的学术立场,才能更好地挖掘习惯法的规范属性并充分挖掘习惯法的司法功能,并依此概念建构法官识别习惯法的法律方法。
纵观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学传统,奥斯丁可能是最早并最翔实地对习惯法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的法学家,奥斯丁基于普通法的学术语境并将习惯法与英美法系的司法制度进行逻辑勾连,所以对奥斯丁知识谱系的学术考察更符合我们司法中心主义的研究进路。奥斯丁在其著作《法理学讲演录》中指出,“在当下,一条纯粹道德规则或者习惯规则可以通过两种路径获得法律规则的属性:它可以被某一主权者或者其从属的立法机构批准并因此以直接的模式转换为法律;或者它可以被作为司法判决的根据并因此随后获得先例的地位;在此种情形,它就在司法风尚的塑造下而转变为法律。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种方式下,道德或习惯规则都可以演变为法律规则。法律得以形成的这些方式昭示了其不同的发源:主权者、从属立法机构以及法官,正是他们将道德规则或未完成的规则转化为法律规则或者完成的规则。”[7]按照奥斯丁的说法,立法和司法均为道德规则或习惯规则获得法属性的进路,即只有经过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路径,习惯才上升为具有正式效力的习惯法,这一论点也符合分析实证主义基本的学术主张,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看来,经由正式的法定程序是法律效力来源的唯一渠道,所以,在分析实证法学看来,所谓习惯法“指经有权国家机关以一定方式认可,赋予其法律规范效力的习惯和惯例。”[8]这一定义强调了习惯法作为法律的形式合法性,但是,这一分析路径不足以为习惯法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因为,经过正式的法定程序,习惯上升为法律的过程其实属于立法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习惯法已经转化为正式的国家法,这无法论证在国家法定程序之外杂陈于社会层面的习惯规则的社会实效问题。
根据社会法学派的研究进路,法律效力与法律实效并非同一的概念。在社会法学派看来,法律实效是法的功能和作用实现的一种状态,更为强调法律运行的结果,而非法律在形式上的效力。因此,在社会法学派看来,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未必具有法律实效,而不具备形式上法的效力的规范反而会对社会生活起到切实的调整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法学派将研究的视野从“纸面上的法”投向“行动中的法”,从国家的正式法投向运行于社会中的“活法”。所以,在社会法学派看来,一个规则规范属性的鉴别不应当只局限于是否经过国家正式的法定程序,而应当将社会是否认可作为鉴别习惯法规范属性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根据社会法学派的研究进路,所谓习惯法,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社会主体就特定事项反复实践而形成的带有权利义务分配性质的社会规范。”[9]
社会法学派在法律实效的意义上界定习惯法的内涵,摆脱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概念循环的理论困境,但是,如果不提供习惯法的具体认定标准,单纯根据社会法学派的理论进路,难免会盲目扩大法的外延。分析实证法学将国家认可作为鉴别习惯法的标准,这一标准无益于在司法实践中扩大司法审判的法源,更无法区分习惯法与国家法。社会法学派将理论的视野投向了广袤的社会或者民间,将运行于社会的“活法”统统纳入法律渊源的范畴,又有可能盲目扩大法的内涵而破坏法治本身的自足性,无从区分习惯、道德与习惯法以及其他社会规范。所以,有必要提供一套系统具体的习惯法的具体认定标准,这对转型社会的司法实践具有深远而重大的理论意义。
关于习惯法的鉴定标准有以下几种学说:[10]其一,惯行说。此说认为人类具有执著性,会因循前代的遗风流俗,逐渐形成惯行,有此惯行又产生出心理上的强制力,而导致法律上效力的产生。其二,实效说。此说认为习惯系经过一定期间内的惯行享有法律上的效力,至于其期间究应多长,并无一明确的标准。其三,承认说。此说系于国家主权发达后所产生,认为习惯必须经由国家有权力之机关承认,方能具有法律上之效力。须经何种机关承认,此说又分为立法机关承认说和司法机关承认说。其四,意思说。此说认为习惯之所以具有法律的效力,主要源于人民的意思。其中尚有不同的观点:有认为习惯法的效力系处于国民中强者之意,又称“强意说”;有认为其效力是由人民意思的集合所产生,可称为“总意说”;此外,亦有认为其效力系来自共同的承诺,是为“合意说”。其五,法信说。此说认为习惯法之效力源于民族意识,凡经某一族群确信其为法律者,必须遵守,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因此,习惯成立之际,即同时存在法之效力。依该说,习惯实则为法律,故亦有称之为“实在说”者。其六,当然说。由于在“实在说”之下,就像“惯行说”一样,所有的习惯均被视为法律,因此,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当然说”,认为发生法律上效力应具备两个要素:一为“法的确信”;另一为“惯行事实”。
纵览上述学说,关于习惯法的鉴定标准,我们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国民对习惯所产生法的确信,其二,事实上的惯行。这些学说从主客观两个方面为我们鉴别习惯法的存在提供了大致的标准,但是,这些学说均是立足于外部视角对习惯法所进行的观察,并未立足于司法中心的立场为法官提供具体的鉴别标准。我们只有立足于司法的立场研究习惯法的认定标准,才能够深刻地区分习惯与法律。正如法律人类学家博汉南所说,“法在法律制度之内被重新制度化,以使社会能够依靠受到如此维护的规则继续井然有序地发挥作用。一句话,习惯以互惠为基础,法律却建立在此双重制度化的基础之上。”[11]博汉南的“双重制度化”理论区分了习惯与法律,我们亦可通过这一理论作为鉴别习惯法的根据,也即习惯法为可被制度化的习惯。习惯法的存在在于国民内心的法确信和事实上之惯行,因习惯法本身是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的社会规范,习惯法本身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规范,经过司法机构的再次制度化,习惯法作为定纷止争、利益分配的社会规范,具有可司法性的规范属性。所以,习惯法的规范属性并非来自于形式,而是来自于实质。在这个意义上,习惯法作为事实性的规范区别于国家法,经过双重制度化后而上升为国家法。
另外,学界关于习惯法的鉴定标准,一般认为习惯法不能违背国家强行法和法律原则。所以,在法源地位上,习惯法被视为“非正式法源”、“次位法源”或者“补充法源”。这一学说的根据在于习惯法在形式上的非正式性。所以,习惯法在司法过程中往往起着漏洞补充的功能。但是,对于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一方面,我国正处于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属于后发型的法治国家,法治秩序正在建立、现代性的法治观念正在形成,国家推进的现代性的法律秩序难免与乡土社会的实质正义观念存在脱节与错位;另一方面,立法理性的有限性使法律难免会出现规范漏洞、规范冲突等不足。而民间习惯法作为社会上的“自生自发秩序”更为符合转型社会的正义观念,并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冲突起到调整作用。在国家正式法秩序严重不符合社会正义观念或者法律规范存在冲突情况之下,民间习惯法在这时往往起到优位法源的作用,来解决那些“合法而不合理”的案件。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难以将习惯法仅仅作为“非正式法源”来对待,在疑难案件中,民间习惯法作为优位法源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是将其称之为“特殊条件下的法源”更为合适。在疑难案件中,为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习惯法可以作为优位法源而存在,但是,习惯法不得与公序良俗原则相违背,法官在运用习惯作为优位法源时,必须考察习惯法背后所体现的法律原则,以及与习惯法相冲突的法律规则背后的法律原则,通过法律原则进行习惯法与国家之间的价值权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习惯法进行如下定义,习惯法为一定地域内国民对之所产生法之确信并予以事实上惯行,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的事实性规范,习惯法是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并具有社会可接受性的特殊条件下的法源。
三、习惯、惯例与习惯法的区分
在民间法研究中,习惯法、习惯与惯例存在着严重混淆。据魏治勋先生所进行的学术考察,无论是在英语法学界还是汉语法学界,都存在着这些概念的混乱使用。[12]26习惯法、习惯与惯例的差别事实上在于这些规则在规范性上的度的差别,所以,为区分习惯法、习惯与惯例提供明确的尺度,为司法过程中民间规则的识别与适用提供标尺,从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首先,习惯与惯例所体现的规则发展阶段不同。无论在法律社会学还是在制度经济学看来,法律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个人习惯到群体习俗,从习俗到惯例,再从惯例到制度的动态发展过程。社会秩序制度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内在的动态发展过程,我们难以用一个确定的标尺将这一发展过程进行量化的定位,从习惯到惯例再到法律的描述大致为我们勾勒了法律发展的过程。但是,至于习惯与惯例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到底孰先孰后的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主张。在经济学学者韦森看来,“习俗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一种事态、一种情形、一种演化博弈稳定性、一种社会博弈均衡,就其实质来说它是一种‘自发社会秩序’。而惯例作为诸多习俗中的一种显俗,与其说它是一种事态,一种情形,不如说它是从人们在社会博弈中产生的习俗中所沉淀或者说硬化出来的博弈规则,尽管这种博弈规则只是一种没有经任何强制性机构或第三者所监督实施的非正式规则或者说非正式约束。”[13]韦森借助于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的研究工具对习惯与惯例进行阐释,在他看来,习惯是一种稳定的演化博弈均衡,属于哈耶克意义上“未阐明的内部规则”。而惯例则属于长期社会博弈过程被硬化的习惯规则,属于被阐明的习惯,因此具有更为高级的规范表达形式。魏治勋持有与此不同观点,魏治勋基于法律实证主义的学术视角对习惯与惯例进行了区分,在魏治勋看来,“习惯和惯例在性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前者是具有规范属性的规则,后者是纯粹的社会事实。”[12]26在魏治勋看来,惯例作为事实性的社会规范本身并不具有“规范性”,而是借助于外在的社会舆论才披上了“规范性的外衣”,而习惯则是基于社会的“内在观点”而本身具有规范性,不需要任何外在性的赋予。在笔者看来,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惯例是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或者从事某种特定行业的过程中,因习惯性的行为而积淀而成的成例。所以,惯例是比习惯更为高级的规范形态,是得到特定社会共同体认可的习惯,可以直接作为民间仲裁或者民间调解依据的规范形式。
其次,惯例相较于习惯更具有行业意义。从我国所颁布的部分法律条文来看,我国一些法律明示了惯例的法源地位。比如《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惯例一般指行业惯例,习惯与惯例相比,习惯具有地方性,但惯例不具有地域的限定性,甚至具有全球意义上的广泛性。因此,惯例的构成要件和习惯是有差别的。美国学者吉尔莱特认为,商业惯例必须具有的品质或构成要件应当包含以下内容:“法律要求惯例应当是确定的,统一的,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存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它应当是合理的,其在实践操作中不会造成非正义的后果。为了创造一种知识推论的根据,惯例必须是普遍适用的;即是说,它不能仅仅被一个孤立的事件所证明,但其应用可以被限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方,比如一座城市。”[14]从吉尔莱特的论述可以看出,惯例更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和普遍适用的特征,所以惯例是比习惯更为高级的规范形态。
最后,习惯与习惯法的区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核心区别在于看两者是否直接关涉权利义务的分配。习惯作为事实上的惯行,属于事实的范畴;而习惯法则是对人们权利义务进行分配的社会规范。另外,不能以是否经过国家认可作为区分习惯和习惯法的标准,否则就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奥斯丁困境”。“在解释法官何以能够通过司法判决形成习惯法时,由于无法解释法官适用习惯的合法性问题,他转而认为法院可以溯及既往地适用‘实在道德’,但却因此陷入了违背自己已然区分的‘法’与‘非法’概念的困境:奥斯丁如果要证明法官适用‘实在道德’这一行为是合理的,他就必须说‘实在道德’在得到司法适用之前就内在地具有法的拘束力了,否则法官没有理由适用‘非法’的规则,这样他就混淆了他一再强调的法与非法之区分;而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无法论证法官适用‘实在道德’的合法性。此一理论困境即为‘奥斯丁困境’。”[12]26对于法官而言,习惯作为重复的惯行并不具备规范形态,需要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证明。未被国家正式认可的习惯法则作为法官适法的经验法则而存在,如果与一般社会正义和国家强行法不相违背,法官可以在审判中直接适用,而无须经过国家机关的正式认可;经过国家机关认可的习惯法则已经上升为国家法的层面,作为一种正式的法源而存在。
四、余论
概念的界定和厘清是进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对于当下正在兴起的“民间法”研究更是如此。当下的民间法研究以国家与社会作为理论范式,将产生于正式制度之外的社会规范都统统归入民间法的范畴,无疑扩大了法学研究的理论空间,并未我们关注乡土社会或者转型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契机,为农村法治建设的研究提供理论范式。但是,民间法的思维范式中存在诸多错综复杂的理论谱系,用“民间法”概念去界定中国乡土社会和转型社会的社会规范,只能在实然意义上去界定社会规范的运行状态,但是,无法在应然意义上为法官的司法实践提供审判规范和法律方法。通过在概念谱系上区分习惯和习惯法,将作为默会性知识的习惯和作为事实规范的习惯法区分开来,无疑在实然和应然的层面上对社会规范的运行状态做出了区分,从而使民间法进入规范法学的研究视野,这为研究民间法的司法适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1]陈金钊.法律方法论——概念及其理论问题[C].全国法律方法论坛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
[2]王洪平,房绍坤.民事习惯的动态法典化[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1):85.
[3]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108.
[4]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2.
[5]萨维尼.论立法与当代法学的使命[M].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1.
[6]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0.75.
[7]John 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Volume 2),Fifth Edition,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ot Campell,John Murray, 1911,p536
[8]孙国华.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59.
[9]王林敏.习惯法概念谱系的辨析与界定[A].民间法2010年卷[C].济南:济南出版社.2010.
[10]黄源盛.民初大理院关于民事习惯判例之研究[J].政大法学评论,1998,(63).
[11]Paul Bohannan,“Law and legal institutions”,in The sociology oflaw,pp7、5(ed,by William M.Evan,The Free Press,1980.
[12]魏治勋.民间法核心概念辨析[A].民间法2010年卷[C].济南:济南出版社,2010.
[13]韦森.从习俗到法律的转化看中国社会的宪制化进程[J].制度经济学研究,189.
[14]John H Gillette,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Indirect and Collateral Evidence, Indianapolis and Kansas City: The Bowen-Merrill Company,1897,pp178-179.
On the Concept Pedigree of the Customary Law Research
WANG Bin,YANG Dan
(Law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
At present,serious confusion of concepts exists in the domestic study of the customary law.To clarify the conceptive chaos,“folk law”concept should not be used in the customary law research.Based on the dichotomy of fact and norm,the custom as a tacit knowledge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norm as customary law.It is helpful for judges to have a clear genealogy of law concepts,which will allow them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to provide recognition standard and applying methods of custom laws.
customary law;custom;convention;tacit knowledge;factual norm
D631.4
A
2095-1140(2012)06-0011-05
(责任编辑:叶剑波)
2012-10-09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指导性案例的创制技术与适用方法研究”(12YJC820096)。
王彬(1980- ),男,山东邹平人,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法律解释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杨丹(1965- ),女,辽宁沈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会计,主要从事财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