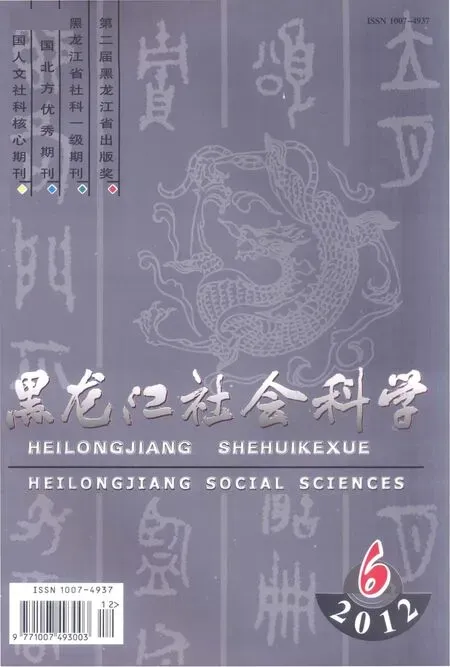符号学视阈中的马克思意识形态
毕芙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顾名思义,符号学就是研究符号的学问。人类世界作为文化世界、意义世界是一个符号的世界。这就是说,人类世界中的任何事物,莫不可作为符号来看待,否则,它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言了。由此可见,符号是意义的载体,它包括语言符号和其他一切非语言符号。就此而言,任何文化现象都是符号现象,任何文化成果都是符号成果,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也不例外。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同样是一个符号系统。因此,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符号学分析是可能的。
但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在于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意识形态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指出,“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30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525,因此,语言符号的思想内容无疑是由人们的物质关系所决定。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排斥对语言形式的研究,但他的确更关注社会发展规律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所以他才会说,“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1]36,那么可想而知,语言形式也就更无关紧要了。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出色地运用了符号学分析方法,揭穿了青年黑格尔派“用词句来反对……词句”[1]23的理论实质。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符号学分析
正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马克思才不得不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揭示出“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都局限于宗教观念的批判”,以及这个运动的“渺小卑微和地方局限性”。[1]21-22可以说,符号学分析几乎贯穿《德意志意识形态》始终。这里我们仅仅以《圣麦克斯》部分对施蒂纳的分析为例。
能指的逻辑是符号学的特有逻辑,尽管马克思不是自觉地采用这种逻辑方法进行文本分析,但他的分析过程和结论都展现了这种逻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施蒂纳的“见灵指导”和在概念之间变换的“花招”。一开始,施蒂纳就指出精神是它自己最初的创造物,那么什么是它的创造物呢?它的创造物就是诸精神,是不纯粹的精神,它们构成了精神世界,按照施蒂纳的话来说,“从言辞变成形体时起,世界就精神化了,就变幻形体了,就是幽灵了”[2]162。施蒂纳开始“见灵”,这种见灵一开始就与言辞相关。然而一个人,如施蒂纳书中的施里加,如果还不是纯粹的精神,所看到的只是这样一些幽灵、怪影,那么他就需要一个先师来指导他追求完善的精神,并最终达到纯粹精神。施蒂纳这样指导道,“总之,圣物不是为你的感觉而创造出来的”,“并且你作为一个感觉的人永远不会发现它的踪迹”,因为感性的对象已经“全部完了”,它们的地位已被“真理”、“神圣的真理”、“圣物”代替了。然而,“对你的信仰,或更正确地说,对你的精神来说(对你的无精神之可言来说)圣物是存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某种精神的东西”。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同位语算术级数,世俗的世界、“各对象”成了“为精神而存在的精神”。如此一来,施蒂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考察作为“各对象”的各种“精神的产儿”,即各种“幽灵”和怪影了。
接下来,施蒂纳历数了十大怪影:最高的本质、神→本质→世界的空虚→善的和恶的本质→本质和它的王国→诸本质→圣子、基督→人→民族的精神→一切。马克思认为这些概念是施蒂纳从黑格尔那里搬过来的,他指出,“实际上,他只是把新名称悄悄地加给自己的以往的历史观,按照这种历史观,人们一开始就不过是一般概念的代表。在这里,这些一般概念起初在黑人般的状态中表现为客观的、对人们来说具有对象性的诸精神,它们在这一阶段叫作怪影或幽灵。主要的怪影当然是‘人’本身,因为根据上述情况,人们彼此只是作为普遍、本质、概念、神圣的东西、异物、精神等等的代表,即只是作为怪影般的东西、作为怪影而存在的;还因为——根据黑格尔的“现象学”第255页及其他的地方的看法——只要精神对于一个人来说具有“物的形式”,这个精神就是另一个人。”[2]166-167因此,人们见到各种“幽灵”、“怪影”,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见灵指导”,“圣物”与“真理”、“精神”之间的互换也就都是可能的了,因为按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释,一切都不过是概念之间的互换。然而,概念之间为什么能够互相转换呢?
马克思指出,“在‘现象学’这本黑格尔的圣经中,在‘圣书’中,个人首先转变为‘意识’,而世界转变为‘对象’,因此生活和历史的全部多样性都归结为‘意识’对‘对象’的各种关系。各种关系又归结为三种根本的关系:(1)意识对作为真理的对象或作为简单对象的真理的关系(例如,感性意识、自然宗教、伊奥尼亚哲学、天主教、极权的国家,等等);(2)作为真理的东西的意识对对象的关系(悟性、精神宗教、苏格拉底、新教、法国革命);(3)意识对作为对象的真理或作为真理的对象的真的关系(逻辑思维、思辨哲学、为精神而存在的精神)。在黑格尔那里,第一种关系被了解为圣父,第二种关系被了解为基督,第三种关系被了解为圣灵,等等。”[2]163显然,在黑格尔哲学框架中,意识与对象的关系是世界和历史各种关系的一个“原型”,这一点在施蒂纳“摧毁思想的形体性,把思想收回到我自己的形体中来”[2]45的自我发现过程中可以轻易地得到证明。既然有这么一个原型,概念之间的相互转换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我们把问题转换到符号学视阈,则可以把这种关系看做能指间相互替代的能指的逻辑。
符号学创始人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中符号所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具有心理性质的语音形象和概念内容,即“能指”和“所指”。但两者的联结是任意的,某一个能指与某一个所指联结在一起,只是约定俗成的,并不必然如是。索绪尔把符号看作一套具有内在差异性的价值体系,符号的价值也就是它的值项由它在体系中的位置来决定,能指因它在本系统内与其他能指所处的关系而成为特定的能指符,所指因它在本系统内与其他所指所处的关系而具有特定意义。这就是说,能指所能获取的意义是由它与其他能指的关系或者说是由它在能指系统中的位置所决定的。那么,不同的能指可以意指同一个意义,换句话说,同一个意义可以在不同的能指间滑动。
如果把意识与对象转换为语音形象与概念内容,即能指与所指,这一问题就呈现出崭新的面貌。马克思把语言看做思想的直接现实,施蒂纳把言辞作为具有了形体的精神,我们这里则把意识视为具有语音形象的能指,那么对象作为概念内容,呈现为某种意义,即所指。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把历史发展诉诸于一般概念,而所有概念都可归结为同一种原型,那么它们就可以看作指向同一种意义的不同所指,那么,概念之间的相互转换,也就是能指之间的相互替代,从而形成一个个转喻系列,从施蒂纳所谓最高的本质、神→本质→世界的空虚→善的和恶的本质→本质和它的王国→诸本质→圣子、基督→人→民族的精神→一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这种能指的链条永远不能终结,因为“意义的意义是能指对所指的无限的暗示和不确定的指定……它的力量在于一种纯粹的、无限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刻不息地赋予所指以意义……它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指定和区分。”①转引自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26页。德里达把这个过程称为意义的撒播,“那些概念是无法加以区分的,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因而会依次从一个转换为另一个,而每一个都喻示着向另一个的转换。”[3]199再换回去说,意识永远达不到对象。意识与对象的统一,或者说精神通过认识对象(对象化)达到自我认识(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永远无法完成的。符号学从符号分析的角度也达到了批判唯心主义的效果。
当然,马克思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进行批判的,他认为“在宗教中,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的、想像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人们对立着。这绝不是又可以用其他概念,用“自我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来解释的,而是应该用一向存在的生产和交往的方式来解释的。这种生产和交往的方式也是不以纯粹概念为转移的,就像自动纺机的发明和铁路的使用不以黑格尔哲学为转移一样。”[2]170然而,“生产和交往的方式”也必须通过语言符号得以表达,其发展规律也具有能指与所指不可闭合的链条关系,作为一个不同的解释系统,也不得不面对能指链条不断滑动的困难,按照德里达的话说,“你必须同意考虑幽灵般的现实性的自治的或相对自治的躯体”[3]198。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复调性”
如果说上一部分我们揭示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符号学方法的无意识运用,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则要通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分析,揭示它的“复调性”符号学特征。
前苏联符号学家巴赫金认为,符号具有意识形态性,“符号并非简单地作为一种实在(reality)而存在——它反映和折射另外一种实在。所以,它可能歪曲或者忠实于它,或者从一种特定的观点来理解它,如此等等。所有符号都从属于意识形态评价的特定标准(例如,它是否真实、错误、正确、公平、有用等。)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相一致,它们相互等同”。[4]11-24因此,任何文本都具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文本也是如此。巴赫金在文艺批评中,分析文本表现在字、词、句中的种种关系类型和风格,提出了“开放文本”中众多意识发出多种声音的“复调”理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文本也是一种“复调”的开放文本,这种复调性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概念的“虚幻”与“虚假”之间。
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这样写道:“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Ideologie)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5]571842—1843年《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在《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一文中写道,“我们且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要成为玄想家(Ideologie)。”[5]402从这两处引文中我们看到,“意识形态”并列于“空洞的设想”,相对于“事情的实际状况”而处于贬义位置。在博士论文随后的段落中,马克思写道,“任何解释都可以接受。只是神话必须排除。但是,只有当人们通过追寻现象,从现象出发进而推断出不可见的东西时,神话才可以排除。”[5]58在这里,“神话”一词与“意识形态”、“空洞”的设想相呼应。那么,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与“神话”究竟是否具有相互对应的关系呢?
博士论文期间和莱茵报期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尽管在具体的政治立场上有分歧,但基本思路还是一致的。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肯定青年黑格尔派所推崇的“自我意识”,称“自我意识”为“最高的人性”,[6]190把上帝的证明解释为“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证明”。[6]285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概念作为一种最终解释力,肇始于《耶稣转》的出版所引起的争论。在《耶稣转》中,施特劳斯用因果关系检验福音故事,指出其中的逻辑错误,区分了历史上的耶稣与基督教信仰中的耶稣,认为基督教中的耶稣是人们对救世主的期盼中无意识创造出来的神话。而鲍威尔则反对施特劳斯用无意识来解释神话、神秘故事的产生,认为《圣经》是个体的创造。自我意识的历史作用凸显出来。由此可见,“自我意识”一词的凸现是揭示基督教“神话”性质的需要,是对于施特劳斯所提出的“无意识”创造的反对。那么,在具有青年黑格尔思想背景的马克思那里,处于贬义位置的“意识形态”,是与作为“自我意识”对立物的“宗教”、“神话”处于同一被否定方面,具有相互对应的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过去的意识形态批判没有离开过哲学或黑格尔体系,如果说德国意识形态批判有所进步的话,就在于它把“所谓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被宣布唯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而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一般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7]64-65我们提到“意识形态”与“宗教”、“神话”的相互呼应关系,在这里得到进一步明确。一切意识形态都被归结为宗教,宗教被归结为神话,那么,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也就是神话的虚幻性。然而,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立足于“自我意识”所做的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了界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正是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决定了人们的意识形态。与生活的历史过程相比,“自我意识”是被决定的第二位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虚假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此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只要是被决定的东西都是虚假的吗?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只有歪曲了自身来源的东西相对于其来源才是虚假的,或者说,只有歪曲地反映“事情的实际状况”的“意识”才是虚假的。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含义发生了转化,由一种“虚幻性”变成了“虚假性”。
但“虚假性”与“虚幻性”是有区别的。如果是虚幻的东西,可以一戳就破,正如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说他们是“用词句反对词句”,揭示现存意识中的神话性质,并代之以“人的、批判的、利己的意识”,也就可以了。而虚假性问题则不能在意识范围之内解决,因为它涉及“意识”与“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7]72,而“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7]43这就是说,意识的一切形式由现实的社会关系产生,消灭由之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消灭这种意识形式。
是否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从此由“虚假性”代替了“虚幻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批判了“商品拜物教”。他这样写道,“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8]89这就强调了商品拜物教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幻性特征。虚幻性与虚假性在意识形态二重奏中此起彼伏。综上所述,符号学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排斥又相互佐证的张力,推动着新理论的开拓,这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那里成为一种理论事实。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3]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99.
[4]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New York:Seminar Press,1930:10.转引自 Winfried Noth:“Semiotics of Ideology”,Semiotica 148-1/4(2004),11-2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90.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