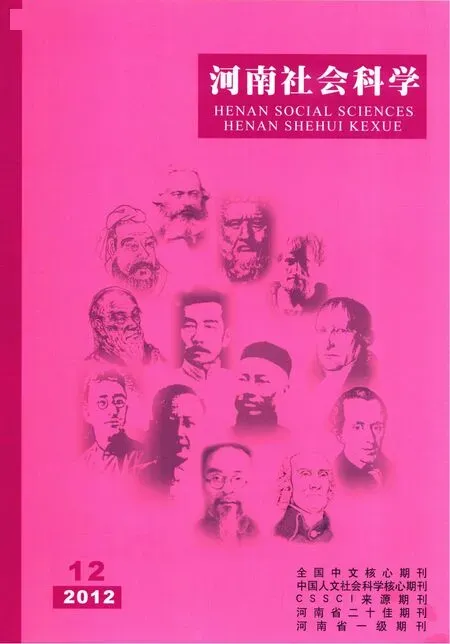基督教启示观视界中的黑格尔宗教哲学管窥
陈 丽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前言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特别注重“启示”(revelation),这一启示观所要传达的理念是人所崇仰的上帝自启、自显给他创造的人,意即人们对创造主、对周遭世界以及对自身等种种的认识都奠基于上帝的启示。而相较于此,其他宗教,它们大都是所谓“人”的主观思想与判断给予宇宙、世界及自己的意义,所以可称之为人文宗教或人文哲学。正如16世纪法国著名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曾经说过的那样:“除非人先仰望神的面并对他的沉思谦卑地省察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自己。”[1]可见,“启示”在这一信仰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启示”一词,源于希腊文apokalupsis,意即“公开”或“揭开”。启示是指,上帝向人类开示、显明他自己。
这个“公开”或“揭开”,从人这方面来看叫做“发现”,但从上帝的方面来看叫做“启示”。所以,假若从人的视角看,人所能够开启的,那不过是自然层面的东西;而在上帝那里能够开启的却是属于上帝的真理,是人的自然能力所难以企及的。启示就是奥秘的彰显,其目的是要建立真正和正确的知识。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知识的基础不在乎理性,也不在乎经验,乃在乎启示。
在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中间,欧陆理性主义认为知识是可能的,知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理性功能上的。因此,在近代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人类对大自然更深切、更精准的了解,导致科学非常神速地发展。这样,仿佛表明人已经可能在有限界里面得到真正的知识了。但以正统基督教神学审慎的眼光来看,这同样是无可企及的。理性的功能尽管透由自然科学的发展似乎是得到了相当的肯认与赞同,然而,设若把所谓“知识”只是释阐为对自然现象的了解,那还是浮于表层,没有做到深入和精准。由圣经所引带出的知识论并不是那么肤浅,换言之,不管这些哲学文化发展到什么地步,如果没有历经上帝的“道”的启发,它必定会走向一个没有方向而自以为义、绝对化、人文化的抵挡真理的道路上去,这亦是用基督教神学的眼光来看整个世界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二、黑格尔宗教哲学认识论
从整个西方哲学史看,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最为庞杂的思想体系。他的宗教哲学也同样具有高度的繁复和令人费解的特点。大多数哲学家认为它是理性时代的“怪胎”,而大多数神学家又认为它是自由主义时代调和基督教与哲学之间矛盾的“拙劣的样板”。这样的苛评大概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代哲学的巨擘康德已经宣称,宗教的核心——上帝——不在理性可以企及的知识领界,而黑格尔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上帝是理性最高成就——“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的体现,这也是他的宗教哲学的核心。二是多数神学家反对将基督教的人格神仅仅表述为带有哲学倾向的绝对存在概念。不管怎样,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理念作为他整个思辨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桥段,本身也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一)早期针对基督教的评断
早期黑格尔写了一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著作,阐发了自己对宗教的认识,并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和批判,亦开始孕育着他宗教哲学的胚胎形式。当然,他对基督教的批判部分是针对当时基督教的传统和现状,而不是否定其本身;是针对教会的组织和体制,而不是针对基督教人格神的宗教本质。
黑格尔认为,西方宗教传统的形成最初肇端于理想的“民众宗教”,而后让位于违反理性精神的被他称为“天启宗教”和“实证宗教”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他认为西方传统中原初的宗教是具有理性和人道精神的古希腊罗马人的“民众宗教”,随着罗马帝制取代了共和制,宗教的性质发生迁变,“罗马皇帝的专制把人们的精神从地上驱赶到天上去了,剥夺了人民的自由,迫使他们抛弃一切永恒的、绝对的东西,逃避到神那里去求庇护。剥夺自由带来的广泛苦难迫使他们在天国里去寻求和仰望幸福”[2]。
他认为,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建立在人的自由选择和理性思考之上的,相反,它利用的是外在于人的天启的权威来迫使人的信仰就范。因此,其堕落的性质和罗马社会堕落的性质是一致的。
(二)针对康德宗教哲学的思考
在康德的宗教哲学思想中,上帝的存在就像“物自体”一样是人类理性所无法认知的,宗教应被置于理性之外的纯信仰领地。黑格尔批评了康德对物自体和现象界的人为割裂,认为其间非为不可逾越之天堑,而有理性为津梁使其为通途。他认为,上帝是可以被理性所认识的,原因在于:代表着上帝的“绝对精神”源自精神,它是理性的终极产物,它既能作为绝对客体自显,也因其与人类理性的同质性而体现在人的精神之中。而且,作为精神实体它们二者之间有同质性,这种同质性是人通过理性的信仰克服异化所带来的差异而达到与“绝对精神”相契合的基础。从本质上讲,黑格尔所理解的宗教“是人对上帝的意识,是作为有限精神载体的人升华并与作为无限精神(绝对精神)载体的上帝的合一”[3]。
在黑格尔所理解的宗教中,“绝对精神”是所有事物的起点和终点,人通过理性地追求“绝对精神”,便可以“卸下有限性所产生的一切负担,为自己寻找到最终的满足和彻底的解脱”[4]。黑格尔强调有限精神的人与绝对精神的上帝的合一,是要表明人类理性在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性。宗教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基于人的理性有可能契合于“绝对精神”,这与康德认为的人的理性无法触及上帝的观念是大异其趣的。
(三)针对启示神学观点的评析
黑格尔认为,宗教不仅是人对上帝的理性认识,而且是上帝通过人的理性认识方式对他自身存在的肯定。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人类“对上帝的理智的爱”正是上帝对自身的爱。人与上帝之间能理智地沟通和情感互爱的基础是它们的同质性,在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所说偏重于理智的哲学和偏重于情感的宗教在内涵上是相同的,相异的仅是外在表现格局。它们的内涵都是体现神意的“绝对精神”以及体现有限精神的人对之的向往与契合。因此,哲学的旨趣不能说是仅限于关于“真理”的理论知识和思维,而且还在于“绝对精神”所担负的将人从有限精神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神圣使命,即哲学不仅限于“寻根问底”,而且还能“安身立命”。同样,宗教的旨趣也不仅限于信仰和默念“绝对精神”,而且还在于获得有关“绝对精神”的“知识”,尽管宗教也通过崇拜和仪式来表显自己,但它主要的论证其存在的依据仍是一种知识系统。
将宗教与哲学类比,说明它们之间的同大于异,黑格尔宗教哲学针对的是传统的天启神学。面对启蒙运动的挑战,基督教内部保守的神学家坚持说,宗教的信仰是独立于理性的,它来自圣经中的启示,而不是人通过哲学思考的结果。这个护教的评断是可以成立的。但是,黑格尔进一步追问:人们不用哲学的概念或理性的思考怎么可能理解启示的意涵?他的答案是:“人们的理性思考中明显地存在着范型、规则和立论等概念,这些概念是理解任何问题的前提和必要手段……确实,交流中被传递的是话语或语词的语义。但是,语词的语义也只有通过思维概念的转换才能在交流中得以实现。”[4]
宗教信仰与哲学的理性思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关联是它们各自存在的凭据,这种关系也反映着人类精神的深层本质,它表明信仰和理性在人的终极追求方面是互为补充的。
(四)针对施莱尔马赫宗教观点的探讨
对于施莱尔马赫将宗教阐释为人对神的一种绝对依赖感,黑格尔也同样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人只将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情感而不是理性之上,人就不能将自己的情感内容与其他人进行交流;没有交流,人类就不能组成社会,没有社会,宗教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依据。
再者,施莱尔马赫所说的依赖感只是宗教体验中的一种情感,它自身也必须依据概念的理性加工才能得到升华并成为可以储存的长期经验,否则稍纵即逝或那种依赖感的内涵必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失真。因此,如果不将被体验到的宗教客体通过理性方式转换成为确定的知识,人对宗教客体的体验就不会升华为人内在的深刻体验,而仅仅是滞留在感官刺激和经验印象层面,人与其所经验的宗教客体之间没有契合、没有亲和力,也就不会有属于人的“自为”的宗教。
与康德、启示神学家和施莱尔马赫的观点相比,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可以说是绝对理性主义的,即他欲求将理性贯彻到宗教现象的一切方面。但是,宗教毕竟是差异性很大的社会文化现象,如果完全排除了宗教的非理性方面,包括康德的社会道德功能假设、神学家获得的启示和施莱尔马赫的体验等,将一切宗教现象都纳入理性或纯逻辑的推理系统,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未必就经得起历史的验证和新的思想挑战。事实上,存在主义的出现就是在向黑格尔式的绝对理性主义提出的挑战。
三、神启光照下的黑格尔宗教哲学论评
(一)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区别
黑格尔之前,历史上有两大运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两个运动明显的相似点是对人的尊严的“重建”和“改造”。依凭基督教神学启示观,它们对人性尊严都有相当的重估,但区别在于:前者的人文主义对“人性尊严”的看法,是透过受造自我的限度去看;而后者的改教家对“人性尊严”的看法,是透过“人受造是有上帝的形象、样式”的神学思想去看。这样,我们会发现对自然的解释、对人的阐解甚至对神的体认,都是在这两条道路的中间:一条是人本主义的解释法,一条是上帝启示的解释法。借由人理性的本身去解释人、自然与上帝,叫做人本主义;但是借由上帝特殊之启示,意即圣经的原则法理去解释人、自然与上帝,叫做神本主义,也就是说,透过特殊启示的关键,去达到对其普遍启示的了解和把握。
此外,基督教神启观也告诉我们,在上帝面前,自然并非自足的、自我存在的。自然的“存”,不是绝对意义的独存;自然的“存”,乃是相对意义的独存。自然之存在,乃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并与上帝的主权和绝对的权能相对。恰恰是因为有了这种相对性,就产生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自然里面有许多的绝对的观念和绝对的结论,于受限的人来说,是无法实现和圆满的。
凡是在有限的自然里面渴盼绝对化一切,这样的渴盼都会深陷于失败的泥沼;凡欲求在自然的里面找到绝对的完全的答案,这种欲求也注定会落在失望当中。凡是远离上帝这独一的生命和真理源流,而预备在受造界的里面寻索到真实的完满,这种导索势必要为自身在无形当中所建构起来的自我抵消、自我消灭的理论所遮蔽。这条路,许许多多有相当分量的哲人正步履其上,行在其间。黑格尔的思想亦是如此,他企图在相对有限的人的思想里面设立一个“绝对”的系统,然而承继而来的历史哲学发出的挑战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事情。
(二)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实质及历史命运
黑格尔认为,从宗教的视角看,上帝就是那位在历史进程中渐次显现自己的“绝对精神”。哲学是思想的历史,历史又是绝对精神的逐步呈现。到最后宗教和神学必定会与哲学相联结,因为只有从上帝在历史中的显现中,上帝的存在才可能被表现出来。神学若超越宗教所发现的表象,进一步了解其普遍性和哲学性意义,神学也就成为哲学知识了[5]。在他晚年的哲学著作中,建立在绝对精神自我实现基础上的思辨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了的神学体系。黑格尔剥夺了基督教的上帝的权威,却把概念、精神当做哲学的上帝加以崇拜;他扬弃了建立在浅薄的表象基础上的传统神学,却构建了奠基于概念运动之上的思辨神学。因此,当黑格尔把神学变成了哲学时,他也就把哲学变成了神学[6]。
葛伦斯和奥尔森认为,黑格尔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被解释成一种道成肉身的比喻的伟大宣言;对道成肉身的关注,构成了黑格尔评估基督教的基础。黑格尔说,基督教的上帝的实体经过了三个阶段:本质的存在、外显的自存和自我的认知。第一阶段是纯粹、抽象的存在;第二阶段,抽象的存在借着世界的被造而进入存在;第三阶段,透过上帝与人的合一,上帝在人里面形成对自己的觉悟,即存在进入自觉中。基督的道成肉身,使人与上帝原本隐藏的合一显现出来。借着基督,上帝从抽象的观念成为历史人物,并在此过程中成为完全的实体。因此,基督教表明,那个绝对真理的存在,即上帝透过人的灵的宗教活动,完成了他的自觉。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原本仅仅是纯粹的或未实现的灵(Geist)的概念,变成了实现的。”[5]这样,黑格尔就把基督教提升到唯一的启示性和历史性宗教的地位,使基督教教义的真理超越历史,变为哲学,以免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攻击[5]。
然而,按照基督教神本主义启示观,黑格尔从他的哲学体系中推演出的神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依循他的观点,上帝只有与受造的人合一才能实现他的自觉,也就是说,上帝不能离开受造的世界独立存在。所以黑格尔说,没有世界,上帝就不是上帝了。这显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黑格尔的这种神观为后来的一种神学思想“万有神在论”(Panentheism)建立了范本。“万有神在论”和“泛神论”都主张神与世界不可分离;二者的区别是:“泛神论”认为神和宇宙是完全同等的,“万有神在论”认为神比宇宙大,有独立的位格,宇宙只是神的一部分,但宇宙也是神[7]。
黑格尔宗教哲学后来遭到了来自信仰和理性两个方面的批判。在神学界,这种“思辨神学”一开始就遭到了基督教正统派的抵制,原因是它把信仰的实证性内容完全消解在了理性的逻辑中。然而在哲学界,宗教哲学又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进行反叛的起点,原因是“它给精神和理性加上了太多的神秘色彩”[8]。因此,黑格尔去世后,他的跟随者最终裂为左、右两翼。右翼被称为老年黑格尔派,他们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基督教的上帝完全等同起来,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理性形式的基督教神学。左翼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他们重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并且力图用它来批判基督教。一言以蔽之,黑格尔用哲学重塑基督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法]加尔文.基督教要义[M].钱曜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4.
[2]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60.
[3]George,F.Thomas.Religious Philosophies of the West[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5.
[4]Hegel.Philosophy of Religion[M].trans.Rev.E.B.Speirs and J.Burdon Sanderson.London:K.Paul,Trench,Trubner and Co.,1895.
[5]Stanley J.Grenz,Roger E.Olson.二十世纪神学评论[M].刘良淑,任孝琦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
[6]赵林.黑格尔宗教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7]杨牧谷.当代神学辞典[M].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
[8]刘淑萍.论黑格尔的“伦理世界”[J].贵州社会科学,2012,(8):28—31.